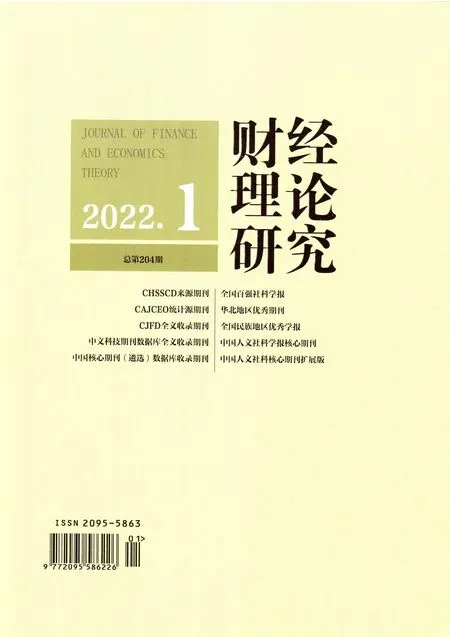海南省旅游業與房地產業的時空耦合發展研究
王公為,黃甜甜
(內蒙古大學 歷史與旅游文化學院,內蒙古 呼和浩特 010070)
一、引言
海南省地處中國疆域南端,并擁有全國最大的經濟特區[1]。得天獨厚的區位條件、旅游資源和氣候環境,促使旅游業和房地產業成為海南省的優勢產業[2]。在2009年“國際旅游島”政策和2018年“自貿港”政策的推動下,海南省旅游業的規模和效益實現了雙提升,旅游業的戰略地位逐步確立,并成為海南省的支柱產業[3]。根據《海南省統計年鑒》顯示,2009年至2019年海南省接待過夜游客人數由2250.33萬人次增加到6824.51萬人次,年均增長24.48%。旅游收入由211.72億元增長到1057.80億元,年均增長率為36.33%。在旅游業快速發展的同時,海南省的房地產業也顯著增長。房地產開發企業營業收入由2009年的268.41億元增加到2019年的1386.33億元,年均增長率為37.86%。作為海南省的核心產業,房地產業既是區域經濟發展的“晴雨表”,也是政府宏觀調控的主要方向。在新時代背景下,海南省的旅游業與房地產業如何發展、如何互動已成為學界和政府部門廣泛關注并亟須解決的重要問題[4]。
旅游業和房地產業的產業屬性和重要地位推動了國內外的相關研究。國外研究主要集中于旅游地產[5]、分時度假[6]以及旅游發展對房地產價格[7-8]和房租[9]的影響等方面。國內研究起步較晚,但涉獵范圍較為廣泛,主要集中于:旅游業與房地產業的聯動性[10]、房地產價格對旅游消費的效應[11-13]、旅游產業政策對房地產價格的作用[14]、旅游業發展對房地產價格的影響[15]等研究領域。現有研究主要從房價、旅游消費、產業政策等某一視角探討了旅游業與房地產業之間的關系,對二者在產業層面如何耦合發展和融合互動并未進行深入的探討,這不利于客觀準確的認識兩個產業之間的關系和作用過程。
海南省旅游業與房地產業獨特的產業地位為探討兩者之間的時空耦合關系提供了適宜而獨特的研究樣本。因此,本研究選擇海南省為研究對象,運用耦合協調度模型和Tobit回歸等方法探討國際旅游島政策推行以來海南省旅游業與房地產業耦合協調度的時空變化及影響因素,以期為海南省旅游業和房地產業的協調發展和轉型升級提供決策支持,亦希望為國際旅游島建設和自貿港發展起到參考借鑒作用。
二、旅游業與房地產業耦合發展的作用機理
產業耦合是指兩個及以上的產業由于生產要素、運行機制的相互作用和關聯,導致產業間出現相互影響、彼此融合的狀態或過程[16]。旅游業和房地產業作為第三產業中的支柱型產業,均具有產業關聯廣、滲透力強和帶動性高等特點[17],二者在生產要素、需求、產品和外部環境等方面具有耦合發展的基礎和內在關聯,具體表現見圖1。

圖1 旅游業與房地產業的耦合作用機理
首先,旅游業與房地產業之間在生產要素和產品構成上存在直接的交叉和融合。旅游業發展為房地產業注入了新的理念,拓寬了房地產業的產品類型和發展空間。隨著兩個產業的逐步發展和融合,構建了具有休閑、游憩、娛樂、商業、運動、度假等多種功能的土地開發方式[18],孕育并形成了文旅地產、康養地產、會展地產、購物地產等兼具旅游屬性和地產屬性的復合型產品形態。
其次,旅游業發展對房地產業具有帶動作用。其一,旅游業發展有利于擴大目的地的知名度,為當地引入大量外來人口和游客,促進房地產業的投資和置業,為房地產業發展創造有力的外部需求。其二,旅游業發展要求當地具備宜人的環境、便捷的交通條件、完善的基礎設施,這些要素對房地產業具有正向外部性,對房地產業的投資與開發具有直接帶動作用。其三,旅游業發展和旅游項目開發有利于提升地塊價值,使“生地”變成“熟地”,產生溢價效應,提升房地產項目的附加值。其四,旅游業作為勞動密集型產業,具有明顯的“富民”作用,有助于提高當地居民的收入水平,促進房地產發展。
最后,房地產業發展對旅游業具有支撐作用。部分房地產項目由于具有較強的美學特征或文化功能而成為旅游者“打卡”和消費的熱點,并成為城市旅游的特色吸引物,這對于豐富旅游產品的供給體系具有促進作用。房地產業中的酒店、民宿、購物中心等產品業態是旅游業“六要素”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業態的發展和升級對旅游專用設施的改善將產生帶動效應。此外,房地產業的發展還有利于完善當地基礎設施,改善居住環境,優化城市空間結構,提高城市承載能力,這有助于為旅游業發展創造有利的物質環境,推動旅游產業發展。
三、研究區概況
海南省全島陸域面積3.52萬km2,海域面積200萬km2[19],常住人口944.72萬人。本研究選擇海南省整體及本島18個直管市縣(不含三沙市)作為研究對象,其中包括3個地級市(海口、三亞和儋州),5個縣級市(五指山、文昌、瓊海、萬寧和東方),4個縣(定安、屯昌、澄邁和臨高)以及6個民族自治縣(樂東、陵水、白沙、昌江、瓊中和保亭)。從空間特征來看,五指山、定安、屯昌、白沙、瓊中和保亭6個市縣為內陸地區[19],其余12個市縣為沿海地區。旅游業和房地產業是海南省的主導產業。國際旅游島建設以來,海南省旅游業持續發展,產業占比從2009年的12.80%提升至2019年的19.93%。房地產業發展呈現先提升后下降的變化趨勢,2017年占比最高達到37.85%,此后開始下降,2019年占比為26.12%。受房地產業變化的影響,兩產業綜合發展水平亦呈現先增后降的變化趨勢,2017年占比最高達到56.05%,2019年下降至46.05%,見圖2。

圖2 海南省旅游業與房地產業占比(2009—2019年)
四、材料與研究方法
(一)數據來源
基于數據的可獲得性和一致性,并考慮《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旅游業的意見》和海南國際旅游島建設政策于2009年年底出臺。因此,選擇2009—2019年為研究區間。海南省旅游業和房地產業發展數據來自于《海南省統計年鑒》,缺失部分數據根據各市縣統計年鑒和年度統計公報予以補充。
(二)研究方法
為了科學測度與評價旅游業與房地產業耦合協調時空格局,本研究通過指標體系構建、數據標準化處理、熵權法、耦合協調度模型[20]以及相對發展模型等過程和方法進行了研究測算。
1.指標體系構建
遵循科學性、系統性和層次性等原則,并結合數據獲取的具體情況,借鑒已有學者的研究,構建海南省旅游業和房地產業發展水平的評價指標體系。其中,旅游業指標體系包括三個2級指標,分別為:旅游需求、旅游供給和產業運行效率。考慮到海南省各縣市數據統一的問題,旅游需求采用旅游飯店入境過夜游客人次和國內過夜游客人次進行衡量。旅游供給采用飯店數量和A級景區數量進行衡量。產業運行效率采用飯店入住率和旅游收入進行衡量。房地產業指標體系包括三個2級指標,分別為:房地產投資、房地產建設和房地產銷售。其中,房地產投資采用投資額和實際到位資金進行測量。房地產建設采用新開工房屋面積和施工房屋面積進行測量。房地產銷售采用商品房銷售面積和商品房銷售額進行測量,具體指標設置見表1。

表1 海南省旅游業和房地產業評價指標體系

續表1
2.數據標準化處理
為了消除數據間的屏蔽效應和量綱差異,使旅游業和房地產業各項指標的數據具有可比性,運用極差標準化法對數據進行無綱量化處理,并在每一個指標標準化值后面都統一加上0.01,以避免可能出現統計結果無意義的情況。計算公式為:
式中,xij表示第i個評價對象的第j個指標的原始數據,yij表示標準化后的指標值。
3.確定熵權
測算各指標的信息熵Hi,并確定熵權Wi,計算公式如下:
式中,fij表示第i個城市j項指標的權重,Hj表示j指標的信息熵,Wj表示j指標的權重[21]。
4.產業綜合評價
構建產業綜合評價函數如下:
式中,Q1為旅游業綜合評價函數,Q2為房地產業綜合評價函數,Wt和Wr分別代表旅游業和房地產業各項指標的權重,yij代表標準化后的各項指標值。
5.耦合協調度模型
耦合協調度是衡量產業間耦合發展的主要指標,其中耦合度反映產業間相互作用程度的強弱,協調度則體現產業間耦合的協調性水平[22]。具體計算方法如下:
Z=αQ1+βQ2
式中,C代表旅游業和房地產業的耦合度。Z代表旅游業和房地產業發展的綜合評價指數,α和β為待定系數。借鑒以往研究,將旅游業和房地產業的貢獻設為等同,因此對α、β均賦值為0.5。D為旅游業和房地產業的耦合協調度,為了清晰反映系統間協調發展程度,參照以往研究成果,對旅游業與房地產業的耦合協調度等級進行劃分,詳見表2。

表2 耦合協調度評定標準
6.相對發展模型
相對發展模型計算方式如下:
δ=Q1/Q2
式中,δ為相對發展度。其中,0<δ≤0.9,代表房地產業領先于旅游業;0.9<δ≤1.1,代表二者同步發展;δ>1.1,代表旅游業領先于房地產業。
五、結果與分析
(一)海南省旅游業與房地產業耦合協調發展的時序分析
根據耦合協調度的計算方法,分別對2009年以來海南省旅游業和房地產業的綜合發展指數、耦合度和耦合協調度指標進行測算,詳見表3。

表3 海南省旅游業與房地產業耦合協調發展指標(2009—2019年)
從旅游業發展指數來看,海南省旅游業發展整體上成逐漸上升趨勢,僅在2018年出現小幅度下降。從房地產業綜合發展指數來看,海南省房地產業發展表現出先揚后抑的軌跡,2017年是房地產業發展的高峰,此后逐漸下降。從系統綜合發展指數看,與房地產業類似,兩個產業的綜合發展水平以2017年為分界點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態勢。從耦合度看,各年度兩個產業的耦合度比較穩定,均處于拮抗階段。從耦合協調度看,旅游業與房地產業的耦合協調度顯著提升,由2009年的嚴重失調轉為2017年的初級協調,此后開始下降,2019年轉為近協調狀態。從耦合協調度類型來看,兩產業之間經歷了房地產業滯后—同步發展—旅游業滯后—房地產業滯后的發展軌跡,詳見圖3。

圖3 海南省旅游業與房地產業耦合協調度指標時序變化(2009—2019年)
(二)海南省旅游業與房地產業耦合度的空間格局及變化趨勢
2009—2019年間,海南省各地區旅游業與房地產業的耦合度分布較為穩定,各地均值在0.41~0.49之間,均處于拮抗階段,見圖4。

圖4 海南省旅游業與房地產業耦合度的時空變化(2009—2019年)
(三)海南省旅游業與房地產業耦合協調度的空間格局及變化趨勢
選擇2009年、2014年和2019年三個年度,探討海南省旅游業與房地產業耦合協調度的空間格局和變化趨勢,詳見圖5。2009年,海口市和三亞市的CCD分別為0.60和0.68,均處于初級協調狀態,瓊海市和萬寧市處于輕度失調狀態,陵水縣和文昌市處于中度失調狀態,白沙縣和瓊中縣處于極度失調狀態,其余地區處于嚴重失調狀態。其中海南省東部沿海地區耦合協調度水平高于其他地區。2014年,海口市和三亞市的CCD分別為0.59和0.66,處于近協調和初級協調狀態,瓊海市和萬寧市處于輕度失調狀態,陵水縣、文昌市、儋州市和澄邁縣處于中度失調狀態,白沙縣處于極度失調狀態,其余地區處于嚴重失調狀態。其中海南省東部、北部沿海地區耦合協調度水平高于其他地區。2019年,海口市和三亞市的耦合協調度分別為0.60和0.58,處于初級協調和近協調狀態,瓊海市、萬寧市、陵水縣、文昌市、儋州市和澄邁縣處于中度失調狀態,瓊中縣處于極度失調狀態,其余地區處于嚴重失調狀態。其中海南省東部、北部沿海地區耦合協調度水平高于其他地區。

圖5 海南省旅游業與房地產業的耦合協調度變化
從變化趨勢來看,依據CCD均值指標,研究期內海南省各縣市耦合協調度呈現先提升后下降的趨勢,其中2017年為極值點,此后逐年下降。各市縣耦合協調度的變異系數從2009年的0.75降至2019年的0.68,差距逐漸縮小,反映出各地區耦合協調度呈現出逐漸趨同的演化特征。
(四)海南省旅游業與房地產業的相對發展度的空間格局及變化趨勢
選擇2009年、2014年和2019年三個年度,探討海南省各市縣旅游業與房地產業相對發展度的空間格局和變化趨勢,詳見圖6。2009年,海南省房地產業占優勢的地區有8個,相對發展度均小于0.9,分別為海口市、澄邁縣、文昌市、瓊海市、陵水縣、保亭縣、五指山市、樂東縣。其余地區屬于旅游業占優勢型,相對發展度均大于1.1。2014年,房地產業占優勢的地區顯著增加,由8個增加到10個,北部沿海地區的海口市、澄邁縣、臨高縣、儋州市,東部沿海地區的文昌市、瓊海市以及南部的東方市、樂東縣、保亭縣、陵水縣均屬于此種類型。中部地區的定安縣、屯昌縣、白沙縣、昌江縣、萬寧市、瓊中縣和南部地區的三亞市屬于旅游業占優勢型。五指山市的相對發展度為0.96,屬于同步發展型。2019年,房地產業占優勢的地區數量減少,僅剩余海口市、澄邁縣、臨高縣、儋州市和東方市5個沿海地區屬于此種類型。文昌市和樂東縣的相對發展度為0.95和0.94,屬于同步發展型。定安縣、屯昌縣、瓊中縣、白沙縣、五指山市和保亭縣6個內陸地區以及瓊海市、萬寧市、陵水縣、三亞市和昌江縣5個沿海地區均屬于旅游業占優型。

圖6 海南省旅游業與房地產業的相對發展度(2019年)
研究期內海南省各縣市旅游業和房地產業相對發展度的均值從2009年的1.55下降至2019年的1.43,呈現先下降后提升的變化趨勢。根據研究期內海南省各市縣耦合協調度表現及變化趨勢,將海南省各市縣分為四種類型。其中,三亞市、萬寧市、定安縣、屯昌縣、瓊中縣、白沙縣、昌江縣屬于旅游業占優型,海口市、文昌市、澄邁縣和樂東縣屬于房地產業占優型,臨高縣、儋州市和東方市屬于旅—房優勢轉換型,陵水縣、五指山市、瓊海市和保亭縣屬于房—旅優勢轉換型。
六、海南省旅游業與房地產業耦合協調發展的影響因素分析
(一)模型構建
旅游業與房地產業的耦合協調發展受到多種因素影響,參考已有研究,并結合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情況,從旅游資源、房地產業發展、經濟發展水平、基礎設施建設、城鎮化、區位條件、政府政策等方面構建計量經濟模型。
CCDit=α0+β1TOURit+β2REit+β3ECOit+β4INFit+β5URBit+β6LOCit+β7POLit+εit
式中:CCDit表示旅游業與房地產業耦合協調度,TOURit表示代表旅游資源,REit表示代表房地產業發展水平,ECOit表示代表經濟增長,INFit代表基礎設施建設,URBit代表城鎮化水平,LOCit代表區位條件,POLit代表政府政策,α0為常數項,βn為待估參數,εit為隨機擾動項。下標i代表地區,t代表時間。
(二)變量測度
耦合協調度指標(CCD)根據前述方法進行測度,其余變量測量方法如下:(1)旅游資源(TOUR),采用A級景區數量進行測度;(2)房地產業發展(RE),采用各年度房地產建設新增面積進行衡量;(3)經濟增長(ECO),采用各年度國民生產總值進行衡量;(4)城市基礎設施(INF),采用固定資產投資規模進行衡量;(5)城鎮化水平(URB),選取常住人口中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進行衡量;(6)區位條件(LOC)采用啞變量衡量,1代表沿海地區,0代表內陸地區;(7)政府政策(POL),采用啞變量衡量,1代表國家發布關于海南省發展的重大政策,0代表當年無重大政策發布。
(三)結果分析
耦合協調度指標在0~1之間變化,被解釋變量存在著被切割的特點,符合受限因變量Tobit回歸模型設定條件。考慮到相對于固定效應面板Tobit模型,隨機效應面板Tobit模型可得到一致估計,本研究采用隨機效應面板Tobit模型進行計量估計,運用Stata16.0進行回歸,結果見表4。

表4 海南省旅游業與房地產業耦合協調度影響因素模型
對海南省整體樣本的回歸表明,房地產業發展對CCD具有正向影響,回歸系數為0.013,原因在于房地產業發展可以刺激旅游需求,促進購房者實現“因房而旅”,推動房地產業與旅游業的融合互動,因此對CCD的提升具有直接的帶動作用。基礎設施和城鎮化對CCD具有正向影響,回歸系數分別為0.015和0.285,原因在于基礎設施的改善和城鎮化水平的提升能夠同時激發旅游需求和房地產需求,構建有利于旅游業和房地產業融合的外部環境。因此,對CCD的提高具有促進作用。區位條件對CCD具有正向影響,影響系數為0.153,即沿海地區的CCD高于內陸地區,原因在于海南省沿海地區具有更適宜的氣候條件和更高品級的旅游資源,更易于產生適于旅游業和房地產業耦合發展的自然環境,因此能夠產生較高水平的CCD。經濟發展對CCD具有負向影響,影響系數為-0.052,可能的原因在于:對于經濟較發達的縣市,產業門類較多,旅游業與房地產業可能會和諸多產業發生關聯,因此二者的耦合關系可能會因此而減弱;反之,對于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縣市而言,旅游業和房地產業是地區的核心產業,在當地經濟中占比較大,因此二者耦合協調度反而較高。旅游業發展對CCD的影響不顯著,說明在研究期內,旅游業發展并未使旅游需求轉化為有效的房地產需求,因此對CCD并未產生較大的帶動作用,“因旅而房”并不成立。政府政策對CCD的影響不顯著,可能的原因在于政策對房地產業發展具有雙重效應,“國際旅游島”對房地產業發展具有促進作用,“自貿港”對房地產業發展具有約束效應,兩種效應可能會相互抵消,因此政策對CCD影響不顯著,見模型1。
對內陸地區樣本的回歸表明,房地產業發展對CCD具有正向影響,回歸系數為0.006;經濟發展對CCD具有負向影響,影響系數為-0.032;房地產政策對CCD的影響不顯著。與整體樣本回歸不同的是,旅游業發展對CCD具有正向影響,回歸系數為0.017,可能的原因在于對于海南省內陸縣市而言,房價相對較低,旅游需求能夠對當地房地產需求產生一定的刺激作用,因而能夠推動CCD的提升。基礎設施建設和城鎮化對CCD的影響不顯著,可能的原因在于海南省內陸縣市旅游資源并不具備較強優勢,基礎設施的改善和城鎮化水平的提升對旅游業的帶動作用有限,并不能促進兩產業的耦合發展,見模型2。
對沿海地區樣本的回歸結果與樣本總體的回歸結果類似,故不做過多解釋。具體結果如下:房地產業發展、基礎設施、城鎮化對CCD的提升具有促進作用,影響系數分別為0.023、0.021、0.340。經濟發展對CCD具有負向影響,影響系數為-0.070。旅游業發展和政府政策對CCD的影響不顯著,見模型3。
七、結論與對策
(一)結論
基于2009—2019年海南省旅游業和房地產業發展相關數據,運用熵權法、耦合協調度、相對發展度以及Tobit回歸等方法和模型,對海南省旅游業與房地產業耦合協調度的時空變化及影響因素進行定量分析。研究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國際旅游島建設以來,海南省旅游業與房地產業的耦合度表現出拮抗—磨合—拮抗的變化過程,耦合協調度表現出嚴重失調—初級協調—近協調的發展特征,耦合協調類型表現出旅游業占優—房地產業占優—旅游業占優的演化軌跡。耦合協調指標變化的原因主要在于房地產政策的影響。2009年“國際旅游島”政策的發布推動了旅游業和房地產業的協同發展,促使產業間的耦合度由拮抗轉為磨合,耦合協調度由嚴重失調轉為初級協調。然而,“自貿港”政策的推出則對旅游業與房地產業之間的關系產生了解耦的作用。自2018年開始,為避免房地產業的過度投機以及推進“自貿港”政策的落地,海南省政府對房地產調控進行了升級加碼,出臺了《關于進一步穩定房地產市場的通知》等一系列去地產化政策。通過嚴控土地供應、全域限購以及提升購房準入門檻等組合政策為房地產業發展“降溫”,促使房屋銷售面積和房屋銷售額大幅下降,這也成為導致旅游業與房地產業的耦合協調發展指標出現轉向的主要原因。
第二,海南省各市縣旅游業與房地產業的耦合度表現較為穩定,均處于拮抗階段。三亞市和海口市的耦合協調度處于初級協調和近協調狀態,其余地區耦合協調度水平較低,東部沿海地區高于其他地區。導致這種空間格局的主要原因在于三亞市、海口市在區位條件、旅游資源、氣候舒適度以及基礎設施等方面優于其他縣市,具備了旅游業與房地產業耦合發展的基礎和環境,因此兩地的耦合協調度相對較高。
第三,各市縣耦合協調度表現為四種類型:旅游業占優型、房地產業占優型、旅—房優勢轉換型和房—旅優勢轉換型。
第四,房地產業發展、基礎設施、城鎮化和區位條件對旅游業和房地產業耦合協調發展具有促進作用,經濟發展水平對二者的耦合發展具有抑制效應。
(二)對策
根據研究結果,對海南省旅游業與房地產業的協調發展提出如下建議。
1.樹立“大旅游”發展觀,加快旅游業轉型升級
樹立“大旅游”的發展觀,加快海南省旅游業的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促進綜合性旅游業的包容性發展。積極推動旅游業與房地產、文化體育、健康醫療、養老養生等關聯產業的滲透、互動與融合發展,探索開發醫療旅游,養生旅游、移居旅游等新產品、新業態,激發旅游發展新活力,帶動海南省經濟社會全面發展。
2.優化宏觀調控促進海南省房地產業有序發展
加強對房地產業的宏觀調控,保持房地產業的適度增長和房價合理穩定,將發展導向由住宅地產轉換為商用地產和產業地產,構建以本島長居型居住房地產為基本、經營性旅游房地產為主導、度假旅居型房地產為特色、商務及其他房地產為補充的多層次房地產產品供給體系。積極引導和發展與旅游業相適應的房地產業,鼓勵開發與旅游、文化、餐飲、康養、社會服務等產業相關聯的經營性房地產,開發產權式度假酒店、民宿、療養、免稅店、會展中心等旅游地產項目,為海南省打造國際一流的營商環境和宜居環境。
3.加強基礎設施建設
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提升島嶼內外聯結便利度。優化高速路網空間布局,尤其針對基礎設施建設比較薄弱的西部和中部山區,著力完善高速路網,修繕省、縣級公路,打破西部和中部交通瓶頸,提升內部交通的通達性。在港口碼頭方面,推進海口市、三亞市郵輪母港建設,為海上交通的改善和郵輪旅游的發展提供良好的基礎設施條件。加強市容、市貌和城市內部基礎設施建設,提升城市公共服務能力和旅游服務保障能力,為市民和旅游者營造和諧、安全、舒適的旅居環境。
4.因地制宜合理推進城鎮化
發揮海口市、三亞市等核心城市的帶動力作用,加速市、縣城鎮化進程、縮小區域差異,推動城鎮化與經濟社會全面發展。對于在旅游資源、民俗文化等方面具有優勢的地區,依托各市縣的資源條件,積極探索和推動旅游城鎮化發展,從而為旅游業和房地產業的協調發展創造有利的外部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