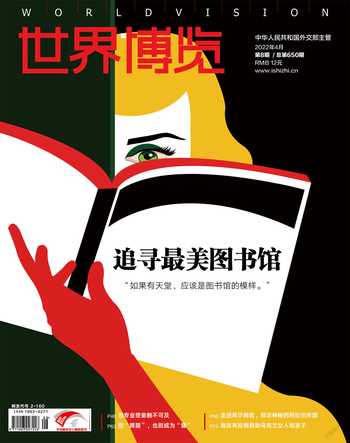當專業壁壘觸不可及
車耳

從1999年開始,“密蘇里”號戰列艦作為博物館艦,停泊在夏威夷珍珠港福特島旁,供來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參觀。
很多人會覺得外行管內行,只能越管越亂,因為外行領導很容易不懂裝懂、瞎指揮。三國時的劉備就是這樣,他一生打仗如同家常便飯,但是大型戰役只親自指揮過一次,還慘敗給了他瞧不起的后生對手。這就是三國時代三大戰役中的最后一仗:夷陵之戰。那場戰役是他拒聽部下勸阻執意為關云長報仇,還御駕親征,有點泄私憤的味道。那場仗開始打得還算順利,之后因輕視東吳對手而被打得七零八落,敗走白帝城。當他病入膏肓、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后,大老遠將諸葛亮從成都招來囑以后事。臨終前他后悔地跟諸葛亮說:“朕自得丞相,幸成帝業。何期智識淺薄,不納丞相之言,自取其敗。”
不過,除了這次慘敗,作為一個外行,劉備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領導其團隊還是不錯的。他武不敵關張,卻能將這些桀驁不馴的武將團結在自己身邊,一生忠心耿耿,永不相棄;他文不及孔明,卻能放下面子三顧茅廬求賢若渴,使其肝膽涂地,死而后已。所以,如果有知人善任的本領,又有雄才大略的眼光,外行可能會領導得更好。
聶榮臻元帥早年投筆從戎,新中國成立后主管全國和軍隊的科技工作,視知識分子為國家的寶貝。在得知反右派斗爭中一些科技專家受到了不公正對待后,他積極向上反映,解決實際問題,也勉勵科學家們以事業為重。他一貫倡導科學求實的精神,提出要尊重客觀規律,堅持按科學規律辦事。他雖然不是學物理的,也不從事科學研究,卻開創了我國“兩彈一星”輝煌事業,是其中主要組織者和領導者,成了國防科技事業發展的奠基人。
新中國的石油部長余秋里,在老一輩人心中也是大名鼎鼎。他剛當部長時對石油工業一竅不通,卻能組織人才、尊重專家,先后發現并建成了勝利油田、大港油田、遼河油田等一大批油田,使國家擺脫了石油一直靠進口的局面,他為中國石油工業發展作出的貢獻是舉世矚目的。
所以,如果內行由外行領導,可能結果更出色,當然,這個外行的戰略眼光和駕馭、溝通、協調等方面的能力要更出色。古今中外,在現實社會中,外行領導內行的情況比比皆是。

1945年9月2日,標志著二戰結束的日本無條件投降的簽字儀式,在“密蘇里”號主甲板上舉行。
有時候不能光靠內行
外行領導內行的一個顯著優勢,就是有可能平衡好利益、協調好糾紛,避免內斗和形成不必要的自身消耗,而這種消耗在戰場上可能是致命的。
比如在戰爭中,陸軍將領重視陸軍,海軍將領重視海軍,他們都會為自己所屬的部門爭取最大化的利益。所以,讓任何一個兵種的人當國防部長都會有偏心之嫌。于是,美國國防部長幾十年來一直是由非軍人出身的人出任,這樣,至少在兵種問題上顯得中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空軍和日本空軍一樣,都還沒有獨立出來,不過都有海軍航空兵和陸軍航空兵,依附在海軍和陸軍身上,并服從海軍和陸軍的指揮。所以,在二戰太平洋戰場上,美軍內部主要是陸軍部和海軍部之間的矛盾。
太平洋戰場的陸軍指揮官是麥克阿瑟,他家世顯赫,很早就是美軍少有的幾位五星上將之一。但是,幾場決定性的戰役都是平民出身、低調的海軍上將尼米茲指揮的,特別是中途島海戰和南太平洋幾次大海戰。陸海軍雙方在太平洋戰場的指揮權、進攻方向的選擇、補給安排等方面的斗爭一直很激烈,雙方一直互不相讓,麥克阿瑟甚至不愿意見雙方,最后還得作為最高統帥的羅斯福總統親自協調。雙方的爭斗始終影響著戰局,直到在戰爭結束時對受降的安排上。
為了凸顯海軍在對日作戰中的作用,海軍部建議將受降儀式安排在美國軍艦上,而不像之前那樣都在陸地上進行。實際上,美軍已經占領了日本,軍艦已經進駐東京灣。在位于日本領海的美國軍艦上舉行受降儀式,既表明是在美國“領土”上,還突出了海軍的貢獻,免得榮耀都體現在陸軍方面。而且,既然在軍艦上舉行儀式,就要懸掛海軍的旗幟。于是,就有了在“密蘇里”號艦受降儀式上那張永恒的畫面:海軍尼米茲將旗和陸軍麥克阿瑟的將旗伴隨著星條旗一起迎風飄揚。
不僅在戰爭中,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也是如此——內行做具體工作,外行則有義務評判,甚至指手畫腳。比如,一個城市的指路牌需要內行人進行具體的操作,但是應該讓外行的路人和駕車者來評判,因為指示得正確與否、符合邏輯與否,主要由后者判定。在西方國家,這個行業甚至有一種不成文的習慣,就是讓外地人而不是當地人來做一個城市的指路牌——只有當任何一個陌生人見到指路牌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不會疑惑、不走冤枉路的時候,一個城市的指路牌才算做得成功。就這個意義上講,北京的高速路標示、地鐵站標示,由上海人或者廣東人來做可能才更為合理。
有時候只能依靠外行
讓一個外行來當領導,不僅可能是相對合理的選擇,也能夠調節內斗,整合資源,還可以避免行業偏見。讓外行而非內行判定一件事,則可能更符合公平和正義的原則。在美國,公民都有被指定當陪審團成員的義務。一般由法官和控辯雙方律師一起從當地居民的名單中隨機挑選,被選中的陪審員要全程參與庭審,費時耗力地聽完整個案件中控辯雙方的全部陳訴和辯護,再憑著自己的良知——而非專業素養,投出有罪或者無罪的一票。
挑選陪審團成員的標準之一,就是不能找內行人士,很少有律師和前檢察官被選中當陪審團成員的——盡管他們更懂得法律,更熟悉法庭上的套路。也正是因為他們更有經驗,也就更會形成固定思維模式和表達習慣。同時,經過多次庭審錘煉的他們往往能言善辯,比外行人更容易用邏輯推理得出傾向于己方的結論,也就更容易影響其他成員。這樣的話,陪審團的意見就容易成為一家之言,而不是綜合了各方面意見的決定,也就失去了成立陪審團判定有罪與否的初衷。
法官在挑選陪審團成員時會采用排除法,將對某個領域有切身體會的人淘汰掉。比如:在審理一個意外槍擊案時,會剔除一名熱衷持槍保衛家園的人士;在審理一個毒品案時,會剔除一名親人因毒品而死的受害者。總之,法官不能讓某個可能對類似案情有經驗,甚至很懂行而難以立場中立的人成為陪審團成員,進而影響判決。
保持中立、不偏不倚,往往體現一個外行領導者的定力,而這常常是專業人士難以做到的。專業知識與領導能力在很多情況下無法集于一身,內行過于專注在專業知識上,往往缺乏整合資源,或者說是掌控宏觀大局的能力。比如:陳景潤是個數學天才,獨自一人都能破解哥德巴赫猜想,令人心服口服,但是讓他當所長肯定不適合。這就像一位醫術高超的大夫不一定能成為稱職的醫院院長,一位講課好的教授不見得能夠勝任校領導崗位一樣。

在美國,公民都有被指定當陪審團成員的義務。一般由法官和控辯雙方律師一起從當地居民的名單中隨機挑選。挑選陪審團成員的標準之一,就是不能找內行人士。
事實上,一位內行領導可能知道把握本行業內的發展方向,但也容易剛愎自用,因循守舊,固步自封,習慣走老路,干事憑經驗,還可能壓制不同的聲音,從而阻撓一個行業的創新。
說到這里,就不得不提及那種偏見意識,就是人們往往用已有的知識、已有的經驗去衡量未知事物、未來的形勢,從而造成對事物的錯誤理解。其實,很多時候更需要的是良知,而不止是專業知識。很多解決問題的辦法來自外界的七嘴八舌,而不是內部的固執己見。
內行當然可以領導內行,可外行也可以領導內行。外行領導內行,憑借的不是技術能力,而是見地、協調能力、組織能力、控制風險能力等,是以最小成本獲得最大利益的那種能力——一句話,就是那種遠見卓識的能力。
借用經典電影《教父》中的那句話總結一下:“在一秒鐘內看到本質的人和花半輩子時間也看不清一件事本質的人,自然是不一樣的命運。”
(責編:常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