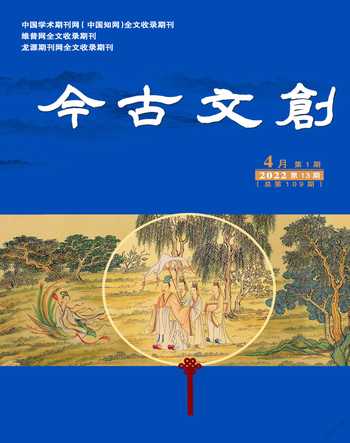“唯美—頹廢” 主義思潮影響下新感覺派小說中的都市形象
【摘要】 20世紀20年代早期,海派作家在唯美—頹廢主義的文學思潮的影響下,以“頹加蕩”的意趣為旗幟,形成了以“獅吼—金屋作家群”“幻社”“綠社”《真善美》雜志社為代表的文學團體。而在20年代晚期,同樣具有強烈唯美—頹廢主義色彩及追求感官享樂的新感覺派作家群也漸漸發展成形,在其作品中塑造了風格鮮明的都市形象。本文將主要以波德萊爾作品與新感覺派小說中的都市形象為例,歸納后者在“唯美—頹廢”主義思潮影響下書寫的都市形象特點,以及與“頹加蕩”作家作品中都市形象的部分異同比較。
【關鍵詞】 唯美—頹廢主義;波德萊爾;新感覺派;都市形象
【中圖分類號】I207?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2)13-0031-04
一、“造在地獄上的天堂”
穆時英在《上海的狐步舞》開篇寫道:“上海,造在地獄上的天堂”。新感覺派小說中景物描寫往往著眼于冒著黑煙如龍般飛馳的火車,高級飯店中的燈紅酒綠,大量的輪船與工廠,無論是有著“東方巴黎”美稱的上海還是(相對于西方文明而言)具有異域浪漫色彩的日本都市,無一不呈現出資本的現代化、工業化滲透的情狀。工業的大力發展進步促成了物質上的豐富,但奢華與輝煌往往建立在社會底層民眾的苦難與回報甚微的艱辛勞作上,同時,上層社會群體在窮奢極欲中也醞釀、滋生出罪惡、精神上的墮落。富裕與貧窮的兩極分化展現出作者對于現代都市矛盾、復雜的情緒。馬泰·卡林內斯庫提出,“現代性不僅僅是在其現時性、短暫特異性和瞬息內在性中被把握的現時,或‘現代生活的畫家’的作者帶著微妙的悖論所說的‘現時記憶’,在美學上,它還是美(這種美甚至可以在邪惡與恐怖事物中見到)的某種更廣泛特性。”新感覺派作品中既有對繁華享樂中剎那間的微妙情愫、精神與官能愉悅的追崇,對工業產物的些許敬畏(對光、電、高速度的描寫常突顯其強勁與力量,體現出都市中的“機械美”),而更多的是并不掩飾地揭露、批判繁華之中的墮落(如對肉欲的放縱、背叛倫理道德的情感關系)、背后暗處的罪惡(槍殺、工人勞動者死于非命)。波德萊爾筆下的都市空間,亦可看出其懷有強烈情感地抨擊現代(都市)文明及工業化之痕跡。《惡之花》中頻繁出現在巴黎街道的“尸體”“娼妓”“酗酒者”等意象無不展現出意圖“遠離這丑惡城市的黑色海洋”,明顯且強烈地表達了對現代都市及其文明的不滿以致憎惡。波德萊爾在《埃德加·坡,他的生活與作品》中的描繪表現出他對資產階級現代性的反對:“從對于自由的不虔誠之愛中伸出了一種新的暴政,動物的暴政……在那里時間和金錢具有如此巨大的價值。物質活動被不適當地強調,以至于成為全國性狂熱,使他們的頭腦中沒有為不屬于這個世界的事物留下任何空間……他指責在其同胞高昂和炫耀性的奢侈消費中,有著作為暴發戶特征的壞趣味的一切征象。”也正如穆時英在《上海的狐步舞》中所言,繁華的飯店舞場是在死尸與血上造起來的,巴黎在波德萊爾眼中既有現代化都市紙醉金迷光鮮享樂的一面,但并不阻礙其看透背后腐敗墮落、對社會底層群體的壓迫之罪惡的一面。
《惡之花》“六個部分的排列順序,實際上畫出了憂郁和理想沖突交戰的軌跡”,是“在一個‘偉大的傳統業已消失,新的傳統尚未形成’的過渡時期里開放出來的一叢奇異的花”。波德萊爾想要回到“沒有遮掩的歲月”,逃避現代都市空間的“腐化”,對充滿田園色彩的鄉村與往昔的淳樸抱有一定精神寄托,這樣的心理在新感覺派小說中也有相似的體現。《梅雨之夕》中的“我”在將陌生女子視作自己的初戀同學,對其描述中凸顯出含蓄憂郁的古典氣質;《熱情之骨》里的法國青年比也爾初來日本也是懷著“浪漫的巢穴的東洋都市”、相比于“動物的西歐女”更可愛的遠東女子的田園詩歌般幻想。然而雙方的期望、追求常以幻滅、失敗而告終:波德萊爾的憂郁未減毫厘,對陌生女子、初戀同學、妻子、倚柜者的夾雜著戀慕與罪惡感的聯想幻象破滅,僅剩惆悵,比也爾意識到這城市同巴黎一般有太多的輪船與工廠,玲玉的一封信如冷水澆醒他,告訴他在這個時代他理想中那種詩和往日的舊夢是不可能尋得的。作家與其筆下的人物只能回到充斥資本工業化氣息的都市中,繼續以頹廢、追求瞬時愉悅的心態度日。
二、孤寂的漫游者
“都市漫游者”的形象早先在波德萊爾的《現代生活的畫家中》被提出:“漫游者通常無名無姓,他們四處觀察……他們寄身于數字之中,棲身于稍縱即逝與恒久不變之中,這是一個巨大的愉悅……四海為家,又好像從未遠離家鄉,身在世界,卻又絕世獨立。”此處波德萊爾觀念中的“漫游者”主要扮演主動觀察者的形象,且往往是有錢有閑、思維活躍的人。但其與新感覺派作品中的“孤寂的漫游者”除了物質條件豐裕的觀察者,其他多種類型的被觀察者也可作為重要的組成部分。
愛倫·坡在《人群中的人》卷首以拉布呂耶爾的一句話做引子:“不幸起因于不能承受孤獨”,以第一人稱敘述視角講述了一段在一整個夜晚內觀察某個不遺余力想要去融入人群的街頭流浪者的經歷。在觀察者犀利而略帶嘲諷的眼光下與煤氣燈的照耀下,都市中的人被其類型化,無論是否表面光鮮,皆流露出性格中卑瑣的一面,是受觀察者鄙夷的,但那流浪老人卻是“獨一無二”的,立刻吸引了觀察者并被與之前的人物模板區別開,待觀察者發現其游蕩的真相后,認為他代表了罪孽深重的本質,擁有最壞的一顆心——這顆心拒絕被“讀”也可能是認識他的最善良的方式。小說中敘述全文的觀察者、被觀察的(具有普遍性的)市民群體以及那個特殊的流浪老人,其實都是都市中“孤寂的漫游者”,是被符號化、陌生化、異化的人,而這樣的帶有類似“零余者”、現代性色彩的人物形象亦充斥了波德萊爾與新感覺派作品中的都市,成為其不可分割的有機構成部分。
最為典型的觀察者形象,波德萊爾與新感覺派作品也常以他們的視角展開情境描述。前者在《惡之花》中以第一人稱視角對現代都市中人所感受到的虛無、孤獨、絕望等情緒做了細致的描寫,雖然其中也有部分詩歌擁有歡愉樂觀的基調,但總體是對于現代(都市)文明的一種強烈的質疑、抗拒。他們眼中的都市風光(一系列的意象)組成了一片“象征的森林”,諷刺抨擊其中的丑惡腐敗(尸體、娼妓、酗酒者、窮苦人的生存環境),對光鮮與奢靡(香水瓶、珠寶、女性的頭發等)抱有玩味的心態,甚至發現或者創造出一些超自然的意象(骷髏農夫、吸血鬼、幽靈)表現自身情緒體驗。施蟄存的《梅雨之夕》中的“我”,即使被淋濕也不愿放棄“用一些暫時安逸的心境去看看都市雨景”的娛樂,也正因此引發了與陌生女子的相遇及之后一系列的觀察、聯想、幻覺的糾纏。《白金的女體塑像》里,穆時英以謝醫師的視角,運用意識流技法,引領讀者了解了其日常的活動,更通過窺見謝醫生的心理活動間接觀察到印象派畫作般的、吸血鬼一樣蒼白無血色的女病患形象。謝醫師雖然不是終日直接在都市街頭游蕩,但這一經歷(或者以謝醫師的角度而言算作“誘惑”)在潛意識中使他感受意識到自己的孤獨,激發促使他去新的環境交際、打破原有的社交圈等(從其破例去應酬、向孀婦獻殷勤等舉動可看出),并為了擺脫孤寂(反日常)而改變,他的臉從“清癯的、節欲者”的臉變成了豐滿的臉,眼中的抑郁氣質也轉為愉快。比也爾(《熱情之骨》)更是為了擺脫原有城市的燈紅酒綠、濃厚的工業化、資本主義商業氣息,懷著“饑餓的精神”、獵奇心態與美好幻想去探索東洋城市,但緩解精神空虛的幻夢被無情而戲劇化地撲滅了,他也意識到這里與他之前生活的西歐都市并無二致,同樣是工業化了的、被資本主義商業氣息浸透而不可能找到往昔舊夢的城市,觀察者再度回到了憂郁與虛無的精神狀態。這群孤寂的漫游者、觀察者們意識到自己的孤獨、精神世界的空虛懷揣探索獵奇的心態去對抗“無聊”這挑剔的怪物,在光怪陸離的都市生活中主要通過(融入都市的人群中進行)觀察的方式發揮其主體間性以追求反日常與瞬息剎那間微妙的心理愉悅體驗,于作者筆下無一不沾染上頹廢—唯美與現代性的色彩。同時,觀察者們在窺探都市中其他對象時其實也是被(讀者)觀察的對象。
被觀察者也是孤寂的都市漫游者中不可被忽視的群體,且往往為女性,并常被男性視角物化、符號化,她們的主體性更多的是一種主體間性,通過與其他男性的交往得以立足、體現。《惡之花》中的女性形象塑造是分化、矛盾的,女性不僅有被神化、理想化的形象,她們還是“美麗與丑陋的矛盾體”“社會邊緣的游蕩者”,不再是(完全)美好、超凡的形象,甚至其群體地位、品質也遭到了強烈貶低與諷刺。《惡之花》中大量運用矛盾修辭,也常體現在對女性的描述上。然而其中女性始終與誘惑相聯系,既是純潔的少女或地位較高的貴婦,有繆斯那般神性的吸引力、給予詩人靈感啟迪、愛意與感官上的愉悅,同時又被視為罪孽的象征,是墮落淫蕩的娼妓,像蛇一般陰險地企圖狩捕獵物(男性),甚至被妖魔化為吸血鬼、怪物等。不論是外貌還是女性的話語,文中多用極具感官刺激性的語詞來描述女性,她(們)會興奮放蕩地聲稱“這張肉墊子興奮得昏厥唏噓”,吸干人(男性)的骨髓。《白金的女體塑像》中,謝醫師也從女病患身上發現出謎一樣的詭秘、骨蛆般的誘惑,而這篇小說最初以《謝醫師的瘋癥》之名發表在《彗星》雜志時,也更直接地描繪了謝醫師充斥了恐懼的預感心理活動:“這位女客人一定是一個妖精”。穆時英深受西方現代思想浸染,尼采的影響尤其出現在其創作中。尼采的哲學思想觀點對于女性有著復雜的情緒與意蘊,涉及從較表面的生物或社會性的到較抽象的哲學(作為隱喻、意象)意義層面上的“女性”。穆時英(及其他的新感覺派)小說中的女性往往體現出被物化(被男性觀賞玩弄的對象)、愛慕虛榮、欲壑難填等較偏負面的特質,與尼采對女性(生物性、社會性)的觀點類同,如認為女性膚淺(所以厭惡對真理的追求)、反對女性獨立,都是建立在女性對男性的依附這一觀念基礎上。雖然作品中她們也常被與“蛇”這一具有狡猾狩獵者色彩的意象聯系起來,也有許多“主動出擊”去追求男子的言行,但本質上她們仍更多是被男性審視狩獵的一方。《上海的狐步舞》里劉顏蓉珠靠丈夫的財產尋歡作樂,追尋刺激,胡同里被婆婆支使著賣身來求得生計的媳婦,街上姑娘們的白腿,無論經濟與社會地位的高低,她們都免不了被賞玩。《白金的女體塑像》里的女病患更是無抵抗力地被光明正大地審視,被看作為剝離了人類道德感情欲望的無機物(塑像),卻被投射了謝醫師自己的心理欲求。《兩個時間的不感癥者》里的“她”連姓名也沒有,作為一個新型的“消遣男子的女性”撩撥了H、T先生的心緒,又繼續她極快節奏的尋歡狩獵。《流行性感冒》里的秦蓁子已有男友,卻同時與“我”維持著復雜的“戀愛”,對男友的情感表達也充滿矛盾,如“將最喜愛的東西送給最不喜愛的人”。《女媧氏之遺孽》里的“我”與青年莓箴有了不倫之戀,以日記、書信的形式記錄了來自外界的審視、評判同時也始終進行著自己對自己的心理審視與對話反省。可見,新感覺派小說中的都市女性塑造在唯美—頹廢主義思潮的影響下,更多受到來自文本內外的凝視,(相比男性)被物化、符號化與非人化的程度亦更甚。她們追求感官享樂與刺激,同時成為這種刺激的載體被追求或消遣,而這一追求或消遣的過程也往往被唯美化(通過增加人物情感的與文本語言風格的感傷性色彩)、常態化。
但總體而言,被異化、充滿空虛、漂泊感同時不受抑制地沉醉于轉瞬即逝的美這一類特質是新感覺派小說中都市市民所普遍共有的(不論性別)。《上海的狐步舞》中劉顏蓉珠在極短的時間內先與繼子共舞戀愛,之后又流連于剛認識的比利時珠寶掮客的床笫,《兩個時間的不感癥者》中的女人更是直白地作出“還未曾跟一個gentleman一塊兒過過三個鐘頭以上呢”之宣言。體現出具有追求短暫、易逝、偶然的現代性色彩,這種對刺激而短時的情緒體驗的追崇如“流行性感冒”般不分性別地彌漫在都市男女中。葉靈鳳在《女媧氏之遺孽》以日記、信件體式表現的不僅有“我”的孤寂痛苦、不受理解,還有莓箴的無奈與歉疚;《梅雨之夕》的“我”對陌生女子的態度并不純粹是帶有享樂性質的“賞玩”,而是與對初戀的懷念、罪惡感、潛意識中的焦慮及惆悵共同糾纏在一起;得知秦蓁子要將領帶送給她正式男友時“我”覺得落選了般的失望悵惘……種種描繪表明作品中都市男女(戀愛)心理上呈現出空虛茫然甚至病態化的傾向,即使獲得過一時的消遣的歡愉,但心緒更長久地歸于孤寂痛苦。
三、與“頹加蕩”作家作品中都市形象的部分異同
以“獅吼—金屋”、《真善美》雜志與幻社、綠社等為代表的“頹加蕩”作家群,在分類上和新感覺派同屬于海派作家,其創作范圍在現代都市這一意象或題材上多有重合,審美情趣也頗有類同,但正如南北(京海)兩派在同一思潮影響中也存在不同的審美情趣,“頹加蕩”與新感覺派兩個文學團體的創作活動間仍存在些許差別,無論是受唯美—頹廢主義思潮影響的源頭還是具體創作中的意趣與手法,皆有相異。
從兩者吸收的唯美—頹廢主義思潮之淵源來看,“頹加蕩”作家群主要受到以王爾德、波德萊爾等為代表的英(美)法唯美—頹廢主義居多,而以穆時英、劉吶鷗、施蟄存為代表的新感覺派作家群主要受到尼采、日本唯美—頹廢主義、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等的影響,因此兩者從受影響的源頭來看即已產生了一定分歧。雖然“頹加蕩”文學團體中也有眾多留日學生,如方光燾、章克標(崇拜谷崎潤一郎),但他們于整個團體的影響作用是略遜于其他受英美法唯美—頹廢主義影響的。以《金屋》月刊及相關書店的創辦者邵洵美為例,其最初的審美趣味是偏向英國浪漫主義的,在赴歐留學后意趣則轉向了英法(西方)的唯美—頹廢主義,并創作了詩集《花一般的罪惡》,從詩集名即可看出對波德萊爾《惡之花》的追崇演化,其中更匯合了王爾德、G·摩爾、魏爾倫和《黃面志》集團等的影響,提取出唯我的、重感官享樂的表現原則。詩集中直白露骨地堆疊了肉欲與官能刺激的意象,毫不掩飾對感官享樂與宣泄生命本能的推崇,卻較少借鑒到波德萊爾所用意象的象征意蘊與更深層次的精神內涵、超驗情趣。除了團體成員自行創作外,其他較小團體如“幻社”“綠社”《真善美》雜志社也同金屋書店共同致力于對英美法唯美—頹廢主義的譯介,將王爾德、波德萊爾、愛倫·坡、戈蒂耶、沃爾特·佩特、G·摩爾、安特萊夫、比亞茲萊等(也包括谷崎潤一郎)的作品翻譯引入國內,亦表明了他們的創作學習傾向所在。
尼采的思想在二十世紀初被知識分子譯介到國內,雖然經過一段時間的沉寂,但其對于現代人生存困境的揭露及相關觀點被經過西方教育的中國知識分子(尤其是在都市中生活的)所接納運用。穆時英即是受其影響的此類知識分子之一,他在(散文)創作中多次直接提及尼采之言論,可推斷出其對尼采的作品是有過較為系統地閱讀、了解的,此外,他其他的創作也間接體現出尼采觀念的浸染,尤其是都市題材相關的小說,如《駱駝·尼采主義者和女人》更是直接將尼采的理論(但經過了曲解變形)化為小說的有機成分。對(都市)女性的描繪塑造上,表露出與尼采對生物性、社會性層面上女性的觀點(膚淺而愛慕虛榮、討厭追求真理)相似的態度,對整體的都市男女的描繪也多浸透了頹廢的虛無主義色彩。劉吶鷗曾翻譯《色情文化》(描寫現代日本資本主義社會的腐爛期的不健全的生活),從中也吸收了一些新技法來描繪現代都市生活,并運用在其作品集《都市風景線》中,描繪出一系列摩登的、色彩鮮明的都市圖景(也將都市的位置直接置于日本,如《熱情之骨》)。雖然施蟄存自身不承認自己具有“新感覺派”屬性,常道前二者的確吸收了日本新感覺主義(橫光利一、川端康成等)的相關因素,但他表明自己確實應用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小說(如《將軍底頭》《梅雨之夕》中大篇幅的性心理分析、意識流的運用),且其小說的現代派傾向仍是與新感覺主義相通的。
葉靈鳳的歸類是有些模糊的,似乎很難生硬界定他屬于“頹加蕩”還是新感覺派的文學團體,其最初以感傷的(都市)戀情小說創作為主,之后不斷追逐新的浪潮,“用跳動不定的充滿感官刺激的意象,新奇的借喻,對話的暗示性、多義性,甚至分鏡頭劇本的直接插入等用最現代的文體來寫最現代的都市男女”。可以說他的創作兼具了“頹加蕩”主義與新感覺主義的部分特點,兩者的異同(部分)也體現于此。對于現代都市生活題材的創作上,葉靈鳳在其中加入了許多直白的肉欲的性描寫,與“頹加蕩”的注重唯我的感官享樂原則不謀而合,同時,對官能刺激與誘惑氛圍的渲染不僅體現出其被英國唯美—頹廢主義的影響的色彩,還表露出對中國傳統艷情甚至色情文學的趣味遺傳(也是“頹加蕩”主義作品中普遍存在的元素)。但與“頹加蕩”將美感降低為官能快感的片面化、庸俗化不同的是,他也會有意識地在創作技法上借用現代的敘事手段(如心理分析法),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審美情感和精神意蘊,這與新感覺主義在敘事方法上的嘗試也是較為一致的,同時,新感覺派對官能享樂的追崇似乎更強調其瞬時性,相對而言難以長久捕捉到的美是產生刺激的重要緣由。
當然,唯美—頹廢主義思潮的影響下,在“頹加蕩”與新感覺派小說中的都市同樣具有較多共性,如資本主義工業化、商業化、消費主義氛圍的濃厚籠罩,都市中不同社會階層生活的兩極分化(極度奢靡、付出與收獲極不對等,一面是光鮮另一面是黑暗,而光鮮中也蘊藏著腐敗黑暗的成分),市民們物質充裕的基礎上更多地付出的是心理代價(作為孤寂的漫游者),不論是否主動去追求短暫易逝、瞬時的感官或情緒上的享樂,是觀察者還是被觀察者,他們的情感精神上大都具有現代人被異化、虛無感與漂泊感(世紀末的頹廢色彩之體現),成為都市文化重要的的有機構成部分。同時,往往備受爭議的那些唯美唯樂的官能快感描寫,也是對海派作家的道德壓力的解除,對傳統禁欲主義、功利性強的現實主義的反叛之體現。但其中過度追求甚至沉湎于聲色之美、醉生夢死這樣飲鴆止渴般的生活哲學與審美情趣,如王國維所批判的“眩惑”之藝術,還是值得反思及適當的取舍。
參考文獻:
[1]馬泰·卡林內斯庫.現代性的五副面孔[M].顧愛彬,李瑞華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5.
[2]夏爾·波德萊爾.惡之花[M].郭宏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
[3]解志熙.“頹加蕩”的耽迷——十里洋場上的藝術狂歡者[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6,(03).
[4]吳曉東.中國化的“頹加蕩”:邵洵美的唯美主義實踐[J].文藝爭鳴,2016,(01).
[5]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記[M].南昌:二十一世紀出版社,2012.
[6]穆時英.上海的狐步舞[M].南昌:二十一世紀出版社,2012.
[7]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8]張磊.論新感覺派的唯美—頹廢性[D].西南大學,2010.
[9]趙鵬.海上唯美風:上海唯美主義思潮研究[D].上海師范大學,2010.
[10]孫松.論穆時英創作中的尼采因素[D].山東師范大學,2017.
[11]匡娉婷.頹風美雨:王爾德在中國[D].暨南大學,2005.
[12]白新歡.尼采哲學的“女人”意象及其意義[J].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8,25(06).
[13]愛倫·坡.愛倫·坡暗黑故事全集(上)[M].曹明倫譯.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13.
[14]魏建亮.本雅明筆下的都市漫游者及其“漫游”[J].理論月刊,2014,(01).
[15]張鐵哲,文軍.主體間性在漢詩英譯中的體現[J].外國語言文學研究,2008,(1).
作者簡介:
梁欣雨,女 ,漢族,上海師范大學碩士在讀,研究方向: 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