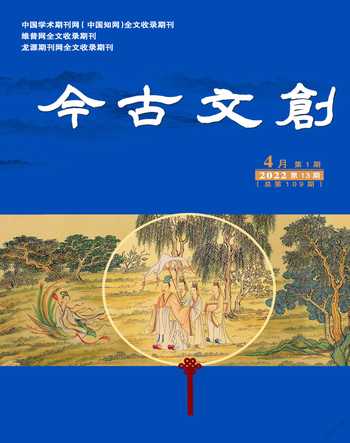《紅樓夢》在日本的流傳
【摘要】 中日兩國文化交流源遠流長,其中書籍起到的媒介作用不容忽視。何種書籍以何種方式傳入以及傳入之后的流傳情況等,是理解兩國文化交流的重要課題。本文以江戶時代傳入日本的清代小說《紅樓夢》為研究對象,在回顧日本《紅樓夢》流傳研究史的基礎之上,對比同于江戶時代渡日的明代“四大奇書” —— 《三國演義》《西游記》《水滸傳》《金瓶梅》在日本的傳播與影響情況,嘗試從傳入時期、清代禁書政策及文學特征等方面探究《紅樓夢》在日本流傳的阻礙,發掘其獨特性。
【關鍵詞】 《紅樓夢》;“四大奇書”;日本江戶時代
【中圖分類號】I207?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2)13-0038-03
一、引言
《紅樓夢》在中國被譽為古典小說巔峰之作,然而在一衣帶水的近鄰日本,它的受眾卻遠比不上被稱為“四大奇書”的《三國演義》《西游記》《水滸傳》《金瓶梅》。據日本學者大庭修,圍繞江戶時代從中國傳入的書籍,研究可分為日本文學研究者的比較文學研究和中國文學研究者的中國文學作品在日本的影響兩個方向。后者以從文獻中考察《紅樓夢》《金瓶梅》等中國文學作品在江戶時代如何被閱讀、被談論為主。①沿著后者的方向,本文試在回顧既有研究的基礎上,通過將江戶時代傳入日本的明代“四大奇書”與《紅樓夢》的流傳情況進行對比,探究《紅樓夢》的獨特性,考察其在日本流傳受阻的可能性。
回顧相關文獻,日本紅學家伊藤漱平在1965年紅樓夢展開幕之際寫作論文,后于1986年修正作成《〈紅樓夢〉在日本的流行——從幕末至現代的文獻目錄簡述》②。此文考證了《紅樓夢》傳入日本的年代及版本,按年代順序詳細考察了從幕末至昭和年代與《紅樓夢》有關的日本文人學者以及誕生的日譯本。可以說是宏觀概述日本《紅樓夢》流傳史的開山之作,為后人研究提供了諸多可能的角度,此后的研究也多繼承了伊藤漱平的研究成果。
受其影響,具體研究多圍繞翻譯學理論視角下對日譯本的分析、日本文人受《紅樓夢》的影響等方面。此外,中日比較文學視角下,相比日本學界,中國學者更多地將《紅樓夢》與《源氏物語》相對比,此類研究在《紅樓夢》與外國文學的比較研究中,所占比重也是最大的。然而,對《紅樓夢》是否受日本大眾歡迎這一問題的研究仍然不足。部分論述中雖有提及但在日本影響有限,卻少見對這一現象原因等的深究。另外,《紅樓夢》與其他中國古典白話小說在日本流傳情況的對比研究也十分缺乏。
為更全面地把握《紅樓夢》在日本的影響與局限,在既有研究基礎之上,本文試以江戶時代為中心,將其與明代“四大奇書”在日本的流傳情況進行對比。
二、“四大奇書”與《紅樓夢》在江戶時代的流傳
(一)江戶時代“四大奇書”的流傳
據德田武所言,白話即口語之意,白話小說即中國明代成立的俗語小說。③其中《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金瓶梅》這四部長篇白話小說尤為經典,均于江戶時代便傳入日本,人稱“四大奇書”,對日本文學產生了深遠影響。
綜合論述“四大奇書”在日本流傳情況的研究并不多見。根據單獨論述其中具體書籍的研究可知,《三國演義》在日本最初的記錄可追溯至慶長9年(1604)的林羅山已讀書籍目錄(《羅山林先生集》附錄卷一)。而最初的《三國演義》翻譯則由德田武(2001)的研究得到確認,早在寬文2年(1662)《為人抄》一書中便有翻譯其故事的部分④。《通俗三國志》自刊行以來,便廣受喜愛軍事故事的日本人歡迎,情節被反復改編、呈現在草雙紙、繪本、歌舞伎、浮世繪的世界中,三國的英雄也成了江戶民眾的英雄。關于《三國演義》之后的傳播情況在此不多做展開,但其在日本的流行程度甚至超越本國這一事實是毋庸置疑的。
《西游記》方面鳥居久靖的研究成果不容忽視。⑤鳥居久靖考察了江戶至戰后《西游記》流傳的軌跡,將傳入日本最多的《西游記》版本——《西游真詮》——抵日的時間精確至正德3年(1713)前后。雖然日本最初的《西游記》全譯本直至1960年才問世,但江戶中期《通俗西游記》(寶歷8年(1758)開始刊行)及《繪本西游全傳》(文化3年(1806)開始刊行)等梗概譯本相繼刊行,為普通民眾所熟知,特別后者直至昭和年代都有廣泛的讀者。
另一方面,胡凱(1990)考察了江戶文壇受《水滸傳》影響的情況。《水滸傳》最初作為唐通事(翻譯)的教科書,經歷了江戶地區學習中文的熱潮,誕生出《忠義水滸傳》這部添加了日語假名和標點的《水滸傳》版本,逐漸滲透至江戶文壇。長崎翻譯岡島冠山的譯本一經問世,更是催生了諸多仿寫和改編作品。通過考察瀧澤馬琴、山東京傳等讀本作者可見,若無《水滸傳》的影響,或許獨占江戶后期文壇的讀本便不會有如此發展,由此可窺得《水滸傳》對江戶文壇影響之大。⑥
最后是從《水滸傳》故事中誕生的明代第一人情小說《金瓶梅》,對此川島優子的研究成果值得參考。川島優子指出,“詞話本”在1643年以前便傳入日本,但被認為“淫書”則是明治時代之后的事。江戶時代的《金瓶梅》廣泛流通,被大眾所閱讀,直接催生了曲亭馬琴所作《新編金瓶梅》(天保2年(1831)至弘化8年(1851))這一作品。⑦通過以上諸多研究成果,可大致了解江戶時代“四大奇書”的流傳情況。
(二)江戶時代《紅樓夢》的流傳
眾所周知,江戶時代德川幕府頒布“鎖國令”,只開放長崎一港進行與荷蘭和中國的部分貿易。相比于江戶初期傳入日本的“四大奇書”,《紅樓夢》傳入的18世紀末,正值江戶后期。
《紅樓夢》渡日的路徑及傳播的詳細情況可參考伊藤漱平的研究成果,以下只略述其概況。根據《江戶時代唐船持渡書研究》一書,日本貿易商村上家的《差出帳》中記載,寬政6年(1794)抵達長崎的寅二番南京船所載六十七宗書籍中,有“《紅樓夢》,九部十八套” ⑧的記錄。這距《紅樓夢》刊行后僅過兩年,也是至今為止發現的《紅樓夢》海外輸出的最早記錄。傳入日本后,便成為在長崎擔任翻譯的唐通事的中文教科書。而關于除此之外《紅樓夢》被怎樣閱讀和接受的史料,伊藤漱平僅列舉出田能村竹田的隨筆《屠赤瑣瑣錄》一種,其中有關于《紅樓夢》的記事。此外,瀧澤馬琴也被認為有受到《紅樓夢》影響的可能性。喜愛中國白話小說的瀧澤馬琴在寫作長篇小說《南總里見八犬傳》時,有證據標明確實閱讀了《紅樓夢》,或許從中受到過啟發。但《八犬傳》受《水滸傳》影響更為顯著,其與《紅樓夢》的關系還無法斷言。
“四大奇書”中,《三國演義》與《水滸傳》尤為江戶時代日本人所喜愛,其接受程度以和刻本、翻譯、改編、注釋書、繪本等各種各樣的形式呈現出來。而與此表現出不同命運的《紅樓夢》,全譯本甚至要等到一百二十年后的大正年間(1921—1922,幸田露伴、平岡龍城共譯)方得問世。
上述研究顯示,在江戶時代的日本,《紅樓夢》的流傳程度遠不如“四大奇書”。
三、試論《紅樓夢》在日本影響有限的原因
(一)傳入日本的時期
江戶時代雖是中國白話小說盛行期,但《紅樓夢》誕生時間較晚,且已在白話小說鼎盛期之后,未能列入“四大奇書”的范圍。
參考青木正兒的觀點,將江戶時代中國白話小說的流行劃分為三個時期進行考察。⑨
第一階段為元祿(1688—1704)之前。這一階段是古文小說的流行期,但自元祿2年(1689)開始刊行的《通俗三國志》是白話小說登上舞臺的轉折點,這部作品也是被稱為“通俗讀物”的白話小說翻譯的開端。
第二階段為寶永至寬政年間(1704—1801),被認為是白話小說的盛行期。促使白話小說開始流行的是岡島冠山,他將《忠義水滸傳》加上日語假名和標點,譯為《通俗忠義水滸傳》(寶歷7年(1757))。岡島冠山還編寫了日本最初的中文教科書《唐話纂要》(享保元年(1716)刊行,當時將中文稱之為唐話、唐音),中村幸彥將其稱為唐音流傳第一功,指出他為中國俗文學研究打下了堅實基礎。
第三階段為享和、文化(1801—1818)之后,被稱為白話小說衰退期。此時從中國白話小說中汲取創作靈感、在文壇大放異彩的是瀧澤馬琴。這一階段雖還留有之前的勢頭,但中國白話小說的流行還是不可避免地步入下坡路。詳細情況可參考青木正兒的論著。
佐以中村幸彥的論述,尤其元祿至享保年間為儒學鼎盛期,知識分子之中盛行文人趣味,中文學習便是其中重要的一環,這為白話小說的流行準備了條件。因中文教科書主要以白話小說為主,除講授與學習之外,還出現了閱讀白話小說的愛好者。因此,“四大奇書”一經渡日便受到日本學界廣泛歡迎。不僅如此,當時從文化到日常生活方方面面都流行中國趣味,對東洋尤其中國的關注度很高。但《紅樓夢》的傳入已是此“中國熱”逐漸冷卻、步入中國白話小說衰退期之時,中文學習也日趨衰落。且18世紀后半葉西洋文化的影響滲入,知識分子中通過學習荷蘭語吸收西洋知識的“蘭學者”越來越多,關注的焦點也逐漸從東洋轉向西洋。
(二)清朝禁書政策
提起《紅樓夢》,許多人認為它被清廷視作“淫書”“反清”而遭禁,禁書對海外輸出是否構成阻礙便成了值得探討的問題。還有這樣的說法,即元祿至寶歷年間白話小說的大量渡日正是因為清朝小說禁令的緣故。然而,在回答禁書政策如何影響海外輸出這個課題之前,《紅樓夢》是否遭禁、其被禁的情況如何等問題,應當首先進行考察。
既有研究中對《紅樓夢》查禁歷史的考察較少。王利器在《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1981)一書中,將元明清三代小說戲曲遭禁的史料按中央法令、地方法令和社會輿論三部分進行廣泛收集,為禁書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史料。其中提示了《紅樓夢》及其續作被認為“淫書”以及《水滸傳》《金瓶梅》《西廂記》等長期被收錄至禁書目錄的史實。⑩受王利器的研究成果影響,之后的學者在研究《紅樓夢》被禁情況時,意見有所不同,但可提煉出以下公認的結論:清朝確以破壞風紀、威脅統治為由,屢次對小說戲曲類作品發布禁令,針對《紅樓夢》的查禁至少在江蘇、浙江等地實行,并曾被認定為“淫書”而實行嚴禁;且“淫書”這種看法也不乏有查禁行為的影響。至于本國的查禁政策對書籍海外輸出有何影響這一課題,需要更加廣泛的資料收集,期待日后這方面的研究成果。
(三)作品特征及日本文學傳統
《紅樓夢》相比于其他白話小說,尤其《三國演義》 《西游記》《水滸傳》等,在日本的受眾較少,作品特征是原因之一。“草蛇灰線,伏脈千里”的《紅樓夢》對日常生活和人情世態進行綿密刻畫,若非讀完全書,難解言辭間的妙處和言外之意,難有目睹人物最終歸宿的感嘆。反觀《三國演義》《西游記》等作品,行文易讀,且故事構成通俗易懂,又多跌宕起伏的情節,兒童也可以領略其妙,單個故事情節便引人入勝。
加藤周一于《日本文學史序說》這一論著中,將日本文學的顯著特征之一總結為“或多或少都擅長描摹局部的精妙之處,而較少考慮作品整體構成”?。較之部分與整體的關系,多為部分自身的精彩而寫作的日本文學,其與《紅樓夢》這樣考慮全局構成的作品是有出入的。差異背后,或許有中國文化對總括性體系的偏愛和日本文化著眼于特殊情境的傾向這一文化特征的影響。
或許是這樣的文化傾向使然,日本人在接納外來文化時,罕見全盤吸收的情況,而是進行取舍,并努力將其日本本土化。此前的“通俗讀物”一直夾雜片假名,但至江戶末期,《繪本通俗三國志》《繪本西游記》《新編水滸畫傳》等廣受歡迎的書籍,幾乎都由插畫畫家繪制插圖,并由平假名構成,因此,普通民眾也可以無障礙地翻閱。以《三國演義》為例,“雖也有直接翻譯的讀物,但日本人更傾向于閱讀進行本土化改編、附上插圖的縮略版本”?。《紅樓夢》也不例外,雖說呈現與日本文學不同的特征,但在忠實翻譯原文的譯本之外,少見本土化改編的作品或許也是被“敬而遠之”的原因之一。
四、總結
在諸多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本文試將《紅樓夢》在日本江戶時代的流傳情況與“四大奇書”進行對比,顯示其流傳和影響有限。究其原因,可從傳入日本的時期已至幕末,關注的焦點由中國白話小說轉向蘭學、目光投向西洋,清代查禁《紅樓夢》的行為影響海外輸出的可能性,以及作品特征與日本文學傳統的差異等方面考察。由于篇幅和能力所限,在此只提出了一些可能性,期待將來更加詳細的論述。
“生于末世運偏消”,《紅樓夢》正靜待讀者發現它的魅力。雖說如此,文學作品只靠作者的苦心是不夠的。還未日本本土化、大眾化的《紅樓夢》,在忠實于原文的古風譯文之外,未來面向一般讀者的簡明略譯本及改編作品也值得期待。
注釋:
①(日)大庭修:《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1967年版,第3頁。
②(日)伊藤漱平:《伊藤漱平著作集第三卷 紅樓夢編》,汲古書院2008年版。
③(日)德田武:《江戸文學と中國》,每日新聞社1975年版,第56頁。
④(日)德田武:《本邦最初の『三國演義』の翻訳——『為人鈔』に就いて》,《明治大學教養論集》2001年1月。
⑤參見(日)鳥居久靖《わが國に於ける西遊記の流行——書誌的に見たる》(《天理大學學報》1955年12月),《続·我が國に於ける西遊記の流行》(《中文研究》1966年1月),《再続·わが國における西遊記の流行—— 「少年西遊記」 書誌》(《中文研究》1969年1月)。
⑥胡凱:《研究発表 江戸文壇における『水滸伝』受容の形跡》,《國際日本文學研究集會會議錄》1990年3月。
⑦參見(日)川島優子《江戸時代における『金瓶梅』の受容(1)——辭書、隨筆、灑落本を中心として》(《龍谷紀要》2010年9月),《江戸時代における『金瓶梅』の受容(2)——曲亭馬琴の記述を中心として》(《龍谷紀要》2011年3月)。
⑧(日)大庭修:《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1967年版,第252頁。
⑨(日)青木正兒:《青木正児全集(第二巻)》,春秋社1983年版,第381-392頁。
⑩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日)加藤周一:《日本文學史序説(上)》,筑摩書房2018年版,第22頁。
?(日)井上泰山:《日本人と『三國志演義』:江戸時代を中心として》,《關西大學中國文學會紀要》2008年3月。
作者簡介:
徐梅婷,女,漢族,山東青島人,北京外國語大學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日語語言文學專業,碩士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日本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