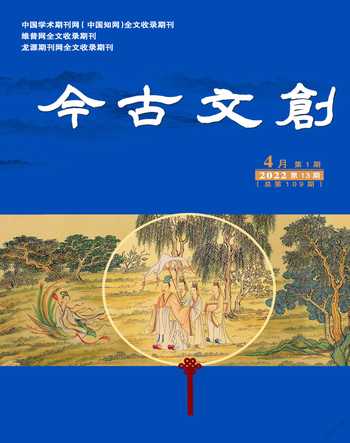農冠品詩歌的民族歷史文化因素探析
【摘要】 廣西壯族詩人農冠品堅守自身的民族身份,積極探索、創作民族詩歌。他從民族神話傳說、圖騰崇拜的土壤里汲取營養,關注民俗文化,把視線投向廣西歷史名人,挖掘民族歷史和民族精神。從民族歷史文化的視角切入,研究農冠品詩歌的民族性,具有重要意義。這有利于深入認識傳統文化與新詩之間的傳承關系,也有利于不斷深化與豐富廣西新詩的民族性。
【關鍵詞】 農冠品;歷史文化;民族性
【中圖分類號】I207?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2)13-0041-03
基金項目:2017年度廣西高校中青年教師基礎能力提升項目“當代壯族詩歌族性寫作研究”(項目編號:2017KY1491)。
隨著現代科技、經濟的發展,全球化的趨勢越來越加強。維護民族文化傳統,傳承民族精神,是各個民族守護自我的底線。在現代文化多元碰撞的環境下,廣西涌現出一批少數民族作家,他們依然堅守自身的民族特性,積極探索、創作民族詩歌,彰顯了一種對民族根基的本位體認,一種對民族家園的精神守望。農冠品就是堅持民族性表述并取得豐碩成果的代表作家。他是壯族人民的兒子,他的作品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凝結著濃郁的壯鄉情結和深沉的民族精神。民族歷史文化,是少數民族作家表現自己民族特色、民族情懷的重要載體。農冠品也不例外,他在詩歌創作中,堅守民族作家身份,充分擷取壯族的歷史文化養分,對民族歷史文化進行審視和反思,具有鮮明的文化意識和民族意識。農冠品詩歌中融合的民族歷史文化因素,主要有壯族民間神話傳說、壯族圖騰崇拜、壯族歷史名人傳說、壯族民俗文化等。
一、壯族民間神話傳說
魯迅曾指出:“古民神思,接天然之閟宮,冥契萬有。與之靈會,道其能道,爰為詩歌。”[1]這句話中的“神思”,應該與神話——遠古人民對生命、對宇宙最初的認識具有密切的聯系,它基本是從詩學的角度闡述了神話傳說與詩歌之間的關系。神話傳說是一個民族最初的記錄,是一個民族重要的精神根祗和文化源頭。廣西這片美麗而神奇的紅土地,蘊含著豐富多彩的文化藝術資源,蘊含著神秘美妙的神話傳說。
農冠品積極地從壯族民間神話傳說資源中挖掘寫作因素,他的很多詩歌對壯族的神話傳說進行取材和改編,繼承了壯族深厚的歷史文化傳統。他的《致虎年之歌》:“我有根兮是盤古/我有源兮是布洛陀/戰神之威力兮/布伯斗倒了天上雷王/染血的、悠長的紅水河兮/是岑遜一手開拓/那悲歡之歌兮,在神奇的花山縈繞不落/莫一大王的趕山鞭兮/歌仙化鯉魚的傳說/血的火焰兮,曾由南天王儂智高點著/良兵女神瓦氏夫人兮,高山雄鷹拔群哥/這不斷的根兮/不散的魂兮/不滅的火。”[2]31
根據壯族巫教經文(壯族宗教文學)《布洛陀經詩》記載,布洛陀是壯族的祖神、創造神。除了布洛陀這位始祖,廣西來賓縣一帶的壯族民間還流行開天辟地、繁衍人類的盤古的神話傳說。這首詩,逐一細數壯族先祖盤古、布洛陀,到壯族傳說中的人物布伯、雷王、岑遜、莫一大王、歌仙劉三姐、儂智高、瓦氏夫人,再到現代壯族的英雄人物韋拔群,簡單梳理了壯族神話傳說和社會歷史,表現出詩人對民族歷史文化的追尋和傳承。
又如《奮飛吧,我的民族》:“我的民族啊從姆洛甲布洛陀古老而遙遠的山洞走來/生存與拼搏創業與代價生與死血與火在史冊中記載……”[2]25亦是如此,不斷挖掘、梳理姆洛甲、布洛陀等壯族神話傳說。《下枧河之歌》把目光投向家喻戶曉的民間形象——壯族歌仙劉三姐:“夢中那位傳世的歌仙/從百丈崖頂跳落河心/濺起一束美麗的浪花/爭得生命與婚姻的自由。”[2]21
壯族古籍文獻《麼經布洛陀》記載有“嘹三妹造友”,結合壯族“嘹歌”發展演變以及民間信仰研究,可以確定“嘹三妹”就是壯族歌仙劉三妹(后來演變為“劉三姐”)的最初形象。劉三姐是壯族民間傳說中美麗聰慧、能歌善唱、敢于爭取美好愛情和自由、敢于反抗的女性形象,她是世界各族人民認識廣西的重要窗口之一。
此外,《雁——壯族傳說》 《金鳳》 《岜來,我民族的魂》《在金鳳凰落腳的地方——右江盆地抒情》等詩歌,也都是改編壯族神話傳說,彰顯出鮮明的民族性。
二、壯族圖騰崇拜
圖騰背后隱藏著遠古文明的起源密碼,它對研究遠古社會和民族文明的演變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神話傳說作為文學和文化的最初形式,往往與民族的樸素原始思維和宗教信仰融合在一起。廣西重要的圖騰形象與稻作文化密切相關,譬如遠古的壯民族崇拜的有太陽、月亮、雷電、鳳凰等,但最具民族特色的圖騰莫過于雷王、蛙、水牛、榕樹、木棉、銅鼓。隨著尋根文化的興起,壯族作家們從壯民族的精神內核出發,找到了“花山文化”之根和“紅水河之根”。許多壯族作家巧妙借用各種圖騰意象和花山(壁畫)、紅水河意象,表達對民族歷史和文化的探究、追尋和認同。“對于任何民族及其個體成員來說,民族認同都是生存命脈之所系。民族認同,既是個體歸屬感的需求,也是民族凝聚力的關鍵。民族認同,主要是文化認同。”[3]
農冠品的詩歌創作,凝聚著他對壯族身份誠摯深沉的情感歸依。在2001年出版詩歌自選本《廣西當代少數民族作家叢書·農冠品卷》中,第一輯《岜來,我民族的魂》充滿民族歷史文化意象,呈現強烈的民族意識。
《七月南方》:“銅鼓上的夢幻,銅鼓上的/舞蹈,銅鼓上的云紋、雷紋、魚紋/青蛙王與羽人,統統請到七月/七月村寨,七月?場,七月向陽坡/聚集追憶一個古老的神話傳說。”[2]10
又如《神鑄》:“青銅鑄的信仰/鑄的信仰/鑄的野獵生活/走向火的年代/群聚的年代……”[2]28銅鼓、青蛙、羽人、雷王等紛呈異彩的意象,被賦予了濃重的民族色彩。而詩人就在圖騰意象的觀照中,完成對歷史文化的追尋和認同。同名詩篇《岜來,我民族的魂》:“岜來,我民族的山,民族的魂……銅鼓一面面似旭日升起/崇拜的神也是民族的魂靈/太陽神十二支光芒閃耀奪目/相伴的是羽人舞的悠遠夢境。”[2]15-16
農冠品在詩中,對銅鼓崇拜這一壯族原始圖騰進行歌頌,表現對壯族遠古文明的追尋和審視。而花山壁畫的形象,就是壯族豐富的歷史文化傳統。詩人與岜來(花山)、銅鼓、太陽神對話,表達了民族尋根和認同的主動構筑。此外,《金鳳》《鄉祭》《紅水河,光明的河》《奮飛吧,我的民族》《桂西行吟》等詩篇,無一不是詩人在民族歷史文化中尋求詩意的表達。
三、壯族歷史名人傳說
黃偉林在《論新世紀廣西多民族文學》中指出:“文化自覺也表現在廣西多民族作家對自身民族重要歷史人物的實事求是的認識和評價。”[4]歷史名人是歷史文化積累造就的,是某一個民族在歷史進程中有較大影響的代表人物,體現著民族的性格特征和精神。許多少數民族作家往往把視線投向本民族的歷史名人,注重構建“歷史名人意象”,突出了本民族人民的精神氣概,凸顯鮮明的家國情懷和民族精神。
農冠品從民族神話傳說的土壤里汲取營養,構建壯族特征明顯的“神話傳說意象”,挖掘民族歷史和民族精神。除了少數詩篇歌頌反抗壓迫的壯族首領儂智高和抗倭女英雄瓦氏夫人,農冠品更多地把禮贊獻給了近現代中國的壯族革命兒女。《廣西當代少數民族作家叢書·農冠品卷》第二輯《啊!桂西的山》,全部是對廣西壯族革命歷史熱情而悲壯的吟唱,對紅七軍革命烈士的追憶和贊頌,主要集中于對壯族人民的優秀戰士韋拔群、韋國清以及在廣西這片熱土戰斗過的鄧小平的緬懷和謳歌。同名詩歌《啊!桂西的山》:“難忘東蘭山中的列寧巖/農講所曾在這里開辦;拔哥帶回真理的火種/把燎原的烈火熊熊點燃/……啊!桂西的山/紅色的山/戰斗的山!”[2]41
韋拔群是廣西壯族人民的兒子,是我國工農紅軍的著名領袖和百色起義的領導者,他大公無私、勇敢堅強、樂于奉獻,深受廣西壯族人民愛戴。這首詩歌,用語樸實平淡,卻寫出對韋拔群等革命志士的深深崇敬和熱愛。《大山的兒女》:“你的名字,與鄧小平、紅七軍、韋拔群/及功勛卓著的將軍們連在一起;你光榮的歷史,與覺醒,與奮發/與流血犧牲相牽又相系……”[2]147大山,走出了韋拔群這樣優秀的壯族兒女,同時也是韋拔群、韋國清等革命志士的象征。歌頌大山,實際是歌頌大山的兒子,歌頌壯族人民不屈的斗爭精神。其他諸如《清風樓之歌》《金色的課堂》《寫在西山之崖(組詩)》等詩篇,塑造革命戰爭年代壯族英雄人物群像,描寫壯族人民的斗爭歷史,寫出壯族人民的堅韌不屈,強調壯族人民在革命歷史中的重要作用,在壯懷激烈的革命抒情中突出家國情懷。將歷史人物與地域情懷、家國命運緊密結合,生動地再現了富于民族性的思考,體現了民族認同的自豪感。
四、壯族民俗文化
民族的文化紐帶深深潛伏于族群血緣的、地域的、情感的、語言的、宗教的、風俗的共同體中。根據人類學視角,民俗文化是一個民族歷史延續和集體意識加強的重要文化紐帶。“民族作為一個獨特的群體,其重要表征就是文化的獨特性。少數民族作家展示族群文化獨特性的本質在于展示族群獨特的文化信仰和生活實踐,明確族群的邊界范圍。”[5]為了展示民族的個性,許多少數民族作家往往對外展示本民族的獨特生活場景和民俗文化,闡釋本民族的文化特征。
農冠品的詩歌,洋溢著濃郁的壯族民俗風情,展示了壯族文化的獨特魅力。他的《家鄉歌節·鄉野間的交響》描繪廣西壯族三月三歌節的熱鬧和吃五色糯米飯的風俗:“家鄉的歌節來到了/金鳳展翅彩蝶飄過山坳/歌的閘門,再封不住了……五色糯飯,吃得飽了/香糯蜜酒,喝得足了。”[2]5廣西的三月三,來源于古代的上巳節。壯族有許多歌圩活動,其中三月三歌圩最為隆重。三月三,除了有對山歌的歌圩,還有祭祖、食用五色糯米飯等風俗活動。農冠品抓住了壯族民俗文化的標志性藝術——三月三山歌文化和歌仙劉三姐的傳說,全面展示了壯族多彩的民俗文化。
《陽春三月三》:“陽春三月三/壯家歌滿山/心花像紅棉/人似浪潮歡。”[6]在詩歌里,壯鄉的歌節多么熱鬧,對歌的壯鄉兒女多么歡樂,生動展現了壯族人民豐富多彩的生活,寫出了壯族民俗文化的異質獨特性。《家鄉歌節·金鳳》《三月三》《下枧河之歌》等詩篇,對壯族風俗文化進行熱情的書寫和禮贊。
尤為重要的是,詩人并非僅停留于對民俗文化的直觀描寫,更寫出了其背后蘊含的豐富多元的歷史面貌和民族特性,表達了詩人對壯族文化的深厚情感。
五、農冠品詩歌與歷史文化因素聯姻的得失
(一)表現壯族民族性格精神,彰顯民族性
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的劃分標準,主要集中在語言文字、作品題材與作者族別這三個方面。由于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復雜性,劃分標準客觀上主要集中于作品題材與作者族別這兩個方面。但任何事物都有內容和形式兩個層面,文學的民族性也不例外。就像俄國作家果戈理所指出的:“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寫農婦穿的無袖長衫,而在表現民族精神本身。”[7]文學的民族性,不僅僅在于作品題材和作者族性等外在的形式層次,更在于內在的、本質的民族內容層次。民族精神、民族性格和民族意識,才是文學民族性的核心和靈魂。通過上文對農冠品詩歌中的民族歷史文化因素的梳理,可以看出其詩中的形象,體現著壯族人民不畏艱難、堅忍不拔、積極進取、自強不息、甘于自我犧牲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凸顯家國情懷。
因此,農冠品通過神話傳說、圖騰崇拜、歷史名人和民俗文化的書寫,創造具有傳統文化意蘊的作品,構筑自己的詩歌世界,形成自己的創作個性,同時在不斷建構壯族文學的民族性。
(二)傳承、反思壯族的歷史文化,具有厚重的品質
農冠品通過壯族的神話傳說、圖騰崇拜、歷史名人及民俗文化等族性“關鍵符號”的大量運用,既有對壯族文化進行風情展示,傳達民族圖騰崇拜心理和民族尋根認同意識,對壯族歷史文化的挖掘和梳理,又有對壯族文化的內涵的傳承和反思。每一個意象,每一場景,每一段追尋,都超越表面意義和鏡像,指向民族尋根反思和認同,指向民族性格精神反思和塑造。詩人對壯族民族歷史文化進行的體認和探索,對民族原初面貌的民族意識的追尋,對于生存的抗爭和禮贊,都使他的詩歌具有了厚重的歷史感和文化品質。
(三)偶有失于直露,缺乏詩味
農冠品積極而努力地探索與呈現廣西壯族歷史文化及精神品性,他對本民族的赤子之心與熱血激情在詩作中得到了很好的抒發。
從整體上而言,他的詩歌創作,在繼承與弘揚廣西獨特的壯族歷史文化傳統方面獲得了較為豐厚的實績。現代詩歌與歷史文化因素聯姻雖具有優勢,但傳統文化與新詩之間的傳承、現代性和民族性完美融合卻非能夠容易實現的。農冠品的詩歌在融合民族歷史文化的過程中,有時難以做到從字里行間自然流露出民族性,顯示出一種刻意的追求。因此,它的部分詩作不免失于直露,缺乏詩味。瑕不掩瑜,農冠品的努力和成就依然是值得肯定的。
六、結語
農冠品的詩歌,是當代廣西少數民族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描畫出廣西壯鄉的風土人情和歷史文化,跳動著壯族人民生活的脈搏,表現并塑造壯族人民的民族精神。以壯族的神話傳說、圖騰崇拜、歷史名人及民俗文化為立足點,觀照、探討農冠品詩歌的民族性,具有較大的現實意義。這必將有利于深入認識傳統文化與新詩之間的傳承關系,有利于不斷深化與豐富了廣西新詩的民族性,同時為少數民族文學的不斷發展繁榮提供啟示作用。
參考文獻:
[1]魯迅.魯迅全集(第1卷)·摩羅詩力說[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65.
[2]農冠品.廣西當代少數民族作家叢書·農冠品卷[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1.
[3]權繪錦.民族認同的詩意建構與女性生命經驗的知性書寫——評土族當代詩人阿霞的詩歌[J].青海社會科學,2015,(2).
[4]黃偉林.論新世紀廣西多民族文學[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2,(07).
[5]農麗嬋.“我族”“我鄉”的族性書寫——壯族詩人農冠品創作研究[M].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20:151.
[6]農冠品.愛,這樣開始[M].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1989:194.
[7]果戈理.文學的戰斗傳統·關于普希金的幾句話[M].上海:新文藝出版社,1953:2.
作者簡介:
梁珍明,女,壯族,廣西上林人,碩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國文學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