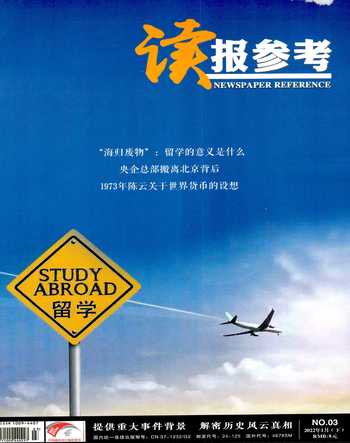最早出版南京大屠殺著作的外國記者田伯烈
在當今眾多論述南京大屠殺的著作中,有一部出版時間最早、歷史最久遠的著作——《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它像一顆明亮的星星閃耀在群星中,為后人了解南京大屠殺提供了可靠的資料。作者田伯烈(H.J.Timperley)是一位外國記者。
奔走于戰火中的上海、南京
? 田伯烈,1898年出生于澳大利亞,1918年來到中國,任英國路透社駐北京記者,1928-1936年擔任英國《曼徹斯特導報》和美國美聯社駐北平記者。這一時期,他雖常駐北平,但其足跡遍布全中國及遠東地區。1936年初,田伯烈從北平遷居上海,在專注新聞工作的同時,積極參與社會慈善工作。同年5月,中國華洋義賑救災總會全票通過田伯烈加入該組織,他還擔任了中央委員會委員,專任駐上海揚子江流域賑災顧問委員會委員。1937年“七七事變”后,考慮到上海因戰事可能會增加難民,華洋義賑救災總會聯合中國紅十字總會、慈善團體聯合救災會、世界紅十字會等組織,共同成立上海國際救濟會。田伯烈又被推選為該會委員。
? 1936年下半年,西班牙內戰爆發。田伯烈奉《曼徹斯特導報》派遣,前往西班牙前線進行戰地采訪。淞滬抗戰爆發后,戰火中的數萬難民聚集于滬西法租界周邊,生活無保障,生命受威脅。當時,已從西班牙回到上海的田伯烈,出于良知與道義,利用自己在新聞采訪與社會活動中形成的人脈關系,爭取到部分日本外交官的合作,與法國神父饒家駒等人共同組建了上海南市難民區,以收容安置驚恐無依的難民。該難民區人數最多時達三十余萬人。
? 淞滬抗戰期間,田伯烈還參加了由上海麥倫書院校長夏晉麟、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國民政府立法委員溫源寧等人發起組織的抗敵委員會,并成為該委員會核心人物之一,從事各項抗日救亡工作。11月,上海淪陷前夕,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在上海設立的第五部改組為國際宣傳處。該處負責人董顯光、曾虛白等人對上海抗敵委員會中田伯烈等人的抗日宣傳活動贊譽有加,稱其為“上海數一數二的(抗日)思想領導者”。從而,田伯烈與軍事委員會國際宣傳處建立了十分密切的聯系和友好關系,并使抗敵委員會成為國際宣傳處開展抗日宣傳的一個外圍組織。
12月13日南京淪陷后,田伯烈仍對中國人民艱難進行的抗日戰爭充滿勝利的信心。有學者考證發現,英國《曼徹斯特導報》于12月17日發表的時評《其后的南京》一文,正是出自田伯烈之手。田伯烈在時評中指出:“首都是淪陷了,但是日軍還沒有給中國的主力部隊以致命打擊。日本陸軍司令官急想在中國民眾的警戒沒有擴大時直追中國軍隊至內陸,但未能得逞。中國雖失掉了主要都市、最大港口和富裕地區,但還不能說已經輸掉了這場戰爭。”其對中國人民堅持抗戰的激勵,躍然紙上。
為真實報道日軍暴行而斗爭
日軍自淞滬地區向南京進軍的過程,實際上是一路殺燒淫掠的過程。特別是1937年12月13日南京淪陷前后,日軍更加喪心病狂地濫施暴行,僅12月內,即在下關長江邊、漢中門外、水西門外與城南郊外的十次集體屠殺中,殺害無辜平民及放下武器的軍人達十九萬五千余人。美國外交官愛利生說:“這里的外國人相信,日軍占領的最初階段,每晚有一千多樁強奸案發生。”
? 田伯烈十分痛恨日軍對中國人民施加的暴行,同時同情中國人民的悲慘遭遇。1938年1月16日,他在一篇發送給《曼徹斯特導報》的新聞稿中寫道:
前幾天回到上海,我調查了日軍在南京及其他地方所犯暴行的報道。據可靠的目擊者直接計算及可信度極高的一些人的來函,充分證明,日軍的所作所為及其持續暴行的手段,使我們聯想到阿提拉及其匈奴人。不少于三十萬的中國平民遭殺戮,很多是極其殘暴血腥的屠殺。搶劫、強奸幼童及其他平民的殘酷暴行,在戰事早已于數星期前即已停止的區域繼續發生。今天《字林西報》報道了特別令人震驚的案件:一個日本兵尋找女人與酒不得而槍殺三名六十歲以上的中國婦女及射傷其他無辜平民數人。
田伯烈在這篇新聞稿中,提及日軍在京滬沿線屠殺了不少于三十萬的平民。其中“三十萬”的數字駭人聽聞、觸目驚心。該新聞稿于當晚為日方有關人員發現,在“征求主管官員的意見”之后,被認為內容“過于夸張”,存在“不適當之處”“可能危及(日本)軍方的感情”。田伯烈被日方無理要求前往日軍軍部接受盤查,要求在對新聞稿作出修改后,方可拍發。田伯烈拒不接受日方這一無理要求,被日方稱為“不服從指示”。他通過英國總領事館,向日方提出抗議,要求日方就無理扣發稿件作出解釋。
? 1月17日下午,在日方的新聞發布會上,田伯烈起立發言,公開揭露他“曾被命令前往日本軍部”的經歷。田伯烈為維護記者真實報道社會狀況的權利而進行的堅決抗爭,使日方大為惱火,被日方指責為“有意以此事制造事端”,并稱“我主管官員對他的態度更是大為不悅”。
? 但田伯烈并不氣餒,仍繼續搜集日軍在南京的暴行資料。1月21日,他根據《字林西報》對日軍在南京暴行的一篇社評,又寫成一篇揭露日軍暴行的新聞稿,“敘述敵軍十七人輪奸一華婦,及南京住戶被劫,各國使領館亦遭同樣命運”。但這篇新聞稿又一次遭到日方扣壓,并被無理要求“將原電撤回”。田伯烈堅決拒絕撤回原電,并將電文抄呈英國總領館。他還在當天日方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嚴詞駁斥日方的無恥狡辯。漢口《大公報》報道稱,他“與日發言人辯論,謂南京暴行消息均可證明,該發言人語塞”。
田伯烈為盡快將自己采訪搜集到的日軍在南京的暴行真相公之于世,在1月16日新聞稿不能由上海發往《曼徹斯特導報》的情況下,決定將其主要內容譯成中文,先在中國報刊上發表。1月24日,武漢《申報》將其中文譯本予以報道:
自余返上海后,余曾設法調查外傳日軍在南京及其他各地殘暴行為之真相。據目睹者之口述及極可靠方面的函述,日軍行動的暴虐,較中世紀匈奴之殘暴猶有過之。在長江下游一帶,被日軍殘殺之中國人民達三十萬人。至于日軍其他之奸淫搶奪之行為,更不勝枚舉。即年輕幼女,亦不免被奸。此種殘暴行為,在日軍占領已數星期之地方,仍極盛行。被殺之華人,亦與日俱增。此種行為,皆為日軍之羞。
? 報道發表后,立即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許多媒體以此報道內容為根據,憤怒聲討日軍的野蠻暴行。
出版第一部南京大屠殺著作
日本新聞檢查官一再對田伯烈的新聞稿無理扣壓、刁難的行為,讓田伯烈心中燃起了正義之火。他決心進一步調查、整理資料,另辟蹊徑,出版一部揭露日軍暴行的著作。他在后來出版的這部著作的序言中寫道:
去年十二月間,日軍攻陷南京后,對中國的無辜平民槍殺奸淫劫掠,無所不為。我身為新聞記者,職責有關,曾將所見所聞的日軍暴行,擬成電稿,拍發《孟卻斯德導報》(《曼徹斯特導報》)。不料,上海的日方電報檢查員向當局請示后,認為內容“過于夸張”,加以扣留,屢經交涉,都不得要領。于是,我決定搜集文件憑據,以證明我所發電稿的真實性,結果我從最可靠的各方面獲得許多確鑿的憑據,同時發覺事態之慘殊出人意表,因此我才想到這些憑據大有公諸世界的必要。這是我寫成本書的原因及經過。
田伯烈大約于1938年1月底開始有了編寫日軍暴行著作的計劃。1月底2月初,他全力搜集整理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成員貝德士、菲奇、馬吉等人提供的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資料以及上海租界《密勒氏評論報》《字林西報》等報刊的相關資料;3月中旬,他由上海到武漢,一邊繼續搜集、充實資料,一邊著手編寫書稿;3月21日寫成全書,正文九章共計十余萬字,連同附錄七篇,總共二十一萬字。該書書名為What War Means:The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戰爭意味什么:日軍在華暴行)。6月,該書英文版相繼在倫敦、紐約出版,各發行六萬冊,后來又有丹麥文、法文、日文等多種版本問世。該書在歐美各國的出版,幫助西方人民認清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兇殘本性和猙獰面目,使中國人民正在進行的反法西斯正義戰爭贏得了廣泛的國際同情和聲援。
中國國民黨國際宣傳處于同年3月下旬購得田氏書稿,并立即組織力量日夜趕譯。該書6月中旬翻譯完成,于“七七事變”一周年前夕,以國民出版社名義出版,譯者署名“楊明”,書名為《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并由著名民主人士、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郭沫若撰寫序言,趕印出首批一萬冊,后又增印至十萬冊。
? 作為全世界第一部揭露南京大屠殺的著作,《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的九章正文中,前四章是全書的核心部分,集中記錄了日軍侵占南京后,在城內外殺燒淫掠的暴行,以及用“良民登記”的欺騙手法,誘殺青壯年的可恥行為。第五至八章為日軍在南京周邊的長江三角洲地區與華北地區的暴行,以及以滬寧地區為主,在全國各地的野蠻空襲與無差別轟炸。第九章為“結論”部分,著者有力地駁斥了日本當局否定暴行的狡辯,一針見血地指出其“以恐怖手段,達到使中國民眾畏懼屈服的目的”之實質,精辟論述了日本統治階級為消弭社會內部不安而發動侵略戰爭的可恥目的,要求英國當局應“實踐以軍火或金錢援助中國的諾言”,強烈呼吁全世界人民都來支持中國人民的英勇抗戰。
該書自1938年出版以來,至今已經歷了80多年漫漫歷程。在這一過程中,曾有新華出版社(1986年)、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15年)、南京出版社(2017年)等出版社先后出版或重新翻譯此書。它的不斷出版,也從另一個方面顯示了該書在研究南京大屠殺日軍暴行及反擊日本右翼否定侵略戰爭方面的重要價值。
? 田伯烈于1938年7月被聘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顧問,并先后兼任該處駐歐洲、墨爾本辦事處主任,積極推動歐美、澳洲民眾團體的援華反日運動。1943年后,他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及印度尼西亞外交部工作,1954年病逝于倫敦。
(摘自《名人傳記》孫宅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