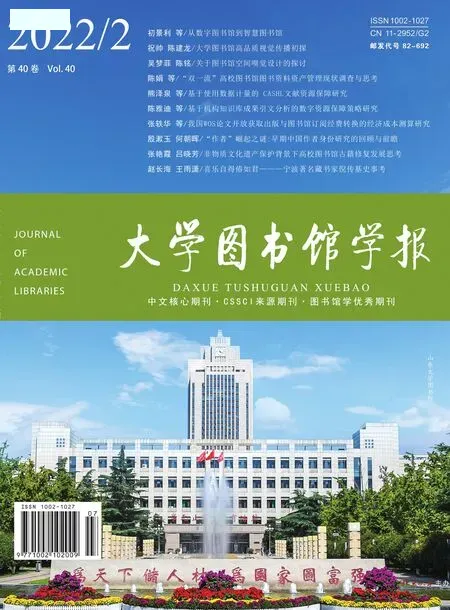大學圖書館高品質視覺傳播初探
——以北京大學圖書館的“尚美創新”實踐為例
□祝帥 陳建龍
無論從滿足大學圖書館用戶日益增長的對于視覺信息的需求來講,還是就大學圖書館支持高校全面加強和改進美育的時代任務而言,視覺傳播都已經成為大學圖書館現代化轉型發展過程中的重要工作之一。在新形勢面前,大學圖書館紛紛通過一系列舉措,服務于校園美育,打造藝術高地,而其中通過現代設計手段所進行的視覺傳播就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重要抓手。在這方面,北京大學圖書館作為一座有著悠久的美育傳統的大學圖書館,在經年累月的美育實踐中,積累了豐厚的美育資源,尤其是在2020年12月1日圖書館東樓重啟以來,通過一系列以視覺傳播為手段的大學圖書館“尚美創新”的實踐,初步積累了大學圖書館在視覺傳播方面的案例。在本文中,筆者將結合有關大學圖書館和視覺傳播理論對相關經驗進行階段性的總結與思考。
1 大學圖書館視覺傳播的歷程與現狀
在某種意義上,圖書館從誕生的那一刻起就有視覺傳播方面的職責和需求。在中國現代圖書館建設之初,已有諸多前輩學者和館員對“圖書館廣告學”的問題展開過理性的思考。尤其是20世紀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中期,隨著對西方圖書館學觀念及其相關研究的引入與介紹,關于圖書館與視覺傳播的話題,一度在民國圖書館學期刊上形成一個小高潮。
1926年,著名圖書館學家劉國鈞即在中華圖書館協會的《圖書館學季刊》上發文,介紹“公共圖書館之廣告術”[1];1929年,陶述先也在武昌曇華林文華圖書科的《文華圖書科季刊》刊文,介紹“圖書館廣告學”[2]。1932年第1期《圖書館學季刊》介紹了美國學者惠勒(J.L.Wheeler)的《廣告術的研究》一文,指出“此文特別注重小圖書館廣告術,作者以為此方面之受忽視,實使社會蒙相當損害。”[3]1935年,該刊再次介紹了凱特·科普蘭(Kate Coplan)的文章《圖像在圖書館新聞廣告上之地位》,指出“新聞廣告是使民眾注意圖書館故事的最有效方法。但是在這些新聞廣告上,如能繼續不斷的印出關于展覽品的種種圖像,則將有更圓滿之結果。”[4]1933年,陳影鶴在《廈門圖書館聲》第二卷第五期撰文《圖書館廣告之理論與實際》指出“圖書館之有廣告學,為時尤暫。1906年,美國圖書館協會,始有圖書館廣告委員會之組織。該會以種種廣告方法,招徠閱眾。所得效果,至為宏著。于是圖書館界,咸知圖書館廣告之重要;群起而研究實施。”該文中還列舉了“圖書館廣告”的幾種常用手段,包括報紙宣傳、張貼壁報、揭示標語、設置布告牌、印發傳單、分送圖書目錄、出版圖書館刊物、開圖書館展覽會、電影宣傳、游行廣告等十四項[5]。
誠然,以上這些論述更多說的是公共圖書館,而并非專門針對大學圖書館。李大釗就已經看到:“圖書館有兩種:一是社會的,一是學校的。社會圖書館的對象是社會一般人民,學校圖書館的對象是學生。這兩種的性質不同,所以形式也不一樣。”[6](166)“現在圖書館已經不是藏書的地方,而為教育的機關,所以和教授法有密切的關系。”[6](167)對于大學圖書館來說,它在公共圖書館的職能之外,還有教育的職能,是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無論如何,民國時期對于圖書館廣告學理論與實踐的探討,為今天討論大學圖書館視覺傳播奠定了一個重要的基礎。但是,僅僅從廣告學的角度探討圖書館的視覺傳播也還只是一個開端。畢竟在整個民國時期,國際范圍內學術界并沒有確立“傳播學”觀念,更沒有平面設計、視覺傳達設計等語匯,所以上述文獻中所說的“廣告學”,常常是包括視覺傳播和設計的內容在內的。從陳影鶴的文章就可以看出,與其說這里所列舉的內容屬于今日所理解的“商業廣告”,不如說和視覺傳播的范圍更接近一些。隨著20世紀后半葉傳播學理念的確立以及設計學的發展,視覺傳播的觀念在今天已經大大拓展。從“廣告學”到“視覺傳播”,是傳播理念的一次質的提升,即不僅僅局限在“廣告”的既有形態和思維定勢,一切和視覺有關的、有助于圖書館與讀者進行溝通的手段,都是圖書館視覺傳播的范疇,它同時研究和解決功能性和視覺美感這一體兩面的問題。
相對于純藝術,建構于設計學基礎之上的視覺傳播有功能性的目的指向,而相對于一般意義上的實用視覺信息,視覺傳播又是利用“視覺”的專業手段來組織信息傳播的一種方式。也正因此,相對于高雅藝術,視覺傳播更有機會與利用圖書館各種資源的讀者打交道。作為一門藝術學、傳播學的交叉學科,視覺傳播在今天日益成為一種專業。近年來,在心理學、傳播學、設計學、信息管理學等領域,可視化與信息設計的問題得到了比較充分的研究。只是隨著專業分工的不斷細化,圖書館學與視覺傳播的交叉學科討論,尤其是可視化在大學圖書館領域的具體應用反而沒有得到理論和實踐方面的充分重視。雖然近年來國內外的公共圖書館和大學圖書館在建筑設計、視覺導視、形象識別乃至文創產品開發方面都有了長足的進展,但與美術館、博物館等領域相比還顯得較為滯后,且多停留在自發的階段。
心理學的研究已經表明,視覺是人最重要的感覺,人獲取的外界信息中通常有80%以上經由視覺渠道,在視覺及其他感覺的基礎上,人產生了復雜的知覺、記憶和思維等心理過程,對輸入的信息加以識別、理解、表達和內化,逐漸認識到事物的本質和結構。信息服務與可視化在用戶和服務者對有關信息內容的識別、理解、表達和內化等信息應用環節存在交叉關系[7]。在圖書館領域,也有諸多文獻探討大學圖書館與設計之間的關系,并對圖書館無障礙設計提出具體的建議等[8]。可以看出,圖書館日益提升的服務意識對當前大學圖書館的信息設計提出了“可視化”的新的需求,大學圖書館也應該在視覺可視化方面為用戶提供更多的便利。
與此同時,視覺傳播作為藝術設計在大學圖書館中的應用場域,也是大學圖書館美育功能的重要體現。北京大學校長郝平提出:北京大學圖書館應該建設成“一流的文獻中心、一流的育人平臺、一流的文化殿堂”[9]。由此可以看出,大學圖書館作為教育機構,是立德樹人的重要場所,在服務于高校教學和學科建設方面,大學圖書館不僅是高校文獻信息的中心,也已經成為高校立德樹人的重要平臺。作為一種美育手段的視覺傳播,和一座現代化、服務型的大學圖書館有多方面的關系。通過視覺傳播的手段在大學圖書館開展美育工作,也隨著北京大學圖書館的東樓重啟提上議事日程。
2 大學圖書館與空間設計
所謂空間設計,包括室外的建筑設計、公共空間設計和室內的環境設計、展示設計等多個領域,是大學圖書館視覺傳播工作的重要內容。盡管狹義上的“視覺傳播設計”(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常常等同于“平面設計”(Graphic Design),但這只是在設計界內部,為了強調視覺設計的平面性區別于建筑環境設計、產品設計等的三維性而做出的一種約定俗成的區分。事實上,視覺設計的工作涵蓋二維(平面)和三維(立體)兩部分,正因為如此,業界也常常把“平面構成”“立體構成”“色彩構成”稱為設計學科基礎的“三大構成”。其中,空間設計當然是視覺傳播的重要組成部分。
大學圖書館向來被稱作“大學的心臟”,大學圖書館的建筑與環境設計也是大學校園建筑的中心所在。在很多高校中,圖書館都擁有獨立甚至多棟單體建筑,因此常常成為一所學校的地標和畢業季“打卡地”。以北京大學為例,北大校園建筑素有“一塔湖圖”的美譽,其所指均為未名湖周邊的地標性建筑。其中,“一”指的是第一體育館(一說未名湖南側的第一教學樓),“塔”指的是原燕京大學的水塔——博雅塔,“湖”指的是未名湖,以上三者均為原燕京大學校園建筑,而“圖”指的就是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也是北京大學入主燕園后的新地標。
空間設計作為一種視覺傳播,體現了建筑學、美術學、設計學、風景園林學、景觀建筑學等多學科的融合與交叉。北京大學圖書館東樓在建筑設計方面堪稱典范,采用的是清華大學建筑學院關肇鄴院士的設計方案。關肇鄴院士作為新中國培養出的第一代建筑師,長期致力于文化、教育建筑的創作和研究。他擅長將傳統建筑元素融入新建筑,創造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建筑;同時又有西方留學背景,他翻譯的《從包豪斯到現在》(新版更名為《從包豪斯到我們的豪斯》)一書,是20世紀80年代初許多中國建筑師、設計師了解“包豪斯”的第一部著作。北京大學圖書館東樓建筑可謂關肇鄴院士的代表作,曾榮獲教育部2000年度優秀建筑設計一等獎,并入選首批“中國20世紀建筑遺產名錄”。2018—2020年,為提高圖書館的安全性和宜用性,北京大學對圖書館東樓建筑進行了修繕,并于2020年12月1日舉辦了東樓重啟儀式。
東樓的修繕維持了原設計仿唐代建筑“歇山頂”的主體建筑結構,但在細節設計上進行了相應的完善。“修繕的意義雖然不能和建成新館相提并論,但依然可喜可賀,它很可能是圖書館和學校邁上發展新征程的新起點。”[10]在色彩方面,修繕維持了原設計以高級灰(或稱“莫蘭迪灰”)為基礎色系的整體色調,但又在細節處理上體現出現代感,如將入口處的頂棚色彩由原先的銀色改為古銅色,在與建筑本身的色彩基調相協調的基礎上更加體現出一種厚重感,讓人更加容易聯想起盛唐氣象。與此同時,重啟后的空間設計也體現出功能導向,即從用戶多元化、“百感交集”的需求出發重新進行空間的規劃與設計,設置了和聲廳、新書展閱廳、藝術鑒賞廳、展覽廳、大釗閱覽室、名家閱覽室等全新的服務空間。
圖書館東樓序廳、門廳進行了全新的設計,新的序廳被打造成由山東省臨朐縣有關方面捐贈的景觀石——紅絲石“鐘靈”和改造后的格柵門共同組成的“文房”的場景,其中,紅絲石是制硯的名貴石材,鐫刻著鄧小平題寫的“北京大學圖書館”館名;格柵門上懸掛著原有的江澤民題寫的“百年書城”木匾。在門廳中后方,矗立著由清華大學美術學院吳詩中、王巍設計的大型青銅浮雕壁畫(內嵌顯示屏)《人與信息》,其色彩與東樓入口處頂棚及室內其他金屬裝飾的紅銅色遙相呼應。2021年畢業季,東樓的序廳和門廳成為畢業生的新“打卡地”,前來拍照的學生絡繹不絕。
步入式新書展閱廳則是又一個展現北京大學圖書館視覺傳播創新的范例,其創意設計與色彩系統均有可圈可點之處。其中,以象形的篆書“水”字、北京大學圖書館Logo及漢字和仿博雅塔景觀為外觀的書架成為新書展閱廳的主體。這種“具象書架”既是向現代設計大師索特薩斯所設計的具象人形書架致敬,又充分考慮了實際功能的需求。在色彩設計方面,“水”形書架仍采用“莫蘭迪灰”色系的灰藍色作為整個新書展閱廳的基調,漢字、塔形書架則采用與墻壁一致的色彩,與整個空間融為一體,北京大學圖書館Logo書架采用“北大紅”標準色。由于新書展閱廳同時也起到圖書館東南門通向東樓中心區的“動線”的作用,所以“水”形書架也有人來人往、“川流不息”的寓意在其中,與其他書架、讀者共同營造出一個“動靜清和”的視覺閱讀空間。
北京大學圖書館東樓還啟動了包括會議室背景板主視覺、遮光幕簾及室內裝飾設計,室內家具(如書架、閱讀桌椅、研修專座等)與陳設設計,南北配殿區域空間設計等一系列空間設計工作。展覽展示設計也是空間設計的重要組成部分,北京大學圖書館作為北京大學校內重要的展覽展示空間,設有600余平方米的展廳,已經成功舉辦館藏珍稀文獻展、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主題展,此外,館內其他空間也承辦了“可愛的中國書”常設展、館史展、“書說黨史”展等多個展覽,致力于探索打造情境式、學術性相結合的新展覽展示設計理念。
3 大學圖書館與平面設計
在設計學理論體系中,就產出作品的體量而論,平面設計也許是最微不足道的,但是其基礎意義卻不可或缺。可以說,平面設計是視覺傳播最基礎的元素,以至于在業內常常把平面設計直接等同為“視覺傳播設計”。從基于印刷和傳統媒體介質的字體設計、Logo與吉祥物設計、書籍裝幀設計、商品包裝設計、廣告招貼設計到新媒體環境下的網頁設計、H5設計、信息可視化設計、動態圖形(Banner)設計等,都包括在平面設計的范疇之內。平面設計包含的子門類又有很多,專門設計書籍裝幀的書籍設計工作室就與專門設計字庫的字體設計公司有很大不同,專門從事包裝設計的機構也與廣告公司各自為政。近年來還出現了專門創作Logo甚至電影海報的工作室,至于各文博機構流行的“文創”,如故宮日歷等,很大程度上也包括在平面設計的范圍之內。因此,對于平面設計內部的不同領域,也需要分別對待。
視覺導視系統與一座大樓的功能息息相關,因此視覺導視系統常常被視作是建筑設計的最后一道環節。與建筑比起來,雖然導視系統體量不大,但往往正是這樣的“細節”決定了建筑物的易用性和人文關懷。視覺導視系統設計所組織的信息和元素——如色彩、指示圖形等——基本上屬于平面設計的內容,但它承載著指引人流的功能,因此與空間設計關系密切。國際上一些知名的建筑設計事務所,往往都會有為之“貼身服務”的視覺導視設計公司。
北京大學圖書館東樓視覺導視系統設計中,設計師選取了東樓建筑細節中的“方格”作為基本元素,色彩選擇與建筑主體一致的灰色,以無襯線字體(中文字體為方正蘭亭黑,英文字體為Akkurat家族)進行系統設計和深化,并由輕型鋁材施工完成安裝。視覺導視是一項系統的設計工程,由于東樓重啟后增加了許多功能性空間,導視方面沒有前車之鑒,同時在使用中也需要不斷調整。因此從東樓重啟后,視覺設計系統的細節一直在逐步完善,尤其是設計師與圖書館的業務部門密切合作與對接,與書籍搬遷同步完成二層自然科學廳、三層社會科學廳的書架導視系統的設計與安裝。在使用過程中廣泛聽取用戶建議,逐步完善其他設計細節,如增加多處導向提示、對樓層導覽的平面圖朝向進行調整等,得到了制作公司的配合,較好地完善了用戶體驗。
視覺系統設計還有利于實現圖書館各個組成部分的整體化和一體化。現今很多高校中,圖書館不只有一棟樓,或分散于校園的多個角落,或建立總館、分館的協同體系。由于建筑物并不在一起,所以在視覺風格上很難一致,此時視覺系統設計就可以提供一個很便利的抓手,讓讀者在圖書館的視覺方面建立起整體的識別性。以北京大學圖書館為例,不僅有剛剛重啟的東樓,也有1975年落成的西樓,還有40余個分館。因此,通過導視系統對各館區進行視覺秩序的整合是一項遠大的工程。
當然,大學圖書館的平面設計也不僅僅體現在視覺識別系統方面。就大學圖書館而言,其最重要的收藏——書籍本身就是平面設計的產品,圖書館本身需要標識設計,圖書館建筑的室內分布、指引等也需要高度依賴視覺導視系統設計,而圖書館服務讀者最直接的視覺渠道——海報、網站等信息,也有賴于文字與圖形圖像的設計與編排。在某種意義上,大學圖書館的館員及用戶每天都在和平面設計打交道,但也因此使得平面設計的專業性常常被忽視。以往在一些大學圖書館中,宣傳海報、借書證卡、中圖分類法標識等常常由非設計專業出身的館員親力親為,雖然工作精神可嘉,但在字體、色彩設計方面常常缺乏專業設計師的敏感,更遑論很多時候在館內張貼的“請保持安靜”“請隨手關門”等指示性標語,也是隨意打印在A4紙上而缺乏平面設計的介入。但問題在于,圖書館又不可能設置專門的設計館員崗位。
有鑒于此,北京大學圖書館在東樓重啟后,于2020年12月依托職能部門用戶關系辦公室設立了視覺設計工作室,并面向全校師生征集選拔具有一定設計基礎的志愿設計服務者,在用戶關系辦公室的協調配合下,從學生中選拔海報設計志愿者,建立相對穩定的隊伍,加強專業培訓、邀請專業設計師授課,通過統一字體、色彩、版面,逐步建立圖書館視覺設計標準與規范,服務于館內各部門。首批工作室成員確立為9位學生、1名指導教師,一年內已產出29套、近50張海報,提供4套海報設計模板,設計了迎新季總體活動及系列活動、畢業季總體活動及系列活動主視覺設計,并承接了新年主題、建黨主題的網站主頁海報制作,邀請函、志愿證明書等設計任務。視覺設計工作室致力于推動圖書館視覺識別系統規范化。2021年6月,視覺設計工作室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微信服務號發布線上展覽“書香色美︱圖書館線上海報展”,集中展示了工作室成立半年以來的設計作品,發布當天閱讀量即破千。
在北京大學圖書館視覺設計工作室目前已完成的各類設計作品中,意義最為重大的當屬北京大學圖書館標志(Logo)的改良設計。北京大學圖書館的標志為上世紀80年代沿用至今,設計者沒有記載。該標志具有識別性強、形式現代等優點,但在字體、圖形等方面有些陳舊,存在改良的空間。同時,在經年累月的使用中,由于缺乏規范,該標志出現多種不同的應用形式,亟待統一。視覺設計工作室所進行的改良設計,在保留原創意(圖形、色彩)的基礎上進行細節的微調,使之更具現代感和視覺沖擊力,具體如圖1所示。具體方法是,首先,在現有圖書館的標志設計中確定唯一方案作為核心圖形;然后,調整細節的形式感,其中最主要的是改變圖形與字體之間的比例關系,并以無襯線字體取代原先的有襯線字體;最后,通過調研、論證、設計等,在學校整體標識設計的基礎上確定圖書館標識系統標準圖形、色彩、字體以及應用規范。這一改良設計目前已經廣泛應用于北京大學圖書館線上、線下各個場合,今后還可繼續延展應用,對信封、名片、PPT模板、網站等標識使用進行進一步的統一和規范。

圖1 北京大學圖書館標志改良設計前后對比
4 尚美創新:大學圖書館視覺傳播的使命
“尚美創新”是北京大學圖書館“四尚”風氣建設內容之一,其含義之一是拓展美育功能,建設美育殿堂。美育,一言以蔽之,即“美感之教育”或“審美教育”。專業藝術教育和美育的關系,有些類似于科學研究工作和科普的關系。已經有學者指出,美育不同于藝術教育,因為“現代藝術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職業教育或者專業教育,而美育更多指的是素質教育。……作為職業教育或者專業教育的藝術教育,更加重視技術方面的訓練,作為素質教育的美育,更加重視趣味的培養。”[11]
專業的藝術教育往往是在專業類高校或綜合大學的相關院系中展開,但面向非專業學生的審美和美感教育,只能開設通識類課程,這對于專業藝術教育機構和院系來說就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大學圖書館則是一個面向所有院系、專業師生開放的場所,是大學的常設機構,并且幾乎可以涵蓋所有藝術類別。如北京大學圖書館設立的“藝術鑒賞廳”“和聲廳”,就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圖書館只能安靜閱讀的刻板印象。因此,大學圖書館在美育方面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可以讓人“百感交集”。事實上,大學圖書館美育不僅體現在舉辦藝術講座、美術展覽、播放電影等外在的環節,還可以從多方面著手介入美育實踐,尋找突破。其中,與讀者的日常審美與信息需求息息相關的視覺傳播設計,便是一個亟待打開的突破口,北京大學圖書館已經開始了相關實踐。但大學圖書館通過視覺傳播推動“尚美創新”仍有許多問題和挑戰,在此提出與業界同人討論。
首先,大學圖書館的設計隊伍與機制建設亟待加強專業性與穩定性。
由于大學圖書館對于信息設計的需求日益增加,且視覺設計成為日益專業的研究領域,因此,建立一支以指導教師和學生志愿者為主體的專業人才隊伍,從事圖書館日常所需的各種設計服務勢在必行。但是由于經費、編制等限制,目前很多大學圖書館尚不存在對應的崗位。北京大學圖書館的做法是在綜合管理中心成立用戶關系辦公室,下設協調學生志愿者服務的專門部門,對內統一招聘具有一定設計素養和技能的學生志愿者,從事館內各種專項設計服務,對外負責與專業設計機構對接,開展空間設計、展覽設計、導視系統設計等大型設計項目的統籌與合作。目前,通過這種方式建設起來的“視覺設計工作室”已經初步建立與館內各部門的協同互動機制,設計的內容還將逐漸從海報設計,擴展到新媒體平臺、展覽展示設計及各類官方短視頻等。由于學生志愿者多來自非專業院系,作為義務工作無法全時間投入設計工作,且學生本身具有較大的流動性,所以設計作品的質量和風格的延續性很難保證。理想地看,有條件的大學圖書館還需要設置專門的設計管理辦公室,承擔設計管理職能,與專業設計機構合作。
在大學圖書館設立設計管理辦公室并不是說館員要親自從事各種設計工作,而是做好專業的把關人,代表圖書館做甲方、用戶和專業設計機構對接的中介。我們可以看到,今天各種類別的設計都已經成為非常專業的領域。不同的設計類別之間更可謂“隔行如隔山”,而各種設計類型作為視覺傳播的具體手段,在大學圖書館中都有不同程度的需求,要求大學圖書館館員掌握各種設計的手段和語言,或是招聘各個設計專業的館員并不現實。但是,設計工作又是一項需要和甲方進行積極配合的工作,甲方(大學圖書館)不需要親自動手設計,但卻需要與設計公司進行積極的配合。所以,大學圖書館需要的是既有設計方面的審美素養,又能積極與各個門類設計公司展開合作的設計管理工作者。同時,該辦公室可以與圖書館標識管理辦公室合署辦公,建立健全圖書館標識系統基本體系及使用規范,并加強對圖書館標識系統使用的規范、管理及授權,研發圖書館定制字體、文創等,進而建設大學圖書館的藝術品牌。
其次,大學圖書館亟待建立視覺傳播的協同創新機制,通過舉辦設計展覽、開展設計教育等手段,切實提升用戶的設計素養。
此前,北京大學圖書館在協同服務方面策劃組織了一系列高水平專題展覽與研討會,開展系列藝術培訓活動、系列講座等。但目前此類藝術講座還更多體現為高雅藝術、影視鑒賞等,在與日常生活、與圖書館服務息息相關的視覺傳播與設計方面的關注還不夠。視覺傳播與設計是心理學、新聞傳播學、藝術學、設計學等多學科交叉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操作領域。各學科可以分別開展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視覺傳播和美育活動。圖書館的優勢在于既能提供服務和促進相關學科建設,又能整合多方力量協同創新美學美育。一方面,圖書館可以為相關制造學科(如工學和交叉學科等)的產品設計、字體設計、圖形圖像設計等提供美學美育介入、展覽展示和通識教育空間;另一方面,與公共圖書館相比,大學圖書館更有利于提供優質的教育資源服務用戶,可以邀請校外的設計業界人士、一線設計師舉辦設計美育及視覺傳播系列講座、案例分享等,使之成為側重于基礎理論類的研究型大學學科建設的重要補充。
最后,突出大學圖書館學術研究方面的專業優勢,加強視覺傳播的文獻資源建設、收藏序列和學術研究積累。
與社會上的公共圖書館不同,大學圖書館,特別是研究型大學的圖書館,在文獻資源建設方面往往具有很強的專業性,服務的人群多為從事學術研究的專業讀者。在藝術文獻整理和研究方面,北京大學圖書館也有著重要的歷史傳統和文獻積累。1918年,北京大學圖書館館員王岑伯(王峻),曾以線裝、石印的方式在北京大學出版部出版了我國第一部新式意義上的書法史著作《書學史》。如今,大學圖書館在視覺傳播、設計類圖書文獻的資源建設和閱讀指導方面有天然的優勢。在學術研究方面,大學圖書館應加強藝術設計類文獻的專題研究,尤其是視覺傳播服務和設計相關問題的專項理論研究,可以設置專門的設計學文獻資料閱覽室,整合相關文獻、數據庫及校內專業師資、研究資源,為學科交叉創新和未來設計學學科建設提供文獻、數據資料和協同服務保障。并且在此基礎上牽頭申報館藏藝術及美育文獻整理與研究項目,設立有關課題,成立虛體研究機構,舉辦設計文獻論壇,發表、出版相關研究成果,成為全國高校設計藝術文獻研究的中心。
與此同時,大學圖書館還有條件建立完善藝術設計收藏和專題展示序列,尤其是在書籍裝幀設計、字體設計等方面,大學圖書館有收藏、展示與開展數據庫建設的條件。以北京大學圖書館為例,作為國務院批準的首批國家重點古籍保護單位,館藏包括150萬冊中文古籍,其中20萬冊善本,這些古籍善本不僅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其裝幀、字體設計等本身也是設計史上的杰作。目前北京大學圖書館的藝術文獻收藏以拓片為大宗,初步建立了完整的拓片收藏序列。大學圖書館還可有意識地進行月份牌畫、連環畫、海報設計、“世界最美的書”等視覺傳播、設計的專項收藏與展示、出版。當然,和其他收藏序列一樣,對設計作品的收藏和展示也要建立嚴格的準入制度,才能在起到甄別品鑒作用的同時,更好地對廣大師生用戶進行審美設計和視覺傳播素養的教育。
5 結語
“不同階段,圖書館事業的發展重點會有不同領域。當前,通過館員全面發展、資源全面升級和用戶全面受益,力行服務空間優化、科研布局優化和事業生態優化,實現服務管理轉型,恐怕是許多大學圖書館的重點領域。”[12]《北京大學圖書館十四五發展規劃》中也提出“打造促進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地標式教育空間”和“充分發揮審美育人、環境育人功能”的具體任務。作為應用美育的一個重要途徑,視覺傳播的水平與專業程度無形中反映出大學圖書館的審美品位與文化軟實力,當前已經開始為包括北京大學圖書館在內的各大學圖書館所重視,但無論從用戶日益增長的現實需求還是視覺傳播所能夠觸及的應用領域來看,都還存在著很大的改進空間。本文的目的在于拋磚引玉,以期引發更多對大學圖書館視覺傳播問題的關注與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