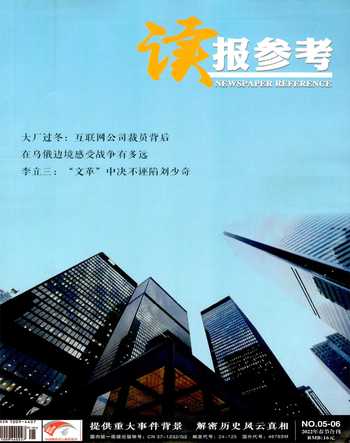她找到的抗體,可以對抗奧密克戎
去年12月8日,由清華大學張林琦教授團隊領銜研發的我國首個新冠病毒特效藥獲得中國藥監局應急批準上市。張綺是張林琦團隊中的一員。12月23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在國際性科技期刊《自然》上發表了一項新的研究成果,研究者找到全球19株有代表性的新冠病毒抗體,檢測它們對抗奧密克戎毒株的能力,其中18個抗體的中和活性為負值,只有張綺找到的抗體的中和活性為正值——2.2,這意味著,面對奧密克戎這個讓全球陷入新一輪恐慌的新冠變異毒株,這個抗體的中和活性較之前提高了2.2倍。
先找到BRII-196抗體
新冠病毒進入人體后,需要感染細胞才可以繼續繁殖并攻擊人體,如果有中和抗體把病毒攔截于細胞之外,那么,病毒就無法在人體內存活。新冠特效藥的研發就是基于這個看似簡單的原理。
張林琦團隊研發新冠特效藥的工作從2020年1月12日開始。當天,我國向世界公布了新型冠狀病毒基因組序列信息。也是在同一天,武漢已累計報告確診患者41例,其中1例死亡。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已在武漢打響,并開始引起全國的關注。
3天后的晚上9點,在離武漢1000多公里外的北京清華園內,張林琦和生命科學院王新泉教授共同召集團隊開會,啟動尋找新冠病毒中和抗體的工作。專門攔截新冠病毒的高效中和抗體混雜在人體內上億個抗體中,團隊遇到的第一個難題便是找到這些抗體。
通過和深圳市第三人民醫院黨委書記劉磊、教授張政與副研究員鞠斌的合作,2020年2月9日,張林琦團隊拿到了初步篩選的206株新冠病毒抗體基因。張綺接棒負責尋找里面中和活性最好的抗體。在拿到抗體之前,張綺就已經搭建好了一個可以測試抗體中和活性的系統,并用其他小分子藥物作了測試,在短時間內做好了前期準備工作。當時,全世界范圍內都沒有抗新冠病毒單克隆抗體的結構信息。張綺是第一撥摸著石頭過河的人之一。由于沒有結構信息提示抗體的作用靶點,張綺只能反復地進行交叉競爭實驗,摸索著前行。
2020年3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來到清華大學考察調研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科研攻關工作。他走進了實驗室,鼓勵和囑托團隊:“人類同疾病較量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科學技術。”3天后,張綺找到了中和活性最強的BRII-196抗體,辦公桌上的那臺電腦里記錄了這株抗體令人欣喜的數據。當天,張林琦、張綺和幾位學生還和顯示器上的數據合了影,以記錄這具有歷史意義的時刻。
可以對抗奧密克戎的BRII-198抗體
在找到BRII-196抗體后,張林琦團隊沒有止步,而是與騰盛華創醫藥技術(北京)有限公司的朱青博士等研發人員共同決定,繼續尋找另一個抗體,一起打配合戰,以應對今后可能會出現的變異毒株。從阿爾法毒株、德爾塔毒株,再到現在肆虐全球的奧密克戎毒株,無不證明了當時這個決定的正確性。
值得一提的是,同樣是冠狀病毒的SARS病毒和MERS病毒其實并沒有很活躍的突變,張林琦團隊對這兩個病毒也進行了相關研究。在2020年初十分緊張的大環境下,如果只選用一株抗體,不再多花時間選用“備胎抗體”,也是合情合理的。然而,張林琦團隊選擇了更加保險、穩妥的方案。
“備胎抗體”的篩選并不是一帆風順的。在確定了第一株抗體后,和它一同配合的第二株抗體,在中和活性需要達到一定標準的同時,還不能與第一株抗體存在競爭性。兩株抗體要達到1+1>2的效果。
兩個抗體的競爭性是指兩個抗體相互競爭著攔截病毒,競爭性高便會影響抗體的聯合使用。經過反復地篩選,張綺剔除掉了很多有50%以上競爭性的抗體,剩下為數不多的抗體中有一株和BRII-196抗體有40%的競爭性。這個抗體被選為了“備胎”。但是“40%”這個數據,在張綺心里一直是個過不去的坎兒。“40%,這是個真競爭還是假競爭?其實有些說不清,像是有個什么東西一直在撓著你,你知道應該問題不大,但就是有點兒不放心。”糾結再三,張綺決定再去試著找一找新的抗體。
在爭分奪秒的緊要關頭,張綺又耐下心來,多花了兩三周的時間,找到了一株和BRII-196抗體基本是0%競爭性的抗體——BRII-198抗體。經歷了一年多,新冠病毒已經變異出了奧密克戎毒株,在這個有著37個突變位點的變異株面前(德爾塔毒株是11個突變位點),眾多抗體都敗下陣來,而BRII-198抗體的中和活性卻更強了。
在尋找BRII-198抗體的過程中,張綺還加入了一點自己的“小心思”,在保證中和活性的前提下,張綺選擇了一個比較“小眾”的抗體。“病毒在突變過程中,為了可以成功逃逸,會針對比較多的那類抗體去突變,而‘小眾’的概率就低了很多。”這里的“小眾”,張綺解釋說:“這個抗體的中和活性肯定是比較好的,但是又不是最好的;此外,和大多數抗體相比,它和病毒結合時的靶點位置比較‘小眾’。”
去年11月下旬,世界衛生組織公布了奧密克戎毒株的基因信息,它的突變位點數量明顯多于近兩年流行的所有新冠病毒變異株。張綺告訴記者,她看到奧密克戎毒株的基因序列信息中病毒和細胞結合的靶點位置后,大概就清楚了自己之前找的BRII-198抗體對它會有效,“比較有信心”。此外,因為擔心新冠病毒變異株會導致抗體失活,張綺及團隊中的其他成員此前還專門針對單個突變位點測試過,抗體均保持了較好活性。此次奧密克戎毒株的37個突變位點相當于是單個突變位點的綜合。
當然,抗體是否能保持活性,最終還需要看實驗室的檢測結果。基因信息公布后,張林琦團隊也第一時間作了針對奧密克戎毒株的抗體活性檢測,經過合成基因、嵌合病毒包裝、中和活性檢測等長達一周多的實驗工作,實驗結果終于出來了——我國首個新冠特效藥對奧密克戎毒株仍保持著良好的活性。
聚光燈之外的地方
2005年從武漢大學畢業后,張綺進入德國哈勒維滕貝格大學攻讀碩士和博士學位,其間,她開始了人工抗體領域的研究工作。
哈勒維騰貝格大學是德國一所著名的綜合性大學。在這所有著500多年建校歷史的大學里,張綺接受了8年系統而扎實的科研訓練。2013年,張綺進入張林琦團隊,開始從事傳染病抗體的研究工作,主要是作艾滋病的抗體研究。艾滋病病毒的變異和新冠病毒的變異完全不是一個量級,前者經常在一個人的身體內就可以變異出多達上百種的變異毒株。在沒有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張綺的日常工作主要是研究艾滋病病毒。
然而,包括張綺在內的眾多科研人員,多年來對艾滋病病毒的研究并沒有取得特別重大的研究成果。
在張綺看來,科研過程中那些閃閃發光的靈感背后都是無數個日夜的積累。“這個積累的過程對我們來說,就像是拿個小錘子在山洞里鑿礦一樣,大部分時間都是黑暗的。”
如何在黑暗中堅持下去?張綺說,需要有一個信念支持。
2020年2月中下旬,是張綺尋找抗體過程中最為膠著的一段日子,當時武漢的抗疫形勢尚未明朗,看著每日大量新增的確診病例,張綺總是在想,自己正在研究的這個藥,萬一能用于患者,拯救了生命,那將會很有意義。
“萬一”這個小概率的對立面是“萬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而這“萬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在張綺看來,并不意味著沒有價值。作為科研人員,用自己的學識儲備去探索未知是本職工作,“你不一定是最后摘得果子的那個人,如果我沒做成,但是我告訴別人我為什么沒成,這也是在貢獻自己的價值”。
(摘自《中國青年報》劉昶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