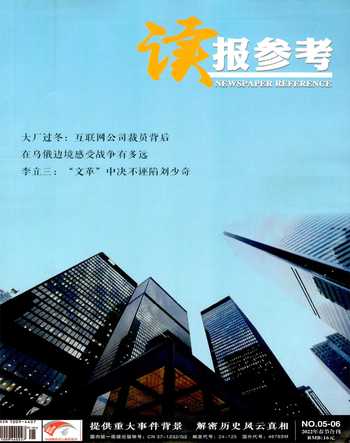疫情之下,全球“后浪”擇業觀“轉向”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全球不同國家的年輕人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工作與生活,職業選擇也出現了新變化。護理、木工、務農等一些看上去并不新潮的職業,又重新在“千禧一代”(泛指出生于19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的一代人)和“Z世代”(泛指“95后”“00后”)中獲得了超高的“好感度”。此外,靈活就業、自由職業和創業也成為不少人的新寵。
追求接地氣
在選專業這件事上,英國學生如今有了些不一樣的想法。
英國大學和學院招生服務中心(UCAS)數據顯示,2021年,英國護理課程的注冊人數在多年下降后出現反彈,約60130名申請者的數字比2020年增加了32%。同時,醫學、工程、教育和建筑等專業的申請人數也出現顯著上升。
而與之形成對比的,是數以千計的學生放棄了申請語言、歷史、哲學等人文類學科。年輕人的態度發生反轉,其背后的深層原因也引起了英國教育界人士及媒體的關注。
UCAS負責人克萊爾·馬切特指出,是那些疫情期間發生在醫院的暖心故事導致申請護理專業的人數激增。英國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所長尼克·希爾曼表示,疫情改變了人們對護理的看法,“如今,學生們普遍認為這是個值得尊敬的職業”。
25歲的弗洛倫斯·里夫正是帶著這份憧憬與敬意選擇了護理專業。在看到作為護士的朋友在疫情期間的經歷后,里夫申請了普利茅斯大學的兒童護理專業。
《每日郵報》分析稱,這也表明疫情之下,許多學生希望未來能走上一條更安全、更穩定的職業道路。希爾曼預測,這些趨勢或會持續一段時間,而疫情的發展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人們從事公共服務類的工作。
為熱愛冒險
面對疫情帶來的不確定性,有人渴求安穩,也有人在重新評估自己的生活后,決定冒險。
美媒報道稱,疫情改變了部分美國“千禧一代”的優先事項,“他們決定掀翻曾經精心安排的人生棋盤,去做自己喜歡的事”。“如果作出這類選擇的人有什么口號的話,那就是YOLO(You only live once,即‘你只能活一次’)。”《紐約時報》認為,一些“擁有財務緩沖能力和緊缺技能的人”更有可能拋卻恐懼和焦慮,去追求自己向往的工作與生活。
33歲的布雷特·威廉姆斯是一名生活在奧蘭多的律師。疫情期間,他在家參加完幾輪線上會議后身心俱疲。他說:“我突然意識到每天都要在廚房的吧臺前坐上10個多小時是多么痛苦。我當時在想,還有什么可失去的呢?或許明年就是末日。”
于是,他離開了身為合伙人的大公司,在他隔壁鄰居經營的小公司找了一份工作,并把更多的時間給了妻子和寵物狗。“我仍然是個律師”,威廉姆斯說,“但我已經很久沒有這樣興奮地去工作了。”
前《每日野獸》記者奧利維亞·梅塞爾也是“YOLO”的一員。歷經漫長的疫情報道,她于去年2月辭職,并從布魯克林搬到了離她父母家不遠的薩拉索塔。從那之后,她一直從事自由寫作。
梅塞爾認為,不是所有人都能有這種“顛覆”的勇氣。但她表示,這種變化是一種恢復,“我對自己的生活可能是什么樣子,以及它能有多充實,有了全新的創造性認識”。
另有一些人是在疫情期間丟了工作,才被動開啟了“冒險人生”。國際勞工組織資料顯示,疫情中,一些25歲以下的年輕人開始轉向創業和打零工,因為他們的失業可能性是25歲以上員工的3倍。
2021年初,巴爾加夫·喬希還是孟買一家高端意大利餐廳的主廚,但疫情沖擊下,他無奈“下崗”。從那之后,他決定將自己的廚藝施展在父母的廚房,并開設了自己的外賣店。經營5個多月后,喬希基本實現了收支平衡。他表示,這份難得的創業經歷不僅讓他成就感滿滿,也讓他重燃了對未來的期盼。
美國非營利組織國際青年基金會總裁兼首席執行官蘇珊·賴克爾表示,現在的年輕人越來越具有創業精神,他們以一種更加非傳統的方式看待職業、就業以及教育。
但挑戰與風險往往是并存的。《紐約時報》指出,“當花光積蓄且新嘗試花開無果的時候,一些人最終又回歸了穩定的工作”。
刮起“藍領風”
老齡化、受教育程度低……在過去,藍領工人總被貼上這樣的標簽。如今,韓國的“千禧一代”,甚至是“Z世代”對這一行業的看法出現了改觀。
19歲的韓國女孩李亞珍從小在澳大利亞長大,受當木匠的父親影響,她從小就立志從事建筑領域的工作。高中二年級,李亞珍放棄了學業,決定給父親打下手。經過多年歷練,如今李亞珍已經是韓國某住宅建筑公司最年輕的員工,薪酬不菲。
李亞珍說,在她長大的地方,房屋建筑或木工等高技能勞動是孩子們夢寐以求的體面職業,但這些工作在韓國卻頗受冷落。“木匠是技工,也是藝術家,他們參與了人們賴以生存的房屋建造工作。”李亞珍表示,社會對這份職業的偏見是不正確的。
韓國《中央日報》分析認為,如今韓國越來越多的年輕一代意識到他們在勞動力市場可以有無數選擇,也開始厭倦了社會的狹隘期望。對于他們來說,藍領工作意味著更為靈活的工作時間,更小的人際關系壓力,甚至是更高的工資待遇。
在一些視頻平臺上,由一群年輕的建筑從業者共同運營的“木工日記”頻道吸引了近萬名訂閱者,他們每周會上傳兩個關于設計與木工的視頻。
35歲的頻道負責人趙秀圣表示:“即便有人不同意,但于我們而言,這是一份充滿意義的工作。”
專家表示,年輕人對藍領工作的“轉向”早該發生。“這個國家需要的遠不只是醫生或律師,所有工作都應該受到尊重并得到恰當的報酬。”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韓國問題學者休·帕特里克說道。
回鄉搞創業
告別城市、回歸鄉村,也代表著當代青年理想生活的新模式。美國、韓國、印度……如今,在很多國家的鄉野間,涌現出很多的年輕面孔。
一項調查顯示,2020年,有48%的美國“千禧一代”表示自己住在大城市之外,這比前一年同期增加了4個百分點。而“Z世代”的這一增幅則更大,從41%增至49%。
10月的一天,韓國京畿道抱川市永中面抱川草莓治愈農場,踏著電動腳踏車的老板安海城正在使用手機應用檢查農場的溫度、濕度和采光情況。2020年,他辭去在建筑公司年薪8000萬韓元(約43萬元人民幣)的工作,打算結合人工智能和大數據技術在鄉村打造一個智慧農場。
據韓媒報道,青年人往往采取“半務農半X”的形式進行創業,“白天務農,晚上經營餐廳,開辦美術課等尋求生活與工作平衡的生活方式,對年輕人來說頗具吸引力”。
數據顯示,在2020年韓國回鄉務農的人群中,30多歲年輕家庭的數量比前一年增加12.7%,達到1362戶,創下歷史新高。據印度媒體報道,農業是疫情期間印度波動最小的部門之一,它吸收了42%的建筑工人,以及40%的衛生和教育人才。
有媒體分析認為,無處不在的競爭、嚴峻的就業形勢,以及高昂的房價和物價,無一不把年輕人推向了城市之外,而疫情讓本就沉重的城市生活變得更加難以喘息。
但鄉村生活對于這些年輕人來說也并不全是“鮮花玫瑰”。對于從未做過農活的他們而言,播種、培育、收獲等每個流程都是新挑戰。若想享受鄉村生活,就要作好放棄城市便利生活的準備。
(摘自《新民晚報》王若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