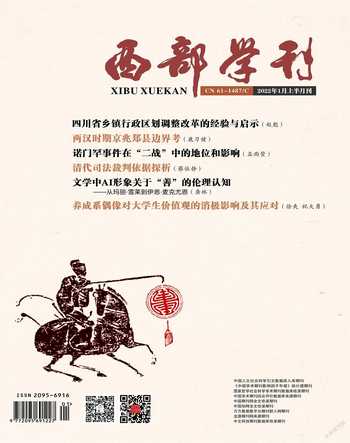淺談認識邊界
柳曉丹
摘要:認識是一個動態的過程,認知的主體自然設定為“自我”,“自我”也正是反思的客體。近代哲學關于認識論基礎問題的研究有認識論和唯理論兩種觀點。從認識知覺的底層邏輯進行論證,以自我的實在性為前提,當感知的載體是A=A時指明了普遍性的“是”,當A≠A則是指明了偶然性與特殊性的“此”,自我與非我之間在相互規定和相互否定中運動;以自我的時間性為邏輯起點,自我意識的雙重辯證下主客達成統一,推出“認識”即是時間性作用下的自我活動,是自我的一種體驗流式的“存在方式”。從時間的序列形式探討“認識”與“疑惑”的辯證關系,這兩者都在同一個“自我之中”,推出理性通過有序化去消解非我,建立意義本質。
關鍵詞:黑格爾;費希特;康德;海德格爾
中圖分類號:B01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6916(2022)01-0141-04
關于認識論的問題,當代哲學主要討論的是知識論(theory of knowledge),就是知識本身的成真條件。然而,近代哲學認識論(epistemology)研究的是認識能力和有效性的問題。從笛卡爾開始,在近代認識論研究上主要有兩條路:一條是以洛克、貝克萊、休謨為代表的經驗主義,一條是以斯賓諾莎、萊布尼茨為代表的唯理論。從康德開始,德國古典哲學就試圖調和兩者。康德認為知識的確定性不是來自于客體,而來自于主體的能力,他為理性劃分了界限,區分了物自體和現象,提出知性的應用應當在現象界之內,理性在知識領域里只有范導性的作用,而在構建性方面是無能為力的。
一、理性的無源之水
關于認識論的問題,在以往的哲學史中主要有兩種區別較大的觀點:一種以笛卡爾等人為主的方法,被稱為唯理論,認為經驗所給我們的東西并不可靠,人們有且只有憑借與生俱來的理性能力才能獲得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知識;另一種看法是以培根、洛克等人為主的經驗論,他們認為認識是從經驗開始的,而且只有從經驗中來并在經驗之中才能獲得知識,所以知識是不可能具有普遍性與必然性的。
經驗論者發現了知識開始于經驗這一重要的、正確的原則,卻沒有為知識找到一個可靠的基礎,缺乏真理的權威性,就像奠基沙地上的大樓,隨時有坍塌之虞;唯理者恰恰相反,他們為知識找到了可靠的基礎,但它們卻是由心靈閉門造車而來,仔細思量卻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康德在《未來形而上學導論》中所言:“我說,作為我們感官對象而存在于我們之外的物是已有的,只是這些物本身可能是什么樣子,我們一點兒也不知道,我們只知道它們的現象,也就是當它們作用于我們的感官時在我們之內所產生的表象。”康德去二者之短,提出知識來自于經驗,如果它有普通性與必然性,那么它必須依靠理性。經驗上升為知識,是何以可能的呢?是人類具有的一種先天的認識能力——感性、知性和理性。其中“感性直觀知識”,康德稱之為數學知識。以經驗作為材料又以先天的抽象運算能力作為后盾的知識,即以知性能力構建的知識為科學知識。理性是拋開經驗去窺探那個超越現象世界的彼岸,那么理性構建的是形而上學的知識。然而超越經驗是人類的一大難題,那么物自體的彼岸,人類的理性能否觸及得到?
二、認識的動態,自我的設定
以下分別從黑格爾、康德、費希特的角度進行論述。
當我們說出“人到底能認識什么”,就意味著已經開始反思了,反思的對象是“認識”。這句話包括以下兩層意思:第一,并不只是要知道認識了什么,而更要知道人認識不了什么。第二,追究認識的結果和認識的對象之間的關系。認識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就是從未知到已知的過程。我們只能和已知接觸,正是因為隔離才成為未知。從某種意義上說,未知永遠和我們無關。那么人們為何有動力去糾葛于未知呢?因為生命是一個“逆”的形式,或者用黑格爾的說法是持存的否定性。作為自我意識的否定本質,作為世界整體的一部分。就是“一部分”這個詞,讓它和整體行動相差別,否則也不會有部分的界限了。這個界限,或者說一個事物是一個事物,是偶然建立的,是差別性讓一事物作為形式和它的本質誕生。于是維護這個差異性,但是這個個別又在以自我揚棄的方式和他物相聯系,改變各自的自在自為,于是就存在“認識”的問題。
我們把認知的主體自然設定為“自我”,而這個設定終究還是由“自我”來完成。這個主體,自然是“自我”反思的客體。而認識的客體,也最終以“自我”的實在性為前提。所以主體和客體,都是在自我的設定中。這個看似矛盾的辯證,毋寧說,所謂認知的“主體和客體”,是“自我意識”的“普遍性”“自在性”和自我意識的“偶然性”“特別性”的相互規定。反思這個“認識”的此刻追問“人可以認識什么”的這個“自我意識”,反而成了“中介”。或者說是黑格爾說的“主人的自我意識”,于是所謂“認識”和“認識的可能”或者“能夠認識什么”的反思,就成了“根據”之始的“自我”(必然性的存在)的“自在自為”和“自我的偶然性”之間的關系研究了。這都在自我內部,也就是認識的主客體都在那個必然存在的“自我”之中。說其是“必然的存在”,因為關于一切認識知覺的最底層根據的邏輯是A=A,而這個直截的“必然”來自“自我”的設定。于是“我”成為一切邏輯的最直截的“基點”。也就是最終的必然存在、感知的尺度和載體,甚至懷疑的否定性也是在“自我”為主語的前提下運動的。這個A≠A的設定也來自“我”,前者(A=A)代表了“概念”的普遍性,指明了“是”。后者(A≠A)代表了現象變化的“偶然性”和“特殊性”,指明了“此”。這個“是”與“此”,在“自我”這個“存在者”的“此在”下以“認識”的表象照面。到這里,“認知”的過程和內容似乎就是從A=A過渡到A≠A再從A≠A返回到A=A,背后得從“我是我”過渡到“我不是我”,再到“非我是我”。
這里分析一下費希特說的,自我和非我之間的相互規定與相互否定。然而,這二者都是“我”的設定結果。那個作為存在者,“源始”的“我”,用“非我”規定否定出“自我”的實在性。所以看似雙重的“自我”其實是先驗的自我和感性經驗的偶然性下的自我的統一或重疊。這里就可以再回到上述說的,認識就是從“我是我”過渡到“我不是我”,再到“非我是我”,我即是世界(這句話背后是先驗和經驗統一在自我意識里)。這一系列過渡,是通過“理性”工作的。
康德提出了“世界有一必然存在”和“世界沒有一必然存在”的二律背反,恰恰從費希特的“我”和“非我”的設定,其“源始”直截根據于“自我”,也就是那個“世界中的必然性存在”——“自我”,到黑格爾的“自我意識的雙重性辯證”,很好地用辯證法統一化解了這個“必然性”的二律背反。這背后也解決了“認識”這個概念,讓認識的主體和對象互相統一而運動,不再是在各自界限內的隔離,把自我屏蔽在物自體的黑暗世界之外,讓“自我”承載了先驗悟性的普遍性與后天經驗的偶然性,把“自我”和“非我”的運動,明示為“自我”的“先驗與經驗”的統一。在康德論述關于世界的必然性存在的二律背反時,他抓住了“時間性”這個對于“經驗”的最底層基礎。這里提到康德的這個二律背反,是因為他的關于這個問題的思辨,雖然沒有直接給出認識的能動法則,但是他的剖析對我們挖掘認識主體和客體的哲學層的奧秘有很大的啟發。
三、自我的時間性邏輯起點
時間性這個經驗的基礎,也是A≠A的根源,以偶然性特殊性被自我規定到“非我”里的即是對方的“時間性”。如果A=A,那么在自我的理性下,對方是確定的。確定性是“自我”的屬性(笛卡爾的“思”即是自我的必然存在),而時間性造就的A≠A,這個不確定性被自我否定為非我。這里不確定的時間性雖可以說是他者或認識對象的時間性,毋寧說是“自我”的“存在”的時間性,因為后者說法更能與“認識”的能動、認識的起始與運動有直接的揭示。
謝林很不滿于黑格爾以概念為“源”始支撐事物的發展揚棄。黑格爾的能動交給了事物包括自我中本來擁有的“否定性”,筆者認為不如直接地說“自我的時間性”。這個說法似乎并不直觀,但是更有哲學意義的思辨效力。因為在我們的直觀感性里,時間性是屬于他物的,但是對于解析“認識”而言,把“時間性”歸入“自我”,則是非常高妙的契機。這是窺探自我以及認識的辯證關系的關鍵點,也就是把“時間性”歸入“認識的主體”一邊,同時它又以客體呈現。由于時間性是自身否定性的能動之源,這里“自我”就成為認識的動力和根源。對于自我,時間性是有一個邏輯上的起點的,我們總是用“之前”去認識“之后”,而這個以“自我”為動力的“認識”,它的“之前”邏輯上的起點就是“自我”的存在,也就是前面說的“必然存在”。對于“認識”而言,在沒有它之前,認識即成為時間性作用下的自我活動,這成為“自我”的一種“存在方式”。
就如佛教說的“一個念頭接著一個念頭”或者如現象學里說的“體驗流”。“認識”成為了本在自在的那個自我,面對時間性下自我的感性經驗——“此時的自我意識”,它成就認識的客體。認識的主體與客體就可以轉述為,“自在的自我意識”和“此時的自我意識”。原來認識的主體和客體,是“同一”的,二者只是后者在時間性下顯示。一個非時間的自我(自在自我),以序列秩序的形式展示,或者說我們需要知道,認識的本質是賦予現象對象以“序列”,也就是因果體系。
毫無疑問,人類的理性是建立時間性序列的工具。似乎人們會把“認識”和“疑惑”聯系起來,甚至把后者當作“認識”的起因。那么什么是“疑惑”?它是不是那些超出“自我”的經驗?顯然不是。前面已經論述了“自我”作為必然的存在,自在的那個自我,它是“確定和不確定”“我和非我”的根據和基礎,所以“疑惑”的對象并不超出“自我”。人只能在“自我”之內“疑惑”或者“認識”。但是這里必須強調,這并不意味著客觀世界的不存在。所以那個自在自我統領的“認識”和“疑惑”,我與非我的只是經驗世界,而經驗世界背后還有一個物自體世界(也就是“缸中之腦”)在哲學上是不成立的,為了強調避免落入“缸中之腦”的認知,筆者試著剖析“缸中之腦”的不可能。因為“缸中之腦”的意識內容以及客體,完全等于主體,并沒有物自體世界。于是自我意識的偶然性和特殊性是有限的,也就是“缸中之腦”的時間性是有限的。因為推動意識持續的是自我和非我的互相規定與揚棄,也就是“缸中之腦”在沒有物自體世界的前提下,其非我以及自我的個別性是非常有限的,其會迅速被自我揚棄而很快全部消解成為“自我”。完全沒有自我和非我的對立,意識也隨之停滯,進入無意識的運動。于是沒有了那個時間屬性的“此時的自我意識”,只留下那個“必然性存在”的非時間性的“自在的自我”。一個閉環的棋盤其斗爭是有限的,所以“缸中之腦”在哲學上,其無法支撐意識的運動,甚至這個意識運動在沒有外在物自體世界的介入,其起始和啟動都是荒謬而不可能的。
四、疑惑與認識的辯證
“疑惑”和“認識”只能在“自我”中存在,疑惑不能超出自在的自我,“疑惑”不直接來自物自體。物自體僅僅只造就“此刻的自我意識”以及“非我”的持續存在(自我的否定性)。物自體僅僅只提供給“自在自我”以時間性,而疑惑的本質是:理性在時間性下“此刻自我意識”或者說經驗中的偶然性特殊性的秩序化的定位延遲(判斷延遲),以他者身份照面卻未被自我理性揚棄的部分,也就是中介滯后,那個作為中介的“主人自我意識”工作滯后,這背后暗含著一個信息:疑惑和認識。
后者是前者的結果,他們都在同一個“自我之中”,只是時差使其成為二者。對于此在,此刻的自我意識,疑惑伴隨生存論上的焦慮甚至恐懼。但是我們要知道,沒有超出自我的疑惑,自然沒有超出理性的疑惑。不存在絕對的疑惑的超載,只有解答的延時,或者理性的暫時缺席。俗語“時間可以治愈一切”無意間暴露了最玄妙的哲理。
因為問題都是時間帶來的,疑惑也是時差帶來的,那么關于“認識和疑惑”問題就明晰了。就是縮短這個時差,也就是面對此在的偶然和感知,盡快讓理性到來,通過其有序化,把非我消解成自我,雜多的現象材料,有待自我去建立秩序,形成意義本質。從非我成為自我,自我吞并“世界”,還是世界消解了“我”?這兩個同樣反時間性的結果,卻是“本質”的“絕對化”和“虛無”的“絕對化”。兩個極端相反的指向,后者是反生命的,至于生命的詮釋參考黑格爾精神現象學。如果只留下前者,有心人會發現,這便是東方的陸(九淵)王(陽明)心學。至于陸王心學,也算“牧童遙指杏花村”,或者只是說“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處”。個中微妙,彼此自知。
五、結語
對于人能夠認識什么,人們容易陷入物理或科學的范疇去思考,而本文從主體到客體的同一的視角進行了比較新穎和深刻的剖析。筆者把經驗表象世界對于未知無能為力的部分,重新以自我非我的辯證歸屬,重新思辨了“認識”的內涵,以及認識的“分對象”。使用了從費希特自我非我的同一到黑格爾主奴意識的辯證原理,使認識的問題提升到另一個哲學辯證的維度,重新詮釋了動態的主客體關系。在認識的主客體的辯證運動中,以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此在理論關照認識問題,用主體先驗的無限消解了未知的偶然經驗的無限,最終落足東方心學鑒賞直觀維度,指向更有意義的思考,統一了認知上主客體的對立。
參考文獻:
[1]黑格爾.邏輯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2]黑格爾.小邏輯[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
[3]費希特.全部知識學的基礎[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
[4]謝林.啟示哲學導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
[5]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
[6]康德.純粹理性批判[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