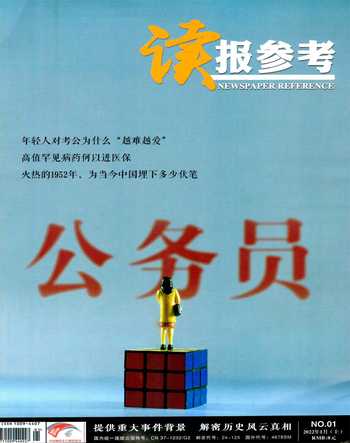淮海戰役,如何從“小淮海”演變成“大淮海”
1948年9月24日晨,濟南內城的巷戰尚在激烈進行中,粟裕即向中央軍委發電,提出了出徐州以東,舉行淮海戰役的主張。
臭招
粟裕最早提出的淮海戰役,在史學界被稱為是“小淮海”,方案為開辟蘇北戰場,攻占兩淮、海州、連云港等地區。顯而易見,這里的淮海指的是兩淮及海州。
粟裕發出電文的第二天,即得到中央軍委的回復:“我們認為舉行淮海戰役,甚為必要。”在復電中,毛澤東還為淮海戰役添加了一個重要指標——殲滅黃百韜兵團。
黃百韜以往就很顯眼,在華東戰場上,無論搏命程度,還是戰斗成果,都在國民黨將官中首屈一指。到了豫東帝丘店戰役,黃百韜親率坦克沖鋒,救出新七十二師之舉,更把他在國民黨軍隊中的聲譽推向了頂峰。豫東戰役結束后,蔣介石在南京親自給黃百韜佩戴上了代表最高軍功的“青天白日”勛章,也因此,在毛澤東預設的“斬將臺”上,黃百韜理所當然地拿到了頭牌。
淮海戰役采取的是華野、中野聯合作戰方式,在初期參戰部隊中,華野有16個縱隊(其中包括暫歸粟裕指揮的中野第11縱隊),中野有4個縱隊。
1948年10月下旬,粟裕完成了淮海戰役的各項準備。
蔣介石很快發現華野、中野在向徐州方向運動,他認為徐州是“四戰之地,易攻難守”,距南京又遠,后方補給線長,因此曾計劃放棄徐州,以便集中兵力“守淮保江,拱衛京滬”。
恰恰在這個時候,遼沈戰役行將結束,東北敗局已定,以李宗仁、白崇禧為首的新桂系趁機在幕后“逼宮”,蔣介石面臨著行將下野的危險,他又猶豫起來。放棄徐州,守衛淮河、長江,在當時國民黨軍已處于全面頹勢的情況下,亦不失為以退為進的妙招,這曾經是粟裕所擔心的,可是蔣介石自己又給推翻了。說到底,國民黨內部那些婆婆媽媽的掣肘和顧慮實在太多,這樣的情況下還能打好仗,只有天曉得了。
蔣介石最終采用了“徐蚌會戰”計劃。該計劃由國防部作戰廳廳長郭汝瑰主持制訂,要點是將兵力集結于徐州及徐蚌(徐州至蚌埠)鐵路沿線,作攻勢防御。此計劃一出,就引得國民黨陣營內議論紛紛,有識之士大多認為這是一步臭招,“未戰而敗局已定”“我們在徐州愈久,就中了敵人之計”。
黃百韜與郭汝瑰是陸軍大學時的同學,他對此也非常有意見,“作戰廳郭汝瑰……作出這樣的計劃,使人傷心,為陸大同學丟丑”。黃百韜并不知道,他的“郭同學”其實是中共在國防部的高級秘密特工,所制訂的計劃自然只會把國民黨往敗路上引。
國防部方略已定,南下是不可能了。
黃百韜有偵察電臺,也獲得了解放軍不斷向隴海路推進的信息,在向徐州“剿總”總司令劉峙進行報告后,黃百韜提出,國民黨軍全都分布于隴海沿線,戰線遼闊,且四面八方都有解放軍在運動,“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所謂“攻勢防御”,不要說攻,防都防不住。
黃百韜建議,仿效“拿破侖的團式集中法”,集結各兵團于徐州四周,然后掌握戰機,在華野、中野尚未會合之前,予以各個擊破。就軍事而言,這是一個極富建設性的意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變徐州“易攻難守”的困境,但是劉峙久無回音。
當初顧祝同升任國防部參謀總長,考慮讓劉峙出任徐州“剿總”總司令。郭汝瑰勸他說:“徐州是南京的大門,應派一員虎將把守,不派一虎,也應派一狗看門,今派一只豬,眼看大門會守不住。”郭汝瑰所說的“一只豬”很明顯是指劉峙,但顧祝同斟酌再三,最后還是選了劉峙。
郭汝瑰的秘密身份在那里,他當眾說過的很多話,現在都必須反著理解,假如劉峙的智商和能力真的只是“一只豬”,估計郭汝瑰就不會這么說了。
顧祝同與劉峙幾乎同時出道,對劉峙的水平算得上知根知底,以徐州地位之顯要,他絕不敢真的找一個庸碌糊涂的人來坐鎮,而在曾經戰將如云的國民黨陣營,劉峙若沒有兩下子,也不可能坐到如今的高位。這位北伐和中原大戰時期的常勝將軍,位居蔣介石“五虎上將”之首,若論指揮大兵團作戰的能力,被公認還在顧祝同等人之上。
黃百韜的建議沒有得到及時回應,并不是劉峙沒有眼光,不肯納諫。事實上,劉峙剛剛上任就感到了力不能支。他的兩大對手,華野粟裕有40萬兵,中野劉伯承有20萬兵,這還不包括地方武裝及民兵、游擊隊,而歸劉峙指揮的黃百韜、邱清泉、李彌、孫元良兵團,總兵力最多也不過20萬,只勉強與中野相抵,何況有的軍還沒有整編完成,不過是個賬面數字。劉峙原計劃放棄徐州,退淮以守,被“徐蚌會戰”方案否決后,又欲集結兵力于徐州附近。包括黃百韜兵團,他早就想撤到運河以西,可是這些設想都沒有能夠得到國防部的批準。劉峙猶如被綁著手腳在跳舞,他自己也非常郁悶,不無怨氣地說:“我好像是童養媳長大,骨頭多大,當婆婆的都摸得清,服從是無條件的!”
由于劉峙及前線將領意見集中,時任參謀總長的顧祝同受蔣介石之托,與郭汝瑰等人專程趕到徐州對部署進行了調整。1948年11月5日,顧祝同召集徐州“剿總”和一線將領們開會,會上黃百韜再次進諫。
這次,他換了個說法,把洋式的“團式集中法”換成了中式的“烏龜戰術”,并主張放棄海州,黃兵團由原駐地新安鎮全部撤往徐州。他對顧祝同說:“不是我怕死,而是只有這樣才能持久,海州守不守并無關系。”
顧祝同在請示蔣介石后,終于批準了黃百韜的建議。黃百韜對此并沒有如釋重負的感覺,他已經隱隱感覺到,自己所面臨的危險正越來越近。在當天返回新安鎮的火車上,黃百韜對第二十五軍(即原來的整二十五師)軍長陳士章說:“可惜我這個計劃批準太晚,現在撤退恐怕來不及了。”
大淮海
粟裕在第一時間便得到了黃兵團即將西撤的情報。淮海戰役的初定發起時間為11月8日,他立即決定提前兩天發起戰役。值得注意的是,此重大決定在上報中央軍委的同時,就已下令部隊執行,如果情報不是絕對的確鑿可靠,粟裕是不會這么做的。
1948年11月6日晚,華野在中野的配合下,分三路向南挺進。當天午夜,解放軍迫近臺兒莊、賈汪一線,直逼黃兵團側背。
臺兒莊、賈汪一線尚有國民黨第三綏靖區的部隊據守,而且從第二天早上開始,黃兵團就將西撤,但黃百韜仍然脫口而出:“太遲了。”因為這是在敵前撤退,所有撤退以這種撤退方式為最危險。
留在新安鎮打,孤立無援;往徐州撤,到不了徐州便可能遭遇解放軍。而所有這些都是拜國防部的一紙命令所賜,黃百韜捶胸頓足:“國防部作戰計劃一再變更,處處被動,正是將帥無能,累死三軍!”
黃百韜通過偵察,得知華野有十幾個縱隊南下,因此預估僅華野就會有30多萬兵力參戰,而黃兵團只有10多萬,若是華野集中來攻,他必敗無疑。
說到這里的時候,黃百韜很是激動:“這次會戰如垮,就什么都輸光了,將來怎么辦?國事千鈞重,頭顱一擲輕,個人生死是不足惜的。”
雖然勝負還未分出,但黃百韜已經非常清楚自己的結局,他讓人給蔣介石帶去遺言,表示自己受蔣知遇之恩,無論如何要予以報效,“臨難絕不茍免”。
1948年11月7日,黃兵團開始西撤。這時的黃兵團包括四十四軍等五個軍,是關內也是徐州“剿總”序列中最大的一個主力兵團。他們要渡過運河才能前往徐州,可是運河上卻只有一座鐵路橋。此前,黃百韜曾寄希望于徐州工兵團,但后者并未來架設更多橋梁,而黃百韜也錯過了自行架設浮橋的機會。
10多萬人馬,要在短時間內通過一座橋,豈是容易的事,四十四軍還拖帶著10多萬非戰斗人員,這支隊伍里面充斥著大車、小轎、箱籠、行李,一上橋就把橋面給堵得嚴嚴實實,部隊根本過不去。在他們后面,追兵即將趕到。
而且,粟裕還加緊完成了另外一項秘密部署。國民黨第三綏靖區副司令官何基灃、張克俠均為中共秘密黨員。早在淮海戰役發起之前,粟裕就在爭取他們率部起義,并針對第三綏靖區制訂了三條原則:一、起義;二、不起義,讓開道路;三、既不起義,又不讓道,堅決殲滅。經過緊張籌劃,何、張決定于11月8日凌晨發動起義,此議一出,便意味著黃兵團難逃生天。
1948年11月8日凌晨,粟裕與參謀長張震聯名向中央發出電文,建議在殲滅黃兵團之后,不再向兩淮進攻,而是向徐州進擊,爭取在長江以北打掉敵方更多的主力兵團。這就是著名的“齊辰電”。第二天深夜,中央軍委復電,同意粟裕的建議,并表示將合華東、華中、中原三大解放區之力,對淮海戰役予以強大的后勤支援。
至此,最初的開辟蘇北戰場發展成為南線戰略決戰,“小淮海”變成了“大淮海”。幾十年后,當談到這封復電時,粟裕仍抑制不住激動的心情說:“這封電報雖短,但是字字千鈞。”
就在“齊辰電”發出不久,何、張率所部2萬多人發動起義,徐州東北大門洞開,華野通過起義防區,迅速朝新安鎮開去。粟裕后來說:“如果再晚4個小時,讓黃百韜竄入徐州,那仗就不好打了。”
華野各縱隊原來的攻擊路線,是以新安鎮為主要目標,一路自北向南開進,一路進行迂回包圍,但前線傳來的一個情報引起了粟裕的重視。山東兵團特務團的偵察員潛入黃兵團駐地,抓到了一些俘虜,經過訊問得知,黃兵團正向運河鐵橋涌去。偵察員將這一情報及時上報華野司令部,粟裕當即調整部署,急令各路縱隊全部改向,對黃兵團進行追擊和截擊。
接到命令,華野各縱隊爭相向運河鐵橋撲去,有的部隊一天的行軍速度已達到120-140里,正好截住黃兵團尚未過河的后衛部隊。大戰的銅鑼尚未敲響,黃兵團便已損兵折將,共計損失一軍一師,其中作為黃兵團骨干的第二十五軍損失了一半人馬。
過河得脫的國民黨部隊齊集徐州以東150里的碾莊,黃百韜面臨著兩個選項,要么繼續西進,要么固守碾莊。這是一個生死選項,一面寫著“生”,一面寫著“死”。
(摘自《戰神粟裕》,關河五十州著,現代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