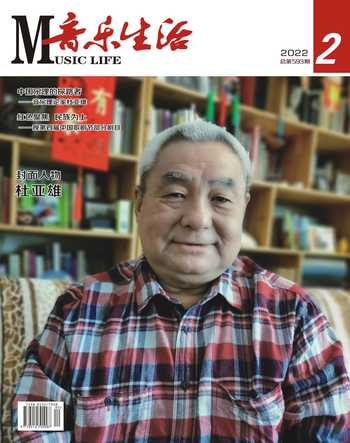辟斯頓《和聲學(xué)》學(xué)術(shù)價(jià)值探析
張濤
瓦爾特· 辟斯頓(Walter Piston)是20世紀(jì)美國(guó)著名的作曲家與音樂(lè)理論家,他撰寫(xiě)的音樂(lè)理論著作《和聲學(xué)》《對(duì)位法》《配器法》等被翻譯成多國(guó)語(yǔ)言,成為廣受贊譽(yù)的經(jīng)典教材。其中《,和聲學(xué)》更被認(rèn)為是“開(kāi)啟了音樂(lè)理論的現(xiàn)代時(shí)期,就像David Thompson所指出的——其理論原則均來(lái)自‘音樂(lè)實(shí)踐的觀察’。”[1]辟斯頓把各種復(fù)雜的和聲理論問(wèn)題化繁為簡(jiǎn),以流暢生動(dòng)的筆觸寫(xiě)出了這本兼具學(xué)術(shù)深度與實(shí)用性的教科書(shū)。1951年《,和聲學(xué)》(Victor Gollancz 1949年版)由中央音樂(lè)學(xué)院華東分院組織翻譯出版[2],為我國(guó)讀者深入理解西方共性音樂(lè)實(shí)踐中的和聲現(xiàn)象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桑桐在評(píng)述離調(diào)與副屬和弦問(wèn)題時(shí)特別提到了辟斯頓的這本著作,他認(rèn)為:“我國(guó)讀者對(duì)副屬和弦能有較深的理解,應(yīng)該說(shuō)是通過(guò)這本《和聲學(xué)》對(duì)副屬和弦的闡述。”[3]
由于特定的歷史原因,我國(guó)學(xué)界對(duì)于和聲學(xué)的學(xué)習(xí)與教學(xué)長(zhǎng)期以蘇聯(lián)教材為主,伊· 斯波索賓等四人合著的《和聲學(xué)教程》占據(jù)絕對(duì)的統(tǒng)治地位。而來(lái)自美國(guó)的這本辟斯頓《和聲學(xué)》雖然也廣受好評(píng),但未能在和聲教學(xué)與學(xué)術(shù)研究領(lǐng)域取得足夠的影響力,尤其在研究領(lǐng)域與其相關(guān)的學(xué)術(shù)成果明顯偏少。近年來(lái),我國(guó)也陸續(xù)引進(jìn)了一些美國(guó)當(dāng)代的和聲學(xué)教材,它們?cè)诶碚擉w系、編寫(xiě)體例以及某些具體觀點(diǎn)上與辟斯頓的教材有著大致相似甚至說(shuō)是一脈相承的關(guān)系。因此,對(duì)辟斯頓《和聲學(xué)》的學(xué)術(shù)價(jià)值進(jìn)行深入探析,一方面有助于完整地認(rèn)識(shí)這部經(jīng)典教材的特色所在,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們?nèi)娴卣J(rèn)識(shí)具有其自身特色的美國(guó)和聲理論與教學(xué)體系,繼而考察它們與俄羅斯理論體系之間的異同,以更好地做到兼收并蓄,推動(dòng)我國(guó)和聲學(xué)學(xué)科的健康發(fā)展。
美國(guó)和聲理論走的是一條從借鑒吸收到融合發(fā)展的路徑。19世紀(jì)三四十年代起直到七八十年代,大量的歐洲音樂(lè)理論著作被翻譯引進(jìn)到美國(guó),其中就包含了以音級(jí)理論為特色的如W· 韋伯、里克特(Richter, E.F.)的著作,把基礎(chǔ)低音與音級(jí)理論融合在一起的澤西特(Sechter)的著作。音級(jí)理論對(duì)美國(guó)和聲理論的產(chǎn)生、發(fā)展、成熟均產(chǎn)生了持續(xù)性的影響,它們似乎成了一種“基因”滲透在美國(guó)學(xué)者撰寫(xiě)的和聲論著中,呈現(xiàn)出與典型的功能和聲理論不同的風(fēng)格特質(zhì)。
功能和聲以主和弦為中心,把一個(gè)調(diào)性中所有的和弦歸為主、屬、下屬三種功能,它們是所有和弦的抽象本質(zhì)。其他和弦可視為由正三和弦通過(guò)特定的轉(zhuǎn)化方式派生得來(lái),或反過(guò)來(lái)說(shuō),其他和弦通過(guò)與三個(gè)正三和弦建立聯(lián)系從而取得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因此,這些和弦所在的音級(jí)位置變得相對(duì)次要,“調(diào)式音級(jí)再也不以其自身權(quán)利而存在”[4]。而抽象的功能標(biāo)簽成為和弦的主導(dǎo)身份,繼而決定了和弦的前后關(guān)系。音級(jí)理論以大小調(diào)音階為參照,認(rèn)為所有和弦都產(chǎn)生于音階的各個(gè)音級(jí)之上,這些和弦用羅馬數(shù)字進(jìn)行標(biāo)記。它們以主音為中心,根據(jù)各自在調(diào)中的不同位置而發(fā)揮作用。調(diào)的呈現(xiàn)通過(guò)各個(gè)音級(jí)上的和弦連續(xù)來(lái)實(shí)現(xiàn),如著名的“澤西特鏈條”[5](Sechterian chain)就是典型的做法。
與功能理論注重和弦的抽象身份不同,音級(jí)理論更加重視根音、根音進(jìn)行在音階中的位置。這種觀點(diǎn)在辟斯頓的教程中得到鮮明的闡述:“兩個(gè)和弦的個(gè)別的音響并不很重要,而兩個(gè)根音的相互關(guān)系以及根音對(duì)所屬的音階的關(guān)系要重要得多。對(duì)和弦的辨識(shí),主要是根據(jù)它的根音在音階中所占的位置。”[6]如果不仔細(xì)揣摩這句話的深意,可能會(huì)覺(jué)得作者在說(shuō)一個(gè)連初學(xué)者都懂的和弦分析技巧,但事實(shí)上卻不是那么簡(jiǎn)單。如果聯(lián)系整個(gè)教程來(lái)看就會(huì)發(fā)現(xiàn),辟斯頓對(duì)變音和弦的身份認(rèn)定往往是與同根音的自然音和弦一樣看待的。例如,他把增六和弦看作是變化的下屬和弦,而不認(rèn)為是重屬變和弦(降低五音);把終止四六和弦前由升二級(jí)、升四級(jí)、六級(jí)與一級(jí)構(gòu)成的和弦看作是變化的二級(jí)七和弦,而不看作重屬導(dǎo)七和弦;在一定條件下,把副屬和弦也看作是同根音自然音和弦的變化形式,如在論述屬七的不正規(guī)解決時(shí),把二級(jí)與重屬三和弦一并作為上主音三和弦、把三級(jí)與六級(jí)的屬和弦一并作為中音三和弦來(lái)看待。
辟斯頓對(duì)變音和弦的看法并非有別于傳統(tǒng)的全新認(rèn)識(shí),恰恰相反,如果從學(xué)術(shù)譜系溯源的話,它很可能是繼承了奧地利音樂(lè)理論家澤西特的觀點(diǎn)。澤西特最重要的貢獻(xiàn)之一是把基礎(chǔ)低音理論融入了音級(jí)理論傳統(tǒng),“他采用了拉莫、基恩貝格爾、舒爾茨的基礎(chǔ)低音概念,和弦進(jìn)行與和弦轉(zhuǎn)化,甚至是高度半音化的,也都是建立在自然音音階的根音之上。”[7]澤西特的經(jīng)典著作《作曲基本原理》(3卷本)的第一卷英譯本于1871年在紐約出版,對(duì)美國(guó)和聲理論的產(chǎn)生起到了重要的影響。
另外一個(gè)值得關(guān)注的是辟斯頓對(duì)調(diào)性概念與調(diào)性建立方法的論述。他對(duì)調(diào)性的定義與18世紀(jì)以來(lái)被稱作“和聲調(diào)性”的概念不同。和聲調(diào)性的概念始自拉莫,他把調(diào)性看作是由主、屬、下屬和弦構(gòu)成的群體,它們的橫向展示產(chǎn)生了音階。而辟斯頓則認(rèn)為調(diào)性是“被組織起來(lái)的音之間的關(guān)系”,“就18、19世紀(jì)共性寫(xiě)作時(shí)期的作曲家而言,這種關(guān)系意味著有一個(gè)中心音,其他所有的音以各種方式支持或傾向于它”[8]。從歷史傳統(tǒng)來(lái)看,這種調(diào)性觀與音級(jí)理論的傳統(tǒng)是吻合的。但是,如果繼續(xù)觀察辟斯頓對(duì)各級(jí)和弦調(diào)性結(jié)構(gòu)力的論述,如把主音、屬音、下屬音看作調(diào)性支柱,把建立在這些調(diào)性音級(jí)上的和弦視為調(diào)性建構(gòu)的主要和弦等,可以發(fā)現(xiàn)他對(duì)調(diào)性的理解又同時(shí)結(jié)合了功能理論的觀點(diǎn)。但是,辟斯頓只承認(rèn)正三和弦對(duì)調(diào)性確立的核心意義,卻不把它們看作調(diào)性與音階的來(lái)源。與很多美國(guó)理論家一樣,辟斯頓也不像里希特那樣“認(rèn)為音階來(lái)源于一個(gè)調(diào)的三個(gè)基本三和弦,而只是認(rèn)為三個(gè)基本三和弦包含了音階的全部音級(jí)。”[9]這樣一種認(rèn)識(shí)是非常深刻的,對(duì)于接下來(lái)準(zhǔn)確理解辟斯頓通過(guò)和聲進(jìn)行確立調(diào)性的方式具有重要的意義。

對(duì)于調(diào)性的建立,辟斯頓采取了層層遞進(jìn)的論述方式。他首先從一個(gè)和弦在調(diào)性上的曖昧性談起,也就是福格勒、G.韋伯所謂的“多重意義”(multiple meaning)的概念。繼而,通過(guò)增加第二個(gè)和弦可以有效減少調(diào)性歸屬的可能,尤其是由下屬與屬結(jié)合起來(lái)的和弦進(jìn)行,即使主和弦不出現(xiàn)也不影響對(duì)調(diào)性的唯一判斷。最后,辟斯頓指出,如果繼續(xù)增加到三個(gè)和弦?guī)缀蹩梢詼?zhǔn)確無(wú)誤地明確一個(gè)調(diào)。總之,作者通過(guò)描述性的方式指出了如何通過(guò)增加和弦數(shù)量逐漸減少調(diào)性“多重性”最終確立一個(gè)調(diào)的做法,但遺憾的是,他并沒(méi)有點(diǎn)明調(diào)性的多重意義是如何一步步消失的。其實(shí),這種做法的依據(jù)依然來(lái)自音級(jí)理論,即通過(guò)自然音和弦的進(jìn)行來(lái)呈現(xiàn)出屬于某個(gè)調(diào)的各個(gè)自然音級(jí),從而確立調(diào)性。
什么是不規(guī)則解決?它是指不尋常的和聲進(jìn)行還是指不合常規(guī)的聲部進(jìn)行?二者之間又有著怎樣的關(guān)系?可能不少人難以給出準(zhǔn)確的說(shuō)法。辟斯頓在論及和弦的不規(guī)則解決時(shí)首先對(duì)它的內(nèi)涵進(jìn)行了解釋,所謂不規(guī)則其實(shí)包含兩個(gè)不同的方面,“可能是指聲部的進(jìn)行違反一般的慣例,也可能是指關(guān)于根音進(jìn)行的純粹屬于和聲方面的問(wèn)題。”[10]
在辟斯頓看來(lái),雖然所有的和弦與和弦進(jìn)行都可以看作是旋律運(yùn)動(dòng)的結(jié)果,但就共性寫(xiě)作時(shí)期的音樂(lè)實(shí)踐來(lái)說(shuō),還是存在著一個(gè)以根音進(jìn)行構(gòu)成的和弦序進(jìn)“詞匯表”。對(duì)每一個(gè)“詞匯”而言,根音關(guān)系是本質(zhì),是最重要的,而每個(gè)具體的和弦結(jié)構(gòu)形態(tài)與聲部走向則屬于相對(duì)次要的“細(xì)節(jié)”。通常所謂和弦的不規(guī)則解決,是指非常規(guī)的根音之間的和聲關(guān)系,而不是非常規(guī)的聲部進(jìn)行。但一個(gè)值得注意與思考的現(xiàn)象是,“在不正規(guī)的解決中,可能有非常正規(guī)的聲部進(jìn)行。”[11]這其實(shí)反映了“不規(guī)則解決”存在的部分原因,即它往往具有對(duì)位即聲部進(jìn)行上的合理性。因此,從更深層的邏輯來(lái)看,它是對(duì)位關(guān)系與功能關(guān)系這一對(duì)基本矛盾達(dá)成妥協(xié)的產(chǎn)物,前者取得了相對(duì)的優(yōu)勢(shì),而后者做出暫時(shí)的讓步(辟斯頓在談到變和弦時(shí)提及了各種類型的變和弦產(chǎn)生的原因)。通過(guò)和聲發(fā)展的歷史線索可以發(fā)現(xiàn),不規(guī)則解決在拓展和聲語(yǔ)匯、豐富和聲色彩、增加和聲進(jìn)行的復(fù)雜程度及由此帶來(lái)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力的提升等方面,均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辟斯頓系統(tǒng)地介紹不正規(guī)解決是從屬七和弦、副屬和弦開(kāi)始的,單辟一章總結(jié)了它們?cè)趯?shí)踐中的各種不正規(guī)解決的表現(xiàn)情形。難得的是,在后來(lái)的減七和弦、不完全大九和弦、完全的屬九和弦、升上主和弦與升下中和弦、增六和弦等知識(shí)點(diǎn)中,辟斯頓均詳細(xì)地總結(jié)了每個(gè)和弦做不規(guī)則解決的各種情形,并用精要的語(yǔ)言對(duì)其和聲效果進(jìn)行了評(píng)價(jià)。學(xué)習(xí)者倘若能把這些用法匯集在一起,一幅全面而系統(tǒng)的和弦不正規(guī)解決表“詞匯表”也就產(chǎn)生了!一方面可供學(xué)習(xí)與分析時(shí)查閱,另一方面,如果能夠結(jié)合自己的聽(tīng)覺(jué)感受對(duì)辟斯頓的相應(yīng)評(píng)價(jià)進(jìn)行思考,并形成自己的判斷與評(píng)價(jià),那么這種“對(duì)話”式學(xué)習(xí)必定是精彩而富有成效的!
雖然可以在理論上對(duì)各種不規(guī)則解決進(jìn)行清晰的界定與總結(jié),但在分析實(shí)踐中還是存在大量復(fù)雜難辨的和聲進(jìn)行。一些看似不規(guī)則的和弦解決,它們其實(shí)應(yīng)劃歸為規(guī)則解決。造成不規(guī)則解決假象的一個(gè)常見(jiàn)的簡(jiǎn)單原因是等音記譜,減七和弦就是典型的例子。由于其結(jié)構(gòu)上的獨(dú)特性,加上作曲家在記譜上的主觀隨意,各種等音記譜往往遮掩了減七和弦原本的真實(shí)身份。但是,當(dāng)減七和弦的記譜在分析中被修訂以后,大多數(shù)表面上不規(guī)則的解決其實(shí)是規(guī)則的。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一些等音記譜幾成慣例為大家熟悉,這里不再贅述。
如果說(shuō)純粹由于記譜法而導(dǎo)致的不規(guī)則解決假象是相對(duì)容易識(shí)別的,那么更隱蔽、深層的原因是分析者沒(méi)能綜合多個(gè)因素對(duì)和聲進(jìn)行做出判斷。在看待某個(gè)具體的和弦進(jìn)行時(shí),要對(duì)多聲部構(gòu)成的諸多要素進(jìn)行綜合化分析,如前后和弦的節(jié)拍、低音、時(shí)值、和聲節(jié)奏以及后和弦所隱含的真正的和弦身份等。在辟斯頓的分析中,他尤其關(guān)注剛才所述的最后一個(gè)因素,即作為和弦序進(jìn)“結(jié)果”的和弦自身是否“表里如一”,很多情況下外表所呈現(xiàn)出的和弦級(jí)數(shù)、功能與其實(shí)質(zhì)是不相符的。
辟斯頓以不完全大九和弦解決到強(qiáng)拍上的四級(jí)四六和弦為例,表面上看這個(gè)和弦序進(jìn)顯然是不正規(guī)的解決,但由于四級(jí)四六和弦在此處的真正涵義是主和弦的倚音和弦,已經(jīng)進(jìn)入了主和弦的領(lǐng)域,該和弦只是延遲了主和弦的出現(xiàn)而已,就像終止四六和弦到五級(jí)和弦的關(guān)系一樣,所以,這個(gè)和弦序進(jìn)實(shí)質(zhì)上就是不完全屬九到主和弦的正規(guī)解決。當(dāng)然,這種觀點(diǎn)一方面與辟斯頓對(duì)“語(yǔ)境”的強(qiáng)調(diào)有關(guān)聯(lián),另一方面與他對(duì)轉(zhuǎn)位和弦的觀點(diǎn)有關(guān)。通過(guò)這樣的分析可以看到,即便在看待一個(gè)微觀的和聲進(jìn)行時(shí),辟斯頓也充分地考慮了和聲語(yǔ)境的因素。其實(shí),這個(gè)特點(diǎn)貫穿在他對(duì)全書(shū)各個(gè)知識(shí)點(diǎn)的論述之中,尤其他對(duì)和聲節(jié)奏的關(guān)注與闡述,成為這本教程最突出的特色之一。
辟斯頓的《和聲學(xué)》是一本簡(jiǎn)潔實(shí)用、融合了功能理論與音級(jí)理論的經(jīng)典教材。早在1987年,這本著作就發(fā)行了第五版,對(duì)原有的內(nèi)容進(jìn)行了不少增補(bǔ)與改進(jìn),而我國(guó)引進(jìn)翻譯的版本是1949年的第二版,這不能不說(shuō)是一個(gè)遺憾,同樣遺憾的是對(duì)于它的學(xué)術(shù)研究還是成果偏少。近年來(lái),一些美國(guó)學(xué)者編著的和聲學(xué)或綜合理論教材也被翻譯引進(jìn),并隨之出現(xiàn)了圍繞這些著作的學(xué)術(shù)研究,這的確是一個(gè)可喜的現(xiàn)象。當(dāng)然,無(wú)論是對(duì)某部著作的縱深研究,還是對(duì)不同理論體系教材之間的比較研究,都是具有重要學(xué)術(shù)意義的專門(mén)課題。辟斯頓《和聲學(xué)》所蘊(yùn)含的學(xué)術(shù)價(jià)值是非常豐富的,本文僅就其兩個(gè)方面進(jìn)行了初步探索,這顯然離充分揭示它的理論特色與價(jià)值還有很大的距離,這有待于在后續(xù)研究中進(jìn)行深入拓展,并在此基礎(chǔ)上探討其對(duì)我國(guó)和聲理論所產(chǎn)生的具體影響。希望這本已有八十年歷史的經(jīng)典著作能得到更多的關(guān)注,能夠繼續(xù)發(fā)揮它所蘊(yùn)藏的學(xué)術(shù)能量,為推動(dòng)我國(guó)和聲學(xué)理論的發(fā)展與繁榮做出獨(dú)特的貢獻(xiàn)。
本文系江蘇省高校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一般項(xiàng)目“中國(guó)音樂(lè)理論話語(yǔ)體系的先行探索——趙宋光民族音樂(lè)形態(tài)學(xué)理論研究”(2021SJA1065)的研究成果。
[1]H. Pollack.“ Piston, Walter (Hamor)”,《新格羅夫音樂(lè)與音樂(lè)家辭典》(第2版),湖南文藝出版社,2012年版,第19卷第792頁(yè)。
[2]〔美〕辟斯頓:《和聲學(xué)》,豐陳寶譯,新文藝出版社,1951年版。
[3]桑桐:《關(guān)于離調(diào)與副屬和弦的理論探討》,《音樂(lè)藝術(shù)》2002年第3期。
[4]Palisca, Claude V.“ Theory, theorists”,《新格羅夫音樂(lè)與音樂(lè)家辭典》(第2版),湖南文藝出版社,2012年版,第25卷第378頁(yè)。
[5]〔美〕D.W.伯恩斯坦:《19世紀(jì)的和聲理論:奧-德遺產(chǎn)》,托馬斯· 克里斯坦森編《劍橋西方音樂(lè)理論發(fā)展史》,任達(dá)敏譯,上海音樂(lè)出版社,2001年版,第748頁(yè)。
[6]〔美〕辟斯頓:《和聲學(xué)》,豐陳寶譯,人民音樂(lè)出版社,1956年版,第17頁(yè)。
[7]Janna Saslaw.“ Scheter, Simon”,《新格羅夫音樂(lè)與音樂(lè)家辭典》(第2版),湖南文藝出版社,2012年版,第23卷第28頁(yè)。
[8][10][11]〔美〕辟斯頓:《和聲學(xué)》,豐陳寶譯,人民音樂(lè)出版社,1956年版,第31頁(yè)、第172頁(yè)、第173頁(yè)。
[9]倪軍:《美國(guó)和聲理論發(fā)展簡(jiǎn)述》,《中國(guó)音樂(lè)學(xué)》1998年第3期。
張 濤 江蘇師范大學(xué)音樂(lè)學(xué)院講師,中國(guó)藝術(shù)研究院2018級(jí)在讀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