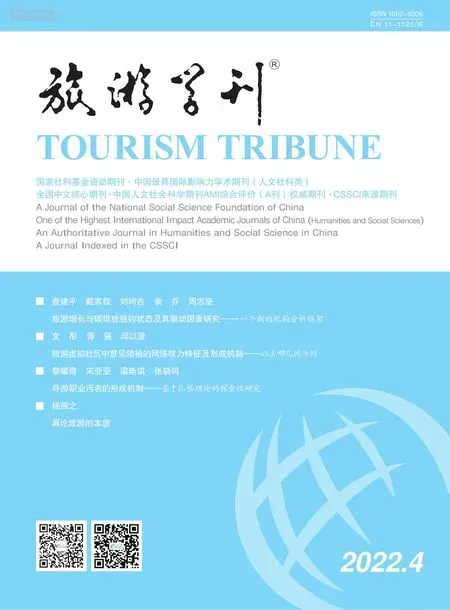在線旅游企業管理層權力對企業成長的作用機制
郭淳凡 王淑筠 方晨 吳小節







[摘 ? ?要]如何協調好管理層權力以促進企業成長是學界及業界關注的熱點。現有研究已證實,管理層權力是通過企業管理行為對企業成長產生作用,但尚未探明其具體的作用機制,且忽略了企業管理行為存在實際意義和象征意義的差異。文章以攜程為研究對象,采用單案例研究法,引入差異化管理行為揭開管理層權力對企業成長作用機制的“黑箱”。研究發現:不同權力水平下,管理層會根據感知的決策自由度與責任感實施差異化的管理行為,若實施的差異化管理行為能夠滿足企業成長主題,則促進企業成長,反之則阻礙企業成長。該文為管理層權力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并豐富了實質性和象征性行為的相關研究,同時也為在線旅游企業合理配置管理層權力提供了指導。
[關鍵詞]在線旅游企業;管理層權力;企業成長;實質性行為;象征性行為
[中圖分類號]F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006(2022)04-0025-14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22.04.009
引言
管理層持股比例的變化是企業成長過程中的重要現象,在線旅游企業(online travel agency, OTA)的管理層持股比例在成長過程中也不斷發生變化。根據各大OTA公布的年報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年底,攜程管理層持股占比由上市之初的18.2%減少為5.9%;途牛則由上市之初的63.6%增加為72.4%。管理層持股比例的多少代表了管理層權力的大小,管理層持股比例的變化反映了管理層權力的變化,而管理層權力能夠促進或阻礙企業成長[1]。一方面,權力的增加有利于提升管理層的歸屬感和責任心,引導其從企業的長期利益出發進行戰略決策,促進企業成長[2]。另一方面,隨著權力的增加,管理層也有可能為了私人獲利而實施機會主義行為,阻礙企業成長[3]。
管理層權力通過不同的管理行為對企業成長產生作用,是企業賦予管理層壓制不一致意見的能力[4],使其能夠在不同的公司環境下憑借自由的意志實施不同的管理行為,如薪酬制定[5]、研發投入[6]、項目投資[7]、信息披露[8]等。然而,企業管理行為存在實際意義和象征意義的差異[9],不同權力水平下管理層實施的管理行為是不同的,有可能是企業采取的實際行動,也有可能只是對未來的象征性承諾。但是,現有研究并未對管理層在不同權力水平下的差異化管理行為與企業成長之間的作用機制進行深入探討。
不同于其他旅游企業和互聯網企業,OTA的管理層權力與企業成長在演變過程中表現出獨特性,即呈現對稱分布:較高的管理層權力下,企業成長速度上升;較低的管理層權力下,企業成長速度下降1。但現有研究未能解釋這一獨特性產生的原因,因此有必要進一步對OTA管理層權力對企業成長的作用機制進行分析。
本文將以攜程國際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攜程”)為研究對象,將差異化管理行為引入管理層權力對企業成長的作用機制中,運用事件路徑法分析攜程管理層權力與企業成長的階段性變化特征及各要素之間的作用機制。希望本文能夠豐富管理層權力與企業成長的相關研究,并為企業合理分配持股比例以促進企業成長提供指導與借鑒。
1 文獻綜述
1.1 管理層權力與企業成長
管理層權力是管理層壓制不一致意見的能力,使其能夠在不同的公司環境下憑借自由的意志做出戰略決策[4]。企業成長是企業為了滿足利益相關者的需求,不斷挖掘未利用的資源與潛在價值,實現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的發展過程[10]。管理層權力對企業成長存在促進、阻礙、促進和阻礙共存3種作用的觀點。
促進作用的觀點認為,提升管理層權力有利于激發管理層工作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助力企業成長。朱德勝指出,權力的提升能夠激發管理層的“管家心態”,管理層會增加研發過程中的監督力度,促進創新成果轉化,形成持續的競爭優勢[11];張汨紅認為,高管權力的增加能夠保證管理決策的順利實施,提升企業的經濟效益[12]。而阻礙作用的觀點認為,權力越大,越有可能成為管理層尋租的工具,不利于企業成長。Veprauskait和Adams指出,CEO權力與企業績效呈負相關,決策自由度的提升會加重管理層的自利傾向,導致企業績效下降[13]。Akram和Muhammad發現,較高的權力水平下管理層可能通過改變高管薪酬等行為來謀取私人利益,降低企業績效[3]。
共存的觀點認為,管理層權力對企業成長的促進或阻礙作用同時存在。權力的增加會提升管理層的積極性,但當權力增加到一定程度時,又有可能帶來新的代理問題,損害企業利益[14]。Drakos和Bekiris指出隨著權力的增加,管理層變成所有者,將減少代理成本和尋租行為,促進企業成長;而當管理層權力超過最優區間后,企業外部監管的難度和成本上升,管理層就有可能為了私人利益偏離企業運營的正常目標,阻礙企業成長[15]。
1.2 企業管理行為在管理層權力與企業成長中的作用
管理層權力通過企業管理行為影響企業成長,如薪酬制定[5]、研發投入[6]、項目投資[7]、信息披露[8]、社會責任承擔[16]等。Keltner等整合了權力的心理影響過程與企業管理行為,提出了趨近-抑制理論[17]。該理論認為,高權力的管理層擁有更高的決策自由度與責任感,將產生更積極的行為意愿,誘發趨近的行為模型,表現為放大管理行為的積極作用和潛在收益,實施更主動、更冒險的企業管理行為。低權力的管理層由于決策自由度和責任感較低,觸發抑制的行為模型,更關注管理行為的消極意義與潛在風險,實施的企業管理行為更為保守。這兩類行為在管理層權力演變的過程中可能促進也可能阻礙企業成長。
一方面,隨著權力的增加,管理層會通過實施更為激進的企業管理行為促進企業成長。Zhao等發現,在實施管理層股權激勵計劃后,管理層會開展更積極的資源整合活動以提升企業績效[18]。Sheikh指出,擁有強權的管理層將會產生更多的專利和專利引用,促進企業的創新投入和發展[6]。白貴玉和徐鵬從管理層決策態度和能力層面出發,指出較高的權力水平使得管理層擁有更多的財務調配權,提升了管理層的歸屬感和責任感,使其愿意并有能力給予研發活動更多的支持,改善產品與服務贏得消費者的青睞[2]。
另一方面,權力的提升也有可能使得管理層為了獲得潛在收益產生機會主義行為,或通過保守經營規避風險以獲得更高的當期收益,阻礙企業成長。Zhang等以2008至2012年中國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研究發現管理層會利用自身的權力改變高管薪酬謀取私人利益[19]。Qian等研究發現,管理層權力較大的企業通常會花費更多的時間發布財務報告,表現出更多的財務不端行為,且股票價格效率更低[14]。Jiraporn等指出,當CEO擁有較大權力時會傾向于次優的資本結構,出現低杠桿融資、逃避債務融資等行為,產生不利影響[20]。
由此可見,不同的權力水平下,管理層會根據感知的決策自由度和責任感實施不同類型的企業管理行為,進而對企業成長產生作用。然而,哪類企業管理行為會在管理層權力與企業成長之間起到促進或阻礙作用,現有研究尚未能明確回答這一問題。
1.3 差異化的企業管理行為
不同類型的企業管理行為存在實際意義和象征意義的差異,可分為實質性行為和象征性行為[21]。實質性行為旨在改變企業的經營活動和經營方向,是圍繞組織目標、結構、過程或制度化等開展的實際行動;象征性行為是旨在讓企業與社會價值觀在形式上達成一致而開展的表征性行動。
實質性行為和象征性行為對企業成長的作用是不同的。部分學者認為,實質性行為能夠通過實際行動提升企業績效,而象征性行為只是企業為了附和公眾所采取的表面工作,無法真正促進企業發展[9]。另一部分學者則指出,象征性行為是企業為了塑造符合社會規范和期望的形象而使用的一種印象管理戰略[22],能夠更容易為企業爭取到發展所需的資源,與實質性行為一樣對企業成長具有促進作用[23]。因此,實質性和象征性行為在管理層權力與企業成長之間起到何種作用,現有研究并不能給出答案。而回答這一問題的基礎,便是清晰界定實質性和象征性行為,明確兩類行為的概念及分關標準。
現階段,實質性和象征性行為的研究大多基于環境保護問題展開。在環境保護領域,實質性行為是指企業為了降低環境污染而做出的實際行動,通常表現為開發新產品或服務、采用新技術或生產流程等直接改變企業經營狀態的行為[24];象征性行為則是對實際行動的一種符號表達,通常表現為開展廣告宣傳、資格認證、信息公布等具有標榜性的行為[25]。借鑒環境保護領域的相關研究,可以將實質性和象征性行為的分類可歸納為以下3個標準。第一,實質性行為大多涉及技術名詞和實施細節,如果企業披露的信息中主要是綱領性陳述、定性披露、簡單照搬上一年的陳述,且信息表述模糊、難以驗證,則可靠程度較低,屬于象征性行為[26]。例如,緱倩雯和蔡寧將企業環境報告中所描述的“公司實施了……染色機替代項目,共投入411.97萬……實現廢水減排8.64噸/年,COD減排……節水10.8萬噸/年……帶來經濟效益266.59萬元/年……”視為實質性行為[27]。第二,實質性行為是企業切實的行為,一定會帶來實際的變化,而象征性行為未必能產生實際的變化。例如,盛光華等將網頁新聞中“Y公司成立了專屬事業部負責‘固體廢棄物再加工技術’的研發,‘固體廢棄物再加工技術’可將垃圾塑料和油墨渣裂解、催化后制成高密度建材”這一事件歸為實質性行為[28]。第三,實質性行為是已完成或正在履行的行為,指企業“正在做”和“已經做了”的行為,象征性行為是企業承諾“將怎樣去做”的行為[29]。
1.4 研究框架
現有研究表明,管理層權力是通過企業管理行為對企業成長產生促進或阻礙作用的,但是忽略了企業管理行為存在實質性和象征性意義的差異。在不同的權力水平下,管理層會根據感知的決策自由度和責任感實施差異化的企業管理行為,進而對企業成長產生促進或阻礙作用,但這一過程背后的作用機制尚未明晰。因此,本文將差異化的企業管理行為區分為實質性行為和象征性行為,探討管理層權力對企業成長的作用機制。這不僅為管理層權力與企業成長的相關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也豐富了實質性和象征性行為的研究。本文研究框架如圖1所示。
2 研究設計
2.1 方法選擇
本文采取的研究方法是單案例研究法,主要原因如下:首先,我國上市的OTA較少,缺乏實證研究所要求的成熟樣本和財務數據;其次,OTA管理層權力與企業成長這一主題鮮有研究,相對于多案例研究,單案例研究具有捕捉新現象和構建理論的優勢,能夠更好地審視研究問題。
在數據分析部分,本文采取了因子分析法及事件路徑法。其中,因子分析法用于提煉管理層權力及企業成長兩個要素,旨在通過量化的方式,呈現攜程不同階段的管理層權力與企業成長的變化。事件路徑法是以貫穿某一過程的事件為分析材料,將事件編排成具有時間順序和內在關聯的整體,保留住事件發展所處的情境,從而揭示過程規律的一種研究方法,用于識別差異化的企業管理行為及攜程發展的階段性特征。
2.2 案例選擇
本文根據三大原則選取攜程作為案例研究對象。首先是代表性原則,攜程由提供單一的住宿預訂服務發展為一站式旅游服務平臺,其成長過程中管理層權力與企業管理行為不斷發生變化,是反映OTA管理層權力與企業成長演變過程的典型代表;其次是數據可得性原則,攜程自2003年在美國納斯達克證券交易所上市,每年按照美國資本市場的監管要求公開財務信息,同時,作為在線旅游企業的標桿,攜程的新聞報道、書籍等二手資料較為豐富,為本文提供了較為詳實的研究數據與素材;最后是適配性原則,前期調查發現,攜程的管理層權力與企業成長在演變過程中呈現對稱分布,說明兩者之間存在邏輯上的關聯性,與本研究的適配度較高。
2.3 數據收集
本文通過多渠道資料的三角驗證,保證數據的可信度。數據來源主要包括高管訪談、企業年報、網頁新聞。
首先,通過高管訪談掌握攜程的背景信息,加深對攜程發展歷程和管理層決策行為的理解。作者分別于2018年6月、2018年11月、2019年1月前往攜程華南總部進行實地調研和深入訪談,訪談對象主要為任職10年以上的高層管理者。每次訪談由4位研究人員、1~3位被訪談者組成,時間控制在1小時~3小時。剔除無關信息后,最終整理得到約4.3萬字的文字材料。由于高管訪談資料無法對每一階段完整的事件進行確認還原,不符合事件路徑法編碼的要求,因此并未作為直接的數據分析材料,而是作為重要的輔助資料,加強本文對攜程發展歷程和管理層決策行為的理解,同時佐證了二手資料,保證事件路徑中各關鍵節點劃分的準確性。
其次,通過年報和網頁新聞收集基礎數據。年報數據用來衡量管理層權力演變與企業成長,網頁新聞數據作為企業管理行為的編碼基礎。考慮到管理層權力對企業管理行為與企業成長的影響存在滯后性,因此,管理層權力的年報數據取自2003—2017年,企業成長的年報數據取自2004—2018年,企業管理行為的網頁新聞數據取自2004年1月1日—2018年12月31日。根據三角驗證原則,網頁新聞數據取自3個信息來源,分別是基于企業視角的攜程官方網站(https://www.ctrip.com/)、基于社會視角的第三方網站新浪網(https://www.sina.com.cn/)、基于行業視角的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http://www.100ec.cn/),以“攜程”為關鍵詞進行站內檢索,利用Python爬取網頁新聞作為企業管理行為的編碼基礎,得到攜程官方網站原始數據716條、新浪網原始數據3777條、中國電子商務中心原始數據2803條,共計7296條。
2.4 數據分析策略
首先,使用因子分析法提煉“管理層權力”和“企業成長”兩個要素。第一步,通過KMO和Bartlett’s球狀檢驗進行指標間的相關性檢驗。當KMO大于0.5時,證明各變量間可能存在公共因子。第二步,確定公共因子與各因子的方差貢獻率。通過因子分析提取出的公共因子與原始標量之間的關系可以寫成矩陣形式:Y=AFi+σ(i=1,2,3,…),其中,Y是原始變量,A是因子載荷矩陣,Fi是公共因子,是Y的特殊因子,σ表示某個變量中不能被公共因子表達的部分。在社會科學領域,當累計方差貢獻率大于60%時,表明公共因子包含了原始變量絕大部分信息,能夠代表原始變量。
其次,應用事件路徑法提煉“企業管理行為”。第一步,對收集到的原始數據進行去重和篩選,剔除不符合研究主題的數據。第二步,對篩選后的數據進行編碼及概念化處理,并加以定性的歸納和維度細化,形成最終的編碼結果。第三步,將編碼后的原始數據集按時間順序排列,觀察并總結企業管理行為的階段性變化特征。第四步,通過跨階段分析,識別出管理層權力演變如何影響企業成長,并根據各階段事件變化特征及趨勢提煉出理論命題。
3 案例分析
3.1 要素提煉
3.1.1 ? ?管理層權力要素
管理層權力的測量大部分研究沿用Finkelstein提出的權力模型,從組織權力、所有權權力、專家權力、聲譽權力4個維度進行測量[4]。組織權力反映了組織賦予管理層的權力,采用董事會規模、兩職合一等測量指標;所有權權力是管理層擁有股份時對企業擁有的權力,采用管理層持股比例、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等測量指標;專家權力是管理層利用專業知識和技能處理偶然事件的能力,采用管理層職稱、管理層學歷水平等測量指標;聲譽權力是指管理層良好的聲望和信譽能夠獲得更多的外部支持,采用管理層任期、管理層在外兼職情況等測量指標。然而,Tang等認為,專家權力和聲譽權力的測量在數據量化及判斷上存在不確定性和模糊性,例如,當管理層擁有高學歷背景時并不能推斷出管理層就擁有更高的權力[30]。因此,本文從組織權力和所有權權力兩個維度出發,采用董事會規模、管理層持股比例、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3個指標測量管理層權力。在上述指標的基礎上采用因子分析法合成管理層權力的綜合得分。綜合得分的零點代表2003—2017年攜程管理層權力的平均水平,數值越大,表示管理層權力越大。
經過檢驗,管理層權力的KMO=0.513且通過Bartlett’s球狀檢驗(Sig.=0.03<0.05),以特征根大于1的標準提取兩個公共因子,累計方差貢獻率達到90.57%,表明其包含了以上3個指標的絕大部分信息。利用公共因子計算出綜合管理層權力(以下簡稱管理層權力,用Power表示)。通過回歸估計法分別計算2003—2017年F1和F2的得分,再以各因子的方差貢獻率為權重,代入公式:Power=(0.5699×F1+0.3358×F2)/0.9057,由此得出2003—2017年的Power數據(圖2)。
結果顯示,攜程的管理層權力演變大致可分為3個階段:(1)2003—2006年為第一階段。此階段Power均大于零,高于歷年平均水平。說明此階段的管理層權力最高。(2)2007—2011年為第二階段。此階段Power由第一階段的最高值下滑至2010年的-0.83,2007—2010年均小于零,2011年也僅為0.03,低于歷年平均水平。說明相對于第一階段,此階段的管理層權力大幅下滑。(3)2012—2017年為第三階段。此階段的Power經歷了先下降后上升的變化趨勢,由2012年的0.55下降至2014年的-1.15,2017年回升至0.28。說明此階段的管理層權力有所回升,但相較于平均水平,回升的幅度并不大。
3.1.2 ? ?企業成長要素
企業成長的測量方法包括主觀測量法和客觀測量法。主觀測量法適用于難以獲取研究對象準確財務資料的情況,通常使用成熟的量表衡量企業成長[31]。而當研究對象財務資料較為完整時,學者們普遍采用客觀測量法,將企業成長視為財務問題,選取財務指標測量企業成長。由于攜程的財務資料較為完整,因此本文采取客觀測量法,參考Aydemir和Ovenc的研究選擇以下4個指標:每股收益率、總資產報酬率、凈資產收益率、營業利潤率[32],運用因子分析法得出企業成長的綜合得分。綜合得分的零點代表2004—2018年攜程企業成長的平均水平,數值越大,表示企業成長速度越快。
經過檢驗,企業成長的KMO=0.541且通過Bartlett’s球狀檢驗(Sig.=0.00<0.05),以特征根大于1的標準提取一個公共因子,累計方差貢獻率達到68.93%,表明其包含了以上4個指標的絕大部分信息。利用公共因子計算出綜合企業成長(以下簡稱企業成長,用Growth表示)。通過回歸估計法分別計算2004—2018年的F1得分,再以各因子的方差貢獻率為權重,得到企業成長的綜合得分(圖3)。
結合管理層權力演變的階段劃分,將企業成長細化為3個階段:(1)2004—2007年為第一階段,此階段企業成長大幅提升,Growth均大于零。(2)2008—2012年為第二階段,此階段企業成長有所降低,Growth由2007年的1.2不斷下滑至2012年的-0.15。(3)2013—2018年為第三階段,此階段Growth經歷了先下降后上升的發展趨勢,由2012年的-0.15下降到2015年的-1.53后,回升至2018年的-1.08,說明此階段的企業成長正在小幅回升。
3.1.3 ? ?企業管理行為要素
首先,對原始數據進行篩選和去重,剔除不符合研究主題的事件。具體操作如下:(1)剔除非管理層主動實施的事件,如消費者投訴、獲獎等。(2)剔除重復報道的事件。如果多種數據渠道在不同時間對同一事件的表述相同,則取一次;多個重復事件中,只保留最具有相對獨立完整情境的事件[33]。最終獲得971條原始數據。
其次,對事件進行編碼。按照事件碼(事件發生的年月日)、分類識別(企業管理行為的分類)、參與人(主要參與者)、事件描述的順序,將971個事件分別編碼。本文使用以下3個分類標準識別實質性和象征性行為。
(1)該事件是否讓OTA產生實質性的改變。Fenwick等認為,平臺型企業實現企業成長的關鍵在于技術創新、開放平臺和內容生產[34]。因此,當事件涉及網站改版、App迭代、平臺升級等技術創新行為,建立戰略合作關系、跨界合作等開放平臺行為,開發新的旅游產品及服務、規范服務標準等涉及旅游產品及服務的行為,則認為該行為產生了實質性的改變。(2)該事件是否涉及技術名詞、實施細節、具體金額等定量表述。Zhang等認為,實質性行為會產生切實和客觀可衡量的結果,如利潤、資本支出、預算和資源分配[35]。而象征性行為會產生無形和主觀的結果,如共享的信念、承諾和忠誠。因此,當事件詳細描述了具體執行方式、包含確切金額時,認為該事件中的行為是實質性行為。(3)該事件是否正在履行或已經完成。當事件表述中包含“將”“計劃”等未來時態的詞語時,認為該事件尚未履行或完成,判定為象征性行為[36]。按照上述分類標準對事件進行整理(表1),形成原始事件數據編碼庫。
在原始事件數據編碼庫的基礎上,采用逐步歸納的方式進一步對事件進行概念化處理[37],不斷提煉事件的分類,細化實質性和象征性行為的維度。例如,2005年7月19日,攜程聯合《申江服務導報》共同舉辦“出游四人行”系列活動,新注冊會員有機會免費游玩該目的地。這一事件反映了攜程與外界聯合組織產品促銷活動,并沒有給OTA帶來實質性的改變。因此,將其歸類為象征性行為,并將“免費游玩”提取為關鍵詞,作為維度細化的行為標簽。根據事件描述和行為目的,推演出此類事件歸屬于“旅游產品促銷”,為事件賦予了一個學術化標簽。經過對同類事件的匯總歸納及補充修正,形成了包含所有事件數據的分類結果(表2)。其中,實質性行為可劃分為內部孵化旅游產品及服務、合作伙伴獲取與配置、技術開發與版本迭代;象征性行為劃分為社區溝通、旅游預警及損失補償、慈善公益、旅游產品促銷。
事件數據處理完畢后,為保證企業管理行為維度劃分的準確性,筆者另尋一名獨立的審核員進行審查,結果顯示本研究的維度劃分是合理且具有可重復性的。同時,針對少量具有爭議的事件組織了專家小組討論,最終達成了一致的分類結果。
最后,分別統計各階段中各類事件的總數量和平均數量,觀測企業管理行為事件的階段性變化特征。由表3可知,攜程的企業管理行為呈現階段性變化特征:第一階段為2004—2007年,管理層均衡實施實質性和象征性行為。實質性行為共89件,象征性行為共81件。第二階段為2008—2012年,管理層以實施象征性行為為主。實質性行為共116件,象征性行為共156件。第三階段為2013—2018年,管理層以實施實質性行為為主。實質性行為共287件,象征性行為共242件。
3.2 管理層權力對企業成長的作用機制分析
3.2.1 ? ?管理層權力對差異化管理行為的作用機制
在不同的權力水平下,管理層將根據感知的決策自由度和責任感,實施差異化的企業管理行為。基于權力的心理影響過程,管理層權力越小意味著感知的決策自由度和責任感越小,限制了管理層配置資源、行使決策,使其更多關注管理行為的消極意義與潛在風險,實施的企業管理行為更為保守;反之,管理層權力越大,其感知的決策自由度和責任感越大,管理層可以利用所擁有的決策自由度,克服外部環境的影響執行自身意愿,實施有利于企業長期發展的管理行為。因此,當感知的決策自由度和責任感較低時,管理層將產生更多的象征性行為;隨著感知的決策自由度和責任感的提升,管理層將產生更多的實質性行為;當感知的決策自由度和責任感提升至高于歷年平均水平時,管理層將均衡地產生更多的實質性和象征性行為。
具體而言,第一階段中,管理層感知的決策自由度和責任感最高,均衡地實施實質性和象征性行為。管理層通過內部孵化旅游產品及服務、合作伙伴獲取與配置等實質性行為,不斷完善服務保障體系,彰顯其在整合資源、產品創新方面的整體實力,并通過社區溝通,降低消費者對旅游安全、企業資質等問題的擔憂。第二階段中,管理層感知的決策自由度和責任感大幅下降,以實施象征性行為為主。管理層一方面通過社區溝通、慈善公益等行為,積極向外界傳遞企業在推動旅游行業發展、改善居民出行條件等方面的努力;另一方面通過旅游產品促銷、旅游預警及損失補償等行為,用性價比高、保障完善的旅游產品及服務吸引消費者,打消消費者的顧慮。第三階段中,管理層感知的決策自由度和責任感有所提升,以實施實質性行為為主。管理層一邊通過合作伙伴獲取與配置結束價格戰,并鼓勵消費者和供應商加入企業的價值創造活動中,共同開發產品及服務;另一邊實施內部孵化旅游產品及服務,激發內部創造力,促進企業成長。
3.2.2 ? ?差異化管理行為對企業成長的作用機制
企業在不同階段的發展重點是不一樣的,存在階段性成長主題。根據企業生命周期理論,企業組織體系隨著生命周期不斷演變將會展現出可預測的行為模式[38]。因此,通過梳理現有文獻并結合攜程的發展背景,可以總結OTA在不同階段關注的重點行為模式,即企業成長主題。當企業的管理行為與成長主題所關注的重點一致時,將會提升社會公眾對企業經營活動的適當性、恰當性、合意性的評價,幫助企業從利益相關群體處獲得成長所需的資源,促進企業的生存和發展[39]。因此,不同權力水平下,管理層實施的差異化管理行為若能滿足企業階段性成長主題,便能夠促進企業成長,反之將阻礙企業成長。
在發展的初期階段,OTA應當考慮如何構建旅游交互空間。發展初期的企業通常資源有限,外部網絡聯系不穩定、內部組織系統不健全,缺乏成熟企業所具有的信譽和合法性[40]。這意味著企業必須將有限的資源投入到核心活動中,以提高資源利用率,取得市場的認可。而OTA作為平臺型的旅游服務商,發展初期的核心活動便是完善平臺的建設,不斷吸引用戶加入,構建旅游消費者和旅游供應商的交互空間,促成旅游交易[41]。
在發展的第一階段(2003—2006年),攜程雖占據機酒預訂市場第一的位置,但仍面臨著雙邊用戶的質疑。一方面,彼時政策規定外商獨資企業不得經營旅行社范圍的業務,攜程被分銷商質疑和舉報存在非法經營現象。另一方面,由于旅游市場缺乏相應的監管,攜程不斷收到消費者的投訴,如香港迪斯尼因爆滿而拒絕買票的游客入園、低價“澳洲游”臨時降低住宿標準等。這一階段,攜程意識到自己尚未完全獲得市場認可,想要繼續發展,就必須消除市場對其經營資質的質疑,構建值得供應商和消費者信任的旅游交互空間。此階段,攜程均衡地實施實質性和象征性行為。一方面通過創新旅游保障服務、簡化預訂流程等舉措,消除用戶的感知風險,還與高星級酒店、航空公司等旅游供應商建立長期的戰略合作關系,豐富旅游供給。另一方面通過傳遞“質量為本”的服務理念,樹立正面的企業形象,從而構建安全、有保障的旅游交互空間,更好地匹配供給與需求,符合階段性成長主題,大幅促進企業成長。
在發展的中期階段,OTA應當考慮如何維持雙邊市場的平衡。平臺企業所構建的交互空間是由雙邊市場共同參與的,兩者相互依存,任何一方的失衡都會導致參與者的離開[42]。對于OTA而言,只有當產品和服務種類足夠多時,消費者的需求才更容易得到滿足,進而傾向于在平臺上交易。同樣地,只有當消費群體足夠龐大時,旅游供應商成功銷售產品的可能性更高,才更愿意在平臺上銷售。因此,如何滿足雙邊用戶的需求,維持雙邊市場的平衡是OTA在發展階段應當關注的重點[43]。
在發展的第二階段(2007—2011年),在線旅游市場爆發的價格戰產生了一系列的負面影響。一方面,價格戰破壞了市場的價格體系,使得供應商的整體收益降低,供應商們紛紛嘗試自建直銷平臺或開發新的分銷模式擺脫攜程的控制。另一方面,由于攜程深陷低價競爭,無暇顧及服務創新與產品質量,導致消費投訴層出不窮,令消費者對攜程的服務能力產生質疑。此時的攜程亟須采取措施留存雙邊市場的用戶。然而此階段,管理層以實施象征性行為為主,無法有效地維持雙邊市場的平衡。具體而言,攜程利用自身的影響力頻繁參與行業研討與社區溝通,積極向社會公眾展示企業在推動旅游行業發展、改善居民出行條件等方面的努力。但由于價格戰的影響,攜程的企業管理行為未落到實處,消費者舉證索賠困難、旅游產品虛假宣傳、壓縮供應商利潤空間等問題層出不窮。這一階段象征性行為無法消除諸多負面影響,攜程喪失了雙邊市場的平衡,不符合階段性成長主題,阻礙企業成長。
在發展的成熟階段,OTA應當考慮如何激發企業創造力。根據組織惰性理論,企業規模越大,內部結構的復雜程度就越高,市場敏感度下降,容易滋生“大企業病”,阻礙企業創新和變革。Nardelli和Broumels強調企業在成熟時期要注重賦能與授權[44]。因此,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張,OTA要不斷響應新興市場的需求,進行產品和服務的迭代創新,消費者才愿意購買并支付溢價[45]。
在發展的第三階段(2012—2018年),攜程通過投資入股的方式將競爭對手收入麾下,結束了價格戰。恢復市場秩序后,攜程意識到低價競爭并非長久之計,只有保持創新才能實現企業的持續發展。此階段,管理層主要通過實施實質性行為不斷激發企業創造力。面對旅游供應商,攜程持續拓展合作伙伴的廣度,不僅加強對旅游+金融、旅游+保險等相關企業的并購投資,還向包價旅行社、單項產品供應商和個人創業者開放加盟入口,進一步完善旅游生態圈。面對旅游消費者,攜程積極捕捉需求,通過推行內部創新活動激發員工創造力,扶持滿足市場需求的新產品的孵化,同時提升產品及服務的品質和標準。這一階段攜程將創新作為企業核心價值觀并使之制度化,有效激發了利益相關者的創新熱情,滿足階段性成長主題,小幅促進企業成長。
綜上所述,本文構建的管理層權力-差異化管理行為-企業成長研究框架的具體作用機制如下(圖4)。首先,管理層權力通過感知的決策自由度與責任感這一心理影響過程,對管理層實施的差異化管理行為產生影響。隨著權力的不斷提升,管理層實施的差異化管理行為由以象征性行為為主轉變為以實質性行為為主;當權力達到最高時,管理層傾向于均衡實施實質性與象征性行為。其次,差異化管理行為通過滿足企業不同階段的成長主題,進而對企業成長產生影響。當管理層實施的差異化管理行為與企業成長主題一致時,能夠促進企業成長,反之將阻礙企業成長。
在攜程發展的第一階段(2003—2006年),管理層權力高于歷年平均水平,感知的決策自由度與責任感也高于歷年平均水平,管理層傾向于均衡實施實質性與象征性行為,滿足“構建旅游交互空間”的成長主題,大幅促進企業成長。在攜程發展的第二階段(2007—2011年),管理層權力水平最低,感知的決策自由度與責任感最低,管理層以實施較為保守的象征性行為為主,未能滿足“維持雙邊市場平衡”的成長主題,阻礙企業成長;在攜程發展的第三階段(2012—2018年),管理層權力小幅回升,感知的決策自由度與責任感也小幅回升,管理層逐漸增加更有利于企業長期發展的實質性行為,滿足“激發企業創造力”的成長主題,小幅促進企業成長。
4 結論與討論
4.1 研究結論及理論貢獻
管理層權力演變是企業成長過程中的重要現象,如何協調好管理層權力以促進企業成長是當前理論和事務界亟須解決的重要問題。本文以反映OTA管理層權力與企業成長演變過程的代表性企業攜程為例,采用事件路徑法進一步探討了管理層權力對企業成長的作用機制。本研究的發現如下:
第一,差異化管理行為是打開管理層權力與企業成長之間“黑箱”的鑰匙。差異化管理行為可分為實質性行為和象征性行為。實質性行為是指OTA為了提高用戶活躍度及參與度而采取的實際行動,是對經營方式和方向的實質性改變,包括3個維度:內部孵化旅游產品及服務、合作伙伴獲取與配置、技術開發與版本迭代。象征性行為是OTA為了向外界展示自身的責任感和專業性,獲得社會公眾的信任和支持而采取的具有較高可視性和標榜意義的行為,包括4個維度:社區溝通、旅游預警及損失補償、慈善公益、旅游產品促銷。
第二,管理層權力對企業成長的作用機制為,管理層權力的變化使得管理層感知到不同程度的決策自由度和責任感。根據行為趨近-抑制理論,當感知程度較低時,管理層更關注企業管理行為的消極作用和潛在風險,產生更多的象征性行為;隨著感知程度的提升,管理層更關注企業管理行為的積極作用和潛在收益,產生更多的實質性行為;當感知程度提升至高于歷年平均水平時,管理層將均衡地產生更多的實質性和象征性行為。企業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有相應的成長主題,若管理層實施的差異化管理行為能夠滿足該階段的成長主題,則將促進企業成長,反之將阻礙企業成長。研究顯示,當管理層均衡地實施實質性和象征性行為時,更容易滿足各階段的成長主題,進而大幅促進企業成長,這與Battilana等學者提出的同時采用沖突的元素能夠讓組織更好發展的研究結論相一致[46]。
本研究的理論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通過構建管理層權力-差異化管理行為-企業成長的研究框架,進一步揭示了管理層權力對企業成長的作用機制。以往研究雖然表明,管理層權力是通過不同類型的企業管理行為對企業成長產生作用[5-8],但卻忽略了企業管理行為存在實際意義和象征意義的差異,因此,管理層權力對企業成長的具體作用機制尚不明晰。本文將企業管理行為區分為實質性和象征性行為,并結合權力的心理影響過程,研究發現不同權力水平下管理層會根據感知的決策自由度和責任感的不同,實施差異化的企業管理行為,進而促進或阻礙企業成長。這一結論打開了管理層權力與企業成長之間的“黑箱”,為未來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論分析框架。
第二,明確了管理層權力對企業成長促進和阻礙作用共存的原因。現有研究表明,管理層權力對于企業成長的促進或阻礙作用可能同時存在[14-15],但并未深入探討為何會出現這種作用效果。本文研究發現,差異化的企業管理行為是促進和阻礙作用共存的原因。提升管理層權力既有可能提高管理層的責任感,激勵管理層從企業長期利益出發實施更多的實質性行為促進企業成長,也有可能會誘發管理層的機會主義傾向,帶來更多的象征性行為阻礙企業成長。需要注意的是,實質性行為與象征性行為本身對于企業成長都十分重要,但從資源配置的角度來看,企業所擁有的資源往往是有限的,只有對已有資源進行合理的規劃配置,使資源配置的結果與企業目標一致時,才能幫助企業構建競爭優勢,獲得成長[48]。象征性行為是旨在讓企業與社會價值觀在形式上達成一致而開展的表征性行動,雖然對企業成長也十分重要,但如果在發展中過多地將企業資源投入象征性行為的實施,便會導致企業缺乏實質性行為的支持,發展難以延續。
第三,豐富了實質性和象征性行為的構念研究。現有的實質性和象征性行為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環境保護領域,以傳統的工業企業和制造企業為主,探討企業實施的實質性和象征性環境實踐帶來的影響[22-29]。但對于平臺型企業,具體什么樣的企業管理行為屬于實質性或象征性的尚不明確。本文通過對多個來源的數據進行提煉,總結在線旅游企業實質性和象征性行為的概念及具體維度,豐富了實質性和象征性行為的相關研究。
4.2 管理啟示
首先,對于企業內部而言,OTA可以通過合理配置管理層持股計劃增強管理層權力,提升管理層的決策自由度與責任感,引導管理層根據企業發展的不同階段均衡地實施實質性和象征性行為,通過不斷豐富旅游產品及服務內容、鼓勵消費者和供應商加入企業的價值創造活動、與外界建立積極有效的溝通渠道等措施促進企業成長。同時,為了避免管理層的機會主義行為,OTA還需把握好股權激勵的力度和范圍,通過增加董事會規模、提升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等方式,充分發揮內部治理機制的監督作用。
其次,對于有關部門而言,應不斷完善法律法規體系,鼓勵和引導OTA正確實施管理層持股計劃。一方面可以對管理層持股計劃予以保障,提高管理層持股的信心,另一方面明確管理層持股主體、持股資格等內容,監督和規范管理層權力的使用,避免因管理層權力上升而帶來的腐敗、權力濫用等問題。
4.3 研究不足與展望
首先,數據收集存在客觀局限性。單案例研究所涉及的各年份的新聞數據并不均衡,盡管已借助企業訪談、書籍等大量可交叉印證的材料進行彌補,但依然不能完全避免這一問題。因此未來研究應增加數據獲取渠道,以提高數據的多樣性和完整性。其次,數據分析存在主觀局限性。由于本文的數據編碼依賴研究者自身的判斷,因此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來可結合定量、定性研究,進行較為完整的、可相互印證的研究。最后,單案例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本文選取行業的典型代表展開研究,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結論的概化能力。后續研究可以考慮采用多案例、多方法的比較研究,驗證本文提出的結論,提高研究結論的有效性。
參考文獻(References)
[1] GABRIELSEN G, GRAMLICH J D, PLENBORG T. Managerial ownership, information content of earnings, and discretionary accruals in a non-US setting[J]. 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 Accounting, 2002, 29(7): 967-988.
[2] 白貴玉, 徐鵬. 管理層權力、研發決策與企業成長——來自中國民營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 科技進步與對策, 2019, 36(9): 110-117. [BAI Guiyu, XU Peng. Managerial power, R&D decision and company growth: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ese private listed companies[J]. Science &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Policy, 2019, 36(9): 110-117.]
[3] AKRAM F, MUHAMMAD A. Assessing the effect of managerial power on firm performance through the perceptual lens of executive remuneration[J]. Pertanika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ies, 2019, 27(1): 293-309.
[4] FINKELSTEIN S. Power in top management teams: Dimensions, measurement, and validation[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2, 35(3): 505-538.
[5] ESSEN M V, OTTEN J, CARBERRY E J. Assessing managerial power theory: A meta-analytic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the determinants of CEO compensation[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5, 41(1): 164-202.
[6] SHEIKH S. The impact of market competition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CEO power and firm innovation[J]. Journal of Multi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2018, 44: 36-50.
[7] LI S. Managerial power, earnings management and investment efficiency[C]//Proceedings of 2018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conomics, Management and Humanities Science (ECOMHS 2018). UK: Francis Academic Press, 2018: 33-38.
[8] SAUERWALD S, SU W. CEO overconfidence and CSR decoupling[J]. Corporate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2019, 27(4): 283-300.
[9] WALKER K, WAN F. The harm of symbolic actions and green-washing: Corporate actions and communications on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nd their financial implications[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2, 109(2): 227-242.
[10] DONALDSON T, PRESTON L E. The stakeholder theory of the corporation: Concepts,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5, 20(1): 65-91.
[11] 朱德勝. 不確定環境下股權激勵對企業創新活動的影響[J]. 經濟管理, 2019, 41(2): 55-72. [ZHU Desheng. The impact of equity incentives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under uncertain environment[J].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Journal, 2019, 41(2): 55-72.]
[12] 張汨紅. 高管權力因素對商貿流通領域企業績效影響機制研究[J]. 商業經濟研究, 2019(2): 97-100. [ZHANG Guhong.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executive power factors on enterprise performance in the field of business circulation[J]. Journal of Commercial Economics, 2019(2): 97-100.]
[13] VEPRAUSKAITE E, ADAMS M. Do powerful chief executives influence the financial performance of UK firms?[J]. British Accounting Review, 2013, 45(3): 229-241.
[14] QIAN M, SUN P W, YU B. Top managerial power and stock price efficiency: Evidence from China[J]. 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 2018, 47: 20-38.
[15] DRAKOS A A, BEKIRIS F V. Corporate performance, managerial ownership and endogeneity: A simultaneous equations analysis for the Athens stock exchange[J].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Finance, 2010, 24(1): 24-38.
[16] LI F, LI T, MINOR D. CEO powe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firm value: A test of agency theor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rial Finance, 2016, 12(5): 611-628.
[17] KELTNER D, GRUENFELD D H, ANDERSON C. Power, approach and inhibition[J]. Psychological Review, 2003, 110(2): 265-284.
[18] ZHAO N, FAN M L, TIAN C, et al. Contract-based incentive mechanism for mobile crowdsourcing networks[J]. Algorithms, 2017, 10(3): 1-13.
[19] ZHANG X, TANG G, LIN Z. Managerial power, agency cost and executive compens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from China[J]. Chinese Management Studies, 2016, 10(1): 119-137.
[20] JIRAPORN P, CHINTRAKARN P, LIU Y X. Capital structure, CEO dominance,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Financial Services Research, 2012, 42(3): 139-158.
[21] ASHFORTH B E, GIBBS B W. The double-edge of organizational legitimation[J]. Organization Science, 1990, 1(2): 177-194.
[22] BANSAL P, CLELLAND I. Talking trash: Legitimacy, impression management, and unsystematic risk in the context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4, 47(1): 93-103.
[23] ZOTT C, HUY Q N. How entrepreneurs use symbolic management to acquire resources[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007, 52(1): 70-105.
[24] HYATT D G, BERENTE N. Substantive or symbolic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Effects of external and internal normative stakeholder pressures[J].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2017, 26(8): 1212-1234.
[25] REYES-RODRIGUEZ J F, ULHOI J P, MADSEN H.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in Danish SMEs: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motivators, initiatives, and strategic effects[J].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14, 23(4): 193-212.
[26] 黃溶冰, 陳偉, 王凱慧. 外部融資需求、印象管理與企業漂綠[J]. 經濟社會體制比較, 2019(3): 81-93. [HUANG Rongbing, CHEN Wei, WANG Kaihui. External financing demand, impression management and enterprise greenwashing[J]. Comparative Economic & Social Systems, 2019(3): 81-93.]
[27] 緱倩雯, 蔡寧. 企業異質性環境實踐方式與績效關系的實證研究[J]. 軟科學, 2014, 28(11): 15-19. [GOU Qianwen, CAI Ning. Research on corporate heterogenic environmental practices and environmental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J]. Soft Science, 2014, 28(11): 15-19.]
[28] 盛光華, 龔思羽, 岳蓓蓓. 企業環保行為如何提升消費者響應?——基于消費者企業認同感和漂綠感知的雙重中介模型[J]. 財經論叢, 2019(7): 85-94. [SHENG Guanghua, GONG Siyu, YUE Beibei. How do the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actions promote consumer response? —A dual mediation model based on consumer corporate identification and green wash perception[J]. Collected Essays on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19(7): 85-94.]
[29] 肖芬蓉, 黃曉云. 企業“漂綠”行為差異與環境規制的改進[J]. 軟科學, 2016, 30(8): 61-64. [XIAO Fenrong, HUANG Xiaoyun. The difference of corporate greenwashing and the improvement of environmental institution[J]. Soft Science, 2016, 30(8): 61-64.]
[30] TANG J, CROSSAN M, ROWE W G. Dominant CEO, deviant strategy, and extreme performance: The moderating role of a powerful board[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11, 48(7): 1479-1503.
[31] 尹俁瀟, 梅強, 徐占東. 創業網絡關系嵌入與新創企業成長——創業學習的中介作用[J]. 科技管理研究, 2019, 39(5): 199-206. [YIN Yuxiao, MEI Qiang, XU Zhandong. The embedding of entrepreneurial network relationship and the growth of new enterprises: The intermediary role of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J].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Research, 2019, 39(5): 199-206.]
[32] AYDEMIR R, OVENC G. Interest rates, the yield curve and bank profitability in an emerging market economy[J]. Economic Systems, 2016, 40(4): 670-682.
[33] 王昶, 胡明華, 周文輝. 技術尋求型跨國并購中公司總部角色演化研究——基于時代電氣的縱向案例研究[J]. 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 2017, 38(3): 56-69. [WANG Chang, HU Minghua, ZHOU Wenhui. Research on the evolution of role of company headquarters in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of seeking technology: A longitudinal case study based on Era Electric Limited by Share Ltd[J]. Science of Science and Management of S.& T., 2017, 38(3): 56-69.]
[34] FENWICK M, MCCAHERY J A, VERMEULEN E. The end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Hello ‘platform’ governance[J]. European Business Organization Law Review, 2019, 20(1): 171-199.
[35] ZHANG P Y, FADIL P, BAYNARD C. Understanding board-CEO power dependency perspective under symbolic management[J]. Competitiveness Review, 2015, 25(1): 50-73.
[36] BASU K, PALAZZO G.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 process model of sensemaking[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8, 33(1): 122-136.
[37] 杜義飛, 王建剛, 趙鵬飛. 新興市場中后發企業吸收能力的過程與困境研究——基于縱向事件路徑分析[J]. 管理案例研究與評論, 2017, 10(2): 162-177. [DU Yifei, WANG Jiangang, ZHAO Pengfei. Research on the process and the predicament of latecomers’ absorptive capacity in emerging markets: A longitudinal event-path-analysi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Case Studies, 2017, 10(2): 162-177.]
[38] ADIZES I. Managing Corporate Lifecycles[M]. Santa Barbara: Adizes Institute Publishing, 2004: 10.
[39] SUCHMAN M C. Managing legitimacy: Strategic and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5, 20(3): 571-610.
[40] HALLEN B L.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initial network positions of new organizations: From whom do entrepreneurs receive investments[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008, 53(4): 685-718.
[41] FU W, WANG Q, ZHAO X. The influence of platform service innovation on value co-creation activities and the network effect[J]. Journal of Service Management, 2017, 28(2): 348-388.
[42] 韓蓓, 劉佳. 銀行卡發卡市場與收單市場的平衡發展: 基于雙邊市場理論[J]. 南方金融, 2011(3): 81-83; 86. [HAN Bei, LIU Jia.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the issuing and receiving markets of bank cards: Based on the two-sided market theory[J]. South China Finance, 2011(3): 81-83; 86.]
[43] 杜軍, 韓子惠, 焦媛媛. 互聯網金融服務的盈利模式演化及實現路徑研究——以京東供應鏈金融為例[J]. 管理評論, 2019, 31(8): 277-294. [DU Jun, HAN Zihui, JIAO Yuanyuan. Evolution path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profit model for internet financial services: A case study of JD supply chain finance[J]. Management Review, 2019, 31(8): 277-294.]
[44] NARDELLI G, BROUMELS M. Managing innovation processes through value co-creation: A process case from business-to-business service practic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novation Management, 2017, 22(3): 1-34.
[45] YE B H, BARREDA A A, OKUMUS F, et al. Website interactivity and brand development of online travel agencies in China: The moderating role of age[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9, 99: 382-389.
[46] BATTILANA J, SENGUL M, PACHE A C, et al. Harnessing productive tensions in hybrid organizations: The case of work integration social enterprise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4, 58(6): 1658-1685.
[47] 崔麗, 雷婧, 張璐, 等. 基于價值主張與動態能力互動的企業資源配置案例研究[J]. 科研管理, 2021, 42(4): 180-190. [CUI Li, LEI Jing, ZHANG Lu, et al. A case study of enterprise resource allocation based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value proposition and dynamic capabilities[J]. Science Research Management, 2021, 42(4): 180-190.]
The Action Mechanism of OTAs’ Managerial Power in Firm Growth:
A Case Study of the Ctrip
GUO Chunfan1, WANG Shuyun1, FANG Chen1, WU Xiaojie2
(1. School of Management,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2. School of Management,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520, China)
Abstract: The evolution of managerial power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firm growth. Coordinating managerial power to promote firm growth has been a discussed topic both in academia and industry. Existing studies have confirmed that managerial power promotes or hinders the development of firms through their management. However, they failed to find out its specific mechanism and ignore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ubstantive and symbolic meaning of management behavior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power, the management staff may engage in different behaviors, such as practical actions or largely symbolic commitments for the future. Differentiated management behaviors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firm growth. Therefore, this paper divides differentiated management behaviors into two categories, namely substantive and symbolic behaviors, and introduces the differentiated management behavior to uncover the “black box” of the action mechanism of managerial power in firm growth.
The managerial power and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OTAs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other Internet enterprises and tourism enterprises, thus, it is necessary to look further into it. This paper takes Ctrip as the object of study, adopting the single-case study method; Ctrip is a representative firm that reflects the evolution of managerial power and firm growth of OTAs. It is found that as the power of the management changes, perceiving different degrees of decision-making freedom and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When the degree of perception is low, they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negative effects and potential risks of their behaviors and show more symbolic behaviors. Along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perception, the management focuses more on the positive effects and potential benefits of their behaviors, resulting in more substantive behaviors. When the level of perception rises above the annual average, the management would carry out more substantive and symbolic behaviors in a balanced way. Firms have different development theme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their development. Differentiated management behaviors, if they can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development theme, will promote growth. Otherwise, they could hinder firms from growth. This paper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research of managerial power, enriches the relevant study of substantive and symbolic behaviors, and provides guidance for OTAs to reasonably allocate managerial power.
Keywords: OTAs; managerial power; firm growth; substantive behavior; symbolic behavior
[責任編輯:王 ? ?婧;責任校對:劉 ? ?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