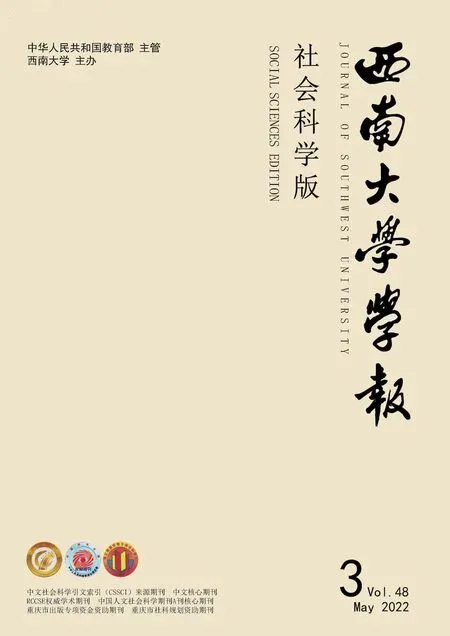明代江防體制演變略論
——以《明史·江防》考釋為中心
夏 強
(海南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海南 海口571158)
明代“東南為財賦具區,而留都乃根本重地”[1]卷243,請增調狼土等兵以安根本重地疏,明廷對于長江下游及沿岸地區的守御極為重視,并頗有興作,《明史·海防》所附《江防》對此有專題論述[2]卷91,兵志三。然而,《明史》行文提要鉤玄,用筆精簡,加之相關的考釋少且零散[3-4],難窺其全貌。目前學界對于明代江防問題雖已有一些探討,但對于江防體制演變的詳細過程均語焉不詳[5-9]。有鑒于此,筆者擬在校注《明史》卷91《江防》的基礎上,兼論其他史實,以期厘清明代江防體制的演變、興廢、效能、弊病等問題。《明史》卷91《江防》一節共七百余字,茲據中華書局1974年校點本,全錄其文,并作校注、議論如下。
一、明初江防單位創設與布置
《明史》載:“日本地與閩相值,而浙之招寶關其貢道在焉,故浙、閩為最沖。南寇則廣東,北寇則由江犯留都、淮、揚,故防海外,防江為重。”
《明史》這二句是說明代日本與華交通及倭寇襲擾的情形,點出江海匯通之勢,為上承海防,下啟江防的轉承句。
明代“倭舶由薩摩州開洋,歷五島,越琉球而南犯”[10]卷3,華夷沿海經略序,故言日本地與福建相接。“倭寇過洋,如遇南風多則犯浙、直,遇北風多則犯閩、廣”[11]卷221,占度載度,中國東南沿海為季風氣候,每年春季多東南季風,秋季多北風,倭寇利用季風駕船往來侵襲,故而每年春、秋季節沿海地方需增調軍隊,嚴加防備,是為“春汛”和“秋汛”。明代名將俞大猷也有云:“倭賊自彼島入寇,遇正東風,徑由茶山入江,以犯直隸”[12]767,防遏倭寇循江內侵便是江防的重要任務,而江防又以南京(1)明代南京名為“應天府”,時人又多以南京、金陵、留都等名稱之。為方便行文,本文統稱作“南京”。的防御為重,明人鄭若曾對此深有洞察:“江防以拱護留都為重。長江下流乃留都之門戶也,遏寇于江海之交,勿容入江,是為上策;截殺于江中關隘,使賊不得溯流而西,是為中策;若縱之過金、焦、礬諸山,震驚留都,罪在不原。”[13]卷1上,兵務舉要
《明史》載:“洪武初,于都城南新江口置水兵八千。已,稍置萬二千,造舟四百艘。又設陸兵于北岸浦子口,相掎角。”
明初建都南京,而“南畿勝勢在長江,留都守御,舟師為急”[13]卷1下,南畿總論,由是朱元璋特在南京新江口設水師,稱“新江口營”,簡稱“新江營”。“新江口營坐落江東門外地方,分中、左、右三營”[14]卷19,職掌十二,是江防的核心力量。江東門位于南京城西稍偏南,非《明史》所稱正南。關于新江口水師的規模,正德時負責江防事務的懷寧侯孫應爵奏稱:“新江口原設操軍萬一千六百五人,戰船、巡船三百四十艘。”[15]卷103,正德八年八月戊戌嘉靖元年(1522),有大臣所奏與孫應爵一致[16]卷13,嘉靖元年四月丁酉,可見《明史》所載“兵萬二千人,舟四百艘”當是約數。除新江營外,朱元璋還在江北浦子口置陸軍,為水師犄角:“江南設新江口水軍以御水寇,江北設浦子口陸軍以御陸寇。水陸二軍,南北掎角,互為聲勢,使水寇不得以登岸,陸寇不得以渡江。”[1]卷161,陳愚慮以奠江防疏如此布防,誠可謂周密。
除守衛南京的水陸軍隊之外,明廷又在沿江設九江、安慶、建陽、新安、宣州、廬州、六安、滁州、鎮江、揚州、儀真、太倉、鎮海等衛,在泰州、通州等地設守御千戶所。這些衛所承擔各地的駐防任務,由五軍都督府和兵部統轄。另外,沿江各地緊要處還設有諸多巡檢司,巡檢司聽命于府州縣官,職能側重于治安防控方面。拱衛首都的新江營水師、浦子口陸軍,加上各地的衛所、巡檢司,這便是明初沿江的防御力量。
《明史》載:“所轄沿江諸郡,上自九江、廣濟、黃梅,下抵蘇、松、通、泰,中包安慶、池、和、太平,凡盜賊及販私鹽者,悉令巡捕,兼以防倭。”
此句是說明初江防的范圍和主要任務,上自江西九江府,下迨長江入海口,涉及南直隸、江西、湖廣一直兩省的沿江地方皆屬江防范圍,其任務是緝捕盜賊、鹽梟和防備倭寇。
明初的江防布置是作為首都南京防御的一環而存在,并未形成單獨的系統。明初社會治安良好,加之首都位于南京,朝廷對東南地區控制力較強,因而沒有設立專職江防官員的必要。隨著政治中心北遷,明廷對東南地區的控制力衰減,天順以來長江沿線的治安一度變得非常糟糕:沿江的很多“無籍之徒”結成團伙,少則幾十人,多則上千人,船只兵器亦頗為優良,他們沿江販賣私鹽以牟取暴利,甚至劫掠客船,與官軍作戰,肆無忌憚,非地方巡檢司所能敵,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17]卷287,天順二年二月辛卯;[18]卷31,成化元年九月辛未,遣官禁治勢在必行。
二、成化時期文武操江的設立
《明史》載:“永樂時,特命勛臣為帥視江操,其后兼用都御史。成化四年從錦衣衛僉事馮瑤言,令江兵依地設防,于瓜、儀、太平置將領鎮守。后六年,守備定西侯蔣琬奏調建陽、鎮江諸衛軍補江兵缺伍。十三年命擇武大臣一人職江操,毋攝營務。又五年,從南京都御史白昂言,敕沿江守備官互相應援,并給關防著為令。弘治中,命新江口兩班軍如京營例,首班歇,即以次班操。”
《明史》這幾句話介紹了文、武兩位江防主官和江防部隊調整情況。江防事務略有二端:一曰操練江防部隊,即操江;二曰督率軍隊巡視江道,即巡江。“命勛臣為帥視江操”,即派遣有公侯伯爵位的勛臣操練江防部隊,其事始于永樂六年(1408),成祖令豐城侯李彬為總兵官“操緣江舟師”[19]卷84,永樂六年十月庚子。英宗初即位,朝廷又令襄城伯李隆“督操江船”[17]卷159,正統十二年十月癸未。此時勛臣操江均是訓練軍隊的臨時派遣,事畢解任。隨著江上治安的惡化,加之新江營“船只朽爛,軍夫逃亡,操江之事有名無實”[17]卷218,景泰三年七月丙辰,成化二年(1466)四月憲宗“命遂安伯陳韶往南京操江,兼巡捕沿江鹽徒、盜賊”[18]卷29,成化二年四月丁卯,此后更迭不輟,遂成常設。成化十三年鑒于勛臣已兼有練兵之差,練兵的“教場距江口一舍余,而練兵、操江同時,非一人所能兼理”,朝廷便“于兩京武職大臣內,專敕一人操江”[18]卷168,成化十三年七月癸酉。專職操江的勛臣被簡稱“武操江”、“操府”。
千里長江,非新江一營所能顧全,更何況新江營還有守衛南京的重任,朝臣便有了使各地駐軍分段據守的動議。成化四年錦衣衛僉事馮瑤上疏請求“操江官軍照舊操守附近巡捕,而于鎮江、儀真、太平、九江等要害之處”選任軍官“提督沿江軍衛有司多方緝捕”,他認為“如此則操江官軍庶免跋涉而不離重地,沿江官軍得以坐鎮而兼守地方矣”,得到了批準[18]卷54,成化四年五月己卯。此后,沿江各府、衛、州、縣相繼改調或添設人員充任巡捕、總巡、巡江軍快等職役負責江防。成化十八年二月,明廷又采納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白昂的建議:“沿江要害守備等官互相應援,并請關防,以便行事”,并成為定例[20]卷161,兵部二十五。這樣一來,沿江地方武裝也被納入互相應援江防體系之中。
請補江兵缺伍一事是在成化十年,南京協同守備定西侯蔣琬因新江營官兵在“調遣、逃亡之余止遺六千九百”而請“令所司追補舊額”[18]卷127,成化十年四月甲子。弘治十三年(1500),朝廷“命新江口兩班軍如京營例”,分為春秋二班,輪番操練[21]卷131,兵部十四。明廷派武操江、“補缺伍”“分班操練”等舉措,其目的都是為了確保江防核心——新江營的戰斗力。
起初,明廷獨以勛臣視操江,成化八年命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羅箎“督操江官軍巡視江道,起九江,迄鎮江、蘇、松等處。凡鹽徒之為患者,令會操江成山伯王琮等捕之;所司有誤事者,俱聽隨宜處治。”[18]卷101,成化八年二月丙戌文臣開始參與江防事務,羅箎當時的職權主要是督率官兵巡江,巡察各地江防情況。次年八月,都御史又被要求不攝院事,專督巡江[18]卷119,成化九年八月丁卯,其在事權上從南京都察院剝離出來,開始成為專設。明廷之所以增派都御史參與江防事務當有監督制約武操江的用意。當時有不少武操江貪贓枉法,如成化三年遂安伯陳韶一度捕獲鹽徒六十人,竟然“俱納賂而縱之”[18]卷44,成化三年七月壬午。后來,明廷鑒于文、武操江并設,彼此掣肘,便又重新劃分了二者的職權:令都御史提督巡江,不涉及操江[18]卷142,成化十一年六月庚子,令勛臣專責操江[18]卷168,成化十三年七月癸酉,二者各有側重。
成化時期,江防事務開始有了專職官員,鎮江、儀真、太平、九江等處皆有江防布置,明廷構建起了以新江營和各地衛所的軍事武官為主體,彼此應援的江防體系。同時,江防也不再僅為南京防御的一環。
三、嘉靖時期江防體制的變革
嘉靖間,先是江上“盜賊”頻發,繼而倭亂又起,江防體制遂多有變革,有些為《明史》所收錄,有些則闕如。
《明史》載:“嘉靖八年,江陰賊侯仲金等作亂,給事中夏言請設鎮守江、淮總兵官,已而寇平,總兵罷不設。十九年沙賊黃艮等復起。帝詰兵部以罷總兵之故,乃復設,給旗牌符敕,提督沿江上下。后復裁罷。”
嘉靖八年七月,時任兵科都給事中夏言以江浙多事,請“專設鎮守江淮總兵官一員,駐瀕江要會之所,凡沿江守備、備倭等官俱聽節制”,并得到了世宗的支持[16]卷103,嘉靖八年七月戊午。“未幾賊平,兵部奏革,以其責任仍歸操江武臣如故”[16]卷238,嘉靖十九年六月庚午。嘉靖十九年,“大盜常熟黃艮、通州秦璠并自崇明,出入海上肆劫”[22]3593,世宗“詰兵部以先年所設江淮總兵官,何因革罷?”于是得以復設[16]卷238,嘉靖十九年六月庚午。嘉靖二十九年,江淮總兵官一職又被革去[2]卷76,職官五。該職旋設旋革,不得久存的原因是其職權與文、武操江高度重合,他們“互相牽制,難以行事”[16]卷104,嘉靖八年八月癸酉。
除了《明史》所載江淮總兵官的興廢以外,嘉靖時期的江防體制還有以下兩方面變化:
第一,都御史權力的擴展。其事始于弘治時期,弘治八年七月,朝廷令巡江都御史“兼管”操江[23]卷102,弘治八年七月己丑,兼有巡江和操江兩責,以巡江為主。至明世宗初期都御史的職任變為“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則以操江為主[16]卷102,嘉靖八年六月甲戌。另外,江上發生治安案件的偵辦、審理也歸都御史負責[24]卷11,蘇知縣羅衫再合。在此背景下,都御史之權日重,武操江之權漸輕,兵部對此也十分清楚:“南京故有武職大臣專管操江,兼理巡捕再三斟酌,應無句讀錯誤。正其職守。止緣敕內開載不專,內有掣肘之嫌,外無節制之權,徒擁虛名。”[16]卷104,嘉靖八年八月癸酉至此,操江勛臣事權無幾,成為一個象征性的職設,又因其地位超然,所以也不為操江都御史節制。
第二,沿江各營的添置。明中期以后,“衛所軍士空虛疲弱,在在皆然”[25]卷23,復楊裁庵,沿江衛所和新江營也不例外。此時新江營“役占、老弱、耗減過半……江船原額三百四十,多不堪用”[16]卷13,嘉靖元年四月丁酉,又因該營“事多關白守備、參贊,掣肘難行”[1]卷99,江防六事疏,在江海不靖的背景下,明廷唯有另建新軍才可調用。除安慶營(設于成化十三年)外[14]卷10,職掌三,儀真營、瓜洲營、圌山營、游兵營、南湖營(又名南湖嘴營)均設于此時,各營俱統轄于操江都御史,營兵多為募得[26],可根據需要隨時增募、裁減。
在歷經嘉靖時期的調整之后,武操江之權幾乎被侵奪殆盡,操江都御史權力大為擴張,提督操江都御史已演變為江防的實際最高管理者,他們又常被稱作“提督操江”“操江憲臣”“文操江”“操院”等。與此同時,新募各營取代沿江各衛所,成為江防的主力。
《明史》載:“三十二年倭患熾,復設副總兵于金山衛,轄沿海至鎮江,與狼山副總兵水陸相應。時江北俱被倭,于是量調九江、安慶官軍守京口、圌山等地。久之,給事中范宗吳言:‘故事,操江都御史防江,應、鳳二巡撫防海。后因倭警,遂以鎮江而下通、常、狼、福諸處隸之操江,以故二撫臣得諉其責。操江又以向非本屬兵,難遙制,亦漠然視之,非委任責成意。宜以圌山、三江會口為操、撫分界。’報可。”
此段介紹了倭患驟熾背景下,朝廷明確操、撫責任的情況。嘉靖三十二年倭患驟熾,明廷一方面調九江、安慶官軍赴京口、圌山等地防守[16]卷432,嘉靖三十五年二月乙巳。另一方面,對于長江入海口地區的江防架構進行了調整,設立江南副總兵和狼山副總兵。嘉靖三十二年設江南副總兵“專管江南水陸兵務”[21]卷127,兵部十。嘉靖三十七年,朝廷又添設狼山副總兵,江北“各參將、守備、把總、備倭等官,及地方衛所悉聽節制”[27]卷26,議設狼山副總兵疏。嘉靖三十三年、三十六年,明廷分別令應天巡撫、鳳陽巡撫提督軍務[21]卷209,都察院一,于是江南、狼山副總兵又成為應天、鳳陽兩巡撫的下屬。
操江都御史的管區本是“上至九江,下至鎮江,直抵蘇、松等處地方”[14]卷九,職掌二,由是操院和應天、鳳陽兩位巡撫的管區便有了重疊部分。南京兵科給事中范宗吳發現:“巡撫二軍門遂以下江海口兵務俱諉之操江所屬,已而操江都御史亦以鎮江而下原系兩巡撫部轄,本非江洋信地,勢遠分疏,兵難遙制,亦泛泛然不肯視為急務。彼此觀望推避,互相耽延,以致倭夷乘機深入,殘害地方。”他便上疏請求“定信地:以圌山、三江會口為界,其上屬之操江,其下屬之南、北二巡撫”[14]卷31,奏議五。世宗同意了他的請求,并令“今后不系操江所轄,地方一切事務都御史不得復有所與”[16]卷524,嘉靖四十二年八月丙辰。此后,圌山、三江口以下屬海防,由應天、鳳陽二巡撫督令江南、狼山副總兵防守;以上屬江防,由操江都御史負責,至明亡不改。
《明史》載:“其后增上、下兩江巡視御史,得舉劾有司將領,而以南京僉都御史兼理操江,不另設。”
這是補充介紹明代巡江御史和操江都御史的情況,但此句有二誤:其一,“其后增上下兩江巡視御史,得舉劾有司將領”有誤,兩巡江御史之設及其舉劾權的獲得均不晚于嘉靖十一年。其二,“而以南京僉都御史兼理操江”一句也有問題:理操江者非專為僉都御史,南京都察院的右副都御史或右僉都御史都曾提督操江。
巡江御史是南京都察院監察御史的外差,有上江和下江兩員:“一員自龍江關,上至九江;一員自龍江關,下至蘇松等處。”[21]卷211,都察院三早在成化時期,明廷已有遣御史巡江之舉[18]卷54,成化四年五月己卯,后漸成常設。《南京都察院志》記載了嘉靖十一年十月初六,世宗分別向兩位巡江御史下達了內容基本相同的敕書,其中詳細規定了其職權:“往來巡歷分管沿江地方,嚴督守備、備倭并軍衛有司巡捕等官,務要整搠官軍、兵快人等……所屬官員如有貪殘廢事,頑寇殃民,應提問者就便提問,應參奏者參奏處治,其巡捕官員聽爾揀選委用。”[14]卷13,職掌六;[14]卷14,職掌七有些學者認為巡江御史直屬于操院,是操江都御史的下屬機構[7],但筆者對此并不認同,依據有三:首先,明代十三道監察御史“于都御史有統無屬”[28]卷10,糾劾老悖大臣以勵世風以開言路疏,他們獨立行事,操江都御史指揮巡江御史于制度無依。其次,如敕書所云,巡江御史的任務主要是巡視沿江防御,他們與江防官員之間是監督的主客體關系,而不是管理的上下級關系。最后,巡江御史與操江都御史各有管區,特別是巡視下江御史的大片管區均在都御史職權之外,不可能出現操院通過巡江御史跨界管理的制度漏洞。
四、隆萬之際江防體制的完善
隆萬之際,明廷對于江防體制進行了諸多的改革、完善,具體如下:
《明史》載:“先是增募水兵六千。隆慶初,以都御史吳時來請,留四之一,余悉罷遣,并裁中軍把總等官。已,復令分汛設守而責以上下南北互相策應。又從都御史宋儀望言,諸軍皆分駐江上,不得居城市。”
初因備倭,明廷每年春便會召募民兵赴三江口等要處防汛。嘉靖四十三年,操江都御史王本固就各地民兵內精選若干,募為水兵,加上之前增募,共計六千余[14]卷31,奏議五,造成了很大的財政壓力。隆慶二年(1568),操江都御史吳時來奏云:“增募水兵六千余人,所費兵餉以七萬余計。今倭寇已靖,宜汰簡以蘇民困。擬量留一千七百余名分守要害,余悉罷遣。”兵部覆議:“冗兵既汰,而中軍、把總等冗員亦當查革”,獲準[29]卷25,隆慶二年十月己亥。
“分汛設守”和“諸軍皆分駐江上”是操院何寬與應天巡撫宋儀望二人聯合推動的結果。萬歷二年(1574),濱江的蕪湖縣庫被劫,暴露出江防體制的諸多問題[30]卷28,萬歷二年八月丙辰。次年三月,何宋二人聯名上疏,提出筑縣城、復將領、增兵額、議兵餉、分信地、專責任、定哨期、課功罪八條整頓建議,主要內容有三方面:第一,建造防御設施,恢復部分職官并添募士兵。第二,推行年終匯報制度,“每年各兵備道將各地方守備、把總官,各府江防官,各衛巡江官功罪重輕備行稽察、開報(操院)”,并據此考核賞罰。第三,明確信地,落實江防官員責任,鑒于守備、把總等官“多住城市,鮮居信地,以故哨捕等役得以買閑偷安,而江上之警或發而不知,或知而不報”,故令其“各駐扎本處,不許仍前住居城市”[14]卷31,奏議五。
《明史》載:“萬歷二十年,以倭警,言者請復設京口總兵。南京兵部尚書衷貞吉等謂既有吳淞總兵,不宜兩設。乃設兵備使者,每春汛,調備倭都督,統衛所水、陸軍赴鎮江。后七年,操江耿定力奏:‘長江千余里,上江列營五,兵備臣三;下江列營五,兵備臣二。宜委以簡閱訓練,即以精否為兵備殿最。’部議以為然。”
萬歷二十年,豐臣秀吉大舉入侵朝鮮,江南亦為之震動,有官員建議在東南地區復設總兵以備倭。次年七月,南京兵部尚書衷貞吉認為京口已歸江南副總兵管轄,建議“省總兵,添兵道”,“每歲春汛,備倭都督統率陸兵三千前赴鎮江京口防汛……汛畢官兵即行撤回”,獲準[30]卷262,萬歷二十一年七月辛末。可見改設兵備道之事在萬歷二十一年,《明史》所載有誤。
值得注意的是,隆萬之際文官更加深入地參與到江防管理之中。早在嘉靖二十三年,明廷便令沿江府州縣佐貳、巡捕官管理江防者“悉聽操江衙門委督,不許別差”[16]卷291,嘉靖二十三年十月辛巳。萬歷二年正月,明廷又令九江、安慶、池州、廬州、太平、揚州、鎮江等府設江防同知專管江防,應天府設江防治中[14]卷31,奏議五。江防同知、治中當時被統稱為江防官,他們常駐濱江地區,統帥“境內州縣巡司之兵”,每月巡行江上,查點官兵、巡船和軍事設施,“凡境內官兵,不論游兵、守備、中軍、軍衛、有司、巡司”俱聽其查點,各部隊“兵糧之退補支給”,即軍餉收支、發放也歸其負責[14]卷31,奏議五。江防官是作為基層軍事單位的稽查者和后勤保障者而存在,并不能調動、指揮軍隊。兵備道創設于成化、弘治年間[31]33-36,嘉靖時期因“東南倭事日棘,于是江、浙、閩、廣之間,凡為分巡者無不帶整飭兵備之銜”[32]569。各兵備道負責統轄幾府的軍事力量,擁有稽查江防官的權力,成為僅次于操院的江防官員。沿江地區相繼設有九江、徽寧、潁州、蘇松常鎮、淮揚海防兵備道[21]卷128,兵部十一,至萬歷二十一年,蘇松常鎮兵備被拆分為常鎮兵備和蘇松兵備,其中常鎮兵備受操院節制[11]卷190,方輿二。
萬歷二十七年,操院耿定力條陳江防事宜,稱:“上江列營五,備兵使者三;下江列營五,備兵使者二。”現綜合各種資料,繪表如下:

表1 操江都御史所轄諸營表(2)明代江防各營軍隊之數和信地屢有變化和調整,本表主要依據《江防考》的記載,另參考萬歷《明會典》《南京都察院志》等資料。另外,游兵營起初是作為操院備用的奇兵而成立的,后因倭患也開始負責分守信地并由應天府江防治中管理,江防治中實際承擔了其他地區兵備道部分的職能。
上表可見:當時兵備道上江有三,分別是九江、潁州和徽寧兵備;下江有二,則為淮揚海防和常鎮兵備,各兵備統轄除游兵、太平、新江三營之外的沿江各營。沿江十營分別是南湖營、安慶營、荻港營、游兵營、太平營、新江營、儀真營、瓜洲營、三江營、圌山營。其中,荻港、三江、太平三營是在寇亂之后增設的,太平營設于萬歷二十年,是操院的親兵,其主要成分是“家兵”和“家丁”[14]卷10,職掌三。太平營和新江營一樣均沒有信地,也不需會哨。沿江各營相繼設立之后,新江營的核心地位也就相應弱化了。
總的來說,隆萬之際江防的改革是從三個方面進行的:在軍事方面,繼續添設新營,調整軍隊規模;在規章制度方面,劃定各營信地,落實責任,嚴格賞罰;在權力架構方面,武官管理江防的局面宣告終結,江防文職官員體系構建完成,形成了操江都御史→兵備道→江防同知和各營的三層架構,江防官設置使操江都御史的權力得以下沉到基層。這些變革使得江防體系更趨于嚴密,也標志著明代江防體制最終定型。
五、晚明江防體制的廢弛與崩解
萬歷間,首輔申時行在給操江都御史王用汲的信中,曾自得地說:“長江上下千里……今設防已密,亦極稀簡矣。”[33]卷6,答王麟泉操江然而,在野士人吳應箕的看法卻與之截然不同:“南京新營之兵不可謂少矣!文、武操江之節制不可謂不嚴重矣!自九江以及金陵為監司者三,府有丞,衛有使,鎮有總把,口有巡司,又別差臺臣歲一按視,又有職方、兵垣等官坐南調度,其防御之設不可謂不密矣!加以水營之操練,沿岸之巡邏日益嚴毖,何謂弛也?然數者皆有名而無實,徒幸無事,官以待遷,兵以偷飽耳。一旦有急,如摶沙畫餅,豈能一有所恃哉?”[34]卷10,策十防江在吳應箕看來,江防體制職官繁冗,且漏洞百出,其中官兵的懈怠是最為主要的原因,對此《明史》也有記載。
《明史》載:“故事,南北總哨官五日一會哨于適中地,將領官亦月兩至江上會哨。其后多不行。崇禎中,復以勛臣任操江,偷惰成習,會哨巡徼皆虛名,非有實矣。”
自萬歷中葉起,神宗倦勤,朝廷上下文恬武嬉,國事日非,江防亦全面廢弛。《明史》所言會哨不過是其中的一例,江防弊病略有三端:
其一,明末江防體系中文、武操江彼此分立的情況更趨嚴重。如前所述,嘉靖以來文操江把持江防事權,武操江雖仍掛名統轄,但其權限于新江一營。明中后期,將帥蓄養家丁之風盛起,文操江據有太平營,武操江則在新江營內編制家丁二百人,又別立旗牌官等項士兵[14]卷10,職掌三。文、武操江各擁部屬,互分彼此,無法形成合力。
其二,文官管理層因循腐朽。明末江防的實際權力集中于各類風憲官之手,當時監察體制由盛轉衰[35],風憲官亦趨墨敗。先是一些操江都御史的腐敗和怠政,例如熊明遇在任文操江時將公事拋于腦后,“費公帑以恣游觀”,還貪污一千二百兩[36]卷70,天啟六年四月癸酉。上行下效,各地兵備道和江防官也懈怠起來,兵備道有“如放兵糧有經月不批者,修巡船有經年不行者”,而不少士人也因江防官一職職任繁重而“百計規避”[14]卷9,職掌二。與此同時,負有監管之責的巡江御史也陷于墨敗,如巡江御史汪有功就因違規批給商船執照而被彈劾[30]卷538,萬歷四十三年十月癸丑。明廷以文制武,文官因循貪墨,軍隊自然也隨之腐朽。
其三,江防部隊戰力衰減。其表現有三:一,營伍空虛。天啟初,巡江御史張繼孟發現:當時軍中各營“不肖將領希圖兵糧、任情占役,以致營伍空虛。……一遇巡閱,緩則借彼應此,急則募民頂兵”[37]卷27,九月。二,船械不足。以新江營為例,“核其官兵,不滿兩千之數……水兵船只十無一可”[38]卷5,疏稿。三,兵驕將惰,會哨諸制俱為空文。各營的士兵多為招募而來,至萬歷末士兵“驕縱成習,各府衛官俱不敢點。有司之兵各自統屬,備總官亦不敢點。遂至勢相抵捂,法亦阻隔”[14]卷9,職掌二。各級軍官們和文官上司們一樣,也變得因循腐朽。當時備總、哨總等官“多彼此通同高坐私家,江上之警或發而不知,或知而不報。甚有與賊交通,暗地分贓,來不拒而去不追者”[14]卷9,職掌二。如此軍隊的戰斗力便不言而喻。
江防官兵上下懈怠,沿江治安遂告惡化。時人吳國倫曾痛斥道:“近者江防公經數年不一按視,以致人心玩愒,保障廢弛。仆頃年里居,見群賊分道入市,而有司者未嘗問也。”[39]卷49,書三十九首江防官兵巡捕盜賊的職任儼然已成虛文。
崇禎十六年(1643),誠意伯劉孔昭在召對時“泣陳文臣掣肘,事權不一”,當時思宗似有南渡之意,故視整肅江防為亟需,為了集中事權,他竟裁去了操江都御史一職[22]5987,把江防職任盡歸于武操江劉孔昭。在當時江防體制之下,思宗的這個決定是一個致命的錯誤:一方面,劉孔昭“實無片長,惟以空言鼓動主上”[40]卷16,崇禎十六年八月辛未,他到任后“以京掣為寶山、視鹽船為金穴”,竟干出了“沿江截詐,殘害異常”的事情[41]卷12,先叔父侍御府君行略。另一方面,也是最為根本原因,嘉靖以后江防部隊由各級文臣統領,勛臣劉孔昭既管理不了原屬文操江的轄軍,也指揮不動各地兵備道。他為此曾抱怨說:“武操見軍通計選鋒、常伍僅七千余人,兩年不給鹽菜,半載不與月糧。而文操見兵不滿三千,叫囂凌玩,不知紀律。至如船敝而缺,器鈍而少,餉壓欠而人無固志。”[42]卷9,瀝明臣職事可見他根本無法調動文官控制的部隊,遑論訓練、作戰,再加上軍餉不濟,船械缺失,整個江防部隊已無戰力可言,明王朝經營兩百余年的江防體制實已崩解。
思宗既沒,劉孔昭又倚仗所謂的“軍權”參與到南明朝廷激烈的政治斗爭中去,于沿江防務便鮮有關注。不久,清軍南侵,廢弛不堪且缺乏組織合力的江防部隊,自然難以像南渡的趙宋那樣組織起有效的防御,甚至連像樣的抵抗都沒有發生,弘光政權自然也未能偏安江左。
六、結 語
江防事關南京安危、財賦征收,洪武時期便已在新江口設有水師,并于沿江地區設立衛所、巡檢司等。首都北遷后,江上治安惡化,明廷派遣武職勛臣管理江防,是為武操江。武操江至成化時期成為常設,明廷又以南京都察院副都御史或僉都御史就近加以監督。嘉靖時期,新募的各營取代新江營和衛所,成為江防的主力,江防事務獨為操江都御史所掌控,而武操江已有名無實。隆萬之際,都御史統領各地兵備道等管理江防事務,各府設立各地江防官,并訂立了嚴格的規章制度,江防體制定型。萬歷中葉以后江防體制全面廢弛,并最終崩潰。總體觀之,明代江防體制演變的過程是漸進式的,與明代文官掌軍權和監察機構行政化這兩大政治發展趨勢相契合。
明代江防制度的改革始終是圍繞著軍事管理層面進行的,其核心是對武將的管理和防控。至萬歷初,沿江各衛所與新設各營武將的指揮、訓練、后勤等權已經被侵奪殆盡,他們幾乎已經成文官們提線之木偶,經年日久,“兵驕將戇”遂成常態[13]卷1上,御將。在財政拮據的背景下,文官們往往并不能改善士兵們的待遇,特別是衛所的軍士常年處于饑寒困苦之中,幾無作戰之力,招募之兵的待遇雖稍好一些,但對于他們武將無權管,而文臣不能制,日益驕悍。明人葉權稱“我朝御將之法極高,養兵之道未善,故歷世無強將,而各省多變兵”[43]186,誠可謂肯綮。舍恤卒練兵之本,求管制將領之末,明代的江防體制終歸于失敗。當然,這一情形不單存在于江防部隊之中,更是明中葉以來各地軍隊的通病。
回頭來看,明代的江防體制運行了二百多年,對于長江下游地區的防御,江上治安的維持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與此同時,也要看其制度雖密,執行欠佳的現實,崇禎皇帝誤以武操江統帥江防,最終促使江防體制的崩解。鑒于明代教訓,清廷在平定江南地區之后立即復設操江都御史管理江防,不久又令操江都御史兼任安廬巡撫,稱操江巡撫,此職再變為安徽巡撫,江防事務則改隸兩江總督管理[44]卷116,職官三,因而操江都御史又可以視為蘇皖分省的職官淵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