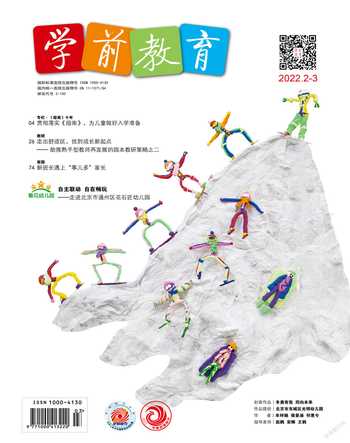親近兒童
余琳
我的辦公室與小一班的活動室對門而開,這是全園離幼兒活動室最近的一間辦公室。我喜歡讓我的辦公室離孩子近一點,這樣在繁瑣的工作中就可以利用一些碎片時間看見兒童。
由于緊挨著幼兒的活動室,這里免不了“嘈雜”。迎接新生開學的9月,對門總會時不時地傳來孩子們撕心裂肺、嗚嗚咽咽的哭聲,甚至嚶嚶啜泣也能被我聽見。但更多時候,傳入耳朵的是孩子們欣喜、興奮、心滿意足的歡笑聲,與教師、同伴的對話聲,好奇的發問聲以及操作玩具的碰撞聲。這里是一個能聽得到孩子們的聲音、感受得到孩子們的情緒、了解得到孩子們的活動體驗的地方。
由于這個班的孩子們經常經過我的辦公室,而我又是一個喜歡和孩子打交道的人,所以我們之間有著頻繁的互動與交往。當他們路過我的辦公室向里面張望、關注我的時候,除非手頭上有非常緊急的工作,我大都會主動走出來,迎上他們,靠近他們,蹲下身來和他們聊上幾句。在這些細微的互動中,幼兒和我之間建立起了情感聯結。他們路過的時候會留意我在不在,會猜測我去哪里了,我們之間還發生了“送小愛心”“婚禮邀請”等小故事。
這天中午,孩子們要去午睡,正好又路過我的辦公室。小丫在外面叫了我一聲,可我正匆忙敲擊著鍵盤撰寫材料,便只是簡單地回應了她。她可能覺得我的回應不夠,就一邊叫著“園長媽媽”,一邊走了進來。
看著小丫走了進來,其他小朋友也跟著蜂擁進來。他們對我的辦公室充滿了好奇,有的趴在沙發上,有的圍在桌子前,有的打開柜子探索著我柜子里的物品,不斷地問我“這是什么”“那是什么”。我趕緊停下了手頭上的工作,起身解答他們關于相框、筆記本、玩偶、靠墊、護頸枕、綠植等的種種發問。直到老師提醒他們要去午睡了,他們還是依依不舍。
這時,拿著猴子靠墊的伊伊問我:“我可不可以拿猴子回去陪我睡覺?”聽到我回答“當然可以”,一時間,孩子們把靠墊、護頸枕、玩偶、熊貓筆記本等柔軟和可愛的物品一掃而空,最后只剩下了空著手的小丫。她找來找去,最后選了一本封面富有童趣的剛剛寄來的11期《學前教育》雜志,如獲至寶般地說“我就要這個陪我睡覺”,然后跟著大家滿意地抱走了雜志。后來聽老師說,有了園長媽媽的“寶貝們”的陪伴,孩子們那天睡得特別快、特別香。
孩子們這趟“探秘之旅”讓我看到了他們的自信、大膽,以及對我的信任和樂于親近,也觸動我去思考:作為一名園長,我長期和孩子們保持互動有何意義?
作為一名集團化幼兒園的總園長,我常常被卷入千頭萬緒的工作之中,但關注幼兒、親近幼兒、積極地與幼兒互動是我長期以來保持的做法。這本是一種職業習慣,但我與幼兒的互動讓幼兒感受到了被接納和被重視,作為一種隱性的情感與社會性教育滋養了他們的自信。我們的互動也成為了園所文化的一部分。作為園長,我對兒童的親近彰顯了在幼兒園中成人與幼兒的相處之道,發揮著示范作用,無形中影響著帶班教師對待兒童的態度和行為;親近兒童也成為我自身專業發展的養料,幫助我保持專業靈性和專業敏感。
我是一名園長,但首先我是一名幼教工作者。看見兒童、靠近兒童,才可能找得到自己,這是園長工作的根基點。
作為園長,我們或許可以常常問問自己:我能夠叫得上幼兒園里多少個孩子的名字?我知道多少孩子們的小故事?我最近和孩子們之間發生有意思的故事了嗎?以此來反思我們與孩子們之間的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