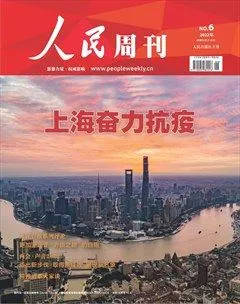特殊精神 特殊擔當

人民日報中央廚房大江東工作室出品的短視頻《守“滬”》截圖
雖然有些起風,還飄落了零星小雨,但上海西部的一個小區,現場一片火熱,居民們激動等待著“解封”的那一刻,還自發唱起了《歌唱祖國》。21時不到,隨著正式解封,居民們開心走出小區,與親友相見,互相合影留念。普陀區和街道負責人還為居民送上鮮花和祝福。
“我們解封啦!”
這是3月14日的晚上,上海市普陀區甘泉路街道,志丹路上的西部名都花園小區門前歡呼聲不斷。
就在14天前——2月28日21時,因有一本土確診病例居住于此,西部名都花園小區開始實施封閉管理。此后的14天,小區里約1500名居民開始了居家抗疫。
“我們平時辦公不在這個小區,但疫情就是命令!”名都居民區黨總支書記朱雪萍帶領4名社工干部立刻“逆行”進入小區。甘泉路街道緊急抽調機關干部、社工以及社區民警等50多人同步進入小區,穿上防護服,與小區居民守在一起。
為準確做好整個小區封控人員的實時監測和信息上報,朱雪萍帶領工作組嚴格落實管控措施,精心安排各個工作環節。面對小區居民多輪核酸檢測任務,工作組提前對物資準備、布點設置、防控措施、人員調度等作出部署,就近設置檢測點。
醫務人員兩兩分組,同步將工作人員與安保人員兩兩編組,形成“2+2”組合,分工明確,責任清晰,逐個樓組挨家挨戶敲門,引導居民做好個人防護并迅速到達距離樓棟最近的檢測點,采樣之后迅速離開。
陸沅茜是一名“95后”社區女警,在小區里配合開展封控篩查工作。小區連夜進行核酸檢測,陸沅茜帶著工作組人員挨家挨戶上門,耐心細致地做解釋工作,等核酸檢測全部結束已是天亮。小區內一名高齡孕婦已經懷孕9個月,由于小區封控,普通的120救護車不能進,而孕婦產檢不能等。接到求助后,陸沅茜和社區干部協調轉運車輛,將孕婦安全護送到醫院,還為孕婦預約好了下次產檢的轉運車輛。
建于1999年的西部名都花園,除了居民住宅外,公共的室內區域面積不大,14天里,大部分工作人員都擠在一間活動室里休息,朱雪萍則干脆把車后座當成了自己的“床”。
“特殊時期,最重要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信任!”朱雪萍說。小區甫一封控,很多居民不適應,特別是剛開始要連夜測核酸,大家挨家挨戶敲門,還碰了不少“釘子”。“有的居民會不理解,為什么非得半夜測呢?但疫情防控,真的是要爭分奪秒。”
經歷開始時72小時的“連軸轉”,居委會和社區干部們布滿血絲的眼睛、沙啞的嗓音,每家每戶送物資、收垃圾……居民們看在眼里,慢慢地,抱怨聲沒了,取而代之的是支持、鼓勵,還有不少居民主動成為志愿者。
解封當晚,居民吳阿姨走過來。朱雪萍說,謝謝她給工作人員和志愿者買了許多水果。“這沒有什么,如果可以捐錢,我還要捐。你們真的太辛苦了!”吳阿姨抓著朱雪萍的手說。
“現在是疫情防控關鍵時期,雖然小區解封了,大家還是要做好防護……”朱雪萍一再叮囑。
小區車位上成立臨時黨支部,“有需要找我們!”
人民日報記者 謝衛群
“這里是臨時黨支部,有困難、有需求請找我們。”在上海市松江區方松街道江中公寓封控管理期間,這樣的話,讓居民覺得很溫暖。
3月6日,周日的中午,因出現一名無癥狀感染者,江中公寓被突然封控。一時間人們有點慌亂,擠在院子門口,七嘴八舌地提出疑問,卻沒人能回答。

臨時黨支部成為小區抗疫的戰斗堡壘。

3月15日下午,社區解封前,黨員志愿者們在臨時黨支部前依依不舍。(方松街道供圖)
江中公寓有118個樓道,1416戶住戶,4000多名居民,周末大都在家,其中,老人占了1/3。可以想象大家不知所措的樣子。更棘手的是,居委會不在小區里,其他社區工作者也進不來,物業力量單薄。幾乎沒有組織者,如何實現圍墻內外無縫隙、24小時的即時聯通?
3月8日,在方松街道黨工委指導下,江中公寓疫情防控臨時黨支部成立。黨員居民寧文玲擔當臨時支部書記,她同時也是方松街道另一個社區居委會的書記兼主任,管理經驗豐富。東鼎居委會夏文雅、街道綜合行政執法隊高勇、街道營商辦王婕、街道社區事務受理中心賈晶晶擔任支委委員。新浜鎮政府黃濤濤則主動參與支委工作。寧文玲在微信群發出征集通知,很快就有30多名黨員響應,她迅速建立起“江中公寓黨員群”。
“就在西大門的一個車位上,臨時黨支部簡單分了分工,就開始工作。”寧文玲說。為了讓居民能找到黨支部,他們請街道支持,做了一塊醒目的標志牌:方松街道江中公寓疫情防控臨時黨支部。掛在臨時帳篷上,一下就吸引了居民。
“這里是臨時黨支部,有困難找我們。”這句口號,在小區傳揚開來。
高勇說:“牌子下設了接待點,我們每天三班倒,從上午7點工作到晚上10點,每個支委輪值,每人守半天,寧書記則全天值守。”黨員亮了身份,貼上大紅胸貼:方松黨員志愿者,有需要請找我。
居民的需求千頭萬緒:有的家里沒藥了,要配藥;有的家里急著要買菜;有的燃氣沒了,著急要充值;還有的家里沒人,兔子沒人喂;眾多獨居老人也亟需有人關懷;大批快遞不斷涌來,亟需分發……“黨支部承諾都盡力滿足。”寧文玲說。
為增加服務力量,以黨員為骨干,寧文玲不斷征集志愿者,居民自告奮勇,“黨員微信群”很快擴展為“黨員和志愿者群”,人數達230人,夫妻檔、父子檔、母子檔志愿者不斷涌現。寧文玲組建了幾個黨員牽頭的小分隊:宣傳隊——負責信息發布、文稿和攝影;快遞隊——分發快遞;醫療隊——由18名住在小區的醫生組成,為有需要的居民服務,配送藥物;采購隊幫助居民買菜,采購急需物資或充值;巡邏隊負責規勸居民居家不出門,不在小區走動,減少流動感染……小區很快有序起來。
高勇說:“工作量非常大,光是快遞,最多的一天分發超過1000個,每一個快遞,志愿者都一一登記,以防出錯。”王婕負責文案,“核酸檢測幾時做,志愿者如何分配,怎么通知居民,都要一一寫出來。還要培訓志愿者,把有關知識寫出來,讓大家提前熟悉。”還有的支委負責疏導群眾情緒……“9天的封控管理,突發情況不斷,每晚服務點的服務結束,還要總結一天的情況,做好第二天預案,從早到晚就像打仗。”寧文玲感嘆。
就這樣,臨時黨支部成了小區居民的主心骨。3月15日下午,小區解封,已成為抗疫戰友的黨員和志愿者們都有些不舍……
封控組、流調組、采樣組、消毒組、檢驗組、數據組……
連日來,位于上海市黃浦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3樓的指揮室徹夜通明。“我們一共有14個專業工作組。一旦發生情況,各組負責人都要第一時間了解信息、各司其職、打好配合。”黃浦疾控黨辦主任阮園介紹。
這里,幾乎是你能想象出的最忙碌的現場。要阻斷病毒傳播,就得拼命與之賽跑。跑在最前線的疾控人,就是竭盡全力的“尖刀營”。
“尖刀營”工作千頭萬緒,流調組要在24小時內排摸清楚疑似人員軌跡。如果確診病例在商務樓工作或途經商場,需要從幾天前的監控視頻開始排查,以確定高篩、次密接管理對象,正如網上熱議的“判定次密接和高篩,可能就差一個口罩的距離”。
更多組也同樣辛苦且重要。大江東工作室見縫插針采訪了采樣組、消毒組、檢驗組的三位組長——
3月15日晚上10時,新的采樣任務來了。正接受采訪的張博趕緊整裝出發。次日一早他對東姐說:“以為要忙到凌晨一兩點,后來零點剛過就完成了!”
黃浦疾控采樣組組長張博,自家小區封控,妻子剛動完手術,拆線換藥他統統顧不上,早就一頭扎進單位,24小時連軸轉。“疾控人的家人這兩年太苦了。經常半夜一個電話叫走,幾天不著家。”他很愧疚。
張博不說,其實他的工作更苦。
采樣組,負責對確診病例或密接人員環境采樣,有“上天入地”之能。“門把手、餐廚用具、床單被罩、毛巾、漱口杯、垃圾桶、馬桶、下水口、空調口……爬上爬下,能觸及的地方都要采到。”張博說。

仁濟醫療隊在臨時集中隔離收治點工作。(仁濟醫院供圖)
一般人會忽略的空調出風口、廁所下水道,是最受關注的重點區域。“特別臟的地方,往往容易附積病毒。‘上天入地’,才能盡快準確厘清傳播鏈。”
在固廢垃圾中轉站最危險的垃圾傾斜口,張博與同事們把自己扣在安全扣上,探身到深處采樣。即便全副武裝,也擋不住洶涌而來的刺鼻味道。
一次性集中采樣,便是連續數小時作戰。最長的一回,采樣組兩天兩夜沒休息。“沖得上、打得贏,疾控人必須的!”他淡淡說道。
“今天最早的任務,是凌晨2點來的。”消毒組組長唐毅告訴東姐,“當時剛躺下。我們疾控中心的人,都是捧著手機睡覺。”
包括確診病例醫院就診過程感染控制和現場消毒評估,陽性病例住所、工作單位等生活軌跡現場消毒處置,隔離點全覆蓋督導評估……消毒組是在織一張防疫“天網”。
“奧密克戎傳染性這么強,陽性人員多,軌跡也多。”唐毅覺得已達到疲憊的峰值,“全天都特別累,躺下卻睡不著,反應慢半拍,經常忘了自己講了什么。”
跟病毒賽跑,無法休息。場所消毒任務,近來日均20多個,坐一下的時間都沒有。一次7000多平方米的辦公場所應急處置,從清晨5時持續做了近6個小時。霧化消毒劑滲進面罩、口罩,結束時,7個人個個涕淚交加。
消毒組的最大難題是“呼吸”。背著沉重的噴霧器,現場霧氣騰騰,這可不是桑拿間水霧,而是顆粒極微小的消毒劑,護目鏡一片模糊,濃郁的酒精味穿過防護面罩進入呼吸道,一般人無法忍耐。
唐毅的兒子上小學,春節后就沒看到父親休息過。妻子也是醫務工作者,同樣忙極了。小學停課,兒子只能靠鄰居幫忙照看。
“從2020年初起,我們一直處于高度緊張狀態。”唐毅說。讓市民生活如常的背后,是這樣一群默默付出的疾控人。
“這是哪家的樣本?”宋黎黎問。“瑞金醫院來的。”
半夜時分,宋黎黎穿好防護服,剛要進實驗室,又來了一批新的樣本試管,實驗室外轉運箱堆積如山。

上海黃浦疾控中心檢驗組工作現場(上海市黃浦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供圖)
“當天樣本必須做完,所有樣本不留夜。”宋黎黎停下腳步,緊趕著跟東姐聊幾句,“核酸結果沒出來,我們更急。早報一分鐘,就能早管控一分鐘,就少一分風險。”
檢驗組負責所有核酸檢測點報來的核酸異常復查、陽性初篩工作,責任巨大——不能錯判一個陰性,也不能放過一個陽性,還要爭分奪秒。
“實驗室機器不停的。凌晨兩三點來的樣本,我們直接做到天亮出結果。”她介紹。防護服穿脫復雜,為了“快”出結果,檢驗組便通過減少吃喝來控制上洗手間的次數。每一輪實驗至少4至6小時,每次換防護服,內衣都濕漉漉的。
“你看我們手上的濕疹,都是長時間在手套里悶出來的。”這位疾控檢驗組組長挺心疼同事們,“大家年紀不輕了,但檢驗工作技術性很強,別人做也不放心。”
在完全零污染的環境中,進行必須完全零失誤的精密操作。僅以“擴增”這個環節為例,提取好的核酸只需加入5微升進入試劑體系進行擴增。5微升是什么概念?一滴水的1/10,用極小的槍頭也只能看到頭上那一點點,而且還要求操作快、穩、準!
這兩年,疾控人完全沒有正常生活。疫情暴發那年,宋黎黎的兒子參加高考,她顧不上;這一回,大二的兒子回家上網課,只在她回家拿衣服時打了個照面。
“疫情不散,我們不退!”她語氣堅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