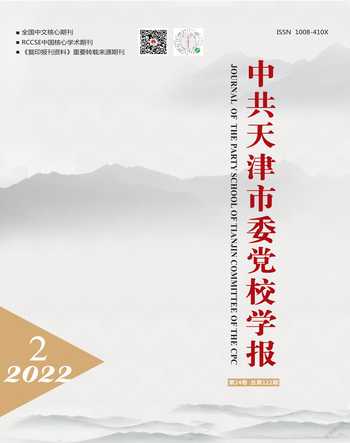數字賦能社區高質量醫養結合的場域矛盾與重整
盧時秀 張勁松
[摘 要]在健康中國與數字中國的雙重背景下,數字賦能已成為社區醫養結合高質量發展的重要策略。數字賦能社區高質量醫養結合的場域構型表現在人機互動生活化、供需匹配精細化、終端響應前置化和數據信息脫域化,場域矛盾顯現出醫養數據使用失范無序、醫養服務工作人員專業慣習固化、醫養服務行動異化等,場域的重整需明晰與整合政府、醫院、社區、企業、社會組織等多元主體的位置及相互關系,從掌握分析業務大數據的能力、數字設備和智能設備協同工作的能力、跨領域整合服務的能力等方面升級與再造醫養服務工作人員“專業性”慣習,在數字賦能進程中持守與遵循均等化共享、歸屬感提升、主體性持存等方面“人本化塑造”。
[關鍵詞]數字賦能;醫養結合;供需匹配;人機協同
中圖分類號:D03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410X(2022)02-0076-11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60周歲及以上人口26402萬人,占總人口比例的18.70%[1]。伴隨老齡化程度的不斷加深和老年人口數量的不斷提高,老年人的醫療服務需求和康養服務需求與日俱增。黨的十九大以來,黨和國家出臺一系列措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提出健康中國戰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指出,“推進老年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建設,推動醫療衛生服務延伸至社區、家庭。推動醫養結合,為老年人提供治療期住院、康復期護理、穩定期生活照料、安寧療護一體化的健康和養老服務,促進慢性病全程防治管理服務同居家、社區、機構養老緊密結合,推動居家老人長期照護服務發展”[2](P10)。202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以下簡稱《目標綱要》)進一步提出,“要構建居家社區機構相協調、醫養康養相結合的養老服務體系”[3](P139)。醫養結合成為黨和政府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打造高質量養老服務體系的重要方略。未來我國老年人采用居家養老服務的比例將達到90%[4]。可以說,絕大多數的醫養結合實踐是在老人所在社區中展開的。社區成為醫養結合養老高質量發展最重要實踐場域,打造高質量的社區醫養結合服務體系是我國高質量醫養結合得以實現的核心環節。與此同時,《關于深入推進醫養結合發展的若干意見》(國衛老齡發〔2019〕60號)明確提出,“要加強醫養結合信息化支撐,充分利用現有健康、養老等信息平臺,打造覆蓋家庭、社區和機構的智慧健康養老服務網絡,推動老年人的健康和養老信息共享、深度開發和合理利用”[5]。《目標綱要》明確提出,要加快數字化發展,建設數字中國。誠然,在健康中國與數字中國建設的雙重背景下,數字技術作為一種新的行動策略已悄然嵌入社區醫養結合的實踐中,并成為賦能醫養結合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路徑選擇。數字賦能必然會形塑出社區高質量醫養結合新的場域構型,同時,隨著實踐的展開會帶來一系列場域矛盾,需要予以重整。
一、數字賦能社區高質量醫養結合的場域構型
場域是由不同社會要素聯系而成的,不同社會要素在復雜的社會聯系中都占有特定的位置,或者說社會不同要素通過占有不同位置而在場域中存在和發揮作用[6](P347)。一個場域可以被定義為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客觀關系的一個網絡或一個構型[7](P345)。場域是一個充滿了秩序與結構的實踐空間,同時是一個動態性與生成性的實踐空間。場域內新要素的嵌入,必然帶來各要素之間位置與關系的變化,從而產生新的實踐空間,并在實踐空間中生成新的構型,此種構型是場域結構性與動態性的外化,更是場域與慣習互構過程的外化。數字技術是作用于社區醫養結合新的行動要素,數字賦能社區高質量醫養結合意味著數字技術作為一種新的要素嵌入社區醫養結合,勢必會在社區這一實踐空間動態性生成高質量醫養結合的場域構型。
(一)人機互動生活化
生活世界是人們生活其中的真實世界,是原初未被主題化的世界。只有回到生活世界的主體間進行自主性對話交流才是有意義的主體間性,而生活世界也只有在主體間進行對話交流才是真正的生活世界[8]。替爾斯提出了“以生活世界為本”的實踐邏輯[9]。該理論試圖通過理解服務對象的生活世界,即日常的生活方式和背后蘊含的意義,去建構社會服務的任務和意義。接近日常生活是社會服務提供的基本準則。以生活世界為本是社區高質量醫養結合重要的實踐邏輯,日常生活已成為社區醫養結合最主要的服務場景。在此種服務場景中,醫養結合服務人員(醫生、康養人員、社區工作者等)之間、服務人員與服務對象之間是一種平等、參與和資源合作的關系,即是一種充滿著意義與溝通理性的主體間性關系。在傳統醫養結合面向日常生活世界中,人機互動并未進入其中,或者只是進入人們特定領域和主題的觀念中。然而,在數字化背景下,人機互動不僅嵌入醫養結合服務人員的生活世界,也嵌入所有服務對象的生活世界,因為數字設備可以部分甚至完全替代人類的某些工作。
服務人員和服務對象實踐感中均有了人機互動的圖示,即人機互動慣習的身體化。以往的行動慣習是人與人之間互動,現在的各種日常服務中,人機互動已經身體化了。對于社區醫養結合而言,日常問診、健康數據監測、各種康養服務等日常服務,在多數情況下是通過人機互動完成的。
比如,醫生使用遠程醫療手段和病人溝通,雖然使用的還是傳統手段,但“面對面”變成了“人機互動”;再如,一個治療型機器人海豹替代人類成為激勵阿爾茲海默病老人,并為其提供精神安慰和日常監護的照護者。此種變化使得以往充滿著主體間性色彩的慣習圖示,包括理念、知識、技巧及其所表達出來的意義,在很多情況下通過數據及其終端設備予以傳遞。顯然,此種人機互動一旦嵌入社區醫養結合真實生活世界,其必然賦能社區醫養結合,生成并形塑出社區高質量醫養結合新的場域構型。
(二)供需匹配精細化
供需匹配的精細化是所有專業性服務供給高質量的重要表征。從價值理性的行動意義而言,精細化是專業服務的一種價值追求,而從工具理性的行動意義而言,其更成為一種實踐邏輯,彰顯了服務的專業性。對醫養結合而言,無論是醫療還是康養服務,精準匹配社區老人的需求本身就是其服務高質量的重要表現。比如,在英國、日本等國家現代福利框架的社區照顧模式中,無論是老人在社區中被照顧,還是由社區照顧[10](P173),服務供給的細分是最重要的工作原則之一。就具體執行而言,分類型與分層次對社區老人展開服務是一以貫之的行動慣習。此種行動慣習是對服務對象的身體、經濟、心理甚至家庭狀況進行全面評估,并在此基礎上對服務對象進行類型與層次的劃分,并提供細致且匹配的各種醫養服務。然而,此種行動慣習在數字時代到來前只能通過服務人員個人的工作經驗和有限的專業知識來實現,因而效率不高且主觀性強。在現代數字技術的賦能之下,對社區老人提供的醫養結合服務會比以往更加有望達到精細化,大數據存儲、暴力算法與智能化運算能幫助服務人員高效分析數據,細分服務對象的類型和層次及服務內容。比如,在社區醫養結合數字化服務平臺中,醫療人員根據各種動態數據信息將社區老人歸為健康、慢性病、半失能、失能、臨終等五種類別。同時,數字化服務平臺根據所在社區老人的歷史消費數據和家庭收入狀況研判其消費能力,服務器可以參照健康層次和用戶消費能力來分析服務對象信息,并與醫療、康養、家政服務等服務供給方進行精準匹配,按照不同類型與層次的精細排列組合綜合研判,為服務對象提供最為精準的醫養服務方案。在數字技術引領下,無論對于服務對象,還是對于服務人員而言,精準性的供需匹配凸顯與以往所不同的新屬性,這些屬性包括高效、適切、普惠等,是社區醫養結合高質量的重要表征。就此而言,供需匹配的精細化成為數字賦能社區高質量醫養結合的重要場域構型。
(三)終端響應前置化
服務終端的概念源自于互聯網領域[11],意指服務器和客戶端的程序鏈接的接觸端口。在日常生活的實踐場域中,服務終端可被視為供給主體與服務對象需求主體的接觸端口。就傳統專業工作而言,其本質是被動反應性的,通常由服務對象先提出需求,然后才是專業工作人員作出響應。也就是說,當服務對象向供給主體提出需求的時候,問題可能已經發生了。而在有些應急事情事態的處置上,等到服務對象發出求助時,不可挽回的后果已經發生了。因此,傳統的專業性工作,包括專業性服務工作,服務終端的響應往往是被動性、補救性和追逐性的。在以往社區醫養結合的實踐場域中,服務終端的響應模式也是如此。比如,社區醫生只有老人生病了才了解到老人的病情,此種醫療服務的提供只能是被動、補救和追逐性的。此種響應模式在很多突發性疾病尤其危及生命的突發性疾病發生時往往是無濟于事的。顯然,此種響應模式形成了一個服務終端的邏輯悖論,影響了社區醫養結合的服務質量。在社區醫養結合服務中,“醫療是工具和手段,養護是根本”[12]。
而數字賦能社區醫養結合后,此種邏輯悖論可能通過數字技術被破解,各種服務終端被前置,變得具有主動性、預防性和前瞻性。在醫療服務提供過程中,遠程監測系統能追蹤居家老人的關鍵體征,并且在其出現問題之前迅速作出響應。這樣就提高了社區老人疾病的風險管理。例如,在深圳某社區,醫養結合居家養老服務平臺以居家老人的健康數據為基礎,能準確預測且自動預警疾病風險,使存在疾病發作隱患的居家老人能得到及時治療。以糖尿病患者為例,服務平臺根據居家老人所佩戴的動態血糖監測儀等設備獲得動態數據,并結合電子健康檔案表的記錄數據,檢測空腹血糖數值等重要指標集,計算出載脂蛋白A1、高密度脂蛋白等重要衡量要素的告警指標,將這些指標與實際數值進行比對,按照對比結果,對居家老人健康程度進行評級,并以此為依據,對居家老人進行疾病風險預測。當動態數據超過告警指標時,服務平臺會根據社區中老人的患病嚴重程度,對居家老人進行緊急救治。數字技術改變了以往居家老人社區醫療服務的響應模式,使醫療服務呈現主動、預防和前瞻性的屬性。此種響應終端的前置化是數字賦能社區高質量醫養結合的重要場域構型。
(四)數據信息脫域化
脫域是時間和空間的分離和它們在形式上的重新組合[13](P14),是社會系統從限定的時空連接中脫離出來的現象,跨越既定的時空組織,伸延到廣闊時空中的結果。脫域的實質是資源和信息跨越原有的時間和地理界限而存在,是現代性的后果。脫域對社會系統并非是解構性的,而是建構性的。服務信息是服務過程的烙印,在以往的社區醫養結合的實踐場域中,服務信息無法被高度數字化,因此,服務信息存儲和流動的時空邊界都是有限的。比如,醫療服務的信息僅限于在醫療系統中存儲和流動,而無法在家政、康養、配餐及日常生活方方面面進行處理和流動,數據信息在各自信息域中未能實現脫域或者脫域不足,往往造成醫療、康養和家政服務及其他日常生活中的數據信息無法充分結合,這影響了醫養結合的高質量發展。而在數字化背景下,社區老人和服務人員在日常生活和服務行動中留下的所有痕跡可能被轉化成數字信息,各種數據信息通過統一數字平臺和環境在不同的虛擬域中脫域“奔跑”。與此同時,這些“數據烙印”會通過大數據、云計算等在更大的場域中被采集、挖掘、存儲和處理,這促進了數據信息脫域的進一步發生與延展。比如,在上海的某些智慧社區,正是由于數據信息的脫域,社區工作人員主要通過家中水表的異動實現對社區高齡老人居家安全的監控預警,若某天早上該老人家中水表變動未超過0.01噸,社區服務平臺自動預警系統就會發出提示,社區服務人員(社區網格員、社會工作者等)就會第一時間與老人聯系或上門查看;在深圳的一些社區,社區服務人員借助智慧門禁系統對社區老人居家安全實現類似的預警性服務,智能門禁系統主要通過獲取處理社區獨居老人和空巢老人到社區活動中心的刷卡次數和進出單元門禁的次數來提示社區工作人員對服務人員的身心健康和居家安全狀況作出預警性研判。上述智能研判得以發生,其背后的技術支撐是數字技術將各類數據信息充分脫域化。在數字化的賦能中,社區高質量醫養結合必然置于數據信息脫域化的場域構型中。
二、數字賦能社區高質量醫養結合的場域矛盾
在社會空間里,場域與慣習之間、位置與資源之間及競爭與沖突之間的張力,使得場域成為一個變動不居的“游戲場”[14](P73)。場域是實踐展開的場所,也可以說是實踐展開的矛盾形式[15](P80)。動態變化的場域不僅會表現出各種新構型,也必然會表現出實踐展開后的矛盾形式。這些矛盾形式是特定實踐場域中各種張力的外化,是實踐展開的必然后果,是伴隨著實踐展開而生成的。數字賦能社區高質量醫養結合實踐的展開必然動態化生成新的場域構型,同時必然產生新的場域矛盾,這些場域矛盾制約著數字賦能高質量醫養結合的實踐進程與效能釋放。在數字賦能過程中,社區醫養結合實踐場域中的各種要素位置會被調整,各種規則需要被重塑,各個行動者的慣習也需要重置,必然帶來社區醫養結合在資源整合、行動目標、實踐慣習等方面的張力,并外化成為實踐的場域矛盾形式。
(一)醫養數據整合失范無序
“現代社會中社會世界是由大量具有相對自主性的社會小世界構成的,這些社會小世界事實上就是一個一個的場域,有著自身特有的邏輯和必然性,并且不可化約其他場域運作的邏輯”[16](P390)。數字技術的嵌入,正是將這些原本具有自身邏輯的不同場域進行整合,形成新的實踐場域。對于一個社區醫養結合數字服務平臺而言,其工作人員至少包含平臺服務人員、家政服務人員、營養配餐供應商、醫療人員、醫療設備供應商、監管人員、平臺維護人員等[17]。而其背后涉及的行政主體包括政府、醫院、企業、生活組織、社區等。這些行動主體需要交互整合于同一數字服務平臺,形成新的場域。然而,這些行動主體在用戶共享、數據管理及業務邏輯等方面的行動慣習趨異,因而當交互形成一個新的實踐場域時,必然無法明晰和確定自己的行動邊界,也無法規范與限定自身的權責。因此,在醫養數據整合上就出現了“數據壁壘”和“數據濫用”的狀況[18]。“數據壁壘”背后的實踐慣習是規制和保守。一方面,基于主觀因素,有些行動主體出于自身利益考慮而“不愿共享”,有些行動主體行動權責未被界定而“不敢共享”。例如,在數據采集方面,當地三甲級醫院由于無法明確權責而不敢共享社區老人的就醫數據信息,而一些大型外賣和電商平臺出于自身利益而不愿共享用戶信息。另一方面,基于客觀因素,由于不同時期、不同平臺上研發出來的信息系統在信息編碼規則、數據庫系統、網絡協議、語義表示、運行環境等方面的執行標準不統一,導致在共享各信息系統的數據時難以調處和使用而“不能共享”,最終導致有些公共數據無法互聯互通、整合利用[19]。而“數據濫用”背后的實踐慣習是失范和無序,即數據使用缺乏監管,數據被濫用。一些機構利用業務需要在獲取用戶信息后,往往模糊用戶信息的歸屬權,這些私人數據給誰用、用來做什么及使用后如何處理等,最終都由數據的采集方決定和控制,而無權責邊界,這必然造成對服務對象的隱私權、平等權、知情權和自我決定權等權利的侵犯。例如,社區服務人員對社區老人家里進行消防安全隱患檢查后,將相關數據信息錄入社區服務數據平臺,由于數據缺乏保護,數據迅速被相關商業App捕獲,老人手機迅速收到了消防設備銷售的智能推薦。無論是“數據壁壘”還是“數據濫用”,均是多行動主體權責不清造成的“醫養”數據整合的失范無序。顯然,這勢必成為場域矛盾影響數字賦能社區醫養結合的高質量發展。
(二)醫養服務工作人員專業慣習固化
在考察場域的過程中要特別注意研究場域的歷史生成過程[20](P110-116)。高質量是新時代我國醫養結合事業發展的未來狀態,是醫養結合這一實踐場域的應然狀態。對于這一場域狀態的生成過程而言,是醫養結合持續深化的實然演化過程。
人機互動生活化、供需匹配精細化、終端響應前置化、數據信息脫域化是數字賦能社區高質量醫養結合的一種應然結構狀態。此種應然結構狀態在實然層面的生成演化過程便是數字技術助推社區醫養結合持續深化的過程。第一,數據深度聚合的過程,即社區老人的醫療、康養和日常生活服務等多方面數據信息高度聚合形成統一大數據服務器的過程;第二,人機深度協同的過程,即提供醫養服務的工作人員與各種數據設備、智能設備合作成為常態化工作形態的過程;第三,服務深度整合的過程,即醫療、康養、日常生活、文娛、心理等各項服務深度整合,以一種整體性方案提供給服務人群的過程。然而,這三方面的演化過程與從事醫養服務各類專業人員的日常工作產生了張力。此種張力事實上是場域矛盾的表現形式,是醫養工作人員專業性慣習歷史性與生成性斷裂的矛盾。慣習本身是歷史的產物,是一種人們后天所獲得的各種生成性圖式的系統,是一種“外在性的內在化”。個體行動者只有通過慣習的作用,才能產生各種“合乎理性”的常識性行為。所以,慣習是“所有選擇所依據的不被選擇的原則”[21](P167-168)。慣習的結構性使其具有歷史性。同時,慣習是一種生成性的結構,它塑造、組織實踐、生產著歷史。慣習的創造性與組織性又使其具有生成性。具體而言,在數字賦能的進程中,醫養結合持續演化出新的場域構型,新的場域構型必然生成新的專業慣習。從事醫養結合服務工作人員的專業慣習大多延續著數字賦能前場域的專業慣習。這在具體實踐層面顯現醫養服務工作人員固有的專業慣習無法適應醫養結合持續深化的矛盾。數字賦能之前,工作人員一直沿用著這些固有的專業慣習。這些固有的專業慣習表現為獨立性、專一性和主觀性等。所謂獨立性即個人獨立完成自身專業領域的工作,比如,醫生獨立
而不是與其他領域工作人員共同判斷老人的病情,康養人員獨立開展老人的康養工作等;所謂專一性即工作人員只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展開實踐,比如,醫生只負責老人的診療,社會工作者負責老人的心理疏導和文娛活動;所謂主觀性即通過自身主觀經驗的判斷開展專業性工作,
比如,醫生只能根據自身所掌握的專業知識和現有的臨床經驗,對老人進行診斷,而并非根據客觀海量的大數據及智能設備的輔助進行診斷。
顯然,工作人員固化的專業慣習與社區醫養結合持續深化的演進過程存在張力,這勢必成為數字賦能社區高質量醫養結合的場域矛盾之一。
(三)醫養服務行動異化
數字技術的賦能必然帶來理性主義的延展和生長。這意味著現行科技運用結構主義知識不斷實現“量化個體”的目標,即將個體視為不同行動算法、語言算法、基因算法的集合,通過充分吸納現有的結構主義知識而不斷認識個體,并試圖幫助個體作出選擇,使得社會更加具有效率及秩序,這種社會形態便是尤瓦爾所稱的“數據主義社會”[22](P295-296)。數據主義社會帶來的是龐大數據與“精準”算法[23],替代了人的認知能力進行決策,數字算法的決策過程對于廣大個體而言更多的是在“科技黑箱”中運行,如果信賴其決策結果就意味著賦予“黑箱決策”相應的程序正義,也就意味著人類事務能夠為科技所承擔。數字化對人類社會的賦能,其初衷是幫助人類自身從“有限理性”走向“全面理性”,而“全面理性主義”必然忽視了人的情感與價值觀念,勢必造成人自身行動主體性的消減,引起行動異化。在社區層面推行醫養結合的高質量發展,其初衷是為了讓老人能夠在原居住社區中既能享受到具有高度“現代性”的高質量醫養結合服務,又能享有“原初共同體”高質量的生活體驗。數字化的賦能,事實上就是通過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和萬物互聯等“全面理性主義”工具與手段更好地實現這一初衷。然而,“全面理性主義”的醫養結合服務行動在很多情況下必然會忽視人的需要、情感、價值觀等人類主體性要素,顯現出行動異化的場域矛盾。這些行動異化矛盾包括真實互動體驗喪失、日常生活的泛媒化、社交網絡的萎縮等。〖JP+1〗具體而言,由于數字化賦能,大多情況下社區老人只需要配備合適的診斷設備、監控設備,甚至不需要與人互動就能自己了解其健康狀況,獲取一定診療建議。同樣,醫生不需要與老人通過面對面互動,只需要通過數字設備及所傳輸的后臺數據來了解服務對象的狀況,這無形中減少了老人與醫生、其他社區康養、服務人員面對面的互動頻次與時間。
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不僅傳遞的是信息,還是情感的聯絡和信任。社區老人不僅需要醫療和康養服務本身,更需要醫療和康養服務過程中所帶來的精神慰藉、情緒疏導等真實體驗,這些真實體驗只有面對面互動才能帶來。面對面互動的減少必然帶來互動真實體驗的消減;數字化的嵌入很容易導致社區老人陷入信息過載、信息迷航等窘境,使老人日常生活落入無盡的數據黑洞,造成日常生活的泛媒化;數字化在老人日常生活中的嵌入會使老人與現實社區中的鄰里、朋友、社區人員的互動減少,造成老人在真實社區中社交網絡的萎縮。顯然,這些都違背了社區醫養結合高質量發展的初衷。
三、數字賦能社區高質量醫養結合的場域重整
數字賦能社區高質量醫養結合的場域矛盾是在實踐展開過程中生成的,這些場域矛盾的顯現影響了數字賦能的實踐進程和效能釋放。
由于場域的動態性和開放性,場域在實踐中是不斷進行調整和重塑的,因此,場域構型的建構、場域矛盾的破解需要不斷對場域實踐空間各個要素進行重整,這些可被調整的要素包括位置、關系、權力結構、慣習、實踐邏輯等。基于此,在數字賦能社區高質量醫養結合場域中,場域重整至少包括各個行動主體位置關系的明晰與整合、醫養服務工作人員實踐慣習的升級與再造、實踐邏輯的持守與遵循等方面。
(一)行動主體“一主多元”位置關系的明晰與整合
與場域相關的概念體系中,與其相對應的概念是位置,在分析行動主體時,必須分析行動主體與場域相對的場域位置,并勾畫出行動者所占據的位置之間的客觀關系結構。事實上,在場域的概念框架中分析行動主體,位置與關系是兩個基本維度。在數字賦能社區醫養結合的實踐場域中,多元行動主體的參與是其基本屬性,要明晰多元行動主體的權責邊界,使醫養結合的數據使用更加規范與有序,澄清多元行動主體在場域中的位置及關系顯得尤為重要。在社區高質量醫養結合的場域中,參與的行動主體包括政府、醫院、社區、企業、社會組織等。每個行動主體必然在場域中占據一定的位置,只有明晰每個行動主體的位置及其相互關系,才能促使場域形成一個動態的開放且規范有序的系統。數字賦能社區高質量醫養結合就是以社區作為空間基礎,以數字技術作為手段和工具,實現多元行動主體資源整合的最優化。然而,由數字化生成的新場域中多個行動主體對資源的爭奪可能導致位置及相互關系的失范與無序,從而產生場域矛盾。因此,明晰與整合政府、醫院、社區、企業、社會組織等多元主體的位置及相互關系顯得尤為重要。
權力場域是所有場域的“元場域”[24](P631)。在諸多行動主體中,政府主體顯然是在數字賦能社區高質量醫養結合的實踐場域中最具權力屬性的行動主體。在明晰與整合多元主體位置及關系時,政府主體應在推進社區醫養結合數字化過程中占據主導位置,
在數字化轉型中應表現出的兩個核心屬性是“智治”和“整體”[25](P82)。就“智治”而言,在數字時代,智能化硬件配備是智能化未來社區的基礎。智能化硬件配備意味著政府主體需要為社區醫養結合的數字賦能發揮主導性作用。政府主體需要研發與提供可接入智慧城市、可優化社區內外部醫療和養老資源整合的數字設備和平臺。比如,在智慧社區平臺中接入智慧醫療平臺,可以實現社區外部醫療資源的統籌配備,為大型醫院的醫療資源的輻射帶動作用提供接入渠道。這一系統的接入既確保緊急醫療服務等救護服務及時可達,又能確保區域內綜合性醫院、專科醫院、社區醫院、家庭醫生在醫療數據上的共享,還能使社區老人在家中能夠在線上輕松“問診”。再如,讓商業配餐、購物、家政平臺提供端口接入智慧社區系統,確保各種商業性質的運營平臺在政府主體的監控下為社區老人提供服務。就“整體”而言,強調政府主體應以民眾滿意為導向,通過實現跨地區、跨層級治理主體的有效協調,避免將行政成本轉嫁給民眾和企業。就數字賦能社區醫養結合高質量發展而言,政府主體在配備統一的數據平臺和設備的基礎上,還需要在信息編碼規則、數據庫系統、網絡協議、語義表示、運行環境等方面為社區醫養結合的多個行動主體行動提供整體性的統一標準,借此確立各個行動主體的權責邊界,以規范有序地使用數據資源。
在“智治”和“整體”的行動框架下,作為在數字賦能社區高質量醫養結合實踐場域中占據主導位置的行動主體——政府至少扮演平臺搭建者、規則制定者、統籌協調者、監督管控者等重要角色。而其他多元行動主體在這一框架下也能確立自己在場域中的位置及其相互關系,并明晰各自扮演的角色。
醫院主體應扮演積極參與者的角色,利用數字技術積極參與到社區層面醫養結合的實踐中,為社區老人提供高質量的醫療服務;企業、社會組織等應扮演協同合作者的角色,與政府協同合作為社區老人提供高質量的養老服務,包括商業性服務和公益性服務等;
社區應扮演民意反饋者的角色,積極反饋數字化平臺運行過程中社區老人的各種訴求與建議。
顯然,在數字賦能社區高質量醫養結合過程中,只有各個行動主體在場域中明確自己的位置及相互關系結構,才能明晰各自的角色定位,從而確立自身的權責邊界。因此,多元行動主體在場域中“一主多元”位置關系的確立與整合對其場域重整是十分必要的。
(二)醫養服務工作人員“專業性”慣習的升級與再造
“場域與慣習之間的關聯有兩種作用方式,一種是制約關系,場域形塑著慣習,慣習成了某個場域固有的必然屬性體現在身體上的產物;另一種是認知建構的關系,有助于把場域建構成一個充滿意義的世界。慣習作為知覺、評價和行動的分類圖式構成的系統,它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同時可以置換”[26](P171-172)。在某種意義上,慣習是那些居于同一位置人的“集體無意識”,提供了認知的和情感的向導,使個體能夠以共同的方式描繪這個世界,以一種特有的態度進行分類、選擇、評價和行動[27](P472)。慣習既是被結構化的,又是可以促結構化的。從場域與慣習的雙重關系中發現,數字賦能社區高質量醫養結合的實踐場域必然使工作人員形塑出新的專業慣習,同時,形塑的過程是建構的過程。只有建構出工作人員新的專業慣習才能適應數字賦能下社區醫養結合持續深化的演進過程,此種新的專業慣習需體現出“專業性”的升級與再造。
專業性是現代社會對知識進行制度化管理的主要方式[28]。在社區這一場域中從事醫養結合的專業性工作人員包括醫生、康養人員、家政服務人員、社會工作者等,他們固有的專業慣習具有獨立性、專一性和主觀性的特點已無法適應數字賦能社區醫養結合過程中數據深度聚合、人機深度協同和服務深度整合的表現形式。在數字賦能的進程中,工作人員需要通過快速學習、自我發展對自身專業慣習的“專業性”進行升級與再造。第一,掌握分析業務大數據的能力。從事社區醫養結合服務的各類專業工作人員應該掌握分析業務有關的大量新數據。醫生要有能力調用自己接觸過的或過往的海量數據集,分析并預測其所服務社區老人未來可能出現的疾病風險,而這樣調用分析數據的能力是以往醫生專業性慣習中所不具備的。第二,與數字設備、智能設備協同工作的能力。在未來的工作中,所有專業工作的環節都會加入與機器合作的元素,并以各種形式變得日常化。工作人員要利用數字設備檢查清單、輸入標準形式的資料、應答各種各樣的智能設備等。
醫養服務人員原本以傳統方式(獨立面對服務對象)開展的工作,如今需通過與數字設備、智能設備的協同來實現。在社區失能與半失能老人的日常照護中,康養人員原來的工作重點只是對老人進行照護,但在數字化的工作環境下,康養人員需要實時與數字設備深度協同,并及時將老人的身體數據輸入后臺數據庫。第三,跨領域整合服務的能力。以往受限于專業工作的傳統結構和邊界,同時受限于專業工作人員固有的專業慣習,服務對象的問題不得不被分割成獨立的任務進行處理。如今受益于數字技術搭建的統一平臺,工作人員可采取整合的方式來探討和制定社區各類老人的整體性醫養服務方案。這就意味著專業服務人員需要跨界合作,展開整合性的服務。比如,在腦卒中老人的社區康復中,社區日間康養中心的社會工作者就需要了解腦卒中康復的相關知識,將老人每天在照護中心中運動康復的相關數據輸入后臺數據庫,并與醫生共同探討老人的康復狀況。
在數字賦能社區醫養結合高質量發展的實踐過程中,工作人員需要掌握各種新的能力,這些新能力的掌握過程事實上是工作人員打破固有專業慣習,對“專業性”進行升級與再造的過程。若置于慣習的概念框架中,該過程是各類工作人員打破業已身體化的獨立性、專一性和主觀性的實踐圖式,在實踐感中建構出分析大數據、人機協同和跨界合作等實踐圖式的過程。顯然,這一過程對于數字賦能社區高質量醫養結合的場域重整顯得尤為重要。
(三)數字賦能進程中“人本化塑造”的持守與遵循
數字賦能社區高質量醫養結合的初衷是使老人在社區中能夠借助數字技術更高質量地享有醫養結合服務。數字賦能旨在滿足老人對“醫”和“養”更高質量的需要,而數字賦能所帶來的行動異化使老人原初的生活世界被“殖民化”,其自身越來越難以控制而成為數字技術的“俘虜”。“動態變化的場域關系所呈現的各種原則,實質也就是實踐活動的邏輯”[29](P156)。因此,在數字賦能的進程中,“人本化塑造”原則實質上應成為實踐持守與遵循的基本邏輯。
其一,均等化共享。所謂均等化共享,就是在社區中的所有老年人而不是部分老年人,更不是個別老年人能享有數字賦能醫養結合帶來的“高質量”。均等化至少包含兩個范疇的意涵。一是老年人群體內部的均等化,即在數字賦能的進程中,要盡可能考慮到社區不同年齡、不同文化程度、不同生活能力、不同收入水平的共享。二是老年群體與其他群體的均等化,即老年人能夠和其他年齡群體均等化共享。在數字賦能的進程中,要更多地考慮社區老人在接入、使用等層面可能出現的“數字鴻溝”,避免老年人被數字“邊緣化”[30]。比如,在老年數字化平臺的設計時,年輕的設計師們往往沒有充分調研評估老年人的支付習慣,而是按照自身“簡潔快速”的支付習慣,設計了“默認無提示的免密支付”功能。由于這一功能違背了老人謹慎、可視的支付習慣,使得老人擔驚受怕,不敢在該數字平臺進行在線支付。再如,很多醫養服務數字設備配備后,社區中的社會工作者應針對文化程度、認知能力和信息素養較低的老人開展數字設備使用的相關課程培訓,并進行一對一指導,避免這些老人面對復雜的操作流程時無所適從。
其二,歸屬感提升。老人社區歸屬感提升本身就是在社區層面醫養結合“人本化”屬性的重要體現,更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表征。
數字賦能的重要表現之一就是為社區老人提升社區歸屬感。
數字技術的使用應拓寬社區參與社會生活、人際交往的渠道,促進社區老人社會資本的積累和增量,享有“共同體”化的生活體驗。但是,數字設備與技術在使用過程中,往往更多的被視為醫養服務供給的使用工具,忽視了其作為社交平臺甚至“人文關懷”媒介的潛在功能。若此以往,社區老人可能會被數字技術與設備切割成一個個“原子化”的個體。數字化終究只是手段與工具,而現實生活體驗才是歸宿和初衷。數字賦能社區醫養結合絕不是使老人“原子化”地存在,而是使社區老人不僅能通過數字化平臺,高效獲取次級支持系統(如醫生、康養人員、外賣小哥等)的工具性支持,而且能夠通過數字賦能增加其初級群體(如家人、鄰里、朋友等)的情感性支持,使其更好地參與到真實的社區生活中,提升其社區歸屬感。比如,在社區醫養結合數字化平臺設計的過程中,設計師在功能模塊的設計上不能一味考慮平臺的服務供給功能,還要重點考慮平臺的社交和信息獲取功能。
其三,主體性持存。在人本主義思想中,主體性持存是其核心要義,任何數字技術的發展都不能侵犯人的主體性。主體性持存意指在數字賦能社區高質量醫養結合進程中,社區老人并不是被動地視為數字技術服務的客體而存在,應被視為能動的積極主體而存在。在養老服務供給中,老年人在使用互聯網、智能設備等方面的弱勢地位,使其面臨需求表達被邊緣化的風險[31]。世界衛生組織提出的“積極老齡化”概念[32],強調人們在增齡的過程中,仍然在生活的各個方面享有機會平等的權利,倡導創造條件讓老年人回歸社會,參與經濟、社會、文化和公益等事務。這意味著參與是老年人在數字浪潮中主體性持存的重要向度。在數字賦能社區醫養結合高質量發展的進程中,數字軟件、設備和環境的設計者并非是被動地接受服務客體,而應該將老人看成是參與設計全過程的主體,將數字技術真正為老人所需要和掌控。同時,許多商業主體、醫療主體在設計和運營數字平臺時,如果考慮的只是如何有效率地服務老人,增加經濟收益,而不是有“溫度”地服務老人,提升人文關懷,
這樣容易形成老人認知層面的“數字鴻溝”[33],造成“信息繭房”[34],導致老人的主體性被消弭和擠壓。因此,在數字賦能社區高質量醫養結合的進程中,社區中老人主體性的持存是其“人本化塑造”持守與遵循需考慮的重要向度之一。
四、結 語
2022年伊始,國務院相繼印發《“十四五”城鄉社區服務體系建設規劃》和《“十四五”國家老齡事業發展和養老服務體系規劃》。
前者明確提出,要加快社區服務數字化建設,開發社區養老等網上服務項目應用,集約建設智慧社區信息系統,開發智慧社區移動應用服務。后者明確提出,在“十四五”時期,提升醫養結合服務質量,健全醫養結合標準規范體系,推動醫療衛生、養老服務數據共享,完善醫養結合信息管理系統。推進“互聯網+醫療健康”、“互聯網+護理服務”、“互聯網+康復服務”,發展面向居家、社區和機構的智慧醫養結合服務。推廣智慧健康養老產品應用,推動智慧健康養老規范化、標準化發展,推進智能化服務適應老年人需求,老年人在運用智能技術方面遇到的困難能得到有效解決,使廣大老年人更好地適應并融入智慧社會。數字化社區建設和高質量養老服務體系建設的步伐加速推進。數字賦能是社區醫養結合邁向高質量發展的發展方向和重要路徑。在今后一段較長的時間內,數字賦能社區醫養結合實踐將在全國不同區域內有序推進,而“高質量”必然成為所有實踐在實然層面的的目標歸屬和應然層面的價值遵循。
本研究對數字賦能社區高質量醫養結合的議題的探討是以經驗事實為基礎,遵循應然狀態、釋然矛盾和破解之道的邏輯予以展開。這樣的探討力求為后續研究議題的深入、研究區域的細化提供些許參考借鑒。同時,借用布迪厄實踐理論中“場域”及相關概念作為研究的分析框架。這一分析框架具有中層理論的屬性,與本研究所要聚焦的經驗事實黏合度較高。一是借助“場域”這一概念可將“社區醫養結合”整合為統一的概念予以分析。由于“場域”這一概念兼具空間性與實踐性的屬性,可將“社區”這一空間范疇概念和“醫養結合”這一實踐范疇概念,用“實踐空間”概念屬性予以整合,這就使得“社區醫養結合”可作為統一的社會事實予以觀察解釋。二是由于“場域”概念的動態性與開放性,使其可適用于解釋新要素嵌入后實踐空間內部的結構變化與過程變遷。數字技術是“社區醫養結合”這一實踐空間中嵌入的新要素,借助場域構型、場域矛盾的概念,可從經驗層面全面觀察和概括出數字技術給社區醫養結合高質量發展帶來的新樣態,同時審視反思數字化進程與社區醫養結合高質量發展存在的張力。三是“場域”概念具有體系性與操作性,這就使在剖析數字賦能社區高質量醫養結合的服務主體、工作人員、供給行動、服務對象時,可有效借助位置、關系、慣習、實踐邏輯等相關概念對經驗事實予以澄清與解釋。
數字賦能社區醫養結合的研究將成為學界關注的熱點,后續研究必然圍繞“高質量”這一核心要義,并伴隨實踐不斷推進而深化。首先,研究議題的深入。隨著數字賦能社區高質量醫養結合實踐展開,實踐中必然會呈現各種問題,這些問題勢必成為后續研究關注的重點。比如,數字賦能如何滿足社區居家老人整合性、專業性、多樣性的醫療和康養需求;數字賦能如何做到兜底性和普惠性;數字技術如何能夠更好滿足老年人急難愁盼的核心訴求;實踐過程如何使得此項實踐的公共性和商業性有效協同;數字技術如何幫助做好鰥寡孤獨、困難高齡、失能失智等特殊老年群體的服務保障等,對這些議題的研究均具有實踐性的特點。后續研究必然需要對具體的實踐“抽絲剝繭”,對該領域的各種實踐議題展開更加深入的研究。其次,研究區域的細化。由于我國各地自然地理條件、城鄉發展融合、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制度環境設置、原有實踐基礎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數字賦能社區高質量醫養結合的實踐進程必然有所不同,所采取的實踐模式也必然有所差異。后續研究可著眼于對國內不同地域實踐模式的細化研究。比如,“長三角”“珠三角”地區,這些區域內各地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高,原有實踐基礎好,老年人對醫養服務需求層次較高。再如,貴州省數字化建設居全國前列,但經濟社會發展相對滯后,城鄉融合水平有待提升,這些區域內的實踐模式必然呈現其獨有的特點。這些都是后續研究需予以觀照之處。再次,研究范式的多元。隨著此項實踐地不斷推進,實踐在宏觀制度設置、中觀執行落地和微觀日常行動中均會呈現出不同的運行規律與實踐特點。比如,在制度設置上、各地“醫”和“養”的制度鴻溝猶存,現在又加入新的制度變量——“數字化建設”,這些要素如何在宏觀制度層面予以協同整合;中觀層面,在社區場域內如何在數字場景中,既能實現高質量醫養結合服務的兜底性和普惠性,又能使市場化運作滿足社區居家老人多層次多樣化的醫養、康養服務需求;在微觀層面的日常行動中,日常服務行動者們的專業能力,尤其是素質素養如何提升,各種醫養、康養、照護、家政服務如何通過數字平臺“完美銜接”,
如何以“整合打包”的方式計價收費等。這些問題均使得后續研究將會從制度主義、結構主義、個體主義等不同研究范式展開敘事,予以回應。
參考文獻:
[1]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情況[DB/OL].[2021-05-11].http:∥www.stats.gov.cn/xxgk/sjfb/zxfb2020/202105/t20210511_1817195.html.
[2]中共中央國務院.“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3]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4]魏 宇.“十四五”時期我國養老服務模式的創新戰略探討[J].西南金融,2021,(5).
[5]關于深入推進醫養結合發展的若干意見(國衛老齡發[2019]60號)[DB/OL].[2019-10-26].http:∥www.gov.cn/xinwen/2019-10/26/content_5445271.htm.
[6]劉少杰.國外社會學理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7]黎 民,張小山.西方社會學理論[M].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05.
[8]茹 婧.空間、治理與生活世界——一個理解社區轉型的分析框架[J].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19,(2).
[9]張 威.生活世界為本的社會工作理論思想——兼論構建社會工作基礎理論的戰略意義[J].社會工作,2017,(4).
[10]夏建中.社區工作(第三版)[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
[11]張 寧,劉正捷.基于用戶認知能力的自助服務終端界面交互設計方法[J].計算機應用研究,2013,(8).
[12]倪語初,王長青,陳 娜.老齡化背景下我國醫養結合機構養老模式研究[J].醫學與社會,2016,(5).
[13][英]吉登斯.現代性的后果[M].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
[14]劉少杰.當代國外社會學理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15][法]布迪厄.實踐感[M].南京:譯林出版社,2012.
[16]侯均生.西方社會學理論教程(第四版)[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7.
[17]侯玉梅,傅 勘,高秋燁,等.醫養結合型智慧居家養老服務平臺設計[J].包裝工程,2020,(6).
[18]陳少敏,陳愛民,梁麗萍.醫療大數據共享的制約因素及治理研究[J].衛生經濟研究,2021,(9).
[19]安 娜,林建成.人工智能在網絡輿情治理中的現實問題與應對策略[J].思想理論教育,2020,(12).
[20]Kelly M.The Encyclopedia of Aesthetic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21]楊善華,謝立中.西方社會學理論(下卷)[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22][以]尤瓦爾·赫拉利.未來簡史:從智人到智神[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23]閆坤如.數據主義的哲學反思[J].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21,(4).
[24][法]布爾迪厄.國家精英:名牌大學與群體精神[M].北京:商務印書館,2020.
[25]浙江大學數字長三角戰略研究小組.數字長三角戰略2020:數字治理[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20.
[26][法]布迪厄,等.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
[27][美]特 納.社會學理論的結構[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6.
[28]徐選國,孫潔開,田雪珍.社會工作的核心屬性之爭及其路徑調適[J].學習與實踐,2020,(11).
[29]劉少杰.后現代西方社會學理論(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30]劉海明,馬曉晴.斷裂與彌合:“銀發數字鴻溝”與人本主義倫理建構[J].新聞愛好者,2021,(3).
[31]魯迎春,唐亞林.數字治理時代養老服務供給的互動服務模式:特質、問題及其優化之策[J].南京社會科學,2020,(7).
[32]李建攀.西方老齡化理念的嬗變邏輯與教育因應[J].成人教育,2022,(1).
[33]楊菊華,劉軼鋒.數字時代的長壽紅利:老年人數字生活中的可行能力與內生動力[J].行政管理改革,2022,(1).
[34]李曉云,王 鋒.“信息繭房”概念外延的合理性考察[J].青年記者,2021,(24).
責任編輯:王 篆
Field Contradiction and Reorganization of High-Quality Medical and Nursing Care in the Digital Empowering Community
Lu Shixiu,Zhang Jinsong
Abstract:Under the dual background of healthy China and digital China,digital empowermen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trategy for combin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medical care and nursing care. The field configuration of digital empowering community combining the high-quality medical care and nursing care is expressed in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life,supply and demand matching refinement,terminal response front and digital data disembedding. Field contradiction shows that anomie and disorder in using medical and nursing data,consolidation in staff professional habitus of medical and nursing service,alienation in action of medical and nursing service,etc. Field reorganization needs to clear and integrate location and relationship of government,hospitals,community,enterprises,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other multiple subjects,requires to upgrade and reconstruct professional habitus on medical and nursing service of staff from the ability to analyzing business big data,working in coordination with digital equipment and intelligent equipment,integrating cross-field service,and tries to keep and follow “humanistic shaping” 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 empowerment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of sharing equalization,promoting sense of belonging and holding subjectivity.
Key words:digital empowerment,the combination of medical care and nursing care,supply and demand matching,coordination of human-computer
收稿日期:2022-01-16
作者簡介:盧時秀(1984-),女,湖北工程學院政治與法律學院副教授,博士,湖北孝感 432000;張勁松(1967-),男,南京審計大學國家治理與國家審計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江蘇南京 211815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智能時代長三角鄉村建設中的空間正義性風險及應對研究”(批準號21BZZ050)的階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