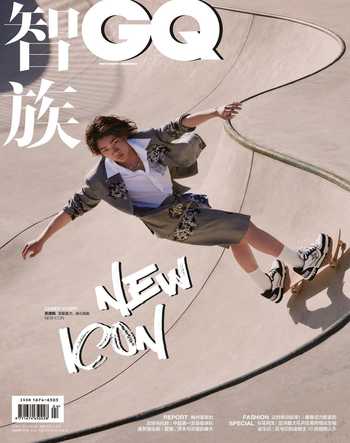明亮世界
王宇翔 Mickey LV 一他

奧斯汀·李 ,《鏡面反射2》,布面丙烯,2021,作品由Peres Projects(柏林)提供 ? Austin Lee, 2021

Austin Li奧斯汀·李,《 藍色放放放松松松松》,纖維和樹脂加固的泡沫、鋼制骨架、丙烯,2020,作品由PeresProjects(柏林)提供 ? Austin Lee, 2021

奧斯汀·李,《 紅色玫瑰》,布面丙烯,2020,作品由PeresProjects(柏林)提供?Austin Lee, 2021

娜塔莉·杜爾伯格&漢斯·博格,駐足(20厘米) ,2021_02

由上至下:娜塔莉·杜爾伯格&漢斯·博格,駐足(79厘米) ,2021_01
過去幾年李一直在使用虛擬現(xiàn)實技術(shù)進行創(chuàng)作,當代主流觀點通常將“虛擬現(xiàn)實”與“物理現(xiàn)實”對立,將“科技”與“人”對立,而時常往返于兩個世界之間的李,卻持有另一種相當溫柔、更為本質(zhì)的看法:“當下我們所處的這個充斥著電腦和科技的世界看似是非自然的,與人性相悖的,但它實則是人類發(fā)展的自然過程和必然結(jié)果,因為人類一直以來都在使用工具。”
李認為使用科技即是人類的天性,是一種HumanNature,“這次展覽的英文標題是‘人性’(HumanNature),我覺得將人類與其他物種區(qū)別開來的就是我們對工具的使用,這是人性的一部分。”因此,重要的不是科技本身,而是以科技為工具展現(xiàn)出來的人性是怎樣的,以及當科技作為日常生活無法回避的部分,會創(chuàng)造何種新的“Human Nature”。
就媒介的獨特性而言,李時常思考:虛擬現(xiàn)實的體驗是怎樣的?繪畫或雕塑的體驗又是怎樣的?李談到人們對繪畫的兩種觀念:窗口和物體——將繪畫視為一件物理實體,或是通過營造景深的錯覺將其視為通往現(xiàn)實世界的窗戶。而虛擬現(xiàn)實則在感官的豐富性上更進一步,“在虛擬現(xiàn)實中,不是透過‘窗戶’看,而是我就處在我所描繪的空間中,并被我所看到的物體所包圍。”
比起繪畫作為物體和窗口,虛擬現(xiàn)實則是成為了空間與環(huán)境。李認為兩者都具有使之成其為自身的獨特屬性,他試圖在這兩個世界之間找到相互滲透、相互交融的平衡,為封閉的空間開一扇窗,讓窗戶通往景觀更為豐富的環(huán)境。

“實際上,我把自己的感知投射到了他們身上,所以作畫就成為了去描繪我的感知和我所認為的他們的感知。我想大多數(shù)時候,我的世界是一個充滿著情感的空間。”在李的創(chuàng)作中,他試圖回答的問題一直是自己的感受,所以當他努力避免將人物作為畫中反復出現(xiàn)的主題,而開始創(chuàng)作花卉作品時,這些“花”最終還是變成了“人”。
“刻畫沒有面孔的花朵很簡單,但當我回看這些畫作時,我仍舊會看到人臉。即使在最為簡單的描繪中,我也會創(chuàng)造一個完整的故事,比如這些花是誰,甚至是他們之間的關(guān)系。并非每幅以花為主題的畫都與人有直接的聯(lián)系,但它們最終都會發(fā)展成以人為中心。”
而這也呼應了他對科技的觀點:問題核心在于人本身。你可以運用科技去創(chuàng)造美麗偉大的事物,也可以用它來造成破壞和毀滅。“那些強權(quán)勢力往往不會優(yōu)先考慮諸如‘什么是對人類最好的’或‘什么是使用和發(fā)展科技的最人性化的方式’這樣的問題,但這些問題實際上是最重要的。如果能夠從這些方面出發(fā),我們會有更好的未來。”
科技最終也會變成“人”,變成人之情感與意圖的承載。那么,但愿它承載的不是恐懼,而是愛、希望、和平與良心。
“人類必須認識到我們想要什么,以及如何去實現(xiàn)這些目標。”
通常,黏土定格動畫是Nathalie常用的表達媒介。由黏土動畫組成的那些帶有冒犯性的畫面,令人并不愉悅的畫面,而主角常常是野獸般的人或者是人一般的野獸,一種混合的產(chǎn)物。Nathalie兒時常常與祖父贈予她的童話故事集為伴,北歐童話中的妖精、矮人、動物、巫師,這些都成為她變成藝術(shù)家之后無意識的創(chuàng)作靈感。那些黏土動畫中的角色甚至是某個童年熟悉的童話角色的變體,這些角色在某種程度上被扭曲,將觀眾投射入一場“噩夢”之中,荒誕不經(jīng),暗黑不安。他們常常是欲望、嫉妒、禁忌、貪婪、懦弱、恐懼的化身,多數(shù)情況下,他們不會發(fā)出自己的聲音,取而代之的是涂鴉版的文字,比如“變成泥,變成許多和蠕蟲”,“這里埋著什么廢話?”而Hans創(chuàng)作的音樂則為動畫增添了更加強烈的情緒色彩,讓原本難以被接受的畫面變得可被忍受。“音樂使作品變得實體化,以非常直接的方式影響了觀眾的情緒,音樂不能被過濾,它更直接。你聽到它的時候,它直接進入你的大腦并觸發(fā)情緒。同時,當眼睛看到圖像時,大腦需要反應的時間,這時候,音樂已經(jīng)先于圖像影響了你的感受,所以音樂為你如何感知圖像鋪平了道路。”

相比起黏土動畫,Nathalie并不常創(chuàng)作碳筆動畫,最新碳筆動畫作品是里森畫廊展覽中的《仿如繩珠》。這是一部關(guān)于哭泣的動畫——關(guān)于悲傷以及深深的傷感。眼淚落下來,文字從水滴中涌現(xiàn)出來,把圖畫弄得一團糟。從黑暗森林樹葉的特寫,再到動物和一只眼睛,水滴或者眼淚落在葉子上肆意彈跳,直到后來,更多的眼淚如瀑布般從一只動物的眼中傾瀉而下。Nathalie在制作這部動畫的時候,父親的去世,讓她將悲切的哀傷全都融入了其中。不知是水滴還是淚水,像雨一樣落到地上,從地面滲出,從屋頂滲出,到處都是,就像要淹沒整個世界。Hans創(chuàng)作的配樂長度是動畫畫面的四倍,每當畫面開始新一次循環(huán)時,碳筆動畫描繪的更多細節(jié)便映入眼簾。“配樂不僅僅是為這件碳筆動畫創(chuàng)造的,樂曲還適用于整個展覽場域。音樂作為一種三維媒介,將展出的雕塑作品和碳筆動畫串聯(lián)起來,并影響參觀者欣賞作品的情緒。”
“一片泥濘的森林”,Nathalie如此形容自己的內(nèi)心,時時刻刻都在迷茫,時時刻刻都在自相矛盾,也會突然把自己投射到一片風景或者是一只動物身上。而Hans則是一杯可以拯救她的清水,幫她捋清思路,不再自我懷疑。“我認為我們之間一直有一種默契。我們從來沒有經(jīng)歷過同樣的事情,但我很感激他帶來的東西,這是另一種東西——另一種理解。”
人類的情感是復雜的,而這會隨著人生的經(jīng)驗而不斷充實、增長。對于Nathalie來說,她并不想停止這種增長,盡管這包含了父親離世的痛苦,但這也成為驅(qū)動她創(chuàng)造新作品的動力。而她,也在最近成為了一名母親,突然之間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情感世界。Nathali覺得“在某種程度上,情感來自于我們作為人類而不斷獲得的經(jīng)驗、學習。我們受到內(nèi)在和外在的世界啟發(fā)來充盈自己的情感。我們一直在嘗試新的材料,以我們自己的當代語言去試圖打破邊界,挑戰(zhàn)傳統(tǒng)方式。”同樣,Hans也認為兩人作為藝術(shù)家仍然在不斷成長中,“新的體驗推動我們前進,讓我們獲得更多的靈感。”

楊勛,虹竹 —加利福尼亞的猜想,160×120cm×3,布面油畫,2021(中)

楊勛,直到長出青苔,30×40cm,布面油畫,2020
楊勛位于北京后沙峪的工作室里放著一件與人等高的作品,這是他在2010年至2012年間完成的一幅油畫《我是誰》。因為一道“白光”的照射,畫中人物像是一張過度曝光的老照片,看不出五官,也無法確認性別。
2012年,這幅畫出現(xiàn)在了個展“游園驚夢”中。在布滿了園林主題作品的展館里,這幅畫顯得太不同了。“它的原型是我在一個美國團體的攝影書里看到的,他實際上是個穿女裝的男性。”當時楊勛正在創(chuàng)作園林系列,這樣的圖片卻很難不讓他聯(lián)想到自己另外3幅描繪昆曲扮相的人物作品——他們都是藝術(shù)中一個似是而非、雌雄同體的境界。楊勛很少畫人,如今回想《我是誰》的創(chuàng)作過程,藝術(shù)家本人把它歸結(jié)于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式的意識流動機。
當失去臉孔之后,一個人最重要的身份便被消解。觀眾都會好奇這些人物的具體身份,卻又只能通過他們的打扮來猜測其所生活的年代和地方。讓觀展者進行集體性記憶的釋放,便是楊勛的目的之一。另一個則是整個游園驚夢系列的目的:營造一個與過去連接的夢境。
2004年,楊勛第一次來到“咫尺之內(nèi)再造乾坤”的蘇州園林,他形容這次經(jīng)歷是一場立體世界的夢游,一種莫名的哀傷和遐想讓他覺得“可能自己上輩子就是在園子里生活過的人”。
然而沒有人能夠真實地重回歷史,相同的空間依然存在,但有些東西已經(jīng)消逝,看不見摸不著,楊勛便想要用光線來人為制造一場回到過去的夢:他在每一幅畫的中央留下一個光球,看上去就像獨自一人提著燈籠游園。“這些作品里都沒有主體,我想用光這個主觀設(shè)定,把人吸引到那個場景里面,像時光隧道一樣,這樣主體就變成了現(xiàn)場的觀者。”
“游園驚夢”讓楊勛在藝術(shù)圈內(nèi)名聲大噪,有人認為他在這個有著無數(shù)先賢建樹的主題里找到了屬于自己的領(lǐng)地,也有人認為他雖然年輕,卻對傳統(tǒng)元素有著成熟的認知。這時的楊勛不過30出頭。
正在人們覺得他會大量輸出作品的時候,楊勛卻突然喪失掉了創(chuàng)作的動力。“成功來得太突然,讓自己一下就蒙了。”他覺得自己突然被好幾道枷鎖束縛:大量的贊譽;中國當代藝術(shù)的興起,讓他質(zhì)疑自己是否落入了影像繪畫的窠臼;更致命的,是在一次次思考和反問自己之后,當初一心撲上去的園林主題似乎無法再進步。“大家覺得你畫得好,風格非常的成熟,但你好像缺乏30歲應該有的那種年輕人的變革精神和創(chuàng)新精神。”
陷入自我懷疑的楊勛躲進了當時位于黑橋的工作室,種起了花。“那個時候的工作室有現(xiàn)在的5倍大,還有一個大院子。”自認為有個老靈魂的他選擇的都是梅花、桃花、杏花這一類古代文人騷客吟詠了無數(shù)遍的品種。“北京的春天總是刮大風,風一吹,海棠花就漫天飛舞,和《三生三世》這樣的古裝片幾乎一模一樣。”那時楊勛就經(jīng)常坐在院子里,從日出看到日落,要不然就是邀請朋友泡茶喝酒,儼然過上了花前月下的生活。
這是楊勛覺得最不自信的時期。直到2014年開始,他才又拿起筆,對著院子里的花畫了起來,“我想要找到自信,找到新的出口,我需要回到之前的那種創(chuàng)作狀態(tài)。”如果說“游園驚夢”的色彩是失真的,那么在畫花的時期,楊勛只想在畫布上直接再現(xiàn)花朵最本真,甚至是有點高更般的夸張色彩。

每個花蕊上的光點,是他從“游園驚夢”時期借來的意象。只不過在此時,光線的含義從夢境、時光隧道,變成了突破自己的力量。“光是萬物的起源,我把它放在了花蕊上,就是想用光一樣的定格,讓它們變成煙火一樣的瞬間永恒。”
在花系列的創(chuàng)作后期,這樣的光點越來越多,甚至彌漫到了圖畫的背景中。“這是我內(nèi)心的真實需要。”
能量積累到一定程度,楊勛的創(chuàng)作對象又發(fā)生了改變。從2019年開始,他畫起了竹子。這又是一個非常具有中國傳統(tǒng)意味的意象。在唐朝以前,古人就已經(jīng)在描繪庭院的繪畫中加入了竹子的元素,到宋朝,竹子已成為傳統(tǒng)繪畫中獨立的一科。在這樣的背景下,楊勛想在向古人致敬的同時,又完全擺脫古人的影子。
竹子每長一段,就留下一個竹節(jié),竹節(jié)如同一個個點,將生命串聯(lián)起來。楊勛想起過去停留在花蕊上的光點,“如果那個時候畫的是花之光,那我來表達竹子的時候,是不是能畫出竹之光?”
竹節(jié)上的一個個光點,賦予傳統(tǒng)的符號與象征以全新的解讀:《花火》畫的是竹葉盛放,曖昧的色彩和直譯自日文的名字,又把人帶到了20世紀90年代蒸汽波流行的時期;帷幕后朦朧的竹子讓人看到光的多變,讓我們思考起它的本質(zhì);竹節(jié)排列在一起,如同現(xiàn)代社會里的LED燈,又讓楊勛想到了薄霧朦朧的家鄉(xiāng)重慶……
這一切都要歸功于光,一道從“游園驚夢”里照射出來,生生不滅的光線。“我所有的創(chuàng)作都像是一棵大樹長出來的分杈,看似意外、互無關(guān)系,實際上早在一開始就埋下了種子。”
疫情期間,楊勛完成了《虹竹》。在這個系列中,他少見地使用了光譜般絢麗的色彩,讓作品看上去非常人工,頗具波普風格。而實際上,這種顏色體驗又完全來自于現(xiàn)實,“夏天的暴雨之后,如果去羅馬湖看日落,能看到紅彤彤的晚霞倒映在湖面上,云朵低低的,一切都顯得非常魔幻。”
楊勛把《虹竹》看作是能量的釋放,一場現(xiàn)在需要面對的挑戰(zhàn),“雖然我這個年齡對于藝術(shù)家來說還算年輕,但我覺得這樣的東西在5年之后我不一定能夠再挑戰(zhàn),”楊勛覺得當下是他最自信的時刻,“我完成了自我的救贖。”
這種自信延續(xù)到他去年開始創(chuàng)作的石頭系列。保持從宏觀到微觀的視角轉(zhuǎn)變,楊勛筆下的石頭從來看不到全貌,它們沒有開始,也沒有結(jié)束。每一張石頭的創(chuàng)作,楊勛都一定要畫到無法添加筆觸的地步,仔細端詳會發(fā)現(xiàn)石頭上布滿了筋絡(luò)一般的筆觸,光線也變得柔和許多,這樣的細節(jié)如果不親自到現(xiàn)場觀看就無法發(fā)現(xiàn)。雖然使用了飽和度沒有那么高的色彩,但在一種奇妙的對比色下,這些石頭卻默默地散發(fā)出一種難以言喻的吸引力。
從園林之光、花之光,再到竹之光、石之光,楊勛一直在延續(xù)一種“固執(zhí)”的創(chuàng)作初衷。現(xiàn)在,他仍然愿意花上幾個月的時間慢慢完成一幅畫,會在工作室里保持一段時間的高強度工作,也會停下來進行休息與思考,就在這樣一緊一松的螺旋式上升中,楊勛在畫布上構(gòu)建起了自己的宇宙,那里紛雜繁復,于自身向外延展出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