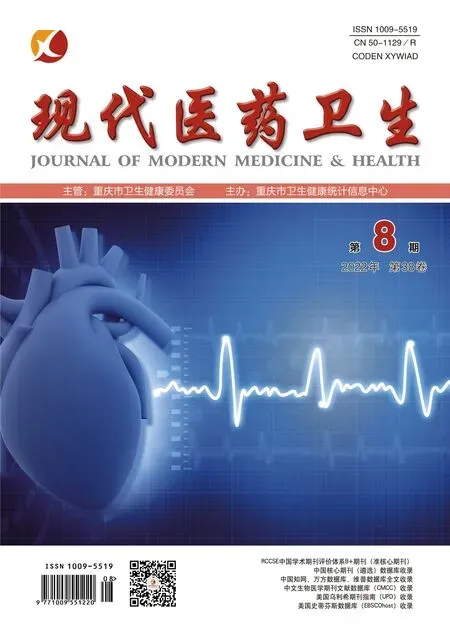不同類型兒童吉蘭-巴雷綜合征變異型診治報道
何運元,王院方,郭愛萍
(濮陽市安陽地區醫院兒科,河南 濮陽 455000)
吉蘭-巴雷綜合征(GBS)是最常見引起兒童急性弛緩性麻痹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主要表現為急性進展、對稱性肌無力及腱反射減弱或消失,呈單相病程[1]。但隨著近幾十年來對GBS的研究,這一經典診斷標準受到極大挑戰。GBS變異型臨床表現不典型,早期多無肌力下降,臨床癥狀復雜、多變,涉及多個系統,臨床上常被誤診及延誤治療。Miller-Fisher綜合征(MFS)、急性泛自主神經病及急性感覺神經病是GBS的特殊亞型,其發病率低,誤診率高,國內僅有少量報道[2-4]。本文通過對不同類型兒童GBS變異型的臨床資料進行分析并總結治療經驗,以期對臨床工作提供幫助。
1 資料與方法
1.1資料
1.1.1一般資料 本院2016年5月至2020年5月共收治MFS 5例,急性泛自主神經病3例,急性感覺神經病4例,回顧性分析臨床資料。所有患者知情同意,符合《赫爾辛基宣言》的基本原則。
1.1.2納入標準 (1)兒童急性起病,快速進展,達運動障礙高峰小于4周;(2)符合MFS、急性泛自主神經病及急性感覺神經病臨床特點,按照中華醫學會神經病學分會制定標準[5];(3)排除脊髓灰質炎;(4)肌張力正常或者輕度減退;(5)腦脊液蛋白-細胞分離現象;(6)自限性;(7)電生理檢查可正常或感覺神經異常;(8)排除其他病因。
1.2方法
1.2.1觀察指標 分析患者的一般資料、起病情況、臨床特點、病情演變(最大運動障礙高峰時間、應用呼吸機情況)、腦脊液檢查、神經電生理,分析其治療措施及預后。
1.2.2功能障礙評分 采用Hughes殘疾等級改變判斷患兒最大運動障礙[6]。0分:正常;l分:不影響正常活動;2分:無扶助可獨自行走大于5 m;3分:扶持或借助工具行走小于5 m;4分:床上或輪椅上活動;5分:需要呼吸機支持;6分:死亡。
2 結 果
2.1一般資料情況 12例GBS變異型患兒中男7例,女5例,男女比例為1.4∶1.0;3~<8 歲10 例,8~10歲2例。多在學齡前期發病,起病至確診時間4~60 d,中位時間為19 d。
2.2臨床特點 12例GBS變異型患兒中83.3%(10例)存在感染誘因,其中上呼吸道感染4例,胃腸道感染3例,皰疹性咽峽炎2例,支原體肺炎治療病史1例;病毒感染8例,占66.7%。首發癥狀具體如下:(1)MFS,眼球運動異常2例,眼瞼下垂伴步態不穩1例,視物重影伴共濟失調2例;(2)急性泛自主神經病,頭暈伴尿潴留1例,行走不穩伴視物模糊1例,抽搐后意識障礙1例;(3)急性感覺神經病,肢體疼痛2例,肢體麻木2例。所有患兒早期均無肌力下降,查體均存在腱反射減弱或消失。2周內出現最大運動障礙為85%,其中1周內達峰為40%,少數病例在起病后30 h左右即達高峰,1例急性泛自主神經病給予呼吸機支持,機械通氣時間為50 h。至確診時肌力正常5例,肌力Ⅲ~Ⅳ級5例,肌力Ⅱ級2例。見表1。
2.3輔助檢查 (1)腦脊液出現典型蛋白-細胞分離80%(10例)出現在第2周,第1周即出現的占20%(2例,其中均為急性感覺神經病);腦脊液常規:潘氏球蛋白定性實驗均陽性,白細胞計數(0~5)×106L-1;腦脊液生化:腦脊液蛋白 0.787~1.612 g/L[平均(1.1±0.28)g/L]。(2)血、腦脊液神經節苷脂抗體送檢6例,其中1例急性泛自主神經病血清抗GM1抗體IgM(+),其余均為陰性。(3)肌電圖:肌肉電傳導減慢(左右尺神經CMAP波幅稍低)1例,軸索損傷為主的周圍神經病變3例,感覺神經動作電位波幅下降(考慮脫髓鞘改變)5例,正常3例。(4)頭顱及脊髓影像學檢查:頭顱影像學檢查陰性10例,頂葉皮層異常信號及大枕大池1例(已進行血氨、乳酸、遺傳代謝、感染等相關檢查、篩查,排除顱內感染、占位、代謝性疾病);行脊髓MRI檢查:腰椎段脊髓受累,腰段神經根明顯強化2例,脊髓輕度水腫(胸椎段)3例,其余均陰性。
2.3功能障礙評分結果 MFS 5例中Hughes功能評分分級小于3分4例,1例4分;急性泛自主神經病3例中1例5分,1例3分,1例2分;急性感覺神經病4例中3例2分,1例3分,1例4分;統計小于或等于3分占75%,>3分占25%。見表1。

表1 12例GBS變異型臨床特點、輔助檢查及Hughes功能評分比較
2.4治療及轉歸 6例給予1個療程免疫球蛋白(總量2 g/kg,分3 d輸注)治療,4例應用2個療程免疫球蛋白治療(劑量2 g/kg,間隔7~14 d),2例伴有明顯神經根疼痛,采用免疫球蛋白聯合甲潑尼龍20 mg/kg,每天1次靜脈滴注×3 d(最大量小于500 mg/d),隨后減量為甲強龍(甲潑尼龍琥珀酸鈉)10 mg/kg,每天1次靜脈滴注×2 d,后改為潑尼松片[2 mg/(kg·d)]口服,每3天減量5~10 mg,直至減停。4例患兒在1周肌力開始恢復,3例在2周內肌力逐漸恢復,本組無1例死亡,出院前5例(表1中序號1、7、8、10及11)進入康復訓練階段,隨訪6個月,4例恢復正常,1例(序號10)因家庭經濟及其他原因,遺留共濟失調、頭暈不適。
序號7,Hughes分級5分,最初以胃腸道感染癥狀(發熱伴嘔吐)起病,呼吸麻痹,給予氣管插管、機械通氣50 h,誤診“病毒性腦炎”,起病第3天予丙種球蛋白免疫(總量2 g/kg,分3 d輸注)治療1個療程,病程中第4、9天均行腰椎穿刺腦脊液檢查均陰性,頭顱核磁陰性。治療1周后意識恢復,肌力下降逐漸顯現,起初左上肢肌力Ⅱ級,其余肢體肌力Ⅲ級,后肌力恢復,出現頭暈、少汗、直立性低血壓等自主神經紊亂癥狀,病程第2周復查腦脊液常規:潘氏球蛋白定性實驗陽性,白細胞3×106L-1;腦脊液生化:腦脊液蛋白1 028 mg/L;典型蛋白-細胞分離現象,血清神經節苷脂抗體:抗GM1抗體IgM(+),肌電圖示周圍神經受損。腰椎磁共振成像(MRI)平掃+增強提示腰段脊髓受累,腰段神經根明顯強化。最終確診患者急性泛自主神經病。間隔7 d后再次給予第2個療程免疫球蛋白應用,總治療時間4周,治愈出院。
3 討 論
隨著GBS亞型的不斷更新及報道,不典型表現逐漸被人們認知。MFS、急性感覺神經病和急性泛自主神經病作為其中少見的類型,其首發癥狀多無肌力下降,其獨有的復雜臨床特點,幾十年內未被收錄到GBS診斷系統內[7]。隨著研究的深入,2019年中華醫學會神經病學分會對GBS亞型進行了更新,這3類變異型[5]被歸納入GBS譜系中,作為GBS變異型,對其臨床特點等進行總結。
對于變異型GBS的診斷,詳細的病史及神經系統查體至關重要,感染誘因、感覺障礙、腦脊液檢查、相關周圍神經病抗體(如抗神經抗原抗體檢測、抗神經節苷脂抗體等)的出現及神經電生理依據則是GBS診斷的支持證據。本研究患兒男性較多,年齡多在學齡前期,83.3%患兒起病前有感染誘因,多數存在呼吸道感染,而其中EB病毒、腺病毒等病毒檢出率高(占66.7%)。以往研究認為,GBS是感染后免疫介導的神經損傷,常見病原菌為空腸彎曲桿菌[8],其次為巨細胞病毒、EB病毒、肺炎支原體等,在兒童中尚見少量報道與之相一致,且病毒感染較成人發揮重要作用[4,9-10],本研究與之相符。本研究中3類GBS變異型首發癥狀以眼外肌麻痹、共濟失調、自主神經及感覺神經受累為特征性表現,早期均無肌力下降,至確診前肌力Ⅱ級僅占16.7%,85%的患兒在2周內達最大運動障礙,其中最短達峰時間為30 h(Hughes功能評分5分),急速進展,給臨床診斷帶來巨大困難,本研究確診周期最長2個月;神經電生理異常占75%,以感覺神經運動電位異常(脫髓鞘改變)多見。因本研究樣本量小、有的疾病在確診早期即給予了免疫治療等因素,周圍神經病相關抗體檢出率低,僅1例檢出抗GM1抗體IgM(+),仍需大樣本進一步驗證。
變異型GBS治療同經典型一致,主要為免疫治療,靜脈滴注丙種球蛋白及血漿置換是同等有效的[11],由于丙種球蛋白治療并發癥更少,臨床上較常用。對于Hughes功能評分小于或等于2分的輕癥GBS,有研究顯示免疫治療與支持治療相比,遠期預后無顯著差異,但也有研究顯示早期丙球應用可明顯改善運動障礙及縮短住院時間[12],但考慮其病情可能進一步進展,仍需積極免疫治療,改善預后;對于Hughes功能評分大于或等于3分的GBS患者,2周內給予丙種球蛋白治療,可收獲最大療效,考慮與丙種球蛋白可結合致病性的抗神經節苷脂抗體,阻斷免疫活化有關系[11]。本組12例GBS患兒均在2周內給予免疫球蛋白治療,7例肌力下降患兒均在用藥后2周有不同程度恢復,短期預后(6個月)良好;研究顯示,約有10%的患者在給予丙種球蛋白或血漿置換治療獲得短暫緩解或病情趨于穩定后,會再次加重,稱為治療相關波動(TRF),由于這部分患者的自身免疫反應延長,從而導致更長久的神經損傷,因此治療時間也需要延長。WALGAARD 等[13]發現,出現TRF的GBS預后療效受益于丙種球蛋白的第2個療程,可明顯改善4周后運動功能結果。但目前尚缺乏充分的循證證據支持,建議根據具體臨床情況個體化選擇[13]。本研究中4例應用第1個療程丙種球蛋白后出現TRF,間隔7~14 d再次給予第2個療程免疫球蛋白治療,肌力均有不同程度改善。本文提及的1例特殊病例1周內達運動障礙高峰,Hughes功能評分5分,予免疫球蛋白治療第1個療程,呼吸麻痹、意識障礙均消失,但出現顯著的自主神經紊亂癥狀,考慮免疫損害持續存在,損害自主神經,早期的免疫治療對現在自主功能障礙無效。因此,間隔1周后再次給予第2個療程免疫球蛋白治療,預后良好,隨訪6個月,未見復發。
研究顯示,單用糖皮質激素治療 GBS 無明確療效,還可影響血糖、血壓變化,臨床上不推薦使用[1,10]。本組發現3例伴明顯神經根痛,核磁共振檢查提示2例有脊髓水腫/腰椎段神經根強化,給予丙種球蛋白治療后肌力明顯改善,疼痛感明顯,考慮激素強大的抗炎作用,可改善炎癥刺激及脊髓腫脹,均加用糖皮質激素(短期),效果顯著,因無大樣本研究支持,仍需進一步研究及改善。
GBS為單相病程,有自愈傾向,兒童神經再生能力更強,短期恢復行走能力優于成人[14],本12例患兒僅1例短期預后出現共濟失調,余均預后良好,肌力均恢復正常。研究中發現Hughes功能評分大于3分的病例3例,均有肌力下降(Ⅱ~Ⅲ級)、脊髓水腫或神經根強化,其中1例肌肉電傳導減慢(左右尺神經CMAP波幅稍低)失電位型,遺留共濟失調、頭暈不適,因此認為神經失電位型、Hughes功能評分大于 3分是GBS短期預后的影響因素,與孫瑞迪等[14]國內研究相一致。而脊髓病變(水腫或神經根強化)也需列入其影響因素范圍,這還需進一步大樣本、多中心研究論證。
總之,兒童GBS變異型發病率低,臨床癥狀不典型,誤診率高,特別是以非肌力下降為首發癥狀的患兒,臨床醫師應重視神經專科查體及詳細的病史采集,拓寬診斷思路,避免誤診。一經確診,早期應給予免疫球蛋白治療,如病程中出現TRF,根據個體情況,可給予第2個療程免疫治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