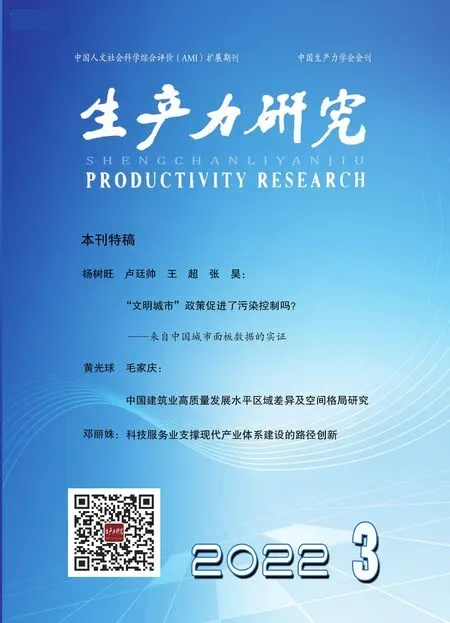長江經濟帶資源型城市創新效率評價及影響因素識別
胡勝梅,鄧宏兵
(1.中國地質大學(武漢)經濟管理學院,湖北武漢 430078;2.湖北省區域創新能力監測與分析軟科學研究基地,湖北武漢 430078)
2020 年11 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南京主持召開全面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強調“要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和十九屆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會精神,堅定不移貫徹新發展理念,推動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而創新處于新發展理念的首位,創新驅動是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的動力引擎。由于自然資源豐富、歷史區位條件良好,長江流域內形成了45 座依托資源開采和加工形成的地級資源型城市,不僅在長江經濟帶占很大比重,也在全國地級資源型城市中占很大比重,所以長江經濟帶資源型城市創新發展不僅關乎本流域的高質量發展,也對全國其他資源型城市轉型具有參考價值。同時,城市創新效率作為創新資源投入產出比,能夠度量城市的自主創新能力,甚至可以反映一座城市的可持續發展能力,為考察資源型城市轉型成效和發展質量提供了新的視角和切入點。
關于創新效率的研究,主要圍繞創新效率的測度、評價及其影響因素。創新效率的定量評估多以創新資源的投入產出效率理論為基礎,目前主流的評價方法是數據包絡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其中范斐等(2013)[1]利用DEA 模型對城市創新效率進行測度,從而實現分析城市科技資源配置情況的研究目的;肖瀅和鄧宏兵(2017)[2]也是基于DEA 模型對長江經濟帶的城市創新效率進行測度,從而實現對其空間演化特征分析。關于創新效率影響因素,朱麗霞等(2019)[3]的實證研究結果表明經濟基礎、信息化進程、外商活躍度都對創新效率有促進作用,而第三產業規模、創新平臺、政府支持力度對創新效率作用的地區異質性明顯;程美林和張潤磊(2019)[4]認為區域開放程度、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科技機構發展、企業科技創新投入水平對創新資源配置效率提升的積極因素;此外,習明明(2019)[5]從創新環境的角度出發,研究結果表明基礎設施環境、經濟環境、金融環境對創新效率有正向作用。然而在研究單元方面,蘭海霞和趙雪雁(2020)[6]、劉樹峰等(2019)[7]、賴一飛等(2021)[8]以省域為研究單元,便于獲得更豐富和準確的數據,從而提高研究的精確度;徐林(2021)[9]以城市為研究單元,更小的研究單元更有助于闡釋其他因素對創新效率的作用機制;鄭國洪(2017)[10]、穆廣杰(2021)[11]認為中心城市是創新資源的集中地,以中心城市為研究單元,更有助于帶動全國其他城市的創新發展;此外,章文光和李偉(2017)[12]、劉鍇等(2020)[13]基于創新型城市的特殊性,以創新型城市為研究單元,更有利于發揮此類城市的引領和示范作用。
資源型城市作為一種特殊類型的城市,以往依靠資源輸出積累了經濟基礎,所以目前資源型城市創新發展問題備受關注。謝遠濤等(2017)[14]對資源型城市創新指數進行測度和研究,但是缺乏對資源型城市創新效率和其影響因素的研究。所以,本文以長江經濟帶資源型城市為研究對象,對城市創新效率進行測度以及差異化分析,突出長江經濟帶上游、中游、下游資源型城市之間的異質性,分類探討創新效率的主要驅動因素,以期為決策部門制訂創新發展政策提供依據和參考。
一、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一)DEA-BCC 模型
DEA 模型作為學術界測度創新效率的主流方法,它是基于不同量綱的多投入和多產出指標測度決策單元的相對效率值,避免了生產函數的誤設,具有更客觀、真實、可靠的優點。由于創新活動是具備知識經濟特征且創新邊際收益具有不確定性,所以本文采取投入導向的DEA-BCC 模型測度長江經濟帶資源型城市的創新效率。具體公式如下:

其中,θ是介于0~1 之間的效率值,xj、yj和λj是第j個決策單元的要素投入量、產出量和投入產出權重,α和β是投入指標總數和產出指標總數,e-和e+是單位向量,S-和S+是投入和產出松弛變量,ε是大于0 且小于任何正數的無窮小量。
當θ=1 且ε(e-S-+e+S+)=0 時,該決策單元的投入產出為DEA 有效,當θ=1 且ε(e-S-+e+S+)>0 時,該決策單元的投入產出為弱DEA 有效,當θ<1 時,該決策單元的投入產出為非DEA 有效。
(二)面板Tobit 模型
考慮到DEA-BCC 模型測度的效率值位于0 和1 之間,采用傳統的最小二乘法進行回歸會使參數結果有偏且不一致,故本文采用受限因變量模型(Tobit)探尋長江經濟帶資源型城市創新效率的主要影響因素,回歸模型具體設定如下:

其中,被解釋變量effi是基于規模報酬可變模型(BCC)計算的創新效率值,eco、edu、fdi、indus1、indus2、infrast、rely、envir、locat分別表示經濟發展水平、地區教育水平、外資利用度、產業結構、基礎設施、資源依賴度、環境規制以及區位條件等解釋變量(見表1),β0為截距項,β1~β9為各解釋變量的回歸系數,u為隨機干擾項。

表1 創新效率影響因素指標體系
(三)指標選取
創新活動是一個從投入到產出的持續性的過程,而創新效率是在現有的投入產出機制下能夠實現的投入產出比,因此創新效率的測算也包含投入和產出兩個方面的指標。創新投入包含人力要素、財力要素、物力要素以及信息要素,分別選取年末單位從業人數、政府教育和科學支出、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以及互聯網用戶數作為具體投入指標;創新產出包含知識產出和經濟產出,分別選取發明專利授權數、地區生產總值作為創新效率的具體產出指標。
根據已有研究,影響創新效率的因素通常有經濟環境、地區教育水平、產業結構、基礎設施等因素,而本文基于資源型城市的特殊性以及城市區位條件的異質性,又提出了資源依賴度、環境規制強度以及區位條件三個影響因素假設(見表1)。
(四)數據來源與處理
結合《全國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規劃(2013—2020 年)》[15],長江經濟帶涉及45 個資源型地級城市,由于其中5 個自治州(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涼山彝族自治州、楚雄彝族自治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和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以及畢節市的相關數據獲取難度大,故以其余39 個資源型城市為研究樣本。樣本數據為2008—2018 年39 座資源型城市數據,主要來源于2009—2019 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各城市統計年鑒以及各城市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其中發明專利授權數來自于佰騰網,部分缺少數據采用均值法插入。考慮到從創新投入到產出具有時間上的滯后效應,所以選取產出比投入滯后一期的數據測度創新效率。為了消除價格因素的干擾,以2008 年為基年對相關指標進行價格平減。
二、實證分析
(一)創新效率的時序變化分析
從長江經濟帶資源型城市創新效率總體變化的視角,長江經濟帶資源型城市創新效率在不同階段呈現不同狀態。在2013 年以前呈現持續下降的狀態,在2013 年以后,由保持平穩轉變為開始增長的趨勢(見圖1)。主要原因可能是資源型城市歷史遺留問題比較嚴重,采掘業占二次產業比重較高,地區發展對資源產生極高依賴度,創新要素集聚能力較弱,創新活動難以開展,創新效率持續走低;2013 年國務院印發《全國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規劃(2013—2020 年)》,提出了建立健全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的長效機制目標規劃,改變了創新效率持續走低狀態;各地政府更加重視資源依賴的問題,積極引導資源型城市創新驅動發展,在2017 年以后創新效率得到進一步的改善。

圖1 創新效率時序變化
從長江經濟帶不同區段城市創新效率的視角,在2013 年以前,三個區段創新效率都持續下降。在2013 年以后,三個區段呈現出差異性變化,其中下游創新效率波動上升、中游保持平穩、上游緩速下降,最后都轉變為增長的趨勢。三個區段相比較,長江經濟帶下游資源型城市創新效率的時序變化情況依次優于中游城市和上游城市,主要因為下游地區創新基礎、創新環境,甚至創新技術都優于中游、上游地區。
(二)創新效率影響因素分析
整體層面資源型城市創新效率影響因素識別的實證結果表明,經濟增長水平、外資利用度、基礎設施建設、環境規制強度以及區位條件對創新效率產生顯著性影響(見表2)。第一,經濟增長水平的影響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因為創新活動具有周期長、風險高等特征,較高的城市經濟增長會增加創新活動所需的財力、人力、物力等要素的投入,創新投入產出機制也更加完善;第二,外資利用度的影響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因為創新技術不僅來源于城市內部自主研發,還來源于對外部技術的引用,李政等(2017)[16]的研究表明,優質的外商資本可以通過技術外溢效應對區域創新效率產生促進效應;第三,基礎設施建設的影響在10%的水平下顯著為正,因為基礎設施環境促進創新活動,是創新活動得以開展的重要支撐因素;第四,環境規制強度的影響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負,楊露鑫和劉玉成(2020)[17]的研究表明,環境規制與創新效率之間呈現U 形非線性關系,基于資源性城市環境污染較為嚴重,且環境規制發展比較滯后,因此仍然處于U形關系的前半段;第五,區位條件的影響在5%的水平下顯著為正,因為長江經濟帶上游地區整體以其優越的創新基礎和創新環境,對資源型城市創新效率的輻射帶動作用依次強于中游地區、下游地區。

表2 影響因素回歸系數結果
不同區段創新效率的影響因素識別的實證結果表明,各因素對長江經濟帶不同區位資源型城市的創新效率產生的影響存在異質性(見表2)。經濟增長水平對上游資源型城市創新效率的影響不顯著,但是對中游和下游的影響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原因是上游資源型城市發展相對薄弱,不足以發揮經濟增長對創新效率的促進作用;教育水平對上游和中游資源型城市創新效率的影響不顯著,但是對下游的影響在5%的水平下顯著為正,因為人力資源是創新活動中最具有創造力的要素,而下游地區教育水平最高,中游地區人才流失情況明顯,上游地區教育水平較低,只有下游資源型城市才發揮出了地區教育水平對創新效率的促進作用;外資利用度雖然對總體資源型城市創新效率產生顯著性影響,但是分別對三個不同區位的影響并不顯著,可能是因為外商投資帶來的技術外溢效應微弱,或者分類回歸導致樣本量減少的緣故;產業結構對上游、中游、下游資源型城市創新效率均產生顯著性影響,但是產業結構對上游和中游產生的影響還停留在從業人員結構方面,對下游城市創新效率產生的影響已經上升到產值結構方面;基礎設施只對中游資源型城市的創新效率產生顯著性影響,可能因為下游和上游基礎設施水平分別太高或者太低,而中游資源型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在研究期內上升明顯,表現出對創新效率的正面促進效應;資源依賴度只對上游資源型城市創新效率產生顯著為正的影響,說明上游的創新活動尚未擺脫對資源的依賴,可能會發生創新效率層面的“資源詛咒”;環境規制強度對上游城市產生的影響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為負,對中游和下游的影響均在5%的水平下顯著為負,環境污染嚴重是資源型城市的通病,環境規制對城市創新效率的抑制作用大于促進作用,長江經濟帶上游、中游、下游城市均位于U 型曲線的左半段。
三、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第一,從創新效率時序變化的視角,以2013 年和2017 年為時間節點將創新效率變化分為三個階段,長江經濟帶資源型城市總體呈現持續下降、平穩波動、增長的狀態;由于長江經濟帶上游、中游、下游資源型城市的創新基礎、創新環境以及創新能力存在顯著差異,所以下游資源型城市創新效率依次優于中游、下游。
第二,從長江經濟帶創新效率總體層面的影響因素視角,經濟增長水平、外資利用度、基礎設施水平均對創新效率產生顯著的促進作用;環境規制對創新效率產生顯著的抑制作用;區位條件也對創新效率產生顯著的影響,其中長江經濟帶下游區位條件對創新效率的促進效應依次大于中游、上游。
第三,各因素對長江經濟帶不同區位資源型城市的創新效率產生的影響存在異質性。產業結構、資源依賴度和環境規制強度是上游資源型城市的主要影響因素;經濟增長水平、產業結構、基礎設施建設和環境規制強度是中游資源型城市的主要影響因素;經濟增長水平、地區教育水平、產業結構和環境規制強度是下游資源型城市的主要影響因素。
(二)對策建議
根據上述研究結論,長江經濟帶資源型城市應該充分考慮自身特征,從如下幾個方面提出差異化對策建議,以期促進創新效率的提升,更好地實現創新驅動。
第一,增強經濟發展對資源型城市創新活動的有效支撐。在保持經濟增長對長江中游、下游資源型城市創新效率促進作用的同時,政府應出臺相應幫扶政策,促進上游資源型城市的經濟發展,發揮出經濟對上游資源型城市創新活動的有效支撐作用。
第二,為資源型城市創新活動提供充足的人才儲備。基于上游資源型城市教育資源匱乏,中游人才流失嚴重,應該加強上游教育水平,提升中游人才承載力,分類推進,有效發揮長江經濟帶上游、中游、下游教育對創新效率的促進作用。
第三,提升資源型城市外資利用水平。資源型城市本身具備資源優勢,所以應該基于自身的資源稟賦引進更多具有高技術和研發能力的外商企業投資,從而提高自身的創新能力和創新效率。
第四,加強資源型城市產業結構升級力度。資源型城市第二產業比重更大,資源型產業也相對較多,產業結構升級有更大的提升空間,因此應積極促進非資源型產業的發展,實現產業的多元化,最大限度地發揮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對創新效率的促進作用。
第五,補齊資源型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短板。長江經濟帶上游、中游、下游資源型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水平不一,應該補齊上游基礎設施建設短板,充分發揮基礎設施對創新活動的支撐作用。
第六,擺脫資源型城市對資源型產業的依賴。基于長江經濟帶上游資源依賴度對創新效率的促進作用并非長久之計,應該積極引導非資源型產業尤其是高技術產業的發展,加快擺脫對資源型產業的依賴,避免創新效率方面的“資源詛咒”。
第七,發揮資源型城市環境規制對創新效率的促進作用。資源型城市環境污染相對嚴重,因此應該逐漸加強環境規制強度,使環境規制和創新效率的關系處于U 型曲線的后半段,實現環境規制對創新效率的促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