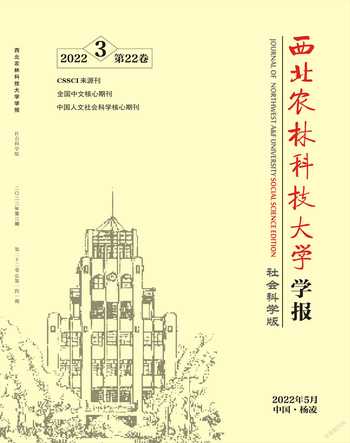“地權集體化”:傳統農區宅基地制度改革的邏輯

摘 要:由于基層多樣的制度創新,傳統農區宅基地制度改革超出了現行政策提倡的財產化改革的范疇,需要在理論上作出新的概括。以兩個村莊的宅基地制度改革案例為分析對象,通過治理視角考察宅基地制度改革背景下,宅基地地權集體化的政治社會效應及其結構性條件。研究發現,傳統農區宅基地地權集體化超越了保障農民財產權的經濟效應,具有提高宅基地管理效率,推進村莊建設,提升基層治理能力的政治社會效應。宅基地地權集體化的實現,有賴于農村集體土地所有制的制度基礎、“權責均衡”的治理基礎及政府支持的政治空間。研究證明,傳統農區宅基地制度改革的關鍵不是擴大權能,而是實現宅基地有效治理。在宅基地制度改革中,“集體”的權利可以被激活,因此,宅基地制度改革需要給村集體留出實踐其所有權的空間。
關鍵詞:宅基地制度;農村地權;集體土地所有制;傳統農區
中圖分類號:F30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07(2022)03-0082-08
收稿日期:2021-10-16" 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22.03.10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20CSH050)
作者簡介:邱麗,女,中山大學哲學系博士研究生,廣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農村社會學、馬克思主義與中國農村問題。
一、問題的提出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并提出:“保障農戶宅基地用益物權,改革完善農村宅基地制度,選擇若干試點,審慎穩妥推進農戶住房財產權抵押、擔保、轉讓,探索農民增加財產性收入渠道”。隨之,宅基地制度改革逐步進入全面試點階段,我國農村摸索出多種宅基地財產化改革模式。一是宅基地有償選位模式,在浙江等東部發達地區,農民宅基地區位意識強、民間資金充裕,村莊運用市場競爭機制,開展宅基地村內競拍的改革。二是宅基地內部流轉模式,即通過“搭地賣房”等方式,讓宅基地在集體經濟組織內部的農戶之間流轉。三是房屋抵押貸款模式,即農戶在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擔保之下,將農房抵押在農村商業銀行以獲取貸款。四是閑置農房盤活模式,即在部分風景較好的農村,政府和村集體引進社會資本下鄉,盤活閑置農房以發展旅游。五是宅基地入市模式,即通過土地“增減掛鉤”政策,農戶自愿有償退出宅基地并將其復墾為農地。政府獲得同等建設用地指標,將其賣給有需求的城鎮,以獲得財政收入。以上財產化改革模式成為學界討論熱點,既有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兩類:
第一類研究側重于探討宅基地財產化改革的現狀和路徑[1]。既有研究主張從立法、制度等層面完善農民的宅基地財產權[2]。一是完善農民住房抵押的財產化收益路徑。譬如有學者主張從法律上實現農村住房的財產權[3]。還有學者認為農民住房財產權抵押的實現應從激活流轉市場、因地制宜采取差異化措施、合理發揮政府和市場作用等方面完善政策[4]。二是保障農民宅基地使用權退出的合法收益[5]。三是保障農民宅基地使用權流轉的收益[6]。
第二類研究探討不同的宅基地財產化改革模式所產生的經濟效應。諸多學者認為宅基地財產化改革具有積極的正面的效應。周江梅等指出宅基地流轉模式打破了宅基地使用區位的固定性,使得宅基地更加靈活,能夠滿足周邊地區的宅基地用地需求,從而提高宅基地利用效率[7]。還有學者對浙江宅基地有償選位模式研究后發現,其能有效整合農村自留地、舊宅基地、曬谷場等資源,推進了新農村建設[8]。當然,也有學者提出不同的聲音,賀雪峰認為通過“增減掛鉤”推動的宅基地入市并不會產生財富,其僅僅是一種財富轉移,造成了資源的浪費[9]。夏柱智則認為宅基地財產化改革,形成的是“有限市場”的經濟效應[10]。
簡而言之,宅基地財產化改革是在私有產權理論的指導下,將宅基地視為一項經濟資源。其資源配置主體是“市場”,多數發達地區農村形成了市場主導型的宅基地管理模式。就村莊內部的地權配置而言,宅基地制度改革總體沿著強化農民權利、虛化集體土地權利的方向推進。然而,近年來有學者發現,財產化改革路徑與傳統農區的宅基地資源配置要求不符,造成了部分地區財產化改革的制度空轉[11]。更有學者通過江西余江等地的宅基地改革實踐提出,宅基地制度在村莊社會落地,遠非簡單的農民權利問題,而是涉及村莊社會結構、地利分配等因素的治理問題[12-13]。實踐中,不少傳統農村地區在宅基地財產化改革的政策背景下,并未開展財產化改革實踐,而是挖掘了集體資源開展了地權集體化實踐。相較于發達地區農村,傳統農區宅基地改革側重于加強集體對宅基地的統籌和治理能力。由于宅基地地權集體化并非經濟驅動的產物,經濟學的私有產權理論難以解釋該現象。治理視角為理解該現象提供了進路,然而,當前治理視角下的宅基地制度改革研究并未解釋傳統農區宅基地集體化的改革路徑及其結構性條件。鑒于此,本文在治理視角下的宅基地制度改革研究的基礎上,重點探討傳統農區宅基地集體化的邏輯。
本文的核心觀點是,宅基地地權集體化的改革實踐在傳統農區表現為多種制度實踐形式,且均有其內在合理性。村社能在宅基地財產化改革的背景下重新統合宅基地地權與一些結構性條件相關。本文的資料源于筆者2018年8月和2020年7月在江西余江和湖北宜城開展的駐村調研。江西余江和湖北宜城均地處于中部地區,村莊二三產業發育不足,農民以外出務工和在地務農為主,屬于典型的傳統農業型地區。一方面,兩個村莊均是2015年國務院指定的首批宅基地制度改革示范點,較早開展了宅基地制度改革實踐并形成相關經驗;另一方面,兩個村莊均通過挖掘政治社會資源實現了宅基地有效治理,還原了宅基地地權的集體屬性。因此,其作為傳統農區宅基地地權集體化的研究樣本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二、宅基地集體化的類型及其形成過程
宅基地財產化改革的典型特征是“還權賦能”,在改革全面試點階段,國家對地方宅基地制度改革的政策實踐保留了較多制度空間。因而,自發性的制度創新在宅基地制度改革中很普遍,形成了多樣化的宅基地治理制度。筆者所調查的兩個傳統農區,其形成的宅基地制度均有強集體統合和支配的特征,表現為:村集體能夠依據村莊規劃及村民公共利益的訴求,調整宅基地的分配、使用、退出等治理制度。由于村莊治理的社會結構不同、集體經濟收入狀況不同,村集體在宅基地治理中依靠的治理主體、治理手段均存在差異。
(一)宗族組織統合:江西余江宅基地治理經驗
宗族組織統合是指依托于宗族理事會等組織,發揮集體統合宅基地資源的功能。由于宗族性地區,宗族組織是集血緣、地緣于一體的組織,其在社會層面具有處理村莊公共事務的合法性,且宗族組織是自發性組織,地方政府介入不多,因而其起作用的關鍵是依托于宗族內部的權威人物和房頭代表。這部分人員一般是有公心且德高望重的人,由于平常主持村民的紅白喜事等公共事務,其群眾基礎好,在村民小組的選舉中更易獲勝,從而成為集社會性精英和村莊權力精英于一體的人物。調研發現,這種情況在江西農村較為普遍。
以江西余江Q村為例。該村宅基地使用存在一戶多宅、一宅超面積、村莊空心化嚴重、違章建房多等情況。Q村所在鄉鎮一戶一宅的有3 065宗,一戶多宅223宗。由此,宅基地制度改革的主要目標包括兩個:一是盤活存量。通過宅基地有償退出和有償繼續使用制度,解決宅基地利用粗放的問題。二是規范增量。通過合理控制宅基地規模,確定宅基地審批面積實現建房規范化,杜絕一戶多宅的亂象。Q村下轄的Y自然村成為余江區宅基地制度改革的試點村,改革目標是加強小組的宅基地管理,解決因歷史原因形成的宅基地超標準占用、閑置浪費等問題。
圍繞以上任務,村莊形成了宅基地治理的組織、制度、實施方法。Y村依托宗族,將宗族理事會吸納為宅基地治理的社會組織。宗族理事會是以自然村為單位的社會組織。需要說明的是,宗族理事會并非宅基地制度改革中形成的,而是村莊一貫存在的社會組織,其在2011年村莊開展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時,也曾發揮動員農民、籌集資金等作用。在新農村建設項目分配的動員之下,宗族理事會無償參與宅基地制度改革事務。自然村的宗族理事會一般有9~12人,由村民選舉出的房頭代表擔任,其采用“理事會長負總責,理事會成員分片包干”的工作機制。每位理事會成員需負責本房頭村民的有償使用費的收繳工作,及“一戶多宅”、閑置附屬房、廢舊房屋的退出工作。
(二)村民委員會統合:湖北宜城宅基地治理經驗
村民委員會統合是指以村民委員會為載體統合宅基地。村民委員會作為宅基地的治理單元與原集體土地所有權的單位一致,宅基地地權著落的社會單元一般是行政村。其基本做法是通過行政村統一規劃村莊,統一分配宅基地,管理農民建房。湖北宜城H村的宅基地治理主要采取以上做法。
事實上,H村在宅基地制度改革過程中,嘗試過財產化改革路徑,即宅基地使用權抵押貸款,但未普遍推行下去。因為農民貸款有一定的門檻,銀行需核實貸款人的還款能力和貸款用途,還需代理人作擔保;且H村是典型的農業型村莊,農民以農業生產為主,創業的較少,貸款需求不強烈。因此,H村僅有2名80后年輕人用房子抵押貸款,一名貸款開農家樂,一名貸款買挖掘機。由此,宜城的宅基地財產化改革實踐并未得到廣泛推行。即使宅基地確權以后,大部分村民認為房產證作用不大。然而,與宅基地財產化改革低潮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村集體統籌的宅基地治理經驗較為先進。
H村下轄9個村民小組,農戶651戶,其中:一戶多宅638戶,占總戶數的98%;宅基地占地超過200平方米的“超面積戶”共507戶,占總戶數的77.8%;超500平方米的80戶,占12.3%。村莊宅基地使用面積超占、一戶多宅的情況嚴重。基于此,其宅基地制度改革的主要目標是:(1)探索宅基地有償使用制度,對因歷史原因形成的超標準占用宅基地、一戶多宅以及非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通過繼承房屋等占有的宅基地,探索有償使用。(2)探索宅基地自愿有償退出機制,允許進城落戶農民在集體經濟組織內部自愿有償退出或轉讓宅基地。(3)規劃引導農民集中居住,以實現宅基地合理布局,規范用地標準,提高集約利用水平。由此H村村民委員會的主要工作包括收取有償使用費,引導農戶有償退出宅基地,引導農民集中居住,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在村委會統合的宅基地治理經驗中,以村書記為代表的村干部在村莊中的權威很重要。宜城H村作為農業型村莊,村書記是當地的經濟精英兼政治精英。作為村莊經濟能人,其率先帶領農民開展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種植經濟作物,農民增收后,書記也獲得個體在村中的威望。其連續擔任村書記18年,形成了緊密的村“兩委”關系;也曾榮獲襄陽市勞模,當過兩屆襄陽市人大代表,亦敢于向政府申請項目建設村莊。在村書記和村“兩委”的帶領下,H村較早進行了村莊規劃,引導農民集中居住,集約使用宅基地。由此,宅基地治理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簡而言之,雖然江西余江和湖北宜城兩地在宅基地治理主體及地權統合機制方面存在差異,但其均形成了宅基地地權集體化的結果,且在宅基地集體化的過程中形成了一定的政治社會效應(見表1)。
三、宅基地集體化的政治社會效應
宅基地制度改革以來,以東部發達地區為代表的宅基地財產化改革往往被當作重要經驗推廣。事實上,宅基地財產化改革在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方面并無如此巨大的功效,反而是傳統農區基層治理現代化與宅基地集體化互相形塑,將宅基地集體化轉化成傳統農區基層治理的制度優勢。與經濟學單純強調宅基地的經濟資源屬性和經濟效應不同,本文結合實地調研資料,嘗試建立更為綜合的分析框架,探討集體主導的宅基地改革模式對宅基地資源利用效率的影響,及對鄉村治理、鄉村建設的政治社會效應。
(一)提高宅基地管理效率
宅基地制度與宅基地管理的關系是宅基地研究的經典命題。經典產權理論認為產權清晰是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宅基地作為一項經濟資源,在傳統的集體土地所有制背景下,宅基地產權模糊,導致資源配置效率不高[14]。因此,經濟學者主張明確農民的宅基地資格權、用益物權,對宅基地進行市場化的改革[15];通過給農民“賦權”,以提高宅基地的資源管理效率[16]。與東部發達地區不同的是,案例中傳統農區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共性是強化集體對宅基地地權的統合能力,農戶享有宅基地使用權,而無宅基地的私人處分權。實踐表明,賦予村集體配置宅基地資源的權利,能夠提高宅基地資源管理效率。
據中央文件規定,宅基地制度改革主要有保障農民戶有所居,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騰退多余宅基地等三項主要目標。由此,完善農村宅基地管理,主要是在保障農民戶有所居的基礎上,讓農民退出“一戶多宅”的宅基地,以及“一宅超面積”的超標準占地。
1.宅基地退出。余江宅基地管理的核心問題是解決超占多占宅基地的退出問題。據余江縣數據統計,截止2017年7月底,全縣共退出宅基地3 2491宗4 537畝,其中有償退出7 670宗1 071畝,無償退出2 4821宗3 466畝資料來源于余江縣地方政府的匯報材料《上下齊心 砥礪奮進 全域推進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三項十點》,2018-08-16。。通過宅改試點,Q村所在鄉鎮消除一戶多宅158戶,附屬設施625處。同時,余江通過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建立了一套現代化的土地管理制度。無獨有偶,湖北宜城H村2011-2013年間亦做了3個批次的宅基地退出工作,騰退出130畝宅基地,并將其復墾為農地,復墾農地所有權歸村集體,承包權歸農戶。
2.宅基地超標準有償使用。農村地區除“一戶多宅”之外,還有“一宅超面積”現象。對于一戶一宅的超面積占用,改革的底線是保障農民“戶有所居”,不能強制讓農民退出宅基地,為此,兩地均采用收取有償使用費的辦法。譬如江西余江Q村所在鄉鎮共收取有償使用費362戶,金額338 900元。湖北宜城H村根據農房建成年份和面積制定差異化的收費標準,其還將收取有償使用費與村莊綠化結合起來,規定村民院子內種植直徑5公分以上的樹木,每棵按照5平方米的有償使用款標準返還。截止2016年,全村收取有償使用費19.1萬元,共646戶,占應收比例的99.3%。
(二)推進鄉村建設
傳統農區宅基地地權集體化以后,便于集體統籌村莊建設用地推動鄉村建設。據調研顯示,宅基地退出后,鄉村建設路徑有兩種:一是以“拆舊建新”的方式開展新型社區建設,通過村莊整體規劃,以推動農民集中居住;二是以“空心村整治”的方式對布局不合理的村莊進行整治,加快公共基礎設施的投入。前者以湖北宜城為例,后者以江西余江為例。兩種方式均能提高宅基地集約利用水平,改善村莊公共基礎設施。
湖北宜城主要通過“拆舊建新”方式推動新型社區建設。其主要做法是行政村統一規劃建設用地選址,農戶可自行協商換地,或以每塊地6 000元的價格向其他農戶購買,村“兩委”幫忙協調。每塊宅基地占地315平方米,建設兩層半,村干部出面請縣國土局、城建局做好規劃,房屋占地面積、高度、朝向等均設計好,農戶按照村集體的規劃建房。用村集體經濟做好房前屋后的道路硬化、綠化、路燈等配套設施。截止當前,宜城H村80%農戶集中居住在村里統一規劃的新農村。此外,H村收取的有償使用費由村、組單獨核算,專款專用于本村本組的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第一輪有償使用費收取以后,經村“兩委”協商,為全村安裝了48盞路燈。
江西余江則通過“空心村整治”的方式結合新農村建設。其主要做法是通過宗族理事會做群眾工作,讓農民退出“一戶多宅”的宅基地,拆除廢舊的祖屋、附屬房。并將新農村建設的項目分配給宅基地制度改革成果優秀的村莊,以此激勵農民退出多占的宅基地。截止2016年,Y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且通過宅基地制度改革促進了美麗鄉村建設,獲得了“余江區十佳美麗鄉村”。據全縣數據統計,截止2018年7月,余江縣新修村內道路478公里,溝渠490公里,新增綠化面積860畝。幫助完善農村道路、水電、通信、文化、休閑、教育、衛生、幸福樓等基礎設施。
(三)提升基層治理能力
與發達地區宅基地的經濟發展能力相比,傳統農區宅基地具有較強的治理能力。雖然這與區位因素有關,但不能忽視宅基地的制度基礎。事實上,已有研究表明,農村集體土地所有制及其實踐,是鄉村治理最基本的制度資源[17]。與宅基地財產化改革強化農民個體土地權利削弱集體土地權利相比,傳統農區宅基地集體化,有利于村級組織主導宅基地制度改革,對村民形成政治動員,重建利益博弈的政治空間,提升了基層治理能力。
1.通過宅基地制度改革重建了利益博弈的政治空間。“政治”的本質是利益博弈,通過利益博弈達成多方利益的均衡是政治過程的最主要內容[18]。盡管利益博弈在江西余江體現得最充分,譬如房頭代表之間探討宅基地退出的補償標準、宅基地有償使用的標準、項目落地的選址等。然而,在湖北宜城H村,關于建房的選址、規劃、宅基地制度改革中的村規民約商定,也是利益博弈的過程。而兩個村莊中,治理“釘子戶”均體現了個體利益與公共利益的博弈過程。
2.宅基地制度改革中強化的集體土地所有制、村規民約、基層組織建制等,為后期的鄉村治理留下制度性遺產。作為基層治理體系的一部分,宅基地制度改革路徑,關系到農村土地制度優勢能否轉化為基層治理的體制機制優勢。Y村和H村均在宅基地治理中,打破了村莊以往的宅基地管理制度,結合村莊實際制定了新的土地管理制度,并以“村規民約”的形式保存下來。這些制度不僅有利于建立良好的村莊土地管理格局,還能強化集體土地所有制,凸顯集體在土地管理、村莊治理中的角色與作用,并為農民參與村莊政治提供了條件。由于宅基地申請、分配、使用、退出補償等事項與農民的具體利益相關,農民被充分動員起來,而宅基地治理中制定的制度、規約,也沿用至其他治理事項。
綜上所述,發達地區農村宅基地財產化改革更加注重農民增收的經濟效應。而傳統農區宅基地的財產屬性不強,宅基地改革形成的地權集體化在完善宅基地管理、推進鄉村建設、提升基層治理能力等方面,形成了政治社會效應。
四、宅基地集體化的結構性條件
當前,在農地市場化改革和宅基地財產化改革的背景下,農民難免對土地產生“類所有者”想象,集體在土地治理中的角色和功能不斷被架空。但江西余江、湖北宜城均通過挖掘本地的政治社會資源,將宅基地治理得良好、有序,這對其他中西部地區的宅基地治理具有借鑒意義。由此,筆者將總結兩地宅基地地權集體化的結構性條件,揭示傳統農區可資利用的資源。
(一)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制度基礎
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是存在于農村地區的一定范圍的勞動群眾或人群共同體對土地等生產資料共同占有基礎上的個人所有制。其內容是共同體內的每個成員均平等地與其他成員共享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并在對生產資料的共同支配中實現成員的個體利益[19]。據《憲法》第10條規定:“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于國家所有的以外,屬于集體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屬于集體所有”。《土地管理法》也明文規定:“集體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屬于村農民集體所有,由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或村委會經營、管理;村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已經屬于鄉鎮農民集體經濟組織所有的,由鄉鎮農村集體經營、管理。已經分別屬于村內兩個以上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農民集體所有的,由村內各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小組經營、管理。”由此,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內涵主要包括兩個方面:其一,所有權歸農村社區的人群共同占有,不可分割;其二,集體土地的經營管理者歸集體,具體而言包括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村委會或者村民小組。實踐中,湖北宜城和江西余江均執行了土地集體所有制,其成為宅基地地權集體化的制度基礎。
據宜城H村土地管理村規民約規定:“宅基地歸集體所有,村委會統一管理,村民只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其制定了宅基地申請、使用、流轉、退出的嚴格程序。(1)宅基地由個人申請,逐級上報審批,鎮土管所、城建所發給建房許可證,再由土地、城建、村委會、村小組現場劃地。(2)農戶新建房必須按照全村統一規劃。建房面積、高度、戶型、門向、下水道埋沒,均按村流標準實行,開工建設須交3 000元保證金。房屋竣工經村委會驗收后,退還保證金。(3)買賣房屋,轉讓宅基地使用權的,須經村委會出具證明,到鎮土地、城建、財政按有關規定辦理手續后,購方才有使用權。(4)新房建成后須將舊屋拆除以退出宅基地。H村的土地管理村規民約與農民利益密切相關,雖然建房交保證金這一規定并無國家明文規定的制度合法性,但村集體可以通過召開村民大會,以民主集中制推行了下去。另外,據湖北宜城市規定,宅基地制度改革過程中村集體以行使“初始分配權、劃歸主導權、監督管理權、宅基地收回權、集體收益權”等五種權利方式,夯實宅基地集體所有權基礎資料來源于中共宜城市委、宜城市人民政府的匯報材料《宜城市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情況匯報》,2019-10-29。。
而江西余江Y村在宅基地制度改革之前,理事會成員集中培訓制定制度,結合集體土地所有制的政策,商議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認定辦法以及宅基地分配、有償使用、退出流轉辦法和建房管理細則等,明確了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底線是保障戶有所居和不能突破集體土地所有制,并通過宣傳集體土地所有制,讓農民明白土地是集體的,甚至達到了農戶無償退出宅基地的政策效果。從農民的角度來看,無償退出宅基地、交有償使用費、預交押金以保證農民按照村集體規劃建房等行為之所以具有可行性,源于宅基地是集體資產,而非個人財產。
(二)“權責均衡”的治理基礎
社會學強調地權是一個關系束[20],集體地權建立在一系列社會關系的基礎上。具體到宅基地地權包括兩對基本關系:一是集體經濟組織內部的成員與成員之間的關系;二是集體與個體之間的關系。由此,宅基地地權的集體化強調的是宅基地作為集體資源的公共屬性,它需實現個體之間利益的公平性以及個體與集體之間的權利義務對等性。
1.成員之間的公平性、平等性。生產資料公有制是我國宅基地制度的起點,村社集體向農民分配宅基地,才形成宅基地的公有私用制度。由此,宅基地的集體所有權不具備一般意義上財產所有權的私有、排他屬性。宅基地作為一項公共資源,需實現集體內部資源的公平配置[21]。本文案例中,江西余江不僅保障了農民在宅基地資源分配、使用、退出中的公平,而且還保障了宅基地制度改革中收取的土地利益分配的公正。譬如對于公共建設項目的類型、選址、建設的先后次序等事項,均開展民主商議。宅基地改革中的所有支出需經宗族理事會會長審批和理事會集體研究決定,較大額度的支出需要經村小組會議討論通過,并將信息張貼公示,以保證公平公正。湖北宜城同樣強調宅基地管理的公平性,新社區的建設經過統一規劃,農民的宅基地占地面積、建房高度都是平等的。
2.成員與集體之間的權利義務對等性。集體內部能夠“算平衡賬”是地權集體化的治理基礎。“算平衡賬”是集體利益分配的內部平衡機制,表現為調整集體和農民之間的權責利關系[22]。其本質是集體與農民之間的“利益博弈”,即通過集體與農民的緊密互動,實現兩者的權利義務對等關系。從農民的角度來看,宅基地地權集體化產生的直接利益包括開展新農村建設,完善村莊公共基礎設施。在余江和宜城,村莊均通過收取宅基地有償使用費,開展村莊公共基礎設施建設。這些公共利益的分配需經過村民會議表決,在公共規則限定的框架下分配。一旦這些公共利益的分配成為大部分農民的呼聲,那么村莊公共建設便成為集體利益的代表。村社組織能夠成為集體利益的代理人,與阻礙集體利益實現的極少部分個體利益代表者“談判”。實踐中,宜城H村通過 “算平衡賬”的方式治理“釘子戶”,以“經濟賬”與“政治賬”平衡的手段,限制“釘子戶”個人利益,以保障村莊宅基地治理順利完成。譬如對于不按時繳納宅基地有償使用費的農戶,待其子代申請宅基地建房時,村里不予分配宅基地;對于村民需要集體經濟組織開具證明的事項,村里不予開具證明。無獨有偶,江西余江的宗族理事會成員以宗族公共身份,要求小家庭服從宗族內部的利益,個體的私人利益要讓位于村莊公共利益,否則個體可能在宗族祭祖、紅白事等公共事務中被孤立。
強調宅基地地權關系中的權利義務對等性,是由于當前宅基地制度改革過于強調地權的經濟屬性,而未注重地權的社會屬性及其蘊含的權利義務關系,因而,宅基地財產化改革雖嘗試增強農民的財產權利,卻會因為缺少“權利”和“義務”之間的微觀通道,而導致個體“權利”的實現缺少公共性的村莊社會基礎。由此,鄉村社會若想通過宅基地制度改革促進鄉村治理,則需保障農民在宅基地資源配置方面的公平性;重建農民與集體在宅基地權利分配上的權利義務對等關系以及權責利相匹配的利益關聯機制。
(三)政府支持的政治空間
宅基地集體化的實踐也離不開政府的支持,其包括兩個層面:一是政府賦權給基層組織的制度創新空間;二是政府的領導和權力支持。
1.政府放權與基層組織的制度創新。相較于農地制度改革,當前宅基地制度改革還未進入完全成熟的階段,因而政府放權能夠激活基層社會的制度創新,使得超越于財產化改革的宅基地治理改革成為一種改革樣態。當然,地方政府為加強宅基地管理,有效實施村莊規劃,必須借助村社集體的力量進入村莊。而村集體得以通過宅基地制度改革的事件,將過去多年因農地制度改革造成的土地物權化,或因宗族村莊結構導致的宅基地祖業化的土地權利重新“集體化”。案例中宅基地治理較好的村莊,均是借助村民自治組織管理宅基地,湖北宜城以村“兩委”為代表,江西余江則是宗族理事會。基層組織最重要的功能是執行政策和開展群眾動員,他們應是能夠承接國家政策并實現在地轉化的能動性政治主體。事實上,傳統中西部農村存在類似的組織資源能夠成為宅基地治理的組織載體。按照當前農村的組織機構設置,大部分農村的集體經濟組織與村委會、基層黨組織,“三塊牌子,一套人馬”,由此,村“兩委”與村民小組能夠成為管理集體土地的主體。
2.政府的領導。缺少政府宏觀的政策和制度引導,完全依靠基層社會組織亦難實現宅基地治理現代化。譬如余江是宗族性地區,如若缺少政府領導,宗族理事會全權主導的宅基地制度改革容易成為家族主義的制度實踐,延續祖業產權規則而非集體產權。由此,在政府領導之下,調動基層自治組織參與,才是宅基地地權集體化的重要經驗。此外,政府也需給予必要的權力與資源支持。以余江為例,地方政府賦予宗族理事會多項土地管理權力,涉及到權利的有12條,職責的有15條。從這些條款的內容來看,除了必須由鄉鎮政府及國土、規劃部門完成的行政審批事務,幾乎絕大多數土地管理權力下放到自然村的宗族理事會。資源則包括宅基地管理過程中的配套項目支持等。
綜上所述,土地集體所有制構成宅基地地權集體化的制度基礎,“權責均衡”機制構成地權集體化的村莊治理基礎,而政府的放權與支持為地權集體化創造政治空間,三者均為宅基地地權集體化的結構性條件。
五、結論與討論
宅基地制度改革是國家發起的旨在提高宅基地管理能力和擴大宅基地權能的體制改革。由于多樣化的改革創新,宅基地制度在全國呈現多種樣態,是制度變遷研究的重要命題。實證研究發現,傳統農區宅基地制度改革超出了當前財產化改革的政策范疇,踐行了地權集體化改革。基于村莊社會結構的差異,集體統籌宅基地制度改革的主體不同,江西余江是宗族社會組織統合,湖北宜城則為村民委員會統合。集體統籌的宅基地制度改革模式超越了保障農戶財產性收益的經濟效應,形成了綜合的政治社會效應,有利于完善宅基地管理,推進村莊建設,提升基層治理能力。
縱觀宅基地地權集體化的歷史進程,有經濟學家認為我國歷史上首次宅基地地權集體化實踐,是《人民公社六十條》制定時,“一不小心順手就把向來是農民私有的宅基地,帶入了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框框”[23]。對于此觀點,有學者認為1956-1962年農村宅基地所有權的“集體化”并非人民公社化運動過程中頭腦發熱的產物,而是當作為“生產資料”的農地全部集體化,農村無法解決新增宅基地“化公為私”的困境,因而通過制度創新將宅基地所有權進行集體化改造,并最終被中央政策接受[24]。反觀當前的宅基地財產化改革,由于傳統農區宅基地“有價無市”、財產屬性不強。因此,部分傳統農區從實踐出發,并未將改革的重點放在增加農民財產性收益上,而是強調宅基地的集體屬性和治理屬性,并為政府所支持,由此形成傳統農區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創新。這說明無論在哪個階段,制度改革需要回應廣大農民的真實需求。唯有如此,才能有效整合各方面的資源,將農民動員起來參與到宅基地制度改革及其他重大的改革之中。
簡而言之,當前以經濟學私有產權理論為代表的研究,過于強調宅基地的經濟屬性,強調宅基地制度改革增加農民財產性收益的經濟效應,并將集體土地所有制視為人民公社化運動后遺留的“負資產”,認為集體產權的邊界模糊,不利于宅基地流轉和農民財產收益的增加,由此要將集體土地確權、流轉[25]。筆者認為,當前傳統農區宅基地集體化的實踐表明,上述觀點忽視了宅基地集體化的現實合理性及其政治社會效應。在傳統農區,農民城市化進程還未完全實現的前提下,宅基地依然是對農民具有保障性的社會資源。由此,傳統農區宅基地制度改革應該依靠集體的組織能力,加強宅基地管理,并借由宅基地制度改革提高基層治理能力,推進鄉村建設。
參考文獻:
[1] 劉守英,熊雪鋒.經濟結構變革、村莊轉型與宅基地制度變遷——四川省瀘縣宅基地制度改革案例研究[J].中國農村經濟,2018,4(06):2-20.
[2] 陳丹.宅基地“三權分置”下農民財產權益的實現路徑[J].農村經濟,2020(07):54-62.
[3] 段瑩,李冰,辛林.實現農村住房財產權的法律研究[J].農業經濟,2020(04):105-106.
[4] 吳群,舒美惠,吳茉謠,等.農民住房財產權抵押的實現路徑及影響因素研究[J].中國土地科學,2021,35(01):40-47.
[5] 茍正金,吳煒.宅基地使用權退出法律規制研究——以江西省某縣為調查對象[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9,40(07):82-86.
[6] 王增寶.基于宅基地使用權流轉的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對策研究[D].鎮江:江蘇大學,2019:25-32.
[7] 周江梅,黃啟才,王熒.共同、共享發展視野下農戶宅基地節余指標異地流轉的利益均衡[J].農村經濟,2019(12):66-72.
[8] 姜立忠.農村開展宅基地有償選位的做法與思考[J].浙江國土資源,2009(08):21-22.
[9] 賀雪峰.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政策的邏輯與謬誤[J].學術月刊,2019,51(01):96-104.
[10] 夏柱智.有限市場:宅基地財產化改革的制度實踐及解釋[J].農村經濟,2020(03):34-40.
[11] 王向陽.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中西部傳統農區宅基地制度改革研究——以湖北宜城宅改為例[J].山東行政學院學報,2019(06):30-35.
[12] 王向陽.超越“保障權”與“財產權”:宅基地改革的治理路徑探析——基于江西“余江宅改”的案例分析[J].理論與改革,2019(05):153-165.
[13] 邱麗.善治視域下的宅基地制度改革[J].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19(01):1-9.
[14] 姚如青,朱明芬.產權的模糊和制度的效率——基于1 010份樣本農戶宅基地產權認知的問卷調查[J].浙江學刊,2013(04):158-163.
[15] 呂軍書,賈娟.提高我國農村宅基地使用效率的途徑分析[J].求實,2012(02):39-43.
[16] 張也.“三權分置”、宅基地流轉與利用效率研究[D].武漢:華中農業大學,2020:21.
[17] 桂華.產權秩序與農村基層治理:類型與比較——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政治分析[J].開放時代,2019(02):36-52.
[18] 陳義媛,甘穎.土地調整的政治邏輯:對土地集體所有權的再思考[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19(02):102-111.
[19] 韓松.集體所有制、集體所有權及其實現的企業形式[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40.
[20] 臧得順.臧村“關系地權”的實踐邏輯——一個地權研究分析框架的構建[J].社會學研究,2012,27(01):78-105.
[21] 桂華.公有制視野下宅基地制度及其改革方向辨析[J].政治經濟學評論,2015,6(05):179-195.
[22] 賀雪峰.農民組織化與再造村社集體[J].開放時代,2019(03):186-196.
[23] 周其仁.土地不準流轉的由來[N]. 經濟觀察報,2013-03-25(48).
[24] 田傳浩.宅基地是如何被集體化的[J].中國農村經濟,2020(11):29-46.
[25] 周其仁.確權是土地流轉的前提與基礎[J].農村工作通訊,2009(14):40.
Collectivization of Land Right:the Logic of the Reform of Homestead System in Traditional Rural Areas
QIU Li1,2
(1.Institute and Department of Marxist Philosophy and Chinese Modernization,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275;2.School of Marxism,Guangzhou University,Guangzhou 510006,China)
Abstract:Due to the diverse system innovations at the grassroots level,the reform of the homestead system in traditional rural areas has gone beyond the path of property reform advocated by the current policies,and a new theoretical generalization is needed.This article takes the case of the homestead system reform in two villages as the analysis object,and examines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effects and structural conditions of the collectivization of homestead land righ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eform of the homestead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ance.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collectivization of homestead land rights in traditional rural areas surpasses the economic effect of protecting farmers’ property rights,and has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effects of improving homestead management efficiency, promoting village construction,and improving grassroots governance capabilities.The realization of the collectivization of homestead land rights depends on the institutional basis of rural 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the governance basis of “balance of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and the political space supported by the government.Studies have proved that the key to the reform of the traditional rural housing land system is not to expand the powers and capabilities,but to achieve effective governance of the housing land. In the reform of the homestead system, the rights of the “collective” can be activated.Therefore,the reform of the homestead system needs to leave room for the village collective to practice its ownership.
Key words:homestead system;rural land right;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areas
(責任編輯:董應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