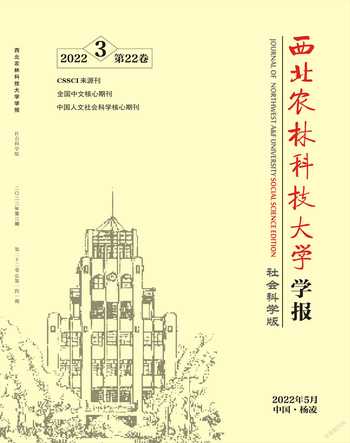農戶政治身份對綠色農業生產技術的引領效應












摘 要:基于身份經濟學理論,在將引領效應分為帶頭效應和帶動效應的基礎上,構建了黨員、村干部發揮引領效應的分析框架,利用秦巴山區678戶茶農的調查數據,采用泊松回歸模型分析了黨員、村干部對綠色生產技術的引領效應。研究發現:第一,在淺綠色生產技術和深綠色生產技術采納中,黨員、村干部不僅發揮了帶頭效應,而且通過“傳、幫、帶”的方式帶動了非政治身份戶對綠色生產技術的采納。第二,黨員、村干部在帶動非政治身份戶采納綠色生產技術時呈現“差序格局”,優先帶動親屬農戶,關系密切農戶次之,關系疏遠農戶最后。第三,“傳、幫、帶”在黨員、村干部帶動非政治身份戶采納不同綠色生產技術中效果存在差異,即在淺綠色生產技術中,“幫”的效果最優,“傳”次之,“帶”最差,“傳”與“幫”存在顯著的交互效應;在深綠色生產技術中,“帶”的效果最佳,“幫”次之,“傳”最后,“傳”與“帶”存在顯著的交互效應。
關鍵詞:政治身份;帶頭效應;帶動效應;綠色生產技術
中圖分類號:F325.1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07(2022)03-0148-13
收稿日期:2021-09-30" 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22.03.18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71873102);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項目(18YJA630124)
作者簡介:薛彩霞,女,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資源經濟與環境管理。
引 言
2020年6月中國農科院發布的《中國農業綠色發展報告2019》顯示,2012-2018年全國農業綠色發展指數從73.46提升至76.12,農業生產方式持續由黑色發展向綠色發展轉型,這得益于中國政府對農業綠色發展的政策推動[1],但也離不開廣大農戶對農業綠色發展政策的認同和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