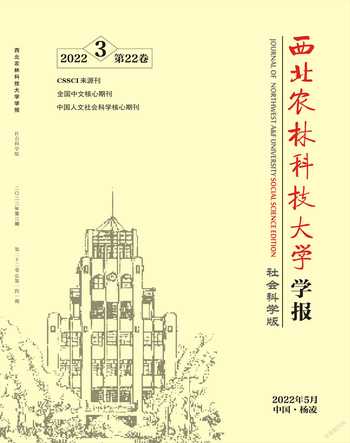從股權配置看集體經濟組織的封閉性與開放性


摘 要: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中股權配置的目標是突破集體經濟組織股權流動的封閉性,為后續股權流動創造條件。基于昆明市27個村莊的實地調研,重點關注股權設置、股權管理模式、成員增減后的股權管理模式以及股權流轉等方面的實踐對集體經濟組織封閉性與開放性的影響。實踐證明,集體經濟發達程度是影響股權量化和分配具體方式選擇的重要因素,而這也直接會對集體經濟組織封閉性和開放性形成產生影響。現階段,股權還是作為身份權利呈現,但未來將逐漸發揮其經濟權利的功能。因此,以注重經濟屬性為基礎的開放性的集體經濟組織將會成為未來發展的方向。
關鍵詞:股權配置;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產權制度改革;股權流動
中圖分類號:F321.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07(2022)03-0098-07
收稿日期:2021-09-11" 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22.03.12
基金項目:云南省省院省校教育合作項目(SYSX202014);云南省組織部和云南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的基層科研工作站項目(201904)
作者簡介:唐麗霞,女,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貧困與農村發展、國際發展援助。
在農村城鎮化和工業化發展新形勢下,生產力發展對生產關系調整提出新要求,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也對農村集體產權制度安排提出了新標準。如今,在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背景下,農村集體制度產權改革工作的順利開展和穩步推進在組織振興和產業振興方面將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從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推進農村集體產權股份合作制改革,到2016年新時期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綱領性文件《關于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的出臺,再到2020年中央一號文件要求全面推動開展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并在“十四五”時期將產權制度改革和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取得重大進展作為目標之一,國家每年都在逐步推進相關工作。從探索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辦法到明確農民六項基本權能,從規定開展工作范圍到明確產權制度改革工作節點,按照規劃2021年底要基本完成全國農村集體經營性資產股份合作制改革,現階段正處于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攻堅時期。
在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過程中,股權配置環節既承接身份認定又為后續確權和分紅提供基礎。股權配置的目標是實現股權流動,激活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活力,為農村集體經濟增值提供發展空間,最終達到村集體和農戶經濟權益有效實現,實現共同富裕。如今大多數農村股份合作經濟組織的產權是以村域為邊界劃定的,股權配置范圍局限于村域內部,具有顯著的封閉性[1],加之現階段相應體系建設和市場環境并未給農村集體資產股份流動創造條件,在此基礎上實現股權流動是十分困難的。因此,只有在股權配置階段創新股權管理模式,才能突破集體經濟組織的股權流動封閉性,為后續股權流動創造條件,為未來實現股權流動的目標打下制度基礎。為實現未來股權流動的目標應該先關注股權配置對集體經濟組織封閉性與開放性的影響,是否可以通過創新管理方式達到促進集體經濟組織開放性的目標。股權配置的工作如何進行,在實現股權流動方面的是否已經有了實質性推進,是否已經在促進集體經濟組織開放性上做出努力,值得進一步關注。
一、文獻回顧
目前,學界對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關注比較多,大多從公共管理和法律規制等領域入手。從公共管理視角出發關注相關政策設計制定和實施情況。在確權賦能領域關注農戶如何能夠公平享受對集體資產股份占有、收益、有償退出及抵押、擔保和繼承權,這些研究對現階段推進權能改革持慎重穩妥態度[2];在村社組織建設方面,關注國家、集體和個人在制度改革方面的作用機制,以及政經分離對改革的作用[3]。
中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實踐工作主要由清產核資、成員界定、資產量化、股權配置與管理、成立集體經濟組織等核心環節構成。農村集體資產股份量化到人、明晰產權是中國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三大核心內容之一[4]。因此,股權設置在整個改革過程中居于重要地位,直接決定著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集體收益分配權的享有和行使。由于在實踐中股權量化操作性較強,采取的具體工作方式也有不同,因此在關鍵問題上呈現不同路徑選擇,主要差異集中在集體股設置和股權交易范圍界定兩個問題上。集體股的作用主要是為集體公共支出提供資金儲備,發揮集體在公共事務上的功能和作用。但是隨著改革持續推進,集體股的設置實際上被認為增加了產權的模糊度,為后期二次分配留下隱患[5]。尤其是在農業人口轉移和鄉村振興人才吸引兩方面作用下,集體經濟組織成員邊界勢必會被打破,集體股份價值如何評估需要進一步探討[6]。由于中國農村發展的特殊背景,具有為成員提供公共服務的集體股權在改革初期和集體經濟發展條件不成熟時有設置的必要性[7]。針對股權交易范圍,2016年國家明確指出有償退出不能突破本集體經濟組織范圍,一切合作制改革都只能在農村集體經濟內部進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不僅承擔著農村集體經濟經營管理職能,還承擔著提供公共產品供給的職能,完全開放在目前階段條件還不具備,但隨著人口和資本流動性的增大,其與農村集體產權結構封閉性的矛盾也將越來越突出[8]。有學者從市場經濟角度出發指出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只有股權自由流轉才能實現生產要素的優化組合,未來股權流動將有條件地突破集體經濟組織邊界,實現產權流動的逐步開放[9]。
現有研究對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關注呈現多樣化,就產權改革三大核心內容之一的股權配置,學者們有不同的見解,包括是否設置集體股,股權交易范圍是否限制在集體內部等。但是在股權配置與股權流動領域關注較少,對未來是否放開股權流動也存在相反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由于集體經濟組織本身承擔的社會服務職能過多,不能讓股權交易范圍突破集體經濟組織自身范圍;然而相反的觀點認為,只有實現股權流動打破界限才能實現產權改革的真正目的。可以看出其爭論的焦點在集體經濟組織對股權流動的封閉性和開放性程度。而如今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已經在全國實行,對關鍵問題的理解需要從基層實際出發,聚焦集體經濟組織在股權配置環節的工作方式和內容,從實踐中了解不同方式的選擇依據和對集體經濟組織封閉性與開放性傾向的深層邏輯,為未來更廣泛的產權改革實踐提供方向。我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先后推出了五批試點,實踐經驗文章都是將重點放在對先行試點的模式分析、經驗總結和實踐推廣;而先行試點地區大多集體經濟發展程度高,與后試點地區集體經濟發展程度一般的現狀有一定的差距,因此某些經驗或者方法的適用性和應用性不強。而作為第五批整省區試點之一的云南省,主要工作重點就包括完善農民集體資產股份權能。因此,昆明市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可以對經濟狀況相似的西南地區產改工作提供借鑒。
二、村集體經濟組織在股權配置環節的不同行為選擇
2018年12月29日昆明市制定出臺《關于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在全市展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而事實上昆明市宜良縣和富民縣就分別在2017年和2018年被選為全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第二批和第三批試點單位,且宜良縣在2019年被農業農村部選定為第一批全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經驗交流20個典型單位之一。昆明市縣區在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進程中呈現三個階段,即改革起步階段、改革推進階段、改革成熟階段。筆者走訪了5個縣區中的21個街道的27個村莊,覆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三個階段。在股權管理模式、股權設置、成員去世后的管理模式以及流轉等方面,各集體經濟組織實踐內容各不相同,而這反映了各集體經濟組織在價值取向和經濟發展方面的差異。
(一)股權設置:集體股、成員股及特殊類型成員股
目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都遵循“一人一股”的原則設置了成員股,而在集體股或成員股中設置特殊類型股份的并不多。集體股是集體經濟組織的全體成員作為股東共同行使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資產量化份額的所有權,體現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核心要義。集體股的設置可以為日后集體公共開支提供資金支撐,緩解集體組織社會性支出和提供公共產品的資金壓力。在成員股下,很多集體經濟組織又會選擇設置特殊類型成員股,該類型股份在政策指導中已經明確并對其中幾個類型的含義和使用范圍已有說明,包括勞齡股、土地資源股、敬老股、獎勵股、機動股、扶貧股等。實踐中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選擇有所不同。因此,在實踐中存在四種類型股權設置模式,即“集體股+成員股”“集體股+成員股(含特殊類型成員股)”“成員股”和“成員股(含特殊類型成員股)”。
調研中發現是否設置集體股與農村集體經濟是否發達沒有直接關系。一些集體經濟發達的集體組織自身就擁有一定資產收益,不需要在股權設置中再設置特殊股份用于收益分紅;而一些集體經濟較弱的集體組織,經濟基礎不牢固,也不會過多考慮集體的收支情況,更傾向于全部設為成員股的模式。由于目前農村集體制度產權改革還處于探索階段,存在因集體股配置不完善導致的產權歸屬不清、再分配隱患等風險,因此大多數村莊還是傾向于只設置成員股。為避免出現集體組織無資金可用的情況,未設置集體股的經濟組織都會在成員分配收益前進行公積金等項目的計提。
成員股中特殊股份的設置情況并不是很普遍,只有部分集體經濟發達的集體組織會設置特殊股份。宜良縣J街道b社區某小組設置敬老股,股份份額為25%,由本村小組年齡達 60歲以上村民享受,并實行動態管理,年底進行增減。宜良縣J街道k社區在成員股中設置村齡股和土地股,這種特殊股份中村齡股占60%,從1984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止所有在冊人口享受(注:五類人員、農轉非人員、戶口遷出或正式領取財政工資之日起村齡股止);土地股占40%,必須是持有土地承包經營權證的人員才能享受。設置特殊成員股可以體現敬老愛老的傳統,也可以通過其他條件標準設置以調動成員的勞動積極性。沒有設置特殊成員股的集體經濟組織大多經濟實力一般,更傾向于先實現一人一股的收益分紅。
除了特殊股份外,在實踐中出現“按百分比持股”的情況。在一些集體經濟發達的村莊,在身份認定環節要求嚴格,多采用靜態管理模式。因此,一些婚遷人口和新生人口由于沒有獲得集體經濟組織認定身份,無法獲得集體經濟組織股份。為了維護該類群體的利益,集體經濟組織會“按百分比持股”。給予非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股份分紅,可以理解為福利或者補貼。如五華區A街道d社區部分小組將成員認定名冊上的成員認定為滿股,婚遷和新生成員享受50%股權,5年后轉為滿股;而h社區針對基準日之后戶口遷入本居民小組的未享受股份人員,不配置股份及股權,享有年終分配滿股40 %的待遇,過節慰問品同等享受。這種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合法權益,也可以減少由于硬性規定導致的某些群體在特定時期無法享受福利的情況,減少社會矛盾的出現。
(二)股權管理模式:靜態管理、動態管理和動靜結合
股權管理模式主要分為三種類型:靜態管理、動態管理和動靜結合管理。在昆明市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股權量化中,三種形式的管理周期分別為30年、5年和1年,使用范圍最廣的為靜態管理,其次是動靜結合和動態管理。靜態模式既保障了集體成員的權益,節約了管理成本,也有利于維持村集體股權的穩定,減少股權糾紛,為股權流轉創造條件。動態管理模式能夠在一定時期內隨著人口增減而相應調整股權配數,充分調動新增人員為本集體經濟作貢獻的積極性。動靜結合有效地吸收了兩種方式的優點,在保證股權穩定的同時也保留了靈活性。
在村集體經濟組織層面,影響其選擇股權管理方式的決定性因素是村集體經濟的發達程度(見表1)。調研中發現,集體經濟較為發達的集體組織有足夠的資金進行分配,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也十分關心和關注自身的分紅收益情況,因此穩定性對于該集體經濟組織來說是最重要的。很多早期發展起來的集體經濟組織,原有股權量化分配機制逐漸運行平穩,集體組織內部成員對已有機制認可度和接受度高,認為沒有改動的必要性;加之,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數量變化和內部結構復雜,改革面臨的風險較大,因此該類型集體經濟組織傾向于選擇穩定性較高的靜態管理模式。對于集體經濟不發達的集體組織,本次清產核資和股權量化后,集體經濟可供收益分配的資金極少甚至沒有,分紅對組織成員來說沒有意義,且在此輪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后集體組織會進一步加快集體經濟發展步伐,需要更加靈活的股權管理方式與之適應,因此該類型集體經濟組織更傾向于選擇靈活性更強的動態管理模式。而對于大多數有部分經營性資產的集體經濟組織,需要穩定的分紅收益運行制度,也需要為未來集體經濟發展預留空間,會選擇動靜結合的股權設置方式。
(三)增減成員股權管理模式:戶內繼承、重新劃分股份
由于股權管理模式調整周期的存在,會出現在非調整期當年的人口變動按照何種標準計算股權的問題。實踐中,除動態管理一年一調整外,動靜結合和靜態管理都會面臨這一情況。面對非調整期當年出現的人數變動,集體經濟組織主要采用戶內繼承和重新劃分股份的形式進行調整。
第一種,戶內繼承。當該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去世后,直系家屬擁有其股份的繼承權,集體并不會收回;若該成員無繼承人,股份收歸集體所有。尋甸縣q村w小組采用靜態管理模式,新增人口通過分享家庭內擁有的集體資產權益,按章程獲得集體資產份額。五華區J街道k社區規定股份量化到個人,個人可以享有繼承權,但只能是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直系親屬,該股份可以在本村內轉讓,但個人持股不能超過總股數的5%。聯合社成員戶整戶滅失時,啟用股份繼承程序,股份繼承根據《繼承法》有關規定辦理。繼承人為2人以上(含2人)時,應當共同協商確定后委托其中1人行使股權。五華區A街道d社區某小組則對直系親屬認領股權時間進行了規定,按火化證的日期5年內直系親屬可以繼承,超過時限則不能認領。尋甸縣R鎮q村村委會則對股份繼承原則進行了明確說明,集體經濟組織依據法律法規制定本集體經濟組織股權繼承辦法。原則上繼承人憑股權繼承法律文書或集體經濟組織出具的股權繼承證明材料,集體經濟組織方可辦理股權繼承手續,進行股權變更登記。
第二種,重新劃分股份。在調整期當年收回去世或遷移人員的股份,由村集體重新劃分。該種方式應用范圍較為普遍,不涉及繼承環節,因此在流程規范上比較簡潔,只需要統計一個調整周期內人口變動情況,凡離世或外遷人口股份一律收回集體。但是該種方式會伴隨人口數量的變動對股份數量產生影響,出現稀釋或者增加每股金額的情況。
(四)股權流轉:不進行流轉、村集體內部流轉、村集體外流轉
相關政策規定現階段農民持有的集體資產股份有償退出不得突破本集體經濟組織的范圍,可以在本集體內部轉讓或者由本集體贖回。實踐中,絕大多數集體經濟組織并未在其集體資產折股量化、股權設置與管理方案中對股權流轉進行說明。調研中發現,沒有對股權流轉說明的集體經濟組織基本沒有考慮過股權流轉這項工作,認為在現有條件下設置相關標準為時過早,且尚未有對該項工作的強制要求和明確指導意見,因此并未將其作為重點工作開展。目前,昆明市僅有極少部分集體經濟組織對股權流轉部分進行了規定和說明,且大多數為集體經濟比較發達的集體經濟組織。五華區A街道c社區規定,在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內部進行股權流轉,每個農戶家庭通過量化或者轉讓、繼承等方式持有的農村集體資產股份,占本集體經濟組織總股份的比例最高不得超過3%。五華區D街道h社區作為集體經濟比較發達的城中村,已經開始了股權流轉的實踐。1993年昆明市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成立時,該社區土地被征用,為更好地分配征地款,該社區開展了身份認定工作,并將1993年12月31日定為基準日,采取靜態管理股權的模式,規定股權可以繼承和流轉。截至2020年底,該集體經濟組織原始配置股權占比98%,流轉股權占比2%。
雖然規定指出股權只能在集體經濟組織內部流轉,但也存在本集體經濟組織股東之外的人員通過繼承取得股份的情況。針對這種情況,多數集體經濟組織對該群體的權利義務進行了說明。流轉給集體經濟組織之外時,新獲得股權的人可以享受股份占有、收益、有償退出、繼承等權益,但沒有選舉權、被選舉權和表決權。通過股權轉讓、退出、繼承等方式持有集體資產的總股份,個人原則上不超過本集體經濟組織總股份的5%,單戶所持股份一般不得超過本集體股份的20%。
可以看出,針對股權流轉工作相關規定較少,真正完成股權流轉的集體經濟組織少之又少。僅有的幾項相關規定也比較簡單,大多存在于集體經濟發達的集體經濟組織中,也說明該項工作還處于探索初期階段。除了股權流轉外,有極個別村莊探索了股權退出問題,但現階段缺乏實踐,僅有相關規定說明。
三、不同行為選擇對集體經濟組織封閉性和開放性的影響
在股權配置環節中,集體經濟組織會根據本集體經濟實際發展情況綜合考量后選擇具體方式。集體經濟發達程度是影響股權量化和分配具體方式選擇的重要因素,而這也直接會對集體經濟組織封閉性和開放性產生影響。本文對集體經濟組織封閉性與開放性的界定主要基于股權流動視角,封閉性指的是股權完全固定于某成員,且長期穩定沒有流動變化;開放性包含兩個層次,第一種是指可以在該經濟集體內部循環聯系,形成內部流動,第二種是指可以和該經濟集體外部產生聯系,形成內外流動。不同行為選擇對集體經濟組織封閉性和開放性的影響見表2。
股權管理模式中靜態管理周期基本為30年,在一個周期內的人員增減均不會對股權配置產生任何影響,只遵照集體經濟成員身份認定基準日當日計算的集體經濟成員人數為準,具體分配方式也嚴格按照最初股東大會通過的規則執行。但30年一個調整周期無法適應農村快速發展的現狀,城鄉資源要素的加速流動會對該管理模式帶來巨大的沖擊,該模式在維持集體經濟組織穩定的同時也在規避和拒絕要素流動帶來的變化,加劇了集體經濟組織的封閉性。而動態管理中,集體經濟組織會根據實際情況接納要素流動帶來的變化,并及時進行調整,促使集體經濟組織實現在內部和內外兩個層次的要素流動。動靜結合的管理模式則是以上兩種模式的混合,在體現封閉性的同時也呈現開放性的特點,本質上還是促進集體經濟組織進一步開放。
就股權設置模式而言,四種模式主要差別在于是否設置集體股和是否在成員股中設置特殊類型成員股,而對封閉性和開放性產生直接影響的為是否在成員股中設置特殊類型成員股。集體股所有權在集體經濟組織,主要用于集體經濟組織公共支出,現階段不涉及股權流轉等問題,因此對封閉性和開放性的影響不顯著。但是該股權類型在未來如何演變會對封閉性和開放性產生影響,若重新劃分給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只是增加每個成員的持股比例,若作為為未來“新村民”等群體股權劃分儲備則會促進集體經濟組織開放性。實踐中,大多數集體經濟組織傾向于設置“一人一股”成員股,基于最樸素的思想,兼顧了集體經濟成員接受程度和實際工作操作難度。但是無論在哪種股權管理模式下,成員股都是嚴格按照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認定結果分配的,并不存在成員之間或者與非組織成員交換的行為,具有明顯的封閉性特征。但是特殊類型成員股會形成集體經濟內部流動甚至是內外流動。敬老股和村齡股將年齡和年數作為劃分股份的主要依據,在動態管理階段也會按照持股人生存狀態及時收回不符合要求的部分股權,這種“回收-發放”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股權在集體經濟成員內部的流動。雖然這種流動并不是自發的且流動范圍仍在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內部,但是已經呈現出開放性的特征。而特殊類型成員股的存在也為今后為吸引和接納“新村民”等群體在制度上預留了空間。
與封閉性和開放性有直接關系的就是股權流轉模式。雖然現階段股權流轉的實踐并不普遍,但實踐中已有部分村集體經濟組織開始推行。不進行流轉具有典型的封閉性特征,而村集體經濟內部或外部流轉均在不同程度上體現了開放性的特征。無論是何種類型的開放,都需要關注每個農戶家庭通過量化或者轉讓、繼承等方式持有的農村集體資產股份的數量,防止出現對集體資產或權利侵占,需要嚴格控制持股比例。實踐中,一些已經開展股權流轉的集體經濟組織一般會將比例控制在3%左右。
而針對成員去世后股權管理模式,無論是戶內繼承還是股份收回集體重新劃分,都可以實現本集體經濟組織內部的股權流動。但是針對戶內繼承的管理方式,該股份依舊歸本戶人口所有,集體并不會收回,實踐中還需要面對兩個問題。第一,股權收益戶間分配差距問題。會出現去世人員在股權非調整區間依舊享受收益分紅等情況,由于家庭年齡結構等因素,會出現戶間收益分配差距,尤其是實行靜態管理模式戶間分配差距會越來越大,存在激發社會矛盾的風險。現階段多數村莊并沒有實現收益分紅,因此并沒有對該問題給予過多關注。但伴隨著收益分配的開始,以及收益分配數額的增多,戶間分配差距會越來越大。即使該種收益方式是通過民主決定或村規民約決定的,但仍不可避免其未來會出現不穩定風險。第二,繼承人的代表性和合法性。戶內繼承后,繼承人獲得被繼承人所持股份,并開始行使選舉權、被選舉權和表決權等權利,享有股份占有、收益、有償退出、繼承等權益。在股東大會等會議召開時,繼承人權利的行使是否能夠代表被繼承人主觀意志。若在表決的環節需要被繼承人的簽字或手印(章)等,在股權證還未及時變更的前提下,在程序上如何做到合法合理。
四、結論和討論:股權是代表身份的權利還是經濟的權利
如今,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是以股份形式將集體股份量化到每個集體組織成員,以明確集體資產的收益權。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對股權量化的工作賦予了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股東的身份,股權的配置讓其擁有了選舉權、被選舉權和表決權,并享受股份占有、收益、有償退出、繼承等權益,前者是代表身份的權利,后者是代表經濟的權利。不同集體經濟組織在股權配置環節的具體方式選擇上均有差異,而這些差異背后代表著對本集體經濟組織未來發展的傾向性,即集體經濟組織封閉性和開放性的傾向本質也是對身份權利和經濟權利的選擇。封閉性傾向于將股權范圍嚴格控制在本集體經濟組織內部,便于管理的同時也可以防止出現非成員人群侵占的風險,更好地發揮集體經濟組織在社會保障等領域的服務,繼續保持其傳統社會職能的發揮。開放性傾向則是將集體經濟組織作為市場經濟的一部分進行考慮,放開股權管理范圍,為今后股權要素對外平等交換和自由流動打下基礎。可以看出封閉性更關注對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利的維護,通過身份的識別將股權交易固定在有限范圍內,側重身份屬性;開放性則不將身份作為唯一識別標準,側重于經濟屬性。
目前,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在全國范圍內推進,首先要確保集體經濟組織順利建立,并通過召開股東大會開展對相關文件的議定工作,確保集體經濟組織在程序上和實體上存在。這一工作的實現是需要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參與的,股權是成員能夠參與進來的必要條件。因此,現階段股權代表的大多是身份上的權利。之所以進行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最終目標是集體經濟的壯大和發展,讓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享受發展紅利。股權作為改革的核心成分,其基本屬性就是交易自由,具備充分的市場流動性。只有讓股權適度流轉,才能活躍農村集體經濟和體現產權制度改革的價值。因此,經濟的權利才是股權存在的最終目標和歸宿。但現階段由于相關規范文件未明確操作說明,缺乏針對性的政策支持,很多集體經濟組織并未開展股權交易等環節的工作。加之股權資產交易平臺搭建不完善、專業人才欠缺,導致股權作為經濟權利的功能無法實現。因此,現階段股權還是作為身份權利呈現,但未來會發揮其經濟權利的功能。隨著城鄉之間要素流動加快,鄉村振興對人才的需求愈發強烈,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與非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交流必將增加,混居將成為常態,可以預見未來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邊界將會逐漸模糊,甚至會被打破。因此,以注重經濟屬性為基礎的集體經濟組織開放性將會成為未來發展的方向。
參考文獻:
[1] 周其仁.產權與中國變革[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7:33-34.
[2] 張浩,馮淑怡,曲福田.“權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理論邏輯和案例證據[J].管理世界, 2021,37(02):81-94.
[3] 高萬芹.村社組織再造及其對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啟示——基于廣東Y市農村綜合改革試驗區的經驗[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21(02):11-21.
[4] 黃延信.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若干問題的思考[J].農村經營管理,2015(01):25-28.
[5] 于國紅.對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若干問題的思考[J].吉林農業, 2019(02):58.
[6] 程民選,黃祖輝,胡偉斌,等.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筆談·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研究[J].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37(06):20-33.
[7] 夏英,曲頌,袁崇法,等.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中的股權設置與管理分析——基于北京、上海、廣東的調研[J].農業經濟問題,2014,35(08):40-44.
[8] 葉興慶.邁向2035年的中國鄉村:愿景、挑戰與策略[J].管理世界,2021,37(04):98-112.
[9] 郭曉鳴,王薔.農村集體經濟股權分配制度變遷及績效評價[J].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18(01):1-8.
The Closeness and Openness of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as Seen From the Equity Allocation
——Based on the Survey of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 System Reform in Kunming
TANG Lixia,ZHANG Yike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Studies,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Beijing 100193,China)
Abstract:The goal of equity allocation in the reform of the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is to realize equity mobility,break through the closed nature of equity mobility of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and create conditions for subsequent equity flows.Based on field surveys in 27 villages in Kunming,the focus is on the impact of equity management mode,equity configuration,management mode after the death of members,and circulation on the closeness and openness of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Practice has proved that the degree of collec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fluencing the selection of specific methods of equity quantification and allocation,and this will directly affect the formation of the closedness and openness of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At this stage,equity is still presented as an identity right, but it will play its role as an economic right in the future.Therefore,the openness of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based on economic attributes will become the direction of future development.
Key words:equity allocation;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property rights reform;equity mobility
(責任編輯:馬欣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