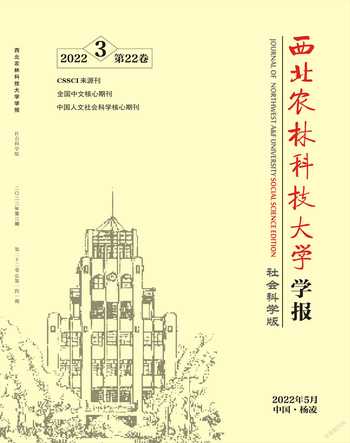鄉村文化的優勢內核、發展困境與振興策略
摘 要:鄉村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底色,也是鄉村振興的價值引領和精神動力源泉,其中所蘊含的鄉土情結、生態倫理思想、耕讀文化、德治文化是最能夠回應當代鄉村振興、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等現實訴求的優勢內核。然而在農業農村以經濟發展為主要驅動力的現代化過程中,鄉村文化被逐漸邊緣化,面臨著載體消失、主體缺位、價值認同危機與話語體系殘缺的發展困境,非但未能發揮其應有的凝聚、引領作用,甚至成為了掣肘鄉村振興進程的短板。在農業農村現代化與城鄉關系轉化的關鍵期,要振興鄉村文化,就必須在繼承其傳統優勢內核的同時,以中華民族的共同利益需求為導向,重新定位鄉村文化的當代價值,并在此基礎上提升鄉村的主體意識與話語能力,講好鄉村故事,同時在全社會樹立起文化共同體意識,從觀念上徹底打破城鄉文化的二元對立,也需要推進政府在文化治理方面的職能轉化與能力提升,完善鄉村文化振興的法制保障。
關鍵詞:鄉村文化價值;文化自信;內核重塑;文化認同;鄉村價值
中圖分類號:G120;C912.8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07(2022)03-0023-09
收稿日期:2021-09-30" 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22.03.03
基金項目:陜西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2019A014);陜西省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項目(sz2037)
作者簡介:楊華,女,西安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思想政治教育理論與實踐。
鄉村振興是黨在脫貧攻堅取得勝利之后,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所提出的新發展戰略,包含產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組織振興五個方面。其中,文化振興作為至關重要的一環,滲透在其他四個“振興”當中,是鄉村振興的價值引領與精神動力源泉。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一直在不斷探尋鄉村文化發展的路徑,但受制于鄉村經濟、教育、資源等因素,文化建設一直都是鄉村發展的短板[1],鄉村文化在城鎮化大潮中逐漸被邊緣化。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首次提出“鄉村文化振興”的戰略決策,將發展鄉村文化作為鄉村振興總體戰略布局中的關鍵一環,這是綜合考量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綜合實力現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鄉村經濟基礎及其現代化發展需要等多方面因素后做出的歷史判斷。脫貧攻堅的成果積累、全國人民文化素質顯著提升,以及新時代城鄉融合發展之大勢,都為鄉村文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振興機遇。
隨著脫貧攻堅取得全面勝利,鄉村發展關鍵詞從“脫貧”到“振興”的轉變中,蘊含著從“基本生存”到“美好生活”的目標調整,也蘊含著從“外生”到“內生”的動力轉化。鄉村文化振興就是要在鞏固脫貧攻堅成果的同時,重建鄉村文化秩序,恢復鄉村文化的“造血”功能,激活鄉村文化自主發展的內生性動力。基于以上現實背景,本文擬從文化本身出發,重塑鄉村文化的優勢內核,探尋鄉村文化突破當下發展困境并實現可持續自主發展的現實路徑。
一、鄉村文化的優勢內核
鄉村文化是孕育中華文明的土壤和智慧源頭[2],鄉村文化的興衰,不僅關系到鄉村的興衰,更關系到中華民族的興衰。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與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大背景下,要振興鄉村文化,就必須跳出“鄉村”的地域局限,轉而面向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在“鄉村文化內核”與“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兩者中尋找交集;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大敘事”中,重新定位鄉村文化的價值坐標;在中國鄉村與中華民族命運的緊密聯系中,挖掘鄉村文化中能夠充分回應現實訴求的優勢內核。
(一)保境安邦的鄉村土地情結
土地情結是指農民在農業實踐中,對所居住、耕種的土地產生占有、熱愛和依戀的一種深厚的情感。保境安邦的土地情結是維持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基石,也是鄉村文化最本質的文化內核。
土地情節最初產生于人對土地的占有和經營。人們圍繞耕地修建房屋,組建村落,興修水利工程,人與自然在長期的互動中,逐漸形成了和諧穩定的村落系統。在物質上,人的生活依賴于一定地域范圍的物質資源;在情感上,人們在農業生產基礎上建立起了相對封閉穩定的社會關系,同周圍的自然環境也建立起了深厚的情感。倘若要離開這片土地,重新組建村落,就需要付出巨大的人力、時間與情感成本。于是為了預防自然災害與外敵掠奪,人們便會組建災害預防與軍事設施,捍衛在固有土地上的生存權。這種對土地的原始占有與守衛,便是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精神的起源。鄉村文化中這種保境安邦、強民富國的精神內核,深深根植于每一個中國人的文化血脈中,在無數次歷史變革中,成為保護中華民族獨立、推動民族富強的強大精神動力。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時期走土地革命的路線,將土地分給農民,就是抓住了農民內心深處最根本的需要,激發了農民的保境安邦的根本精神動力,為抗戰勝利、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打下了堅實可靠的基礎。
然而在當代,土地情結被一些人片面地認為是落后愚昧的小農思想,是阻礙農村土地整合流轉的絆腳石。這種觀點的本質誤區是只片面看到了農民對土地占有的欲望,而沒有認識到鄉土情結的深刻內涵與時代價值。黨的十八大以來,在鄉村振興政策的號召下,縮小城鄉差距、大力發展鄉村經濟成為時代發展之大勢,一些城市已經出現了“逆城市化”的現象,大量人口開始向鄉村回流。在返鄉大潮中,不乏大量在鄉村出生卻在城市取得成就的“新鄉賢”,以及在城市接受過高等教育后決心返鄉創業的青年新農民。一方面,鄉村文化中的鄉土情結被賦予了現代化農村建設的新內涵;另一方面,大力宣揚鄉村文化中的鄉土情結內核,也能夠激發農民的責任感,使他們產生眷地效應,吸引其留在當地振興家鄉,同時增強返鄉建設者的榮譽感與價值感,從而使鄉村土地情節真正發揮凝聚力和感召力。因此,鄉村文化中保境安邦的土地情節,不僅不會過時,更是鄉村振興的精神引領,具有不可替代的時代價值。
(二)綠色和諧的鄉村生態倫理思想
鄉村文化是指在具有農耕生產方式的地域,以農業生產關系為基礎,衍生出的行為習慣、社會風俗、社會價值觀以及物質文明等構成的有機整體,人通過勞動實踐為自然增添人的痕跡,成為“人化的自然”,而在此過程中,人本身也必然會受自然環境的影響,成為“自然化的人”。“人化自然”與“自然化人”是鄉村文化產生的根本邏輯。受制于這一根本邏輯,從古至今無論鄉村文化如何演化,關于“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的理性思考一直都是亙古不變的議題。
《荀子·天論》“夫天有其時,地有其才,人有其治,是為之能參。”就是要將天、地、人看作一個相互制約相互依靠的系統,唯有三者各盡其責,相互配合,才能夠達到和諧的狀態。《呂氏春秋·審時》中指出“夫稼,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也是天地人合一的觀點。在千百年來的農耕文明演進中,中國農民將人的生命周期與自然變化規律相結合,總結出“不違農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等因氣候、時令變化而適時勞作的系統方法,樸素地認識到了人的實踐活動與自然物質基礎之間相輔相成的辯證關系,形成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態倫理思想體系。
生態倫理思想是當代鄉村文化的優勢內核。一方面,鄉村生態倫理思想蘊含著綠色發展的價值向度。只有堅持綠色發展觀,形成生態文明意識,才能在發展經濟的同時積極保護環境,避免重蹈以生態環境為代價換取一時的經濟增長的覆轍。另一方面,鄉村生態倫理思想中蘊含著的萬物和諧共生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理念,是我國堅持協調發展的方法論遵循。目前,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依然突出,面對單邊、霸權主義盛行的復雜國際形勢,以及國內經濟發展方式轉化、產業結構變化、發展動力轉變的關鍵時期,必須要以文化為引領,規劃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協調、綠色、可持續的高質量發展路線。
于鄉村文化本身來說,綠色和諧的生態倫理思想也是當代提升鄉村文化自信的重要支撐。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的提出,中國共產黨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體布局中,結合馬克思主義綠色發展觀,大大豐富了生態倫理思想的理論內涵,將其理論地位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縱觀全局,生態環境仍是當今社會的短板,人民群眾對優美生態環境的需求日益提高,綠色、低碳、生態優美、生活舒適等已經成為人們的迫切需要,社會生態意識顯著提升以及人民日益增加的生態文明需求為鄉村文化振興提供了肥沃的現實土壤。
(三)躬耕樂道的鄉村耕讀文化
耕讀文化是中國在以小農經濟為主要生產方式的基礎上,結合科舉制度的需要,形成的一種“耕”與“讀”相結合的社會文化。耕讀文化起源于春秋時期,并伴隨著科舉制度的完善于唐宋時期最為興盛。然而自明代以來,工商業逐漸取代了農業成為我國的支柱產業,耕讀文化所依附的“農耕”“科舉”等要素逐漸消失,并且隨著教育資源從鄉村向城市的轉移,傳統耕讀文化已不再興盛。然而不論時代怎樣發展,艱苦奮斗、科教興國、知行合一等這些耕讀文化所倡導的價值取向,都是構建文明國度、和諧社會所必須遵循的。可以說,耕讀文化是鄉村文化經久不衰的核心構成要素,也是農耕文明乃至中華民族能夠不斷開拓創新的保障。
1.耕讀文化中蘊含著艱苦奮斗的民族精神。古書中記載:“山川奇秀,土狹人貧,讀且耕者十家而五六”,鄉民即使是在困苦的生活條件下,也依然不放棄對于精神文化的追求,追逐著能夠改變命運的可能。中古鄉村傳統耕讀文化與在中國共產黨帶領無產階級在革命過程中形成不畏艱苦、頑強奮斗的品質和作風一脈相承,具有通過艱苦奮斗改變命運,實現個人解放的價值追求。
2.耕讀文化中蘊含著科教興國的發展方略。在耕讀傳家的社會風氣下,大量具有教育背景的社會精英紛紛“下鄉”,著成《農桑通訣》《齊民要術》等我國農業科技發展中里程碑式的著作。古代統治階級也十分重視耕讀文化對國家發展的推動作用,例如漢武帝時期,通過修正科舉制度鼓勵鄉民參與科考,不少鄉野士人得到重用,有效緩和了統治階級與農民階級固化的社會矛盾,也提升了農民的整體素質,為國家發展貢獻了大量的人才。
3.耕讀文化中蘊含著知行合一的教育理念。“耕”不僅僅指耕種,而是包含農業生產所需要的一切勞動實踐;“讀”不僅指以科考為目的讀書,而是泛指對知識、真理的探索與追逐。古代知識分子在長期的農耕生產實踐過程中,一方面對農時、農事、農務有了基本了解,涌現出大量的農學家、田園詩人;另一方面也養成了知識分子身體力行、經世致用、知行合一的作風傳統。古人也常常以“耕”喻“讀”,常將撰寫文章比喻為“筆耕”,預示“耕”與“讀”的內在精神聯系。
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鄉村傳承耕讀文化,堅持科學發展觀,以科技創新為驅動,拓展設施農業、機械農業、現代化農業生產園等新的產業模式,糧食產量連續超過7個千億斤大臺階,實現了從“供小于求”到“供需平衡”的根本性轉變[3]。進入“振興”階段后,科技創新依然是推進鄉村發展的重要驅動力。必須要傳承和發揚耕讀文化中艱苦奮斗、科教興國、知行合一的精神內核,以科學教育提升農民的綜合素質,培養自主發展的能力;以科技創新替代投資和外需導向,實現鄉村經濟的轉型發展和新的邊際增長[4]。
(四)良法善治的鄉村德治文化
準確把握中國傳統文明的本質特征,就要把握住兩個關鍵點:一是以血緣宗法家族為紐帶的氏族體制,一是理性化了的巫史傳統。兩者緊密相連,結成一體,并長久以各種形態延續至今[5]。在傳統氏族體制與理性認識的辯證統一中,中國鄉村形成了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德治文化。良法善治的德治文化是鄉村文化的價值導向,也是鄉村文化在制度文化方面的具體呈現。
自古以來,中國統治階級都十分重視社會道德倫理,將德治作為治理國家的手段。在以家庭為基礎經營單位的農業經濟基礎上形成了以家庭、宗族、鄉村為基本層次的社會結構,并相應形成了家訓、族規、鄉約等層級的道德規范,共同構成鄉村道德規范體系。從內容上來說,德治文化包含著具有普遍適用性的社會道德規范,也囊括被鄉民自覺遵守的“隱性制度”;從治理手段上來說,鄉村德治依附于熟人社會,通過社會輿論、自我反思等方式,起到協調社會利益矛盾、約束鄉民日常行為、凝聚鄉民參與公共生活等社會作用。
鄉村德治文化中,蘊含著從勞動實踐到理性認識的轉化邏輯。中國農民從農業實踐中體悟人與自然的關系和發展規律,在萬物和諧共生的秩序認知基礎上,更進一步探索出人類社會的文化秩序和政治秩序,逐步實現了從巫覡文化、祭祀文化向禮樂文明的邁進[6]。因此,鄉村德治機制的合法性,從根本上來源于鄉民在農業基礎上建立起的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普遍性認同。千百年來,鄉民們為了提高生活幸福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自覺自發地遵守著鄉規民約。隨著鄉村傳統道德內涵的日益豐富與沉淀,對公認道德規范的自覺遵守以及對高尚理想人格的追求,已經內化成為了中華民族的鮮明性格特質。
現階段鄉村傳統德治文化已經成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法制鄉村的文化營養。只有深刻把握鄉村德治文化的內涵與價值追求,才能使法律法規充分體現人民共同的價值追求,從而提升當代法律的治理效能。
二、鄉村文化的生存困境
在脫貧攻堅的戰略部署下,鄉村經濟、教育、民生等各方面的提升,為鄉村文化發展提供了可靠的物質基礎。然而經濟基礎的變革往往會帶動上層建筑的波動,在“傳統”與“現代”的矛盾沖突中,鄉村文化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發展困境。
(一)鄉村文化的載體衰減和流失
文化依賴于載體進行表達、傳播與傳承,但鄉村文化的傳統載體正在衰減和流失。近年來,由于鄉村人才流失、文化設施建設緩慢、傳統村莊衰落等原因,鄉村文化所依附的人才、技術、設施、器物、村落空間、語言文字等載體正在衰減,而新形態的網絡媒體中又具有較高的資本、人才、技術門檻,使得鄉村文化一時間無法適應。鄉村文化面臨著無處安放、無人繼承、無處可尋的危境。
一方面,鄉村文化的空間載體正在逐漸消失。村落是以當地自然環境為基礎,在“方便勞作”的基本邏輯下,逐漸擴張形成的有機空間結構,是鄉村文化賴以生存的空間載體。據統計,在2000-2010年,十年間已有10萬個村落消失,平均每天就有250個自然村落消失,而這個消失的速度,目前還在加快[8]。與空間載體共同消失的,還有依賴鄉村空間所存在的傳統民俗活動、生產技能等。比歷史更替更具破壞力的,是“行”先于“知”的鄉村文化建設。一些人在掌握鄉村文化的發展規律之前,憑借片面的理解,就著手實施鄉村文化建設,這樣本末倒置的行事邏輯,更破壞了鄉村文化生態。一些地方采用喬遷改造的方式,將村民從庭院趕進了樓房,然后在原有的村落上修建現代化民俗村和生態園區,表面上看是振興鄉村文化,實際上是將原有的鄉村文化從空間載體中趕走,然后按照工業文明的思路重建鄉村。在機械化推行下,大量有特色的文化瑰寶被破壞和掩埋。這種推倒重建的文化建設模式不可取,原本應該進行的資源開發,變成了資源補充和文化改造,其本質就是不尊重本土文化,導致獨具特色的鄉村文化的流失和被同化。
“人”作為鄉村文化的重要載體也在不斷流失。由于城鄉之間發展不均衡,鄉村人口面臨著整體受教育水平低、人力資源文化水平不高、資源利用結構性不足、青壯年流失量大等問題,使得鄉村文化面臨無人繼承、喪失了自主創新的根本驅動力的危境。
在鄉村現代化的推進下,農業生產關系的迅速轉變也加劇了鄉村文化中“傳統”與“現代”的矛盾沖突。土地整合和流轉,使大量農民失去了自主支配耕地的權利,其身份從自給自足的“耕地農民”變成了在農業園區上班的“雇傭工”。這樣在制度驅動下而非鄉村自發的生產關系巨變,傳統鄉村文化一時間難以適應,不可避免地出現了轉型時期鄉村文化斷層的現象。
(二)鄉村文化的價值認同危機
“鄉村文明是中華民族文明史的主體,村莊是這種文明的載體,耕讀文明是我們的軟實力。”[9]中國的現代化建設進行得再深入,鄉村文化也依然是中華民族不可忽視的文化底色,深刻影響著人們的精神需要與價值判斷。鄉村文化的價值認同,始終關系著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與自信。過去幾十年中,以工業化、城鎮化為主要手段的國家發展戰略,使得城市不僅成為了經濟發展的中心,也成為了文化的集散中心,在這樣的局勢下,鄉村文化的生存空間被不斷擠壓,鄉村文化的價值被淡化、質疑。鄉村文化的價值認同危機,造成了鄉村文化的衰落,從更深的層面來講,也動搖著中華民族文化自信的根基。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引領,不斷推進鄉村改革。尤其是近年來,農村土地開始整合流轉,改變了改革開放初期以家庭為單位的土地經營模式,向著規模化經營的方向改革。鄉村經濟構成也從以農業經濟為主拓展為農業、商貿、旅游業等多種經濟模式共同發展,村民的生活方式也悄然發生著改變。然而在鄉村轉型取得顯著成效時,傳統鄉村文化價值觀尚未實現從“傳統”到“現代”的有效轉化。一方面傳統民俗文化日漸式微,賭博、跟風、攀比等低俗文化在鄉村抬頭,短視頻、手機游戲等“短平快”的娛樂方式填充了鄉民的閑暇時間;另一方面以政府為主導的鄉村文化建設工程收效甚微,公共文化活動參與度低,鄉村圖書館、文化館等大量廢棄。人們對傳統鄉村文化的價值認同出現危機,本土文化喪失了本該有的教化與娛樂功能,造成本土文化價值與鄉村發展的需要“水土不服”的尷尬局面。
跳出村民文化生活的視域,從城鄉融合發展需要這個相對宏觀的角度來看,鄉村文化的價值認同危機,也直接影響著人們對于城鄉關系的判斷,阻礙著新時代城鄉融合發展戰略的推進。在城市中心主義的影響下,很多人以城市發展的需要衡量鄉村文化的價值,主張按鄉村城鎮化發展的需要“改造”傳統鄉村文化。一些人認為,中國要實現的現代化,必然是以工業化和城市化為內容的現代化,而鄉村文化作為農業文明時代的產物,無法成為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推動力量。“改造論”與“過時論”都是忽略我國以鄉村文化為底色的實際國情而產生的脫離現實的錯誤認識。正如習近平指出,“歷史和現實都表明,一個拋棄了或者背叛了自己歷史文化的民族,不僅不可能發展起來,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場歷史悲劇”[10]。鄉村振興與中華民族復興兩者都呼喚著鄉村文化價值的重構,從而重新建立起深厚、穩定的鄉村文化價值認同,牢固中華民族自信的根基。
(三)鄉村文化的主體缺位
當代鄉村文化的主體具有二元性,這是由我國鄉村的歷史特性決定的。從以農耕文明為主的農業大國,到改革開放初期的城鄉二元分離,再到黨的十八大以來的城鄉一體化發展,中國城鄉關系經歷著從整體到分離、再到融合的歷史過程。在城鄉融合剛剛起步的特殊時期,當代鄉村文化的主體在空間上橫跨城市與鄉村,兩者在歷史上統一于中國傳統的鄉土記憶,在價值上統一于城鄉融合發展并實現現代化的遠景目標。
然而,無論是鄉村主體還是城市主體,都在鄉村文化建設中長期缺位。在村落文化建設中,農民的主體地位被淡化。在中國農村,原本就有村民參與村務決策管理的傳統,但隨著村委會不斷行政化趨向,形成了以行政命令方式推動工作的習慣,一些做法在客觀上排斥農民的主體地位,如文化培訓、活動中心建設等都通過招標,給所謂“有資質”的公司干,農民由主人變成看客。由于沒有農民的直接參與,致使很多決策、文化工程都脫離農民實際需要,文化工程形同虛設。農民主體參與性的缺失,也導致了鄉村文化被異化,鄉村文化屬性被村民之外的建設者賦予,造成文化建設脫離農民需求和鄉村文化的本質,不少有資歷的農民一邊哀嘆傳統鄉村文化被“文化工程”破壞,一邊又苦于沒有有效參與鄉村文化建設的途徑。在現有的新農村建設案例中,能夠實現文化供需精準對接的并不多見,許多都以農民不參與、沒效果的慘淡結局收場。在城市中,城市居民的鄉土記憶被淡化,鄉村文化在城市中成為了“他者化”的被表述對象,人們在認知上將自身與鄉村文化劃清界限。在這樣的觀念影響下,鄉村文化在思想層面就被禁錮在了“鄉村”中,從根本上喪失了同其他文化融合、交匯的可能。
(四)鄉村文化的傳播受阻
傳播是保持文化生命力的基本保證,一種文化只有被廣泛傳播,才能夠在交互運用中保持創新性和延續性。在當代,文化傳播方式已經突破了地域、時空的障礙,從口耳相傳的示現媒介系統與文字、物品等再現媒介系統,拓展至了視頻、音頻等機器媒介系統[11]。雖然城市文化與鄉村文化在技術手段上已經具備相互交流的現實條件,但受制于城鄉文化權力分配不均的現狀,城鄉文化并不是在彼此平等的前提下交流,而是在城市中心主義的話語體系下,形成了現代與原始、先進與愚昧的二元對立局面。城鄉媒體技術上的巨大差異,使得城市占據著網絡媒體的主導權,規定著網絡媒體的話語機制,鄉村文化話語難以掌握該語境下的有效話語形式,從而造成了鄉村文化在網絡媒體的失語。
一方面,農民作為鄉村文化的主體,不具備足夠的話語能力。多數農民無法準確把握國家發展走勢[12],導致鄉村文化建設無法針對城鄉發展的共性需要設置相關議題,從而無法贏得廣泛的理解和支持。受文化程度的影響,大多數農民駕馭語言及其他符號的能力較弱,對媒體傳播機制的理解較淺,利用現代科技創新傳播手段、優化傳播策略的能力不足,使得鄉村文化常出現自說自話、不易被大眾接受的局面;另一方面,鄉村文化作為文化領域中的“弱勢群體”,成為了被“他者化”表述的對象。傳媒呈現的鄉村景象或農民形象大多以城市視角進行構建,鄉村景象和農民形象呈現出“他者化”的想象,使得鄉村文化在數字傳媒中被異化。例如一些以鄉村為題材的紀錄片,為了迎合消費市場需求,在內容上只選擇對鄉村文化中易于被開發的內容進行表達,刻意營造新奇、神秘、原始的鄉村文化形象,使得客體化的想象代替了真實的鄉村和鄉民形象,擠占真實鄉村的話語空間。
(五)鄉村文化的話語體系殘缺
鄉村經濟模式的改革,顛覆了傳統鄉村文化的載體,重新定義了鄉村文化的價值體系,而在這樣的變革中,鄉村文化的話語體系也亟需完善。
在城鄉二元融合發展的大趨勢下,鄉村文化早已超越了“鄉村”的標簽,在城鄉經濟、產業交匯發展洪流的裹挾中,不斷流入到了更廣闊的話語場中。這就要求我們不能僅僅以地域為依據劃分鄉村文化的邊界,而需要從內核出發,重新定義鄉村文化的不可替代性。對于“鄉村文化是什么”這一問題的話語表達,不僅是概念定義的推敲,更是在思考“鄉村文化將走向何方”的過程中,探尋對鄉村歷史、語言和文化的繼承與發揚路徑。然而,受鄉村教育、文化產業發展較為遲緩的局限,鄉村文化尚未具備完備的話語體系。
一是鄉村文化的核心思想尚不明確、基本理念模糊不清、價值取向搖擺不定,使其無法確定穩定的發展目標與行動方略。二是鄉村文化缺乏被廣泛接受的概念體系,其基本內涵、本質特征等都尚未達成廣泛共識,使得鄉村文化的有關議題無法被準確領會與深入闡釋,造成鄉村文化“找不到”“講不出”“研究不透”的僵局。
從文化樣態來看,鄉村文化多是傳統技藝、民俗活動等的實踐性樣態,缺少準確的文字記述,使得人們難以運用語言工具將對鄉村文化的感性認識上升為理性認識,從而難以形成文化共同體意識和行為。
鄉村文化的本質內核是劃清鄉村文化邊界,使其區別于其他別的什么文化的根本所在。如果對鄉村文化本質的認識模糊,就會造成主體在繼承與創新鄉村文化的過程中,不斷陷入“是我”與“非我”的爭辯。一些人將文化歸屬感寄托在現象中,一旦鄉村文化表現的形式有所改變,主體便陷入“非我”的懷疑中,無法對新形式的文化產生認同感,造成對鄉村文化守舊的保護,從根本上否定了鄉村文化的創新性與包容性。另一方面,對本質的錯誤闡釋與把握,將會導致對鄉村文化忘本的發展。例如改革開放以來,不少文藝作品打著創新的旗號,確已然丟失了鄉土氣息,喪失了精神文化內核,只剩下形式與軀殼,成為了僅僅掛著鄉村標牌的“偽鄉村文化”。
三、鄉村文化振興的策略選擇
鄉村文化振興的重點在于通過重建文化秩序,從而激發鄉村文化發展的內生性動力,具體需要通過文化價值的重塑、主體作用的激發、社會觀念的轉變以及治理能力的提升來實現。
(一)繼承傳承內核,重塑當代價值
文化是人類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總和,可以被人們從多角度闡釋。只有站在主體的立場,以滿足主體利益為目的,將歷史文化進行解構與重塑,才能發揮出文化的凝聚作用。面對現代化進程中的價值認同危機,必須通過價值重塑,重新審視鄉村文化對人的發展、社會進步的意義,調整價值坐標,使其真正成為推動社會發展的文化力量。
第一,要以人們美好生活的需要為導向,重構鄉村文化的價值。要回應農民在現代化進程中產生的新的精神文化需求,著重挖掘鄉村文化中的平等、開放、法治、理性等內容,并發揮文化的道德教化作用,加快新經濟模式下鄉村社會秩序的重建。要挖掘鄉村文化的美學價值,以鄉村振興為物質基礎,探尋在鄉村實現現代、綠色、生態美好生活的現實模式。
第二,要加強黨對鄉村文化振興工作的領導,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鄉村文化價值的重塑。積極弘揚符合社會意識形態發展需要的優秀傳統鄉村文化,對抗拜金主義、封建迷信等腐朽價值觀的侵蝕。
第三,要回應當代多元文化共生的價值訴求,樹立包容、開放的文化價值取向。理性認識鄉村文化的優勢與局限,科學處理鄉村文化與其他文化的價值沖突,保護鄉村文化的多樣性。
第四,要拓展鄉村文化的發展視野,跳出“鄉村”的地域局限,反思鄉村文化之于中華文明、人類文明發展與研究的重要意義。
總體而言,價值重塑是鄉村文化重新煥發生機活力的必由之路,但必須要明確,“重塑”不是對傳統鄉村文化的全盤否定,而是要在價值重塑中保持鄉村文化的內核,在發揚鄉土情結、耕讀文化、生態倫理思想、德治倫理思想的同時,抓住鄉村文化民族性、農耕性、眷地性、農民主體性的基本特征。
鄉村文化的民族性具有雙層內涵,一是鄉村文化是在中國農耕社會發展中形成的,具有鮮明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的文化,二是鄉村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底色,鄉村文化的興衰直接關系到中華民族的興衰。因此,在鄉村文化價值重塑中堅持民族性,就要尊重不同民族、地域的風土人情,鼓勵傳承鄉村特色文化,維護鄉村文化多樣性。要將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作為鄉村文化建設的目標導向。另外,鄉村文化是以農民為實踐主體,在農業生產勞動中產生的文化,具有農耕文明特有的眷地性。在鄉村文化價值重塑中維持農民主體性、農耕性與眷地性,就必須深刻認識鄉村文化對于土地和農業生產關系的依賴性,堅持以經濟發展作為鄉村文化振興的物質載體,并充分發揮鄉村的主體性作用。
(二)發揮主體作用,講好鄉村故事
主觀的表述是最能影響人們對事物看法的方式,鄉村文化要想真正地被廣泛理解和接受,除了需要外部全面、客觀的理解,也需要鄉村自身積極、準確的講述,將鄉村文化的內容轉化成為易于被人們接受的話語表達。總而言之,就是要充分發揮主體作用,生動地講好鄉村故事。
要講好鄉村故事,首先要求主體具有發掘自身文化的基本意識,具備能夠明晰自身文化的歷史發展過程、籌劃與預測自身文化的發展方向以及對現實文化需求進行觀察、反思與回應的能力。然而鄉村主體的文化自覺不可能憑空生成,而是需要主體具備基本的文化素養,同時樹立多元、可持續發展的文化觀。這就需要在鄉村文化教育中,建立長遠、有效的文化教育機制,既要發揮學校教育的主導作用,在課程設置上增加文化觀塑造方面的內容,酌情融入本土優秀的鄉村文化教育,使青少年建立起多元文化觀與鄉村文化自信。也要發揮基層村委會教育作用,通過村民教育,使其樹立多元文化觀,并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提升鄉民的文化審美能力。要鼓勵民間組成文化自治、交流的組織,激發鄉民學習、創新自身優秀文化的主體動力。
講好鄉村故事,還需要鄉村主體具備過硬的表述能力。文字、影音在信息時代是最具時效性與廣泛性的傳播方式,而這正是鄉村文化的短板。鄉村文化是在農業實踐中總結提煉成的精神文化,具有很強的交互性和實踐性,在表達方式上大多采用“言傳身教”,以直接經驗的形式傳遞,卻少有成體系的文字記載和影像記錄。因此,在表述能力方面,要發揮教育主陣地的作用,增強農民駕馭語言及其他符號的能力。要通過技術推廣提升農民對媒體傳播機制的理解,提高農民利用現代科技創新傳播手段、優化傳播策略的能力。必須堅持增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于鄉村意識形態的引導作用,加強鄉村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的培養與宣傳,讓農民能夠自愿、自發地將自身文化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敘事中。
在講述方法方面,要拓展鄉村故事的載體與傳播渠道,促進鄉村文化內容形式的轉化,將經驗、習慣性的文化內容通過文字記錄下來,保護家訓、族規、鄉約等成文的文化遺產。要以政策為導向,鼓勵更多的文學、藝術工作者投入到鄉村文化的研究工作中去,創作更多反映鄉村歷史與現實且能夠被大眾接受的文學藝術作品;在講述內容上,以時間線為軌跡,梳理挖掘歷史中的鄉村故事,鼓勵鄉村使用當地語言記錄村史,尤其是要將地方村落發展史放在中華民族發展的宏觀敘事中,將地方發展史與中華民族的歷史結合起來,講述中國鄉村在社會變革中艱苦奮斗的偉大歷程。
另外,要以政策引導、資金支持等手段,鼓勵主流媒體積極承擔社會責任,發揮媒體的教育、宣傳作用,以優秀的文化作品,在培養觀眾的多元文化觀的同時,盡可能地向大眾展現全面、真實、立體的鄉村文化形象。
(三)打破二元對立,構建城鄉文化共同體
城鄉文化共同體是指城市和鄉村能夠在享有平等經濟發展機會的基礎上, “城、鄉文化作為兩種不同的文化形態,平等共存,尊重包容,交流互鑒,良性互動”的文化關系[12]。構建城鄉文化共同體,是從觀念上打破城鄉二元對立局面的必然要求。
第一,要構建文化共同體的經濟基礎,制定城鄉“雙驅動”的現代化戰略。城鄉二元文化對立產生的根源是城鄉經濟發展分離。扭轉二元對立的局面,就需要從經濟基礎層面入手,賦予城鄉文化平等的發展機會;在政策規劃上避免“城市優先”或“以鄉補城”,而是要將城鄉兩者視為一個有機整體,以城鄉優勢互補為主要方法論原則,尋找城鄉現代化的新路徑。
第二,要夯實文化共同體的觀念基礎,打破城市中心主義的舊思想,喚醒城市居民的鄉土記憶。新中國成立70年以來,中國城鎮化率從10.64%上升到60.6%,城鎮人口由5 765萬上升到8.5億人[13],一半以上的城鎮人口都來源于鄉村。由于上學、務工、親緣關系、宗族傳統等因素,通過留居、遷移、城鎮化最終定居城市的人口,往往具有深厚的鄉土情節,他們的子孫后代也會受長輩們的影響,對鄉村具有情感上的向往和依戀。這種大部分城鎮居民共有的鄉土記憶,恰恰能夠成為緩和城鄉文化矛盾的穩定劑,也是促進城鄉二元融合的黏合劑。喚醒城市居民的鄉土記憶,一是要以傳統鄉村民俗節日為載體,增強鄉村文化活動的交互性,使人們能夠相互交流鄉村記憶,引起情感共鳴,從而激發鄉村記憶的凝聚力。二是要保護傳統村落、民俗、技藝,以物質文化載體觸動城市居民的鄉土記憶,同時,要借助媒體科技對鄉村文化資源進行數字轉化,增強鄉村文化的傳播廣度與效能。三是要發揮教育主陣地的作用,增強青年人的鄉土情懷。在各階段教育中,加入鄉村歷史、文化等方面內容,培養學生的“三農”情懷。尤其是農業類高校在培養學生專業技術的同時,也要增設鄉村文化類的課程,培養出真正“懂農業、愛農民、愛農村”的“三農”人才。
第三,構建城鄉文化共同體,就要增強鄉村文化自信,增強農民對自身文化的認同。要通過宣傳教育,幫助農民建立多元文化觀,使其在文化平等的基礎觀念上,建立起更深刻、更客觀的鄉村文化自信。與此同時,要以制度為抓手,提升新鄉賢和新型農村合作組織的表達權,鼓勵農民在自己作為文化建設主體的基礎上,形成自我決策、自我管理、自我發展的群眾性文化組織,從而讓農民在自主參與到鄉村文化建設的過程中,形成對鄉村文化的認同感與歸屬感。
(四)提升文化治理能力,完善文化振興制度保障
文化治理是指以政府為主導,協同政府、企業、公民三方動力,使得國家、市場、社會在文化領域維持和諧、平衡的最佳狀態的過程。近年來,鄉村經濟、產業、人才、組織解構的完善,為鄉村文化治理創造了更加廣闊的提升空間,而鄉村文化發展過程中逐漸顯露的新的社會矛盾也迫切需要鄉村文化治理能力的提升。
1.要推進政府職能從“管理”到“治理”的轉化。鄉村文化“管理”與“治理”的本質區別,就是能否形成高效的多層級互動的文化秩序,從而發揮企業、公民、社會組織等各方面的主體力量,進而推進鄉村文化的自主管理與創新[14]。要實現政府職能的轉化,就要放松對于文化活動、資源、成果、人員配置等基礎層面的管制與占有,轉而從宏觀上調控文化發展方向,充當戰略制定者和調控者的角色,賦予基層文化組織更靈活的發展空間。
2.要在鄉村公共文化服務的相關決策中充分發揮民主協商制度的作用。在提升農民文化素養與文化自覺意識的同時,開通民眾建言獻策的通道,使得鄉村公共文化服務能夠最大限度契合農民主體的文化需求。
3.要提升基層干部的文化素養和文化治理能力。基層干部是鄉村文化建設的排頭兵,基層干部對農業有信心、對鄉村文化有信仰,鄉村文化自信才能夠在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實踐中充分顯現。要提升基層干部對于鄉村文化的了解,發揮先進典型的示范作用,開展優秀鄉村黨組織書記示范培訓、異地掛職鍛煉、外出考察學習等,鼓勵村黨組織書記參加學歷教育,提高綜合文化水平,打造出一批真正“懂農業、愛農民、愛農村”的“三農”工作者。
4.要發揮法治在文化治理中的決定性作用,完善對于鄉村文化治理成績的評估機制,避免“唯項目論”“唯經濟論”。制定更加科學規范的鄉村文化治理體系,避免“懶政”“一刀切”。要以法律為保障,保護鄉村文化的村落載體,避免破壞性的開發與占用。完善知識文化產權方面的法律體系,切實保護傳統鄉村文化傳承人的實際利益,從根源上促進優秀鄉村文化產品的流通,減少低劣鄉村文化產品的產生與傳播。
參考文獻:
[1] 齊驥.社會結構變動中鄉村振興的文化動力和思想范式研究[J].東岳論叢,2019,40(08):32-40.
[2] 范玉剛.在中華文明與全球化雙重視域中領悟鄉村文化復興的意義[J].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04):122-133.
[3] 尹成杰.后疫情時代糧食發展與糧食安全[J].農業經濟問題,2021(01):4-13.
[4] 宋保勝,楊貞,李文,等.科技創新服務鄉村振興的內在邏輯及有效供給路徑研究[J].科學管理研究,2020,38(05):116-124.
[5] 李澤厚.由巫到禮——釋禮歸仁[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4.
[6] 陳延斌,王偉.傳統家禮文化:載體、地位與價值[J].道德與文明,2020(01):124-129.
[7] 朱啟臻.把根留住——基于鄉村價值的鄉村振興[J].北京:中國農業大學出版社,2019:289.
[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605-606.
[9] 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7.
[10] 劉洋,羅小洪.鄉村文化建設的媒介傳播與振興策略[J].理論月刊,2021(03):100-107.
[11] 黃羽新.同票同權視閾下的農民話語權實現之對策研究[J].求實,2010(11):88-92.
[12] 胡寶平,徐之順.價值認同與城鄉文化和諧共生[J].南京社會科學,2018(02):135-139.
[13] 李蘭冰,高雪蓮,黃玖立.“十四五”時期中國新型城鎮化發展重大問題展望[J].管理世界,2020,36(11):7-22.
[14] 柯尊清.公共文化治理的理論維度、過程邏輯與實現路徑[J].理論月刊,2021(01):105-112.
The Advantage Core,Development Dilemma and Strategy of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Culture
YANG Hua,FAN Yue,DU Tianxin
(School of Marxism,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49,China)
Abstract:Rural culture is not only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Chinese nation,but also the value guidance and spiritual power source of rural rejuvenation.Among them,the local complex,ecological ethics,ploughing culture and rule of virtue culture are the dominant core that can best respond to the realistic demands of contemporary rural vitalization,the great revival of China and the needs of the people for a better life.However,i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the main driving force,rural culture has been gradually marginalized,facing the development dilemma of disappearance of carrier,absence of subject,crisis of value identity and incomplete discourse system.Rural culture has not only failed to play its due role of cohesion and leadership,but also has even become a drag on the proces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In the critical period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rural relations,in order to revitalize rural culture,we must inherit the core of traditional advantages and be guided by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on this basis,we should enhance the subject consciousness and discourse ability of the countryside,tell rural stories to the outside world; shape the consciousness of cultural community in the whole society, and break the dual opposition of urban and rural culture in concept;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and ability in cultural governance,and improve the legal guarantee for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culture.
Key words:rural cultural value;cultural self-confidence;core reshaping;cultural identity;rural value
(責任編輯:張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