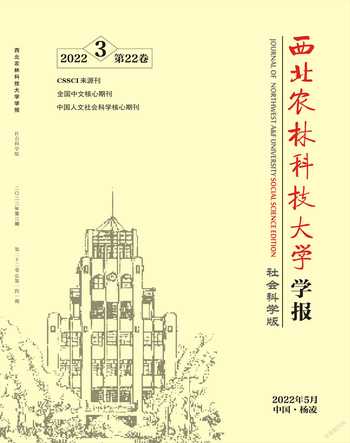關系化用工:農業規模經營的社會基礎
摘 要:農業規模經營是中國鄉村振興進程中的關鍵議題。農業規模經營在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呈現出用工效益的差異,從而使一些規模農業經營主體陷入困境。采用嵌入性視角探討農業規模經營中用工模式嵌入社會關系的邏輯及其影響。研究發現,農業規模經營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市場化用工無法有效解決農業規模經營中的勞動監督問題。而將市場規則嵌入關系規則的關系化用工使得雇傭雙方產生了利他傾向,進而在很大程度上調動了工人內在的勞動積極性,從而使農業規模經營主體擺脫經營失敗困境。關系化用工的實現依賴于農業規模經營主體在用工選擇、生產管理和日常生活中充分發揮社會關系的積極作用,但社會關系范圍和程度都是有限度的。因此,農業規模經營的健康發展不僅需要處理好經濟關系,而且需要處理好社會關系。
關鍵詞:農業規模經營;市場化用工;關系化用工;社會基礎
中圖分類號:C912.82;F32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07(2022)03-0090-08
收稿日期:2021-08-14" 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22.03.11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19CSH031)
作者簡介:孫新華,男,西北農林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發展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農業治理與農地制度。
一、問題的提出
隨著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和土地流轉的推進,農業規模經營已成為中國農業現代化的發展方向。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促進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的意見》指出:“發展多種形式適度規模經營,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是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業競爭力的有效途徑,是建設現代農業的前進方向和必由之路。”
近年來,中國農業規模經營得到快速發展,各類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異軍突起。截至2019年底,全國家庭農場超過70萬家,依法注冊的農民合作社220.1萬家,從事農業生產托管的社會化服務組織數量42萬個。然而,中國農業規模經營的發展卻呈現出一幅復雜畫面:在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大量涌現的同時,一些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卻面臨經營虧損、“毀約棄耕”、跑路等現象[1-2],但也有不少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尤其是經營規模較大的主體經營效果較好[3]。為什么有的農業規模經營能夠取得成功,而有的則走向失敗?對于這一現象的解釋既是中國農業規模經營發展中的重要現實問題,又是農業轉型研究中重要的理論命題。
有關農業規模經營效果的研究,在學術界存在多種分析視角,其中,農業雇傭視角無疑是一個積累深厚而又影響廣泛的解釋角度。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認為“商品生產+雇傭勞動”是資本主義農業的標志,依賴雇傭勞動的資本主義農業既有進步的一面又有異化的一面[4]。自由主義經濟學者普遍認為,在工業生產領域取得成功的雇傭勞動實踐在農業生產領域也一樣能夠成功,依賴雇工生產的農業規模經營較之于小農生產具有絕對優勢[5]。近年來,在國內鼓勵農業規模經營的很多學者基本也是基于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觀點做出的判斷[6]。
但是,農業發展的現實對以上論述提出了有力挑戰,即家庭經營仍然普遍存在,甚至構成了全球主導的農業經營形式[7]。有學者發現,農業生產中存在的自然環境的不確定性、勞動時間和生產時間的差異,使得農業生產過程的標準化、程序化和定量化程度較低,致使工人勞動的速度和質量都難以監督和控制[8]。如果不能解決勞動監督和計量困難,就會導致偷懶和搭便車等機會主義行為[9]。此外,農業的勞動對象是具有生命的,農業生產要根據農作物生命運動而展開,農作物生命運動的連續性和不可逆性決定了農業生產不像工業生產有半成品或中間產品。要準確評價農作物在各個生產環節中所需要付出的勞動數量和質量,就要求勞動者在農業生產中對農作物生命活動的整個周期負責[10-11]。基于以上農業生產的特殊性,使得依賴雇傭勞動的工業大生產向農業領域推廣時會遇到無法克服的勞動監督難題,這種難題在世界各國均普遍存在[12]。
而家庭成員在農業生產中具有足夠的工作積極性,也不需要內部計量和監督。家庭經營在農業生產上具有的天然合理性和優勢,使得家庭經營成為農業生產最有效的生產方式,而依賴雇傭勞動的規模經營則難以維系。對農業雇傭的特殊性進行深入研究后,就能夠在很大程度上解釋大量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經營虧損的問題,但卻無法解釋同樣依靠工人進行生產的規模經營主體為何有的成功、有的失敗,而且很多成功的規模經營主體能夠較好地解決雇傭生產中的監督難題。這主要是因為這類研究忽視了雇傭行為的社會基礎。格蘭諾維特提出了“經濟行動嵌入社會結構”的觀點,指出建立在信任、親屬及朋友關系基礎上的社會關系網絡對于經濟行動和經濟制度的重要影響[13],農業生產中的雇傭行為亦是如此。雇傭雙方不僅是理性的經濟人,同時也是感性的社會人,雇傭雙方的行為邏輯受到社會關系的影響。以上研究在指出家庭經營合理性的時候已經表明家庭關系能夠有效解決家庭內部勞動之間的監督問題。如果我們將這種關系因素進一步放大到家庭之外的社會關系,就會發現社會關系也能影響雇傭行為,從而為解釋現實中的農業規模經營現象提供新的視角。
近年來,學術界已有一些學者關注到社會關系在農業雇傭中的作用,但是,他們或側重于資本積累[1],或側重于土客結合[14],而對社會關系在農業雇傭中的具體作用機制及其對農業規模經營效果的影響缺乏系統探討。鑒于此,本文試圖從嵌入視角來探討農業規模經營主體的用工模式及其社會基礎。筆者首先基于經驗調查中發現的典型案例,從中區分出市場化用工與關系化用工兩類用工模式及其效果,繼而進一步分析關系化用工運作的內在機制,闡釋關系化用工的限度。
二、農業用工的類型及其效果
農業規模經營繞不開勞動雇傭問題,即使隨著農業技術提高和機械化程度增強,農業規模經營中雇傭勞動所占比重有所下降,但農業生產中依然有很多環節嚴重依賴勞動力完成。
筆者在實地調研中發現,同樣都是雇傭工人進行農業規模經營,但是因為受到不同規則的影響在農業生產中會產生完全不同的結果。一般而言,雇傭雙方一方出賣勞動力,一方支付工資,是一種典型的市場交易行為,雇傭雙方所遵循的交易主要是市場規則,因此可將這種用工模式稱為市場化用工。此外,實踐中也出現了另一種勞動力雇傭,即雇傭雙方不僅僅是作為理性的市場主體,而且相互之間存在一定的社會關系,從而使雙方的交易不僅僅受市場規則支配,還受到社會規則尤其是社會關系的影響。筆者將這種在市場規則之外還受到社會關系因素影響的用工模式稱為關系化用工。兩種用工模式中工人的勞動質量差別很大,從而使農業規模經營的結果存在巨大差異。
(一)市場化用工及其困境
市場化用工下,經營主體無法解決“磨洋工”問題。同時,很難對工人的勞動數量和質量進行計量,也只能給予固定工資。用農民的話說就是,“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快干慢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這也使農業規模經營主體無法調動工人的勞動積極性。“磨洋工”的大量存在,不僅增加生產成本而且影響生產質量,致使農業生產出現入不敷出的經營困境。
案例一:B,市民,農機銷售商,2009年來到臨縣皖南河鎮流轉土地,共流轉1 071畝土地種植水稻。他斥資上百萬元建造了住房倉庫、車棚、烘干房、并購買了全套的農機具。由于經營規模較大且本人也不懂農業生產,B主要采用雇傭本地工人進行生產。具體而言,他將流轉到的土地分成三個區域,每個區域聘請一位本地的生產隊長,每個區域的具體用工由生產隊長去安排,農機手也是需要時進行臨時聘用。B只是負責生產安排和監督,具體生產環節都由雇工完成。然而這種經驗模式最終以失敗告終。經營三年后他發現每年虧損二三十萬元,最終不得不選擇將資產變賣并轉包土地。他總結失敗的關鍵原因就是工人太難監督,最終影響到水稻的產量和品質。他甚至感慨道,“只有在田里安裝上高清攝像頭,才能監督這些工人”。
案例一中農業規模經營主體B所面臨的正是農業用工帶來的經營困境。作為一名外生型農業規模經營主體,他與當地工人沒有先賦性社會關系,是后天建立的市場關系。較之于內生型農業規模經營主體,他與工人的關系更加陌生,行為邏輯更加理性化,用工模式也更加接近于理想型的市場化用工。首先,雇傭雙方都是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而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實現建立在減少對方利益的基礎上。其次,雇傭雙方的交易完全按照市場規則進行,受市場支配。正是因為市場化用工中雇傭雙方完全按照理性人的邏輯行事才導致農業規模經營中的勞動監督難題。
(二)關系化用工及其作用
市場化用工及其經營困境在中國農業規模經營中普遍存在,但不是所有農業規模經營主體都無法克服。從實踐來看,不少農業規模經營主體能較好地克服勞動監督問題,甚至實現持續盈利。
案例二:L,皖南河鎮農民,原在外務工,2012年本村土地整理后回村流轉土地400多畝,2018年又流轉200多畝。由于愛人照顧孩子讀書,加之自己又做村干部,家庭勞動力在農業生產中的投入非常有限,主要依賴雇工。由于L是本地人,他雇的大部分工人都是熟人,其中不少還是自己的親戚。因此這些工人在農業生產中都比較認真負責,“磨洋工”現象較少。這使他的經營效果非常好,正常年份每畝可以賺400元左右。而且他認為即使將自己的經營規模擴大到 1 000畝,每畝的單產和利潤也不會有太大變化。
案例三:X,皖中地區農民,自1999年結婚后便去福建流轉土地種植西瓜,2005年從福建轉到皖南河鎮經營。十多年來夫妻兩人在河鎮一直保持多種經營,以種植西瓜、草莓和各類蔬菜為主,水稻為輔。一般種植100畝左右的經濟作物、200畝左右的水稻。由于主要種植經濟作物,勞動力投入非常大,而且常年如此。按說作為外地人,在勞動監督問題上應該會更加困難。但是事實上,X能在河鎮經營十多年,每年都有非常好的經營收益,這充分說明他已經比較好地解決了勞動監督問題。他說,雖然工人沒有在自己家勞動那么積極,但是工作普遍比較認真。這主要是因為他們夫妻倆與工人處理好了關系,用他的話說就是,“我們對工人比對家人還好”。他還特別提到,對于長期給他務工的工人,只要他們家里有紅白喜事,他都會去送人情。
案例二和案例三中的農業規模經營主體采用關系化用工較好地解決了勞動監督難題。關系化用工與市場化不是決然對立的。在市場經濟下,勞動力價格凸顯,換工、幫工等傳統互惠經濟少見,勞動力市場上的交易雙方必然主要受市場規則支配。而在關系化用工中雙方除了受制于市場規則,還受到關系規則的制約,雙方除了交易關系還有一定的社會關系,此時雙方并非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而是在考慮自身利益的同時也兼顧對方利益的社會人。
社會關系在經濟行為中發揮重要的促進作用。格蘭諾維特在嵌入性研究中特別提出“關系性嵌入”概念,指出互動雙方既有關系中存在的對各種規則性的期望、對相互贊同的渴求以及互惠性交換直接約束著雙方的經濟行為,能夠有效地阻止違反互惠性義務的發生,減少機會主義和不確定性從而減少交易成本[15]。因此,當雇傭雙方具有一定的社會關系,并將社會關系運用于生產之中,工人的行為邏輯就會發生變化,在生產過程中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也形成利他性傾向,農業生產中的“磨洋工”現象自然會減少。換言之,將市場規則嵌入關系規則中的關系化用工改變了工人在農業生產中的行為邏輯,避免了市場化用工帶來的經營困境。
一般而言,內生型農業規模經營主體天然地具備先賦性社會關系,更有可能采用關系化用工模式。案例二中的L便是因為采用關系化用工模式減少了工人的“磨洋工”問題,從而能夠長期保持盈利狀態。但并非外生型農業規模農業經營主體不會也不能采用關系化用工模式。隨著人們認識到社會關系的重要性,有些農業規模經營主體也會主動采用關系化用工模式,案例三中X便是典型代表。他長期在外從事農業規模經營,深諳用工之道,不僅在生產中主動與工人處理好關系,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積極融入到當地的生活中以加強與工人的社會關系,這也是他長期保持盈利的關鍵因素。
三、關系化用工的運作機制
關系化用工發揮作用的核心機制是將市場規則嵌入關系規則,這就需要農業規模經營主體在用工的全過程充分發揮關系因素的積極作用來調動工人的積極性。具體而言,農業規模經營主體在篩選工人時便將社會關系作為關鍵標準,在生產管理中積極處理好與工人的關系,在日常生活中也主動通過人情來往維系和加強與工人的關系。
(一)篩選機制:用工選擇中的關系取向
農業規模經營主體在雇傭工人時首先要面臨工人的篩選問題。勞動力特征直接影響勞動質量,不同勞動力的勞動素質、勞動態度(是否勤勞、可靠、積極等)有很大差異。而用工雙方的信息差在勞動力市場普遍存在。雇主僅憑勞動力的外在表現很難全面獲取信息,加之農業生產的特殊性,雇主很難有效辨識工人的實際表現。因此,在市場化用工模式中,農業規模經營主體難以對工人進行有效篩選,也難以保障工人后續的勞動質量。而在關系化用工模式中,農業規模經營主體在篩選工人時具有明顯的熟人社會優勢。費孝通說,鄉土社會是“一個‘熟悉’的社會,沒有陌生人的社會”“熟悉是從時間里、多方面、經常的接觸中所發生的親密的感覺”[16]9-10。雖然農村勞動力的流動使得農村陌生化增強,但是熟悉的底色沒有改變。熟人關系既可以彌補雇傭雙方的信息差,又可以彌補農業規模經營主體的監督難題。這在內生型農業規模經營主體表現得最明顯。以案例二中的L為例,他長期雇傭的工人主要有4人。其中1人是遠房親戚,另外3人都是本村或鄰村的村民,屬于熟人關系。據L介紹,他們4人不僅都是種田能手,而且為人勤勞踏實,再加上與他們有著千絲萬縷的社會關系,對他們都非常放心。臨時工也基本都是熟人,而且篩選工人基本都是按照“差序格局”進行選擇。較之于內生型農業規模經營主體,外生型農業規模經營主體是作為陌生人進入當地社會的,缺乏先賦性社會關系,但是他們依然可以借助各種后致性社會關系來篩選工人。以案例三中X為例,他是在2005年被當地政府引進的種田大戶,當地鄉鎮政府和村“兩委”有一定義務為他提供基本服務。他也比較主動與村組干部維持關系,也借助村組干部篩選工人。在生產過程中他發現幾位非常好的工人,就注重維持與工人的關系,發展為親近的朋友,相互之間進行人情往來。目前他長期雇傭的6位工人都是這種關系,而且可以借助工人的熟人關系來篩選工人。因此,他特別強調“到一個地方首先要把社會關系網支起來”。他在皖南河鎮長達十幾年的經營過程中積極結識并建立了各種社會關系。他在當地的人情開支便是一個很好的體現。據他介紹,每年他在當地都有1.5萬元左右的人情開支,比當地的一般農戶還要多。這些社會關系都為他篩選工人提供巨大幫助。
總之,關系化用工模式在用工的起始階段便表現出明顯的關系取向。一方面農業規模經營主體充分利用社會關系作為識別工人勞動特征的重要資源,另一方面在同等條件下農業規模經營主體也根據與工人的關系遠近來選擇其他新工人。
(二)管理機制:生產過程中的關系處理
確定工人后,農業規模經營主體需要在具體生產過程中對工人加以管理,其中的關鍵是如何調動工人的勞動積極性。當外在監督無法實現的情況下,關系化用工將重心轉向生產過程中的關系處理。這種關系處理既包括經營主體與工人的關系又包括工人之間的關系。
首先來看雇主與工人的關系處理。案例二中L在談到工人管理時強調:“我雇工人,雇的不是‘工’,而是‘人’。他們是農民,我也是農民,我們都是平等的”。當地很多農業規模經營主體尤其是下鄉資本都是按照工業生產中的科層關系或傳統社會中的等級關系來處理與工人的關系。他們不僅在觀念中認為工人低人一等,而且在生產中也經常訓斥工人甚至辱罵工人,致使工人在生產中產生報復行為。案例一中的B便是典型。他經常對干活不積極的工人橫加指責,導致工人故意“磨洋工”、偷稻子等。而L將工人看做平等的個人,并給予足夠的理解和尊重,自然更容易換來工人的尊重和積極工作。進一步而言,“工”和“人”之間的差別不僅包括雇主和工人之間的地位問題,而且包括深層次的關系問題及其處理規則。“工”蘊含的是理性的雇傭關系,而“人”則蘊含的是感性的社會關系。因此,雇主與“工”處理關系時只要按照工作的規則處理即可,而雇主與具體的“人”處理關系時則要強調感情和“處”的藝術[17]。比如同樣是飲食供應,前者只需按照當地基本標準提供即可,而后者則需要注重工人的需求。按照L的說法便是“要提供全面而又周到的后勤服務”。他提供的午餐不僅有菜有肉還有煙酒,下午配有點心,夏天免費提供啤酒飲料等。這些服務其實不會增加太多開支,關鍵是用心與工人相處。這種資金和感情上的投入在生產中帶來的收益遠遠超過常規做法。總之,農業規模經營主體與工人處理好關系,有利于激發工人的勞動積極性,以彌補外在監督的缺失。
其次來看工人間關系的處理。費孝通指出,鄉土社會呈現明顯的“差序格局”。工人與農業規模經營主體的關系也存在親疏遠近。與農業規模經營主體越親近,工人在勞動中越積極并且會主動監督、帶動其他工人;而與農業規模經營主體越疏遠,工人在勞動中越可能出現“磨洋工”。調查發現,很多農業規模經營主體也在有意利用這種親疏遠近。比如關系化用工中常見的措施是農業規模經營主體往往安排與自己親近的人做領工或生產隊長,以起到近距離監督帶動的作用。雖然這些具體負責人與農業規模經營主體的關系和利益一致性也有限,但是這種較為親近的關系在勞動監督中發揮了很大作用。
與此同時,面子也是鄉土社會中社會關系的關鍵一面。農民好面子是因為面子反映自己在當地社會中的社會評價、聲望與地位,而且面子具有正向的褒譽機制和負向的排斥機制。一般而言,面子大的人能從村莊社會中獲得較高的聲望評價和更多的互助合作,生活會愈發便利;而沒有面子的人則會招致大家的鄙視,被社會邊緣化,使他“社會性死亡”[18]。基于此,采用關系化用工的農業規模經營主體往往也會利用工人的面子觀來調動工人的積極性。例如安排同樣數量的雇傭工人在相鄰的地塊同時展開勞動,干得太慢和質量太差的一方就會沒有面子,以此形成的競爭就有利于形成積極的勞動風氣從而調動工人的積極性[19]。除了利用整體意義的面子競爭,不少農業規模經營主體還注重個體意義上的面子競爭。在陜西調研時,一位種植100多畝蘋果園的規模經營主體表示:“對待工人要抓兩頭,對于正面典型要多抬舉,比如大家中午在一起吃飯時多跟他說幾句話,多套近乎;對于負面典型就直接讓領工告訴他以后不用來了”。這種抓兩頭的方式就是利用個體意義上的面子競爭,通過給予正反兩種典型不同的面子,從而激發中間工作狀態的工人的勞動積極性。
總之,關系化用工在生產管理中注重關系的處理,包括農業規模經營主體處理自己與工人的關系和處理工人之間的關系。正是通過關系處理,從工人內在調動勞動積極性,以彌補外在監督的難題。
(三)維系機制:日常生活中的關系維系
在市場化用工模式中,雇傭雙方的關系主要是生產過程中的雇傭關系,雙方在生產結束后的日常生活中缺乏社會互動。關系化用工中,農業規模經營主體注重在日常生活中與工人關系的維系,并積極通過各種方式維系和鞏固現有雇傭關系,以便在今后的生產過程中發揮積極作用。
在鄉土社會,人情是維系人與人之間關系的主要方式。人情往來的范圍非常廣泛,既包括“儀式性人情”又包括“日常性人情”,前者指生育慶典、婚禮、喪禮和蓋房等儀式性場合中的表達性禮物饋贈;后者指生產生活中的互助、日常互訪、探望病人等人情往來[20]。正因如此,鄉土社會中人與人之間形成了多方面的人情關系。如費孝通所言:“親密的共同生活中各人互相依賴的地方是多方面和長期的,因之在授受之間無法一筆一筆地清算往回……欠了別人的人情就得找一個機會加重一些去回個禮,加重一些就在使對方反欠了自己一筆人情。來來往往,維持著人和人之間的互助合作”[16]72-75。正是在人情來往中形成的“給予”和“虧欠”關系在人與人之間起到了關系維系作用。因為人情往來范圍廣泛且無法清算,“當人情‘給予’的場合再次出現時,往往只能在某個層面上了結‘虧欠’,而不可能徹底清算所有層面的‘虧欠’。這樣,雙方最終都有義務將人情關系繼續下去,且不應過于關注人情中的得失。在對方需要而又力所能及的情況下,便負有‘給予’的義務”[21]。
調研發現,在關系化用工模式中,無論是內生型還是外生型農業規模經營主體都注重與工人之間的人情往來,特別是人情“給予”。當然,人情往來既有儀式性人情又有日常性人情。在儀式性人情方面,如案例三中的X,作為外生型農業規模經營主體每年在當地1.5萬元的人情開支中相當一部分便是“給予”工人的;案例二中的L,作為本地人原本便與很多工人有人情往來,而據他介紹因為發生雇傭關系后與他們之間的人情往來明顯增加。在日常性人情方面,農業規模經營主體也注重在日常生產生活中的人情給予。如筆者在陜西調研中發現,農業規模經營主體會主動提出讓工人在水果成熟時摘些回家,過年時還會給工人發小禮品,對于關系較親近的工人,每年還會單獨請他們吃飯。
農業規模經營主體主動的人情往來在用工中至少起到兩方面的積極作用。第一,人情往來促使工人更加積極勞動。農業規模經營主體在日常生活中主動的人情“給予”自然會使工人產生“虧欠”,而且其中不少“虧欠”是工人很難償還的,從而使工人產生一種對農業規模經營主體的“虧欠感”。這種虧欠感將驅動工人在生產中更積極地勞動,甚至雙方都保持一致的默契,即農業規模經營主體平時送給工人的人情本來便不希望工人同等償還,而是希望工人回饋在生產工作中。正如一位農業規模經營主體所說:“日常生活中與工人的關系最重要,就像處朋友一樣,平時的關系處好了,干活的時候他就當自己的事干,就給你多操心。”第二,人情往來有利于雇傭關系的穩固。在農業勞動力市場上,勞動力就業具有較強的不穩定性。對于農業規模經營主體來講,如何保障足夠的勞動力就成為需要思考的問題。而對于采用關系化用工的農業規模經營主體來說,如何穩定住現有工人更加重要。因為現有工人是自己篩選出來的在生產中比較積極的勞動力。而人情來往中工人形成的“虧欠感”同樣有助于現有雇傭關系的維系。至少在其他雇傭方給出的價格差別不大的情況下,工人會選擇現有農業規模經營主體。案例二中的L在2018年擴大經營規模后,需要增加一個長期雇傭的工人,經朋友介紹認識鄰村的一個人,當時這個人在給本村的一個外生型農業規模經營主體務工。L給他開出比原有工資每天多20元也沒有請來,原因是這個人種的田與原有雇主的田相鄰,原有雇主在灌溉、耕田等過程中經常給予幫助,他不能僅僅因為工資高就換雇主。
以上,筆者從用工選擇、生產管理和日常生活三個方面總結關系化用工的運作機制,具體包括篩選機制、管理機制和維系機制三個相互聯系的運作機制。從中可以看出,農業規模經營主體在三個機制中始終圍繞與工人的關系做出各種努力,主動運用雙方的關系來激發工人內在的勞動積極性,以彌補外在監督的不足。這種隱蔽的處理方式在解決農業規模經營勞動監督難題中發揮了較為穩定而有效的作用,并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市場化用工的難題。
四、關系化用工的限度
關系化用工借助社會關系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市場化用工無法解決的勞動監督問題,從而解釋了為什么在實踐中農業規模經營主體的經營有的成功而有的卻失敗。但是由于社會關系本身的特殊性,關系化用工在解決勞動監督問題的范圍和程度上都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1.社會關系的先賦性決定了關系化用工主要被內生型農業規模經營主體采用。關系化用工發揮作用的前提是社會關系的存在。從農業規模經營主體在當地所擁有的關系資源來看,內生型農業規模經營主體相對于外生型農業規模經營主體具有更大優勢,這主要是兩者在社會關系建立方式的差異所導致的。前者長期生活在當地鄉土社會,他們的社會關系既有先賦性社會關系又有后致性社會關系。而后者雖然在進入當地社會后也可以通過各種努力建立后致性的社會關系,但是要比前者付出更大的成本,同時鄉土邏輯中對陌生人的歧視觀念也使其建立社會關系的范圍有限。這些都使外生型農業規模經營主體在采用關系化用工模式時會碰到更大的困難。正因如此,從調研中獲取的資料來看,采用關系化用工模式主要是內生型農業規模經營主體,只有少部分外生型農業規模經營主體能夠成功采用關系化用工模式。以皖南河鎮為例,筆者發現當地大部分內生型農業規模經營主體都較為成功地采用了關系化用工模式,而2007年以來當地產生了50多個外生型農業規模經營主體,但是像案例三中的X一樣成功采用關系化用工模式的總共不超過5例。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往往是內生型農業規模經營主體較之于外生型農業規模經營主體更容易取得成功[22]。
2.社會關系的有限性決定了關系化用工只能在一定經營規模范圍內發揮作用。筆者調研中發現,無論是內生型還是外生型農業規模經營主體,當經濟規模過大時都無法改變經營失敗的局面。這是因為農業規模經營主體的社會關系網是有限的,關系化用工無法真正發揮作用。關系化用工在勞動監督中發揮作用的前提是農業規模經營主體與所雇傭的工人之間存在一定的關系并能利用這種關系。但是經營規模越大,需要雇傭的工人就越多,從而遠遠超過了社會關系網所能覆蓋的范圍,關系化用工就無法再進行有效運作,進而無法使社會關系在勞動監督中真正發揮作用。所以成功運用關系化用工模式的農業規模經營主體會將經營規模控制在雇傭的主要勞動力都在自己的社會關系網覆蓋范圍內[4]。
3.社會關系的差序性決定了關系化用工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勞動監督問題。關系化用工在勞動監督中發揮作用的核心機制是利用社會關系因素牽制個人理性的自利傾向。但是社會關系具有明顯的差序性,即農業規模經營主體與工人的社會關系存在明顯的親疏遠近差別,這意味著與農業規模經營主體的關系越疏遠,工人在生產中“磨洋工”的可能性就越大。即使是與農業規模經營主體關系較近的工人,在生產中的勞動積極性也無法達到在自己家干活的程度。正如案例三中的X對自己雇傭的工人的評價:“我長期雇的這些工人整體上干活比較認真,比一般的工人好很多,但是還是沒法與在他們自己田里干活相比。假如一般的工人一天只能拔1畝田的草,這些工人在我這里可以拔1.2畝田的草,如果在他自己田里可以拔至少2畝田的草。”這種差異的根本原因還是工人沒有勞動成果的剩余索取權,缺乏經濟激勵。農業規模經營主體與工人的關系沒那么親近的情況下,社會關系雖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磨洋工”,但是無法從根本上克服這一問題。這就解釋了為什么農業規模經營主體的經營效果不如家庭農場,即使農業規模經營主體采用關系化用工模式也無法從根本上改變這一現象[23]。
基于以上分析,筆者發現關系化用工的應用對社會關系具有高度的依賴性,從而決定關系化用工只能在一定范圍內被采用,即關系化用工并非萬能,而是具有明顯的限度。總之,對農業規模經營復雜性的理解要將市場化用工和關系化用工結合起來。依賴工人勞動的農業規模經營主體如果采取市場化用工模式,將無法解決勞動監督難題,往往面臨經營失敗。如果主要采取關系化用工模式,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勞動監督難題,從而實現盈利。但關系化用工本身具有限度,只能在一定范圍和程度上有效,即關系化用工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農業規模經營中勞動監督無法實現的理論,并將適度規模經營的規模由家庭勞動力承擔的范圍擴大到關系化用工承擔的范圍。
五、結論與討論
雇傭視角是理解農業規模經營效果的重要視角。隨著農業規模經營的快速發展,既有研究無法解釋現實中農業規模經營的復雜性,即主要依賴工人進行生產的農業規模經營既可能成功又可能失敗。這主要是因為既有研究忽視了雇傭行為的社會基礎。本文采用嵌入視角嘗試探討雇傭行為嵌入社會關系的邏輯及其影響,從而較好地解釋了農業規模經營的復雜性。
研究發現,農業勞動力市場的用工模式主要包括市場化用工和關系化用工兩種。在市場化用工中,雇傭雙方作為理性的經濟人按照市場規則采取行動,無法有效解決農業規模經營中的勞動監督難題,導致主要依賴工人進行生產的農業規模經營主體陷入經營失敗的困境。而在關系化用工中,雇傭行為嵌入到社會關系之中,雇傭雙方既受到市場規則約束又受到關系規則制約,這使雇傭雙方在生產中不僅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而且是具有一定利他傾向的社會人。雇傭雙方行為邏輯的改變在很大程度上調動了工人內在的勞動積極性,從而可能擺脫外在勞動監督缺失帶來的經營失敗困境。關系化用工的實現依賴于農業規模經營主體在雇傭全過程中充分發揮社會關系的積極作用。具體而言,在篩選工人時便將社會關系作為關鍵標準,為社會關系在生產中發揮作用奠定基礎;在生產管理中積極處理好與各類工人的關系,從而激發工人內在的勞動積極性;在日常生活中主動通過人情來往維系和加強關系化的雇傭關系。但是鑒于社會關系的特征,關系化用工也只能在一定范圍和程度上解決農業規模經營中勞動監督問題。
這一研究結論有助于推進對農業規模經營復雜性的認識。對于主要依賴工人進行生產的農業規模經營的發展前景,既有研究基本持兩極看法:或者認為農業規模經營將如工業大生產一般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優越性,或者認為農業規模經營因為難以解決勞動監督難題而必將走向失敗。本研究的啟示是農業規模經營在現實中的經營狀況受農業規模經營社會基礎影響,特別是農業規模經營能否將雇傭行為嵌入到社會關系之中,充分發揮社會關系對工人的積極作用。農業規模經營主體如果能在實踐中有效采用關系化用工模式,便能在很大程度上解決市場化用工無法解決的勞動監督難題,從而產生較強的生命力;而如若因為各種原因無法采用關系化用工,則難以解決勞動監督難題,走向經營失敗。也就是說,將社會關系納入到農業雇傭研究之后,可以對現實中農業規模經營的復雜性給予較好地解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農業規模經營的發展不僅僅是經濟建設的內容,也是社會建設的內容;農業規模經營的健康發展不僅需要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處理經濟關系,而且需要處理社會關系。
參考文獻:
[1] 陳義媛.資本下鄉的社會困境與化解策略[J].中國農村經濟,2019(08):128-144.
[2] 朱雋.“毀約棄耕”當警惕[N].人民日報,2015-06-07(09).
[3] 陳靖.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如何“嵌入”鄉土社會[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18(05):18-24.
[4] 葉敬忠,吳存玉.馬克思主義視角的農政問題與農政變遷[J].社會學研究,2019(02):1-24.
[5] 黃宗智.中國過去和現在的基本經濟單位:家庭還是個人?[J].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2(01):76-93.
[6] 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中國土地問題》課題組.土地流轉與農業現代化[J].管理世界,2010(07):66-85.
[7] 孫新華,劉秋文.農業經營主體發展的多向性及其啟示——基于世界農業發展歷史的分析[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學科版),2019,19(03):78-86.
[8] 伯恩斯坦.農政變遷的階級動力[M].汪淳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134-137.
[9] 阿爾欽,德姆塞茨.生產、信息成本和經濟組織[M]//科斯,羅納德·哈里·科斯,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44-69.
[10] 周其仁.家庭經營的再發現——論聯產承包制引起的農業經營組織形式的變革[J].中國社會科學,1985(02):31-47.
[11] 羅必良.農地經營規模的效率決定[J].中國農村觀察,2000(05):23-24.
[12] 賀雪峰.論農地經營的規模——以安徽繁昌調研為基礎的討論[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11(02):6-14.
[13] 格蘭諾維特.鑲嵌: 社會網與經濟行動[M].羅家德,譯.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1-31.
[14] 陳航英.土客結合:資本下鄉的用工機制研究[J].社會,2021(04):69-95.
[15] 格蘭諾維特.社會與經濟——信任、權力與制度[M].王水雄,羅家德,譯.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9:27-30.
[16] 費孝通.鄉土中國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17] 王德福.做人之道——熟人社會里的自我實現[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166-181.
[18] 董磊明,郭俊霞.鄉土社會中的面子觀與鄉村治理[J].中國社會科學,2017(08):147-160.
[19] 賀亮,張翼.在地化:資本農場中的農業雇工管理實踐——基于湖北李村金川農場的實地調研[J].農村經濟,2021(02):1-11.
[20] 楊華.農村人情的性質及其變化[J].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研究生學報,2008(01):41-44.
[21] 陳柏峰.熟人社會:村莊秩序機制的理想型探究[J].社會,2011(01):223-241.
[22] 孫新華,冷芳.社區本位的農業規模經營及其社會基礎[J].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06):1-10.
[23] 趙曉峰.農業現代化的中國道路[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20(05):120-133.
Relational Labor:The Social Foundation of Agricultural Scale Operation
SUN Xinhua,WU Na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Research Center for Shaanxi Rural Governance and Social Construction,Northwest Aamp;F University,Yangling,Shaanxi 712100,China)
Abstract:Agricultural scale operation is a key issue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While China’s agricultural scale operation is developing rapidly,it also presents a complicated picture.In view of the complexity of China’s agricultural scale operation,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logic and influence of employment patterns embedded in social relations in agricultural scale ope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eddedness.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difficulty of large-scale agricultural operations is that market-based labor cannot effectively solve the labor supervision problem in large-scale agricultural operations,and the relational labor that embeds market rules into relational rules makes both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have altruistic tendencies,to a certain extent, to mobilize the inner labor enthusiasm of workers,so that the main body of agricultural scale operation can avoid the predicament of business failure.The realization of relational employment depends on the main body of agricultural scale operation in the employment selection, production management and daily life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positive role of social relations. However,due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relations,the scope and extent of the role of relational employment are limited. Therefore,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scale operation requires not only dealing with economic relations,but also dealing with social relations.
Key words:agricultural scale operation;market-based labor;relational labor;social foundation
(責任編輯:董應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