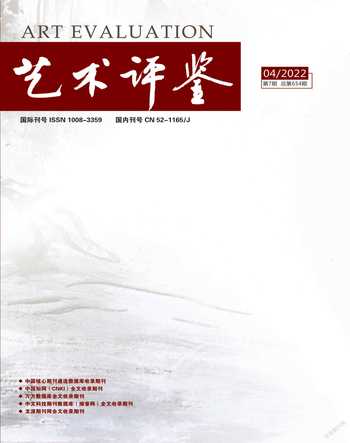于蘇賢《24首鋼琴賦格曲》的歸類介紹及審美價值
劉曉靜
摘要:《24首鋼琴賦格曲及創作分析》于2013年出版,是于蘇賢先生歷時六年的力作(2005-2011)。這套作品包括了多種音樂風格,是于蘇賢先生對自己復調研究成果的一次廣泛實踐,其中包括民族民間音樂、戲曲音樂、中國當代音樂、文人音樂,以及西方的調性音樂和十二音等不同的音樂風格。本文主要對24首賦格曲的主題數量、音樂風格特點、調式特點等進行歸類。
關鍵詞:于蘇賢? 對位法? 賦格
中圖分類號:J624.1??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3359(2022)07-0001-04
于蘇賢,作曲家、音樂理論家。1931年出生于哈爾濱市,1953年畢業于華東藝專音樂系并留校任教,1955年考入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本科,1960年畢業并留校任教。出版有《復調音樂教程》《20世紀復調音樂》和《中國傳統復調音樂》等理論性著作,奠定了于先生在復調音樂理論領域的權威地位。除此之外,其還發表了《調式思維在20世紀復調中的發展》《非序列無調性音樂的復調結構》《雙調性與多調性復調結構》《20世紀賦格的多元發展》《20世紀復調音樂中的節奏思維》等多篇論文。于蘇賢先生具有較高的學術地位,在數十年的教學生涯中,總結出自己的一套教學體系,并影響了很多當下活躍的作曲家,對我國作曲技術理論教育的發展有著突出貢獻,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24首鋼琴賦格曲及創作分析》①于2013年出版,是于蘇賢先生歷時六年的力作(2005-2011)。24首作品在調性安排上,從C大調、c小調開始按半音上行,依次按照24個大小調排列;在聲部數量上,包括二聲部、三聲部、四聲部;在結構上,包括單主題、二重賦格、三重賦格以及四重賦格;在曲式安排上,包括二部、三部、并列式、重疊式、回旋性、重疊與并列相結合結構等;主題的來源也非常豐富,既有自創主題,也有來自中西方音樂的主題,包括巴赫的姓氏、冼星海的《怒吼吧!黃河》《夕陽簫鼓》和《蘇武牧羊》的旋律片段、京劇音樂的素材、中國少數民族的音樂等;調式包括自然大小調、和聲大小調式、民族五聲調式和七聲調式、十二音序列等。以下是對于先生24首鋼琴賦格曲的歸類介紹。
一、于蘇賢《24首鋼琴賦格曲》基本要素歸類
在于先生的這部曲集中,共有24首賦格曲。筆者對這24首賦格曲的基本要素即主題數量、聲部數量、結構安排等做了一定的統計。
于先生的這部曲集中,賦格主題的數量有四種,分別是單主題賦格、二重賦格、三重賦格和四重賦格。其中單主題賦格的數量最多,占比最大,分別是第3、4、6、7、9、10、11、12、13、14、15、16、18、19、20、21、24共17首;二重賦格分別是第1、5、8、22、23共有5首;三重賦格是第2首;四重賦格是第17首。
《24首鋼琴賦格曲》中的聲部數量分為二聲部、三聲部以及四聲部。其中二聲部的賦格有第3、4、13共3首;三聲部的占比較多,分別是第6、7、8、9、10、11、12、14、15、18、19、20、21、24共有14首;四聲部的是第1、2、5、16、17、22、23共有7首。
24首賦格曲中的結構安排包括三部性結構、二部性結構、并列結構、重疊結構以及并列與重疊結構。
在傳統的賦格作品中,三部性結構最為常見,分別由呈示部-中間部-再現部組成。這三部分小節的數量相當,在規模和音樂展開上都具有平衡性。所以這種賦格總體來說具有三部性的結構特征。在于先生的作品中,具有三部性特征的分別是第3、4、6、7、9、10、12、14、15、16、18、19、20、21、24共有15首,占比非常大,可見于先生對于傳統賦格曲的繼承精神。
在二部性結構中,共有2首,分別是第11和13首。其中第11首也是繼承了傳統的呈示部-中間部-再現部的結構布局,但是這首作品的后半部分為前半部分全部音樂的逆行,因此它的整體結構原則為二部性。這種分布不均的小節數不具有三部性布局結構間的平衡性,所以將這首賦格的結構劃入二部性范圍之內,因為其逆行部分的起始點是全曲的中點。第13首同樣也可分為呈示部-中間部-再現部。這部作品共67小節,其中呈示部的長度為11小節,中間部50小節,再現部5小節。作者對于這部作品的整體結構設計與第11首相似,同樣為二部性。不同的是,這首作品的后半部分為前半部分的倒影變形,倒影始于作品中點靠前位置,即第31小節,并列式結構為第一首和第二十三首。之所以叫并列結構,是因為這兩首都是二重賦格,有兩個呈示部和兩個中間部。這部曲集中,作者對于二重賦格的曲式結構為呈示部Ⅰ-中間部Ⅰ-呈示部Ⅱ-中間部Ⅱ-再現部的這種并列式設計,因此作者稱其為并列結構。
重疊式結構是第5、8和第22首。這三首作品都是二重賦格作品,但是作者并沒有分別為每個主題寫作呈示部和中間部,而是兩個主題共用一個呈示部與中間部,因此屬于重疊式結構。
重疊與并列式結構的賦格是第2首和第17首。第2首是三重賦格,其中第一主題和第二主題共用一個呈示部Ⅰ-中間部Ⅰ,第三個主題為呈示部Ⅱ-中間部Ⅱ,因此屬于重疊式與并列式相結合的曲式結構。第17首作品為四重賦格,第一主題與第二主題共用一個呈示部Ⅰ-中間部Ⅰ,第三主題和第四主題共用呈示部Ⅱ-中間部Ⅱ,因此這兩首的曲式結構為重疊式與并列式相結合的結構。
綜上所述,從對于《24首鋼琴賦格曲》主題數量、聲部數量以及曲式結構安排的統計來看,賦格結構中的構成要素及布局主要是以傳統的賦格曲構成為依據的,但是也有一些例外,比如在曲式結構的安排上有很多創新,如出現了“重疊式與并列式結合”的賦格結構布局方式,這也體現了作者對賦格這一體裁的寫作可能性和容納量的更深入挖掘。
二、音樂風格特點的歸類
《24首鋼琴賦格曲》音樂風格特點可分為中國風格與西方風格兩大類。中國風格包括戲曲風格、文人音樂改編風格、少數民族風格、中國現當代音樂風格,以及自創的具有中國民族音樂特點的作品。其中戲曲風格的賦格有第4首、第7首和第12首,這三首作品都是吸收了中國傳統戲曲音樂,如京劇的元素來創作的。借鑒文人音樂的賦格有第6首和第10首。其中第6首的主題來自李煥之記譜、編合唱及伴奏的古琴弦歌《蘇武牧羊》中男低音聲部的旋律元素;第10首是依據中國傳統琵琶曲《夕陽簫鼓》中的旋律元素創作的。借鑒中國現當代音樂風格元素的有第1首,它的第一主題是作者用《怒吼吧!黃河》中的旋律元素創作的。中國少數民族音樂風格賦格是第19首,這是一首具有新疆風格的作品,不論是色彩性的裝飾音,還是節奏律動都體現了新疆音樂的風格特點。還有一種是作者自創的具有中國民族音樂風格特點的主題,共有八首分別是第、3、5、14、16、17、20、21首。第24首是以帕薩卡利亞的形式來創作的,雖然帕薩卡里亞是西方的體裁和技法,但是作者選擇了中國民族五聲調式作為主要的音高素材,選擇了宮、商、角、徵、羽五種調式之間的交替和變化作為這首賦格的音高發展原則。
在《24首鋼琴賦格曲》中,西方風格體現在十二音序列風格、通過巴赫相關的主題而形成的巴赫式風格、由自創主題形成的大小調風格。其中第23首的第二主題作者是運用十二音序列的主題來創作的賦格曲。第8首的第二主題是巴赫《十二平均律鋼琴曲集》第一冊第八首#d小調賦格主題的逆行變化。第22首的第一主題是以巴赫的姓氏(BACH)為音名創作的。這兩首作品都表達了作者對復調音樂大師——巴赫的極高敬意。另外有8首是作者自創的主題,都是使用了傳統的西方調性音樂寫作技法創作的賦格曲。除中國和西方兩大類風格之外,還有一首復風格作品的賦格即第23首。它的第一主題來自中國的文人音樂《蘇武牧羊》,第二主題的音高以序列音樂的構成方式為組織原則,且第二主題的呈示和展開都運用了十二音序列原則。
三、調式特點的歸類
《24首鋼琴賦格曲》中的調式方面使用了中國五聲性民族調式的賦格共有15首,分別是第1、4、6、7、9、10、11、12、13、15、18、19、22第二主題、23第一主題以及第24首;使用了西方大小調的共有11首,分別是2、3、5、8、14、16、17、20、21、22以及第23首中的第二主題。前文中提到的第23首賦格具有特殊性,它的第一、第二主題分別使用了中國民族五聲調式和十二音的音高組織原則。但是,在再現部中,作者將這兩個主題以豐富的對位技法重組,將它們融入進B大調的背景中,因此在這里將這首賦格歸在了兩個類別中。
相對來說,于先生的《24首鋼琴賦格曲》中,中國風格的賦格曲占比更大一些,從而也體現了作者對中國風格賦格的寫作投入了大量精力。中國風格主要體現在主題的旋律來源以及音階素材的五聲性或者七聲性的民族音階調式;還體現在和聲都是附加音或者是四五度疊置的平行聲部等。西方風格主要體現在作品是西洋大小調的調式,音高素材來源于自然或者和聲大小調的音階;和聲方面多以主、下屬、屬的功能性和聲,以及屬-主的和聲進行為主,從而起到強調和穩定調性的作用。賦格這一體裁在西方音樂幾百年的發展中,積累與沉淀出了一大批經典作品。中國風格的賦格曲雖然發展時間較短,但在近些年中國作曲家們孜孜不倦的努力下,也產生了許多高質量的、值得細致研究的作品,而且中國風格的賦格曲是非常有特點的,它在繼承西方傳統寫作技術的同時,還加入了本民族的音樂語言,具有用西方體裁與技術展現東方文化和魅力的二元性。
目前我國復調音樂的發展已經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很多作曲家、音樂理論家、音樂教育家都運用這種“東西方”結合的手法進行創作,具有較強的綜合性及創新性。例如:賀綠汀、羅忠镕、陳銘志、于蘇賢、段平泰、汪立三等許多作曲家都創作了多首中國風格的復調音樂作品,但是像于先生這種成套的24首賦格曲的創作目前并不多見,它是我國第一套延續了以西方24個大小調為排序方式寫作傳統的賦格套曲。雖然它借用了西方的寫作傳統,但是這本作品集在素材方面有多個來源,如戲曲主題、民族民間音樂主題、文人音樂主題,還有來自中國近現代音樂的主題等,這些能看到于先生的創作深刻扎根于我國優秀傳統音樂文化中。
四、于蘇賢《24首鋼琴賦格曲》的審美特征及其意義
于蘇賢的作品與理論研究成果豐厚,除《24首鋼琴賦格曲》外,《復調音樂教程》《20世紀復調音樂》《中國傳統復調音樂》等皆為開創性、奠基性著作。在創作中,于先生認為民族的“聲調”最能顯露特性,但如果只有民族性,又顯得有些單薄,只有吸取世界各民族、各地區的精華,才能真正提高民族的音樂創作水平。
于先生在創作中沖破傳統大、小調和聲體系的調式格局束縛,系統梳理出中國傳統復調音樂的形式、結構、技術等,同時將我國民間音樂和專業創作相結合,使民族風格與創作實踐聯系更緊密。
于先生強調中國民族風格五聲性的重要性,《24首鋼琴賦格曲》中將五聲調式的運用發揮到淋漓盡致。有14個主題運用了中國傳統民族調式進行創作,都具有清晰的調性結構。如第九首賦格曲主題,是在明確的E大調(宮系統)中吸納了傳統調式中的“清角”和“變徵”,形成了交替的調式結構,體現出對傳統民族五聲調式的擴展。
于先生將表現中國人民堅韌不拔精神的主題作為題材進行創作。如《24首鋼琴賦格曲》中第1首在創作時,正值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于先生選用冼星海《黃河大合唱》中《怒吼吧!黃河》的旋律作為這首賦格的第一主題,為曲目確定堅定有力、慷慨激昂的基調,力圖用器樂表明自身深刻的思想性。
于先生以戲曲、曲藝音樂為基礎,確定新的復調音樂形式,其用大量實例展現中國傳統復調音樂有別于西方音樂的獨特一面。如《24首鋼琴賦格曲》中第7首,再現部出現的中國戲曲音樂“小墊頭”特點的變形緊接模仿,使旋律連貫流暢。第12首的再現部中,運用中國傳統戲曲音樂中的加花裝飾技巧,構成特有的且獨具民族韻味的復調音樂。于先生多樣化的創作主題,具有中國鮮明的傳統文化特征。
極具特色的京劇元素常出現在于先生的作品中。京劇與賦格隸屬于東西方文明不同時域、不同層級的兩種藝術形式,在《24首鋼琴賦格曲》中第4首 #c 小調賦格曲的主題,具有明顯的京劇音樂聲韻及節奏感。曲目采用京劇典型的原板(2/4拍)板式,運用弱拍入唱、跳進為主的西方唱腔特點,增強節奏的不穩定性和旋律的流動感,給人們一種流暢如行云之感。
中國式的旋律發展邏輯在于先生的《24首鋼琴賦格曲》中得到了全面應用,充分顯示出中國傳統創作理念的魅力。中國傳統音樂中的結構模式慣用“鳳點頭”“鳳擺尾”“魚咬尾”“蛇脫殼”“唐大曲”“歌腔衍生”等結構方式,使音樂擁有此起彼伏的流動感。在于先生的第10首賦格曲中,也保留了“魚咬尾”的結構特征。
在于先生的作品中,不乏東方美學意象的作品。第13首的這部作品是一首二聲部黑鍵的賦格,音高素材是中國民族五聲音階構成。這首作品的呈示部雖為二聲部,但不像巴赫或其他西方作曲家那樣將兩個聲部的賦格織體用均值的、流動的音符寫得很滿,而是有大量的長音和空拍,類似于中國畫中以“留白”表現山水畫的意境,有一種金湘先生的美學理念“空、虛、散、含、離”中“空”的東方美學意象,從而產生“無聲勝有聲”的效果。這種美學理念在賦格曲織體中的體現,對于作品也是一種創新。
于先生充分吸取中西音樂之長,以西方傳統對位技法、和聲語言等進行擴展,同時不斷完善方法、技巧,努力發掘、利用中國傳統音樂素材,使音樂創作能自由、充分、深刻地表現當代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其在《中國傳統復調音樂中》提到:“中國傳統復調音樂形式這一概念,是特指在中國大地上形成發展起來的、蘊含著中華民族最古老、最純粹的遺傳基因的復調音樂形式,與西方9世紀的奧爾加濃開始的復調音樂是不能混淆的兩個概念。當然也存在著共性特征,這就是構成復調音樂規律的科學性方面的共同原則,如對節奏、音高、音色、音階、調式、調性、單音、復音、結構形式等方面的處理技巧都存在著共同點。中國復調音樂與西方復調音樂分屬于不同的領域、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生存環境和各自所經歷的不同發展道路,總之,是傳承著各自民族審美價值的兩個事物。”②這些觀點在她的作品中具體表現在以下方面。
其一,于蘇賢的《24首鋼琴賦格曲》在24個大小調上與五聲性音調相結合譜曲,充滿了中國特色,但性格又各不相同;從旋律的走向、節奏的安排及材料的發展方面來看都具有極大的發展空間,為中國復調的長遠發展提供了范本。
其二,于蘇賢的復調體系多源于多元結合,不僅對歐美、俄-蘇等西方傳統復調理論全方位繼承與發展,同時系統性地研究20世紀新的復調技術,對中國傳統復調理論進行新的構建,其為建立屬于中國自己的復調教學體系作出了貢獻。
其三,于蘇賢胸懷開闊,其認為無論蘇俄、英美,無論過去還是現在,只有是優秀的、正確的成果就要吸收;只要符合音樂內容的審美需要,能夠表達音樂內涵,具有審美價值的音樂作品就是好的作品;作曲技術理論的學習就是為了應用,只要運用得當,符合作品所要表達的內涵,就是好的技術、就是好的運用。這樣的觀念,對于推動我國作曲技法的創新發展、對于建立科學的技法體系、對于繁榮我國音樂作曲事業,寫出我們祖國和人民的偉大音樂作品,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24首鋼琴賦格曲》可以說無一例外的都展現了于蘇賢縝密的復調創作思維以及高超的復調創作技法。最重要的是這些技法與中國傳統音樂語言的主題相結合的絕妙之處,不僅具有音樂價值,而且具有學術價值,值得我們分析研究。
于蘇賢對祖國的熱愛、對民族音樂的熱愛,對中國傳統復調音樂的思維特性、調性結構特征、獨特的聲韻體系、結構體系等各個方面,都體現在了這部帶有鮮明中國民族音樂神韻的《24首鋼琴賦格曲》中。
《24首鋼琴賦格曲》是于蘇賢在耄耋之年歷時六年的嘔心之作。其將西方復調技法與我國民族音樂有機結合,對中國民族賦格曲的創作有著教科書般的指導意義。評析于先生的美學思想,不僅為全面解讀其作品提供幫助,更重要的,則是對研究復調技術,尤其是中國傳統復調創作發展狀況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考察依據。
于蘇賢強調民族性,并不是要摒棄已有的復調體系。所謂中西文化,既相互沖突又相互交融。中西方的文化之間存在著共性,所以兩者之間必然存在可比性。于蘇賢是我國作曲領域的自覺探索者、開拓者、引路人,其創新思想理念與嚴謹執著的精神,非常值得后輩終身學習;其復調教學體系具有鮮明的個性和優越性。緊隨其后的復調學者們,定會在共同努力下,以開闊、包容、不斷優化的內容和理念深入到中國專業復調教學中,擴大中國傳統復調理論與技法在世界的影響力。
①杜曉十,《于蘇賢〈24首鋼琴賦格曲及創作分析〉》序言,2011年仲夏。
②于蘇賢,《中國傳統復調音樂》,第五章緒論,200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