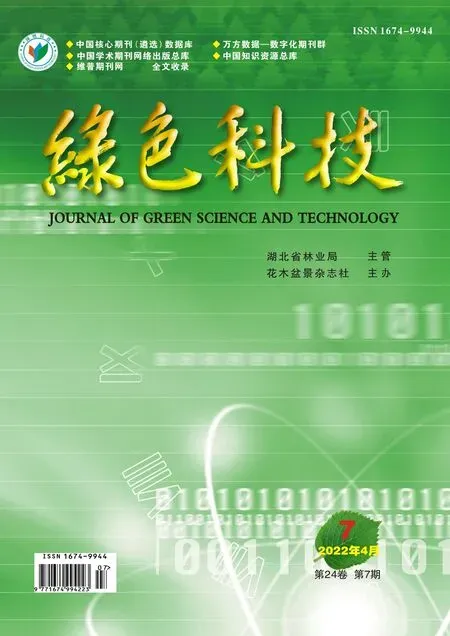濟南中心城區公共服務資源時空演化分析
張 晴,邢雅涵,趙金麗
(山東師范大學 地理與環境學院,山東 濟南 250014)
1 引言
公共服務設施是指由政府部門直接或間接提供,供全體國民使用的服務或設施,一般包括教育、醫療、文體、商業、市政等社會性基礎設施[1]。公共服務設施的建設完善和優化配置,是推動區域可持續發展和新型城鎮化的重要環節。公共服務分配不均衡會加劇居住分異和社會隔離,擴大城市內部發展差距,影響社會公平[2]。
目前,地理學界已對公共設施空間分布與空間公平進行了深入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空間區位選擇和布局優化研究。1968年Teitz[3]率先提出了公共服務設施理論,并探討了公共服務配置與福利最大化的問題;Murray[4]對影響公共服務設施布局的區位因素進行分析,發現土地適宜性、空間可達性和土地價格是主導因素;劉萌偉等[5]采用Pareto多目標遺傳算法探討了深圳市公用設施選址問題。二是公共服務設施可達性研究。Pacione[6]運用潛能模型方法對格拉斯哥地區的中學設施進行可達性的測度;吳建軍等[7]基于各種不同的空間可達性模型,詳細剖析了河南省蘭考縣各行政村的醫療設施可達性特征;廖宇亮等[8]通過等時線模型對教育設施進行可達性量度,并對其設施劃片合理性進行分析。三是公共服務設施社會分異研究。高軍波等[9]研究了廣州市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的社會分異性,發現其社會分異極其突出;Panter等[10]研究了家庭收入與公共服務設施布局之間的關系,其結果表明,平均收入越低,使用公共服務設施越頻繁,到達距離也越遠。
縱觀相關研究文獻,學者們主要是從城市規劃、城市社會的視角開展公共服務設施研究,通過公共設施“點的數量”和“點的位置”研究城市公共設施的布局、規模、可達性、服務能力等,其中大多集中于公共服務設施現狀分析和布局優化,長時間跨度的研究相對較少[11]。本文擬利用濟南中心城區中小學及醫院的成立時間、位置和發展規模等數據,對1990年以來濟南基礎教育和醫療服務資源時空演化特征進行分析,以期為濟南市公共服務設施空間優化提供參考和借鑒。
2 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2.1 研究區域與數據來源
本文以濟南中心城區為研究區域,共包括歷下區、歷城區、市中區、天橋區和槐蔭區5個市轄區,在街道(鄉鎮)這一空間尺度上,對其1990年以來中小學與醫院的時空演化特征進行研究。利用濟南市各個市轄區人民政府提供的中小學名錄信息及微醫平臺(https://www.guahao.com/)提供的醫院名錄信息,共得到濟南市中心城區448所中小學信息和66所二級、三級醫院信息,經過官網查詢和網絡搜索,得到各機構的成立時間等相關屬性信息,并利用百度拾取坐標系統將各機構地理位置矢量化,構建濟南中心城區基礎教育設施和醫療服務設施空間數據庫。其中,對1990年以來新建學校,主要獲取其成立時間和學校經濟類型并進行評價;對1990年以來新建醫院,主要獲取其成立時間、醫院等級、醫院類型等屬性信息并進行評價[12]。
2.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核密度估計法揭示濟南市中心城區教育和醫療設施的空間格局現狀和空間演化過程。核密估計度法(KDE)揭示了地理現象空間擴散的距離衰減規律,距離越近的對象賦予較大的權重。該方法在顯示和分析點狀要素時極為有用[13]。
(1)
式(1)中:K(x)是為核密度方程;h是閾值;n是搜索窗口內點數;d是數據的維數,當d=2時為最常用的核密度公式:
(2)
式(2)中:(x-xi)2+(y-yi)2表示點(xi,yi)與(x,y)的離差。
3 結果與分析
3.1 新增資源視角下濟南中心城區公共服務資源的時空演化特征
3.1.1 新增基礎教育資源的時空演化特征
采用核密度估計法對濟南新增基礎教育資源的時空演化特征進行分析(圖1)。從圖1中可以看出,1990~2000年,新增資源的核密度高值區集中于陡溝街道、舜玉街道和姚家街道等;2000~2010年,核密度高值區集中于四里村街道、北園街道、唐冶街道、荷花路街道和王舍人街道等;2010~2020年,核密度高值區集中于唐冶街道等。隨著時間推移,教育資源進一步向外部擴張,次級集聚的特征明顯,尤其是在2010年之后,唐冶街道、王舍人街道的核密度值有較大幅度的提高,峰值區不斷擴大。相反的是,濟南中心城區的南部山區新增教育資源始終較少,教育資源分布不平衡。
在新增學校的類型上,以公立學校為主,但隨著居民收入提升及對教育重視程度的提高,民辦學校和國際學校逐漸蓬勃發展,新增民辦學校和國際學校主要集中在歷下區智遠街道、姚家街道和歷城區荷花街道和董家鎮街道以及市中區舜玉路街道。同時,由于外來務工人員大量增多,濟南市教育部門出臺相對寬松的政策,并劃定定點外來務工子女就學學校,保障外來務工人員子女的入學權利,主要集中在歷下區、槐蔭區和天橋區。

(a)1990~2000年 (b)2000~2010年 (c)2010~2020年
3.1.2 新增醫療資源的時空演化特征
采用核密度估計法對濟南新增醫療資源的時空演化特征進行分析(圖2)。從圖2中可以看出,1990~2000年,新增資源的核密度高值區集中于南村街道、五里溝街道和姚家街道等;2000~2010年,核密度高值區集中于濼源街道、魏家莊街道、華山街道、姚家街道和臘山街道等;2010~2020年,核密度高值區集中于段店北路街道、大明湖街道、舜玉路街道和鮑山街道等。相比于基礎教育資源,新增醫療資源分布更為集中,且醫療資源向外圍擴散的速度較為緩慢,高值區始終集中于歷下區,歷城區、天橋區等外圍城區始終處于低值區。
在新增醫院等級上,新增高等級醫院較少,但醫院的綜合性能力較強。隨著濟南人口總量不斷擴大、流動人口不斷增多,老齡人口持續增加等特點,醫療設施在供給總量、供給結構及空間配置等方面均面臨巨大的壓力,部分高等級醫院逐漸建立新院區或分院區,但依然不能滿足人口增長、結構變化以及城市功能調整對醫療服務設施的需求。
在新增醫院的經濟類型上,以國營為主,民營醫院極少,且民營醫院的服務質量和社會效益較低,政府應在人口聚居但醫療資源相對缺乏的區域,鼓勵社會資本設置綜合性醫療機構提供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在醫療資源相對充足的區域,鼓勵社會資本舉辦水平高、規模大、特色突出的醫療機構,引導錯位發展,實現優勢互補[11]。

(a)1990~2000年 (b)2000~2010年 (c)2010~2020年
3.2 整體資源視角下濟南中心城區公共服務資源的時空演化特征
3.2.1 基礎教育資源的時空演化特征
采用核密度估計法對濟南基礎教育資源的時空演化特征進行分析(圖3)。在空間演化格局上,濟南市基礎教育資源熱點區域始終集中在濟南市中心城區的中部,即泉城路街道、制錦市街道、趵突泉街道,分布范圍較廣,且高值區基本相連,呈現集中連片的“單核結構”。隨時間推移,學校向外部擴張的趨勢逐漸加強,尤其是東部高新區及周邊地區核密度值有較大幅度提高。在空間差異上,外圍地區尤其是歷城區南部山區核密度值始終較小,應加強外圍地區尤其是南部山區的教育設施建設,促進公共服務均等化。在時間演化趨勢上(圖4),各區不同時間階段增速有一定差異,2010年之后增速均呈現明顯增長趨勢。未來應加強各個地區之間學校的聯系和合作,“以強帶弱”,提高教育質量,改善基礎教育資源的空間不均衡性。

(a)2000年 (b)2010年 (c)2020年

圖4 1990、2000、2010和2020年各年份濟南市
3.2.2 醫療資源的時空演化特征
采用核密度估計法對濟南醫療服務資源的時空演化特征進行分析(圖5)。在空間演化格局上,濟南市中心城區醫療資源主要集中在濟南市中心城區的中部,即大明湖街道—趵突泉街道—解放路街道—千佛山街道—泉城路街道圍合的片區、北村街道片區和大觀園街道片區,分布范圍相對較少,且高值區相對分散,呈現“多核結構”。相比于基礎教育資源,醫療資源的高密度區范圍更小,且向外擴張的趨勢不明顯。在空間差異上,與基礎教育資源相似,外圍地區尤其是歷城區南部山區核密度值始終較小。在時間演化趨勢上(圖6),除天橋區外,各個地區的醫療機構均有明顯增加。未來應在規范醫療服務設施主體決策行為與科學城市規劃的引導下,積極醫療服務設施的空間疏散與均衡布局,縮短居民就醫時間,減少交通擁堵。

(a)2000年 (b)2010年 (c)2020年

圖6 1990~2020年歷年濟南市中心城區二級、
4 結論與討論
本文采用濟南市中心城區5個市轄區的基礎教育和醫療服務資源數據,從新增和整體兩個視角探討了其時空演化特征,得到如下結論。
(1)從新增資源來看,濟南新增基礎教育資源主要集中于王舍人街道、唐冶街道等街道,分布較為分散,向外擴張明顯;而新增醫療服務資源主要集中于姚家街道等街道,分布較為集中。
(2)從整體資源來看,濟南市中心城區的基礎教育和醫療資源主要聚集在濟南市中心城區的中部地區,而濟南市南部山區的基礎教育和醫療服務資源始終較少。其中,基礎教育資源高值區呈集中連片的“單核結構”,且次高值區向外擴張明顯,醫療服務資源高值區分布范圍較小,且呈現出較為穩定的“多核結構”。
(3)濟南市公共服務資源分布不均衡,且民營學校及醫院較少。為了提高濟南市的教育和醫療水平,促進公共服務均等化,政府應加大對基礎教育和醫療服務等公共服務設施空間布局與優化的主導作用,增強對南部山區的轉移支付力度,并加強對民營學校和醫院的監管與扶持,加大人才的引進,鼓勵民營學校和醫院的發展。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有待深入探討的方面。其中對于基礎教育及醫療服務兩類資源的綜合評價,分別將小學、中學以及二、三級醫院整合在了一起,但考慮到中小學以及二三級醫院的服務半徑和人口門檻存在差異,將來需要開展對小學、中學和一、二、三級醫院的分類研究,以更加細致地了解其現狀和空間演化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