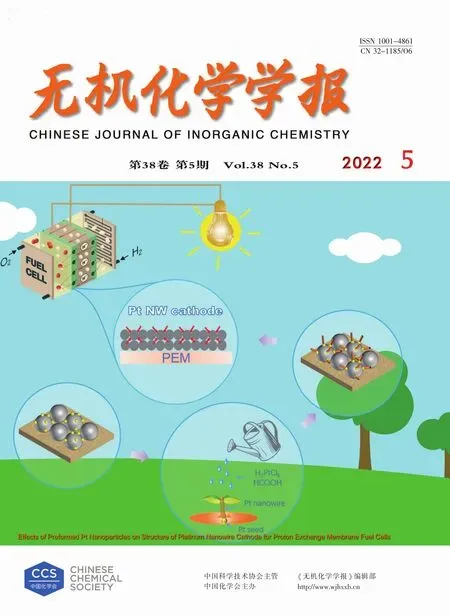ZnS@C/rGO復合材料的制備及其電化學可逆儲鋰性能
徐 剛 姜孝男 陳衛祥
(浙江大學化學系,杭州 310027)
0 引言
鋰離子電池具有比能量高、循環壽命長和環境友好等優點,已廣泛地應用于便攜式電子設備、電動汽車和儲能等領域。目前,商業化的鋰離子電池仍主要使用石墨材料作為其負極。但是,傳統石墨電極材料的電化學儲鋰理論比容量較低(372 mAh·g-1),倍率性能也不夠好[1?2],難以滿足其在電動汽車和儲能等應用領域對高能量密度、高功率密度和長循環壽命等方面的要求。因此,研發電化學儲鋰比容量高、倍率特性好和長循環性能穩定的新型電極材料對高性能鋰離子電池具有重要意義。
與傳統石墨負極材料相比,過渡金屬硫化物具有更高的電化學儲鋰容量,其電化學儲鋰性能和在鋰離子電池中的應用研究吸引了人們的廣泛關注[3]。其中ZnS材料的電化學儲鋰理論比容量可以達到963 mAh·g-1,被認為是一種具有發展潛力的鋰離子電池負極材料[4],其電化學儲鋰的電極反應主要包括轉化反應(ZnS+2Li++2e-→Zn+Li2S)和隨后Zn與鋰的合金化反應(Zn+xLi++xe-→LixZn,LixZn=LiZn2、Li2Zn3、Li2Zn5、LiZn4,最后生成 LiZn)[5?6]。但是,ZnS電極材料在反復的嵌鋰/脫鋰過程中會產生明顯的體積變化,導致活性物質的粉化和電極結構的坍塌,最終導致其儲鋰比容量的快速衰減。另外,ZnS材料低的電導率也不利于電極反應過程中的電子傳遞,會明顯降低電池的高倍率性能[7]。
針對ZnS材料電化學可逆儲鋰過程中體積變化和電導率低等問題,構建合理的納米結構并與導電性能好的碳材料復合被認為是克服上述缺點的一種有效策略。納米級的ZnS晶體可以減緩其嵌鋰/脫鋰過程中的體積變化,并可以縮短和提供更多的鋰離子擴散路徑。與導電性能好的碳材料復合可以增強其導電性能和提供更多的導電通道,增強電極反應過程中電子的快速轉移能力,提升倍率性能。同時,柔性的碳材料可有效地緩沖可逆儲鋰過程中活性物質的體積變化,提高充放電循環穩定性能。葡萄糖[2,4,8?11]和聚多巴胺[12?13]等常被作為碳源,通過溶劑熱或水熱反應及隨后的熱處理可以制備無定形碳包覆的金屬硫化物的復合材料,并使所制備的復合材料具有高的電化學儲鋰比容量和穩定的循環性能。如,Bai等以葡萄糖作為碳源制備了1T?MoS2/C復合材料,改善了其電化學儲鋰性能,在1.0 A·g-1電流密度下循環300次后仍保持870 mAh·g-1的可逆比容量[9];Ma等以葡萄糖為碳源制備了H?ZnS@C空心亞微球[11],得益于無定形碳的多孔結構和良好的導電性,以及無定形碳層的緩沖作用,H?ZnS@C顯示了優異的電化學儲鋰性能;Du等以葡萄糖為碳源,通過溶劑熱反應途徑制備了核-殼結構的ZnS/C復合材料,在100 mA·g-1電流密度下循環300次后,其電化學儲鋰可逆比容量仍有741 mAh·g-1[8]。
與無定形碳材料相比,石墨烯具有更高的導電性能、更大的比表面積、穩定的化學性質和固有的柔韌性等眾多優異的特性[3]。石墨烯可以更好地增強金屬硫化物復合材料的導電性能,同時能緩解電化學儲鋰過程中的體積膨脹效應,改善充放電的循環穩定性[14?17]。Zhang等制備了ZnS量子點與石墨烯的復合材料,該復合材料在100 mA·g-1電流密度下充放電循環100次后仍保持了759 mAh·g-1的可逆比容量[14]。Feng等將ZnS納米晶與還原氧化石墨烯(rGO)復合,作為電化學儲鋰電極材料,其可逆比容量在100次充放電循環后仍有776 mAh·g-1,顯示了其穩定的循環性能[16]。另外有研究表明,利用不同碳材料(如無定形碳和石墨烯)的特點,可以構建2種不同碳材料與金屬氧化物的復合納米材料,并使其具有優異的電化學儲鋰性能[18?19]。如:Wang等將ZnO納米粒子負載在rGO上,再以葡萄糖作為無定形碳的碳源,制備了ZnO/rGO/C復合材料,作為電化學儲鋰電極材料,該復合材料在100次循環后仍有830 mAh·g-1的可逆比容量[18],但該復合材料的長循環穩定性能沒有被進一步研究。
為了制備電化學儲鋰可逆比容量高、倍率特性好和長循環性能穩定的電極材料,我們通過溶劑熱反應-水熱處理的途徑,首先以葡萄糖作為碳源制備了無定形碳包覆的ZnS納米顆粒(ZnS@C),然后再與水熱還原的rGO復合,制備得到ZnS@C/rGO復合材料。與ZnS@C和ZnS/rGO復合材料相比,ZnS@C/rGO具有更優異的電化學儲鋰性能,在2.0 A·g-1電流密度下其可逆比容量可以達到1 460 mAh·g-1,并在1 200次循環后仍保持有1 096 mAh·g-1的可逆比容量,展現了其優異的長循環穩定性能。
1 實驗部分
1.1 ZnS@C復合材料的制備
將1.0 mmol(0.297 g)Zn(NO3)2·6H2O、0.4 g咪唑和0.05 g葡萄糖在不斷攪拌下溶解于30 mL甲醇中,再加入2.5 mmol(0.303 g)L?半胱氨酸并繼續攪拌2 h得到均勻的混合液。將該混合溶液轉移到100 mL的水熱反應釜中,在180℃下保溫24 h,然后自然冷卻至室溫。將所得沉淀分別用去離子水和無水乙醇洗滌,然后冷凍干燥24 h,將干燥后的沉淀產物在氬氣氛圍中,以5℃·min-1的升溫速率加熱至500℃并保溫2 h,最后得到ZnS@C復合顆粒。另外,在不添加葡萄糖的條件下用同樣的溶劑熱法制備單一的ZnS材料。
1.2 ZnS@C/rGO復合材料的制備
將100 mg上述制得的ZnS@C復合顆粒加入到35 mL去離子水中,并超聲處理使其均勻分散,再緩慢逐滴加入10 mL氧化石墨烯的水溶液(含量相當于用改進的Hummers法將0.045 g的石墨制備為氧化石墨稀[20?21]),磁力攪拌12 h,隨后將均勻的混合分散體系轉移到100 mL的水熱反應釜中,在120℃下保溫48 h,然后自然冷卻至室溫。將所得的沉淀分別用去離子水和無水乙醇洗滌,冷凍干燥24 h,最后得到ZnS@C/rGO復合材料。作為對比,將先前制得的ZnS納米材料,按類似的方法和步驟制備得到ZnS/rGO復合材料。
1.3 材料的表征
樣品的晶體結構表征在Ultima Ⅳ X射線衍射儀(XRD)上進行,工作電壓40 kV,工作電流30 mA,Cu Kα靶,λ=0.154 056 nm,掃描范圍2θ=20°~80°,掃描速度為 15(°)·min-1。用場發射掃描電鏡(SEM,SU?8010型,工作電壓5 kV,工作電流10 μA)和高分辨透射電鏡(HRTEM,JEM 2100F型,加速電壓200 kV)對樣品的微觀結構和形貌進行表征。用X射線光電子能譜(XPS,Thermo Scientific ESCALAB 250Xi,鋁靶)表征了復合材料的元素組成及化學價態。熱重(TG)分析在熱重-差示綜合分析儀(Mettler,TGA/DSC1 1100SF)上進行(氧氣氣氛,從室溫升至700℃,升溫速率為5℃·min-1)。
1.4 電化學儲鋰性能測試
工作電極的制備過程如下:將上述制得的ZnS@C、ZnS/rGO或ZnS@C/rGO復合材料作為電化學儲鋰活性物質,與導電劑乙炔黑和黏結劑聚偏氟乙烯(PVDF)按質量比7∶1.5∶1.5混合,以N?甲基吡咯烷酮為分散劑,充分研磨混合后得到均勻的漿料,將該漿料均勻地涂覆在銅箔之上,在120℃下真空烘干12 h后,壓制成工作電極。在充滿氬氣的手套箱中,將工作電極與對電極鋰箔組裝成兩電極的測試電池(LIR2025 扣式),電解液為 1 mol·L-1LiPF6的碳酸二甲酯與碳酸二乙酯混合溶液(體積比為1∶1),隔膜為Celgard?2300。充放電實驗在LAND CT2001A電池測試系統上進行。循環伏安(CV)和電化學交流阻抗(EIS)測試在CHI660E電化學工作站上進行。CV測試的電位范圍為0~3.0 V,掃描速度為0.5 mV·s-1;EIS測試的頻率范圍在0.01 Hz~100 kHz,正弦波的振幅為5.0 mV。
2 結果與討論
2.1 材料的微觀結構和形貌
圖1a為樣品的XRD圖。從圖中可知,ZnS和3種復合材料在2θ=27.4°、28.7°、30.6°、47.7°、52.0°和56.6°處出現了衍射峰,分別對應ZnS晶體的(101)、(102)、(103)、(110)、(109)和 (202)晶 面 (PDF No.89 ?2739),ZnS晶體為纖維鋅礦?6H晶型。用TG分析探究了復合材料的組成。圖1b是ZnS@C、ZnS/rGO和ZnS@C/rGO復合材料的TG曲線。如圖所示,在100℃之前的失重可以歸因于復合材料中少量水分的揮發。ZnS/rGO和ZnS@C/rGO在200~400℃之間顯示了一段緩慢失重過程,可對應rGO中含氧官能團的氧化降解。3種復合材料在400~600℃之間都顯示了一段較明顯和較快的失重過程,對應無定形碳和rGO材料的氧化分解,以及ZnS在O2氛圍的氧化。ZnS@C、ZnS/rGO和ZnS@C/rGO復合材料最后的失重比例分別為24.9%、43.4%和49.4%。由于無定形碳和石墨烯碳材料最后都被氧化成CO2,復合材料最后余下的固體應該僅為ZnO。因此,可以計算得到ZnS@C、ZnS/rGO和ZnS@C/rGO復合材料中ZnS、無定形碳和rGO含量,結果如表1所示。

表1 ZnS@C、ZnS/rGO和ZnS@C/rGO復合材料各組分含量Table 1 Component contents of ZnS@C,ZnS/rGO,and ZnS@C/rGO composites

圖1 樣品的(a)XRD圖和(b)TG曲線Fig.1 (a)XRD patterns and(b)TG curves of the samples
圖2是ZnS和復合材料的SEM圖。從圖2a和2b中可以觀察到,ZnS顯示了尺寸在0.3~1.0μm的不規則顆粒形貌,這些顆粒是由更細小的ZnS納米晶體聚集形成。如圖2c和2d所示,ZnS@C復合材料為0.4~1.0μm的顆粒,并具有較明顯的多孔結構,這些顆粒是由分散在無定形碳中粒徑更小的ZnS晶體組成的復合粒子。圖2e和2f表明ZnS/rGO復合材料中0.3~1.0μm的ZnS顆粒較均勻地分散在rGO表面。從圖2g和2h中可以看出,在ZnS@C/rGO復合材料中,0.3~1.0μm的ZnS@C復合顆粒較好地負載在rGO表面并分散在rGO的導電網絡結構中。圖2i顯示了ZnS@C/rGO復合材料的元素分布,其中Zn與S元素分布范圍與ZnS@C的形貌一致,C歸屬于無定形碳和rGO,O主要來源于rGO中的含氧官能團。

圖2 (a、b)ZnS、(c、d)ZnS@C、(e、f)ZnS/rGO和(g、h)ZnS@C/rGO復合材料的SEM圖;(i)ZnS@C/rGO的元素分布圖Fig.2 SEM images of(a,b)ZnS,(c,d)ZnS@C,(e,f)ZnS/rGO,and(g,h)ZnS@C/rGO composites;(i)Element mappings of ZnS@C/rGO composite
用TEM和HRTEM進一步表征了ZnS和復合材料的微觀結構。如圖3a~3c所示,ZnS材料主要由平均粒徑為12 nm的納米晶體組成,由于其較大的表面能,這些ZnS納米晶體多數聚集在一起形成0.3~1.0μm不規則形貌的二次顆粒。圖3d~3f顯示平均粒徑為10 nm的ZnS納米晶體均勻分散在無定形碳中,形成了類球形的ZnS@C復合顆粒,其平均直徑為500 nm,顆粒之間相互連接或重堆在一起,與SEM表征結果一致。圖3f進一步顯示了ZnS納米晶體的晶格條紋,可以發現ZnS晶體的晶格條紋在到達其邊緣前就消失了,說明ZnS納米晶體被無定形碳包覆。圖3g~3i顯示在ZnS/rGO復合材料中,平均粒徑為12 nm的ZnS納米晶體均勻地分散在rGO表面。圖3j~3l顯示在ZnS@C/rGO復合材料中,ZnS@C復合顆粒和少數離散的ZnS納米晶體分散在rGO表面。這些少數離散的ZnS納米晶體應該是在第二步水熱處理步驟中,超聲波處理將ZnS@C再次分散于去離子水中時,從ZnS@C復合顆粒表面掉落的。由圖3中HRTEM圖可知,ZnS晶體的(102)和(101)晶面的層間距分別是0.31和0.32 nm。
用XPS分析表征了典型ZnS@C/rGO復合材料的元素組成及價態。ZnS@C/rGO復合材料的XPS全譜圖(圖4a)表明,復合材料的元素組成為Zn、S、C和O,其中Zn和S的原子比為1∶1.1,接近ZnS的化學計量比。另外,O元素主要來源于rGO中的含氧官能團。在1 022.0和1 045.0 eV處出現的2個峰(圖4b),分別歸屬于 Zn2p3/2和 Zn2p1/2。圖 4c 是 S2p的XPS譜圖,其可以卷積擬合為3個峰,分別對應161.7 eV處的S2p3/2峰和163.0 eV處的S2p1/2峰,而在164.7 eV處的擬合峰表明硫化物與碳材料之間有共價鍵相連[22]。圖4d顯示了C1s的特征峰,其可卷積擬合成在284.5、285.0、286.0和288.5 eV處的4個峰,分別對應C=C、C—O、C=O和O—C=O[16,23]。

圖4 ZnS@C/rGO復合材料的XPS譜圖:(a)總譜圖、(b)Zn2p、(c)S2p和(d)C1sFig.4 XPS spectra of ZnS@C/rGO composite:(a)survey spectrum,spectra of(b)Zn2p,(c)S2p,and(d)C1s
2.2 電化學儲鋰性能
用CV法研究了ZnS和復合材料電極電化學儲鋰的氧化還原反應電對。如圖5a和5b所示,ZnS和ZnS@C復合材料電極顯示了相似的CV特征。在首次陰極掃描過程中,在0.8~0.4 V處的陰極電流對應ZnS儲鋰過程中的轉化反應(ZnS+2Li++2e-→Zn+Li2S),同時,在該電位區間也伴隨著固體電解質界面(SEI)膜的形成[12];在0.4~0 V電位區間的陰極電流對應Zn與Li+的多步合金化反應(Zn+xLi++xe-→LixZn,LixZn=LiZn2、Li2Zn3、Li2Zn5、LiZn4)[6,24],最后在 0 V 電位處Zn完全鋰化成LiZn合金。在首次陽極掃描過程中,0~1.0 V的氧化電流對應LixZn合金的多步去鋰化反應;在1.41 V處出現的1個明顯氧化峰代表Zn與Li2S生成ZnS。另外,在首次CV過程中,在1.91 V/1.60 V處出現了一對還原氧化峰,這是由于樣品中少量的ZnO雜質不可逆生成Li2O的反應[8];在2.40 V處出現的陽極峰對應Li2S的去鋰化生成S的反應[25?26]。在第2次和第3次的CV曲線中,1.91 V/1.60 V處的一對還原氧化峰和2.40 V處的陽極峰基本消失。對于ZnS/rGO和ZnS@C/rGO復合材料電極,如圖5c和5d所示,在首次陰極掃描過程中,在1.62或1.55 V處出現的還原峰主要是由于rGO中含氧官能團的還原[27];在0.8~0.4 V和0.4~0 V處的陰極電流分別對應ZnS的轉化反應和Zn多步鋰化的合金化反應[28]。在陽極掃描過程中,在0~1.0 V電位區間的氧化電流是由于LixZn合金的多步去鋰化反應,在1.41 V處出現的氧化峰代表ZnS的再次形成,而在2.38 V處的氧化峰代表Li2S去鋰化生成S。相應地,第2次陰極掃描過程中,在2.08 V出現了對應S鋰化反應的陰極峰。值得注意的是,與另外3種樣品相比,ZnS@C/rGO復合材料電極在3次CV測試中1.42 V處的氧化峰幾乎完全重合,顯示其具有穩定的電化學儲鋰性能。

圖5 (a)ZnS、(b)ZnS@C、(c)ZnS/rGO及(d)ZnS@C/rGO復合材料電極在0.5 mV·s-1掃速下的CV曲線Fig.5 CV curves of(a)ZnS,(b)ZnS@C,(c)ZnS/rGO,and(d)ZnS@C/rGO composites electrodes at a scanning rate of 0.5 mV·s-1
圖6為ZnS和復合材料電極在100 mA·g-1電流密度下的前3次恒流充放電曲線,相應充放電曲線的電位平臺與圖5的CV曲線相符合。在首次充放電循環過程中ZnS、ZnS@C、ZnS/rGO和ZnS@C/rGO電極的放電(鋰化)比容量分別為1 408、1 324、1 646和1 733 mAh·g-1,初始的電化學儲鋰可逆比容量分別為551、660、940和1 101 mAh·g-1,相應的首次充放電庫侖效率分別為39.1%、49.9%、57.1%和63.5%。一般認為首次不可逆儲鋰容量的損失主要是由于首次儲鋰過程中SEI膜的形成和其他不可逆的電極反應[29]。對于ZnS電極,其在儲鋰過程中會產生較大的體積變化,導致其粉化和電極結構的破壞,粉化后的活性物質脫離了有效的電接觸而不能被利用,這也是其首次充放電庫侖效率相當低的重要原因。通過碳材料的包覆或復合,可以緩解ZnS材料在儲鋰過程中的體積變化引起的不良結果。對于ZnS@C/rGO復合材料電極,經無定形碳包覆并與rGO復合后,能更好地緩沖ZnS在鋰化/去鋰化過程中的體積變化和保持電極結構的穩定,從而改善其電化學儲鋰性能。盡管ZnS@C/rGO電極的首次充放電庫侖效率還不夠高,但是在第2次和第3次充放電時,其庫侖效率分別增加到90.5%和92.5%。
圖7a顯示了ZnS和復合材料電極在100 mA·g-1電流密度下的充放電循環性能。如圖7a所示,ZnS電極在前3次充放電循環的電化學儲鋰比容量快速下降,在第3次循環時其可逆比容量已降低為231 mAh·g-1,在100次循環后其可逆比容量僅有84 mAh·g-1。ZnS電極儲鋰比容量的快速下降主要是ZnS材料在鋰化/去鋰化過程中產生較大的體積變化,導致活性物質的粉化和電極結構的坍塌。與ZnS電極相比,ZnS@C復合材料電極的充放電循環性能有所改善,但是其儲鋰可逆比容量隨著循環次數的增加還是有明顯的下降,在100次循環后其可逆比容量為173 mAh·g-1,容量保持率為25.9%。對于ZnS/rGO電極,除了在前3次充放電循環過程中儲鋰比容量有所下降,在隨后的循環過程中顯示了穩定的循環性能,循環100次后保持了702 mAh·g-1的可逆比容量。與ZnS@C和ZnS/rGO電極相比,ZnS@C/rGO復合材料電極顯示了更高的電化學儲鋰比容量和更穩定的循環性能。ZnS@C/rGO電極的初始可逆比容量為1 101 mAh·g-1,隨著循環次數的增加其儲鋰比容量有一個上升的趨勢,在100次循環后儲鋰可逆比容量為1 569 mAh·g-1。圖7a還顯示了不同電極的充放電庫侖效率隨循環次數的變化,從圖中可以發現在前5次循環過程中,ZnS@C/rGO電極具有比其他電極更高的庫侖效率,在第5次循環時,ZnS、ZnS@C、ZnS/rGO和ZnS@C/rGO電極的充放電庫侖效率分別是87.6%、84.9%、91.7%和95.1%。在第6次循環后,ZnS@C/rGO電極的充放電庫侖效率基本都在97%左右。圖7b是ZnS和復合材料電極在不同電流密度下的倍率性能。與ZnS@C和ZnS@rGO復合材料電極相比,ZnS@C/rGO電極展現了明顯增強的高倍率特性。在1.0和2.0 A·g-1的充放電電流密度下,ZnS@C/rGO的儲鋰可逆比容量分別為778和593 mAh·g-1。當電流密度再降低至100 mA·g-1時,ZnS@C/rGO復合材料電極的儲鋰可逆比容量也迅速恢復至原有水平,并在隨后的充放電循環過程中顯示出與圖7a中ZnS@C/rGO復合材料電極幾乎相同的循環行為,表明其在不同充放電電流密度下都具有穩定的循環性能。
為進一步討論ZnS@C/rGO復合材料電極的長循環性能,電極循環100次后再在2.0 A·g-1的電流密度下進行了充放電長循環性能測試。如圖7c所示,在2.0 A·g-1的電流密度下,ZnS@C/rGO復合材料電極的儲鋰比容量隨著循環次數的增加開始呈上升的趨勢,在500次循環左右,其儲鋰比容量達到了最大值1 460 mAh·g-1。這種儲鋰比容量的上升趨勢主要是由于在不斷充放電循環過程中,活性物質的顆粒尺寸不斷變小和缺陷增加,提高了電化學儲鋰的容納能力,使復合材料電極在一定循環次數內顯示了一個儲鋰比容量增加的趨勢[30?32]。圖7c表明500次循環后,盡管電化學儲鋰比容量隨著循環次數的增加有緩慢的降低,但ZnS@C/rGO復合材料電極依然保持了相當穩定的循環性能,在1 200次循環后,其電化學儲鋰可逆比容量仍有1 096 mAh·g-1。上述結果表明,通過合理設計的無定形碳包覆及與rGO的復合,所制得的ZnS@C/rGO復合材料與ZnS@C和ZnS/rGO復合材料相比,顯示了更高的儲鋰可逆比容量,以及更好的高倍率特性和長循環穩定性能。

圖7 (a)不同電極在電流密度為100 mA·g-1下的充放電循環性能和(b)在不同電流密度下的充放電倍率性能;(c)ZnS@C/rGO復合材料電極的長循環性能Fig.7 (a)Charge?discharge cyclic performance at a current density of 100 mA·g-1and(b)rate capability at the different current densities of different electrodes;(c)Long?cycle performance of ZnS@C/rGO composite electrode
為更好地理解ZnS@C/rGO復合材料優異的電化學儲鋰性能,測試了ZnS和不同復合材料電極儲鋰的電化學阻抗,并討論了其電極過程動力學。圖8為EIS測試結果和相應的等效電路。其中,Re為測試電池的內阻,Rf和CPE1分別為活性物質顆粒或晶體之間的接觸電阻和界面之間的恒相位元,Rct和CPE2分別代表電極反應的電荷轉移電阻和電極/電解液界面的恒相位元,Zw是鋰離子擴散中的Warburg阻抗。通過對EIS數據擬合可以得到相應的電極過程動力學參數,結果如表2所示。ZnS顆粒包覆無定形碳或復合rGO材料后,其Rf和Rct都有明顯的降低,較小的Rf值歸因于無定形碳或rGO的引入提高了復合材料的導電性,Rct的降低說明碳材料的引入有效降低了電化學鋰化/去鋰化過程中電荷轉移阻抗。在這些復合材料中,ZnS@C/rGO復合材料電極顯示了最小的Rf和Rct值,這主要是由于ZnS@C復合顆粒負載在rGO表面并分散在rGO導電網絡結構中,進一步增強了ZnS@C/rGO復合材料的導電性和降低了其電極反應的Rct,從而顯著改善其電化學儲鋰電極過程的動力學性能。

圖8 ZnS和復合材料電極的EIS譜圖及其等效電路(插圖)Fig.8 EIS spectra of ZnS electrode and composite electrodes and equivalent circuit model(Inset)

表2 ZnS、ZnS@C、ZnS/rGO和ZnS@C/rGO復合材料電極的阻抗擬合值Table 2 Resistance fitting parameters of ZnS,ZnS@C,ZnS/rGO,and ZnS@C/rGO composite electrodes
3 結 論
以葡萄糖為碳源,經過溶劑熱反應和隨后的熱處理制得ZnS@C復合顆粒,然后經水熱處理使ZnS@C與rGO復合,制備得到ZnS@C/rGO復合材料。與ZnS@C和ZnS/rGO復合材料相比,ZnS@C/rGO復合材料具有更高的電化學儲鋰可逆比容量和更好的高倍率充放電特性,以及穩定的長循環性能。在100 mA·g-1電流密度下,ZnS@C/rGO復合材料的首次電化學儲鋰可逆比容量為1 101 mAh·g-1,循環100次后保持了1 569 mAh·g-1的可逆比容量。在不同充放電電流密度下循環1 200次以后,仍保持1 096 mAh·g-1(2.0 A·g-1)的可逆比容量,顯示了穩定的長循環性能。ZnS@C/rGO復合材料的優異儲鋰性能主要是由于ZnS@C/rGO中ZnS納米顆粒與無定形碳及rGO形成的不同層次的復合結構。ZnS納米顆粒高度分散在無定形碳中形成了ZnS@C復合顆粒,然后再負載在rGO表面及導電網絡結構中,最后形成了ZnS@C/rGO復合材料,這種復合結構能很好地緩沖在反復充放電過程中活性物質的體積變化和保持復合電極材料的穩定,確保了在長充放電循環過程中活性物質有良好電接觸,同時rGO導電網絡也明顯降低了電極反應的電荷轉移阻抗。這種電化學儲鋰性能優異的ZnS@C/rGO復合材料在高性能鋰離子電池中具有很好的應用前景。
- 無機化學學報的其它文章
- 雙功能Pd/ZrHP催化劑的制備及其在苯酚選擇性加氫反應中的應用
- 硫/多孔碳納米管復合材料的制備及電化學性能
- R6G@γ-CD-MOFs復合物的制備及其在Fe3+離子傳感中的應用
- Effects of Preformed Pt Nanoparticles on Structure of Platinum Nanowire Cathode for Proton Exchange Membrane Fuel Cells
- Effects of Cr,Sn,Co Doping on Electronic and Optical Properties of Layered Two-Dimensional Material MoSi2N4
- Mixed Metal-Organic Frameworks with Supercapacitor Performance Constructed by Succinic Ac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