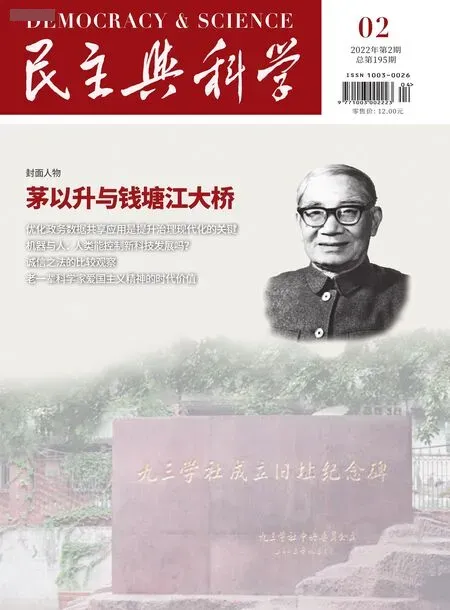老一輩科學家愛國主義精神的時代價值
李婧銖 董貴成
習近平總書記在科學家座談會上的講話明確指出,要大力弘揚老一輩科學家的愛國主義精神。[1]以吳文俊、吳良鏞等35位科學家為代表的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獎者(簡稱“最高獎獲獎者”)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集中而鮮明地體現了我國老一輩科學家的愛國主義精神。他們的愛國主義精神既具有獨特的典型性,又具有廣泛的代表性。作為一種優秀的民族基因,愛國主義精神穿越時空,在當代以及未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過程中,具有重要的示范引領價值。
老一輩科學家愛國主義精神是中華民族精神基因傳承的典范
習近平總書記曾強調:“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愛國主義精神深深植根于中華民族心中,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基因。”[2]老一輩科學家特別是最高獎獲獎者的愛國主義精神正是這種精神基因傳承的典型代表。
我國歷代知識分子都有著濃厚的家國情懷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內圣外王”的士大夫情結和“以身許國”的救世情懷伴隨他們的人生追求,他們自覺地將個人追求和家國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從司馬遷“常思奮不顧身,而殉國家之急”到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從文天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到陸游“位卑未敢忘憂國”;從林則徐“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到魯迅“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無數中國傳統知識分子高貴的人格和崇高的價值追求已內化為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資源,成為支撐中華民族不斷進步的愛國主義精神財富,流淌在中華民族的血脈之中。
最高獎獲獎者作為同時代知識分子的杰出代表,大多出生成長于20世紀二三十年代,他們求學的青少年時期,親歷外敵入侵、顛沛流離帶來的痛苦。2019年最高獎獲獎者、中國核潛艇之父黃旭華,小學畢業時正值抗日戰爭爆發。輟學半年后,與長兄背著書籍行囊,步行跋涉,抵達了因日寇侵略而遷入揭西山區的聿懷中學。由于戰事吃緊,聿懷中學很難保障正常學習,黃旭華不得不踏上了去往桂林的求學之路。1941年夏,黃旭華經興寧、越韶關、奔坪石、掠湘南,經過整整兩個月的曉行夜宿,終于抵達桂林,考入桂林中學。1944年,日寇的鐵蹄逼近桂林,黃旭華在匆匆結束高中學習后,再度開啟了求學之旅。出廣西、越貴州,走走停停、歷經艱險,兩個月后終抵達重慶,但錯過了各大學的招考,只好再過一年后,才進入了國立交通大學造船專業學習。[3]嚴酷的現實和國家民族危亡的憂患意識,使最高獎獲獎者們切身感受到,沒有國,哪有家?“學以致用”“救國圖存”成了那個時期青年學生思想的主旋律。
2011年最高獎獲獎者、中國粒子加速器之父謝家麟,當年在燕京大學就讀,每次從海淀往返城里必經日本兵的崗哨,日本兵荷槍實彈對行人搜身、毆打等行為讓他倍感屈辱。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的第二天,日本軍隊占領燕京大學。在物理系只差半年就要畢業的謝家麟不愿在日本統治下的燕京大學讀書,秉持著“航空救國”的思想選擇了在樂山復校的武漢大學航空系從頭念起。[4]
在戰亂頻仍的時代背景下,從中學到大學都紛紛高舉愛國主義旗幟,肩負起愛國主義教育的使命。學校長期開展傳統愛國思想教育,實行“讀書救國”辦學理念,激勵最高獎獲獎者中的一批青年人,最后成長為傳承和賡續中華民族精神基因中最為核心的愛國主義精神的代表性科學家。
老一輩科學家愛國主義精神是愛國奉獻與人生價值的高度統一
最高獎獲獎者群體歷經了當時國家積弱積貧、外敵入侵、民不聊生的痛苦,深深地明白一個國家獨立富強的可貴,把“富國強民”融入個人的發展中,并當做自己義不容辭的使命。1950年前后,出現了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次海外學人的“歸國潮”,最高獎獲獎者中的一批科學家義無反顧回到祖國。他們不顧危險,沖破種種阻力,拋棄發達國家重金與富裕生活的誘惑,為的就是報效祖國。首屆最高獎獲獎者、中國拓撲學奠基人吳文俊,談到回國的原因時說:“每個人都有愛國之心,我們這些留洋的,盼望著學成回國為祖國做些事。”[5] 1951年回國后,吳文俊一心撲在科研和培養人才事業上,在數學眾多領域作出開創性貢獻,是新中國數學發展的重要開拓者。2013年最高獎獲獎者、中國核試驗科學技術體系的創建者程開甲曾說,在國外繼續待下去,學術上也許會取得更大的成就,但沒有幸福感,只有把自己所學與祖國緊密聯系才是最大的幸福。
在新中國建設中,老一輩科學家自覺自愿把祖國的需要、國家的利益放在首位。最高獎獲獎者群體把國家需要作為強大的科研動力,把他們一生的精力無私奉獻給科技興國事業。在“兩彈一星”研制工作中,2009、2013、2014年最高獎獲獎者孫家棟、程開甲、于敏等一批科學家長年隱姓埋名,甚至在學術界銷聲匿跡;2008年最高獎獲獎者、中國稀土之父徐光憲為了適應祖國的需要,從量子化學、絡合物化學到核燃料萃取方向再到稀土化學等,橫跨多個領域,為了國家需求多次轉變研究方向;2017年最高獎獲獎者王澤山帶著“強軍興國”的使命,選擇火炸藥領域作為主攻方向,常常在戈壁灘現場“風沙拌飯”,用“一甲子”的時間書寫了我國火炸藥實力進入世界前列的傳奇。
老一輩科學家們,有的在戈壁灘上隱姓埋名,有的在漫漫長夜苦心演算或建模,有的在實驗基地熬紅雙眼,他們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凝聚形成了“兩彈一星”精神、“載人航天”精神等愛國主義精神的豐碑,在新中國科技事業發展進程和綜合國力的提升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老一輩科學家以“小我為大我,為大我忘小我”的胸懷和實際作為,深刻詮釋了愛國主義精神,是愛國奉獻和人生價值的高度統一。
老一輩科學家愛國主義精神具有重大的時代意義與作用
第一,弘揚老一輩科學家愛國主義精神,堅持“科技自立自強”發展。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6]實現我國科技自立自強發展,需要持續的自主科技創新,更需要持續的愛國主義精神滋養和武裝我們新一代的科學家隊伍。縱觀新中國的科技事業發展,只有那些有民族氣節、有愛國主義精神、有堅定信念支撐的科學家才能走得正、走得遠,才能攻克一個個科技難關、干成一件件大事、完成一項項事業。新中國成立初期的老一輩科學家,面對國內科研“一窮二白”、國外技術嚴密封鎖的困境,將對祖國的熱愛和忠誠轉化為獨立自主的創新勇氣,轉換為探求新發現新發明的持久動力,立足國情,靠智慧和毅力走出了一條自主創新的科技發展之路。
當前,我國還有許多基礎領域、核心技術和關鍵部件工藝等還落后于世界發達國家,高端芯片、農作物種子等在內的一些“卡脖子”難題依然阻撓和困擾著我們的發展。新一代科技工作者要全面繼承老一輩科學家的愛國主義精神,獨立自主、艱苦奮斗,肯在難度大、周期長的基礎研究及應用領域上下功夫,“坐得住冷板凳、下得了苦功夫”,勇闖科學技術“無人區”,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第二,以老一輩科學家為榜樣標桿,樹立青少年正確的人生價值觀。
當今,在多元價值文化影響下,急功近利的浮躁之風漸漸蔓延到學術界、科技界和其他領域。一些青少年的價值取向出現嚴重偏差,“精致的利己主義”等價值觀影響著他們的成長,長此以往將不利于我國科技事業發展和現代化強國建設。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最深層、最根本、最永恒的是愛國主義。”[7]我國老一輩科學家愛國主義精神具有具象性、生動性、典型性和代表性,以他們的愛國主義精神為范例,在全體公民特別是青少年中,可以有效地塑造我們民族崇高的價值觀。2014年最高獎獲獎者、中國氫彈之父于敏曾說:“青年人選擇職業和專業方向,首先要選擇國家急需的。每個人的前途和命運都與國家的興衰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才會有所作為,才會是一個無愧于祖國和民族的人。”[8]發揚老一輩科學家將“小我”融入“大我”的奉獻精神,以老一輩科學家愛國主義言行為榜樣,將國家長期重大需求、迫切需要與個人專長和志趣相統一,將愛國奉獻、人民利益與個人價值和利益相統一,建樹全民正確的社會主義人生價值觀。
第三,發揮老一輩科學家精神引領作用,進行愛國主義精神教育。
老一輩科學家體現的愛國主義精神是熱愛祖國忠誠國家的感情、思想、信念和行為的綜合。培養受教育者特別是青少年對祖國深厚的感情和為國家繁榮昌盛而努力奮斗的精神,應該是各行各業開展愛國主義精神教育的題中應有之義。近年來,由于金錢至上、享受主義和娛樂主義的流行,再加上一些網絡自媒體的炒作發酵,社會上崇拜影星、歌星、球星和成功商人的風氣遠遠超過了對科學家的敬慕,這種現象在一些青少年中尤其普遍。產生這種現象,除了社會轉型的原因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包括愛國主義精神在內的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和紅色文化,主流媒體宣傳的不到位,在文化教育界的普及性差,而對老一輩科學家愛國主義事跡的宣傳與普及常流于表面,特別是未能對青少年產生持續深遠的影響。老一輩科學家愛國主義精神的言行是那樣的生動鮮活和可歌可泣,這種言行本身就是活典范,充分利用現代科學技術手段特別是網絡多媒體等新穎的宣傳形式,才會更加有效地發揮老一輩科學家愛國主義精神對社會特別是青少年的引領作用和示范作用。
注釋:
[1]習近平:《在科學家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20-09-12(002)。
[2]張啟華主編:《中國共產黨歷史重要會議辭典》,中共黨史出版社;黨建讀物出版社,2019年版,第594頁。
[3]王艷明:《誓言無聲鑄重器 黃旭華傳》,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17年版,第30-47頁。
[4]謝家麟:《沒有終點的旅程 謝家麟自傳》,科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3-14頁。
[5]黃祖賓,吳文俊:《走近吳文俊院士——科學史家訪談錄之四》,《廣西民族學院學報(自然科學版)》,2004年第4期。
[6]《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134頁。
[8]解放軍總裝備部政治部編:《兩彈一星——共和國豐碑》,九州出版社,2001年版,第301頁。
(李婧銖為中國石油大學(北京)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董貴成為中國石油大學(北京)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近代科學社團資料的整理、研究及數據庫建設”〔19ZDA214〕部分成果,本研究受到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教育工委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名師工作室專項資助)
責任編輯:尚國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