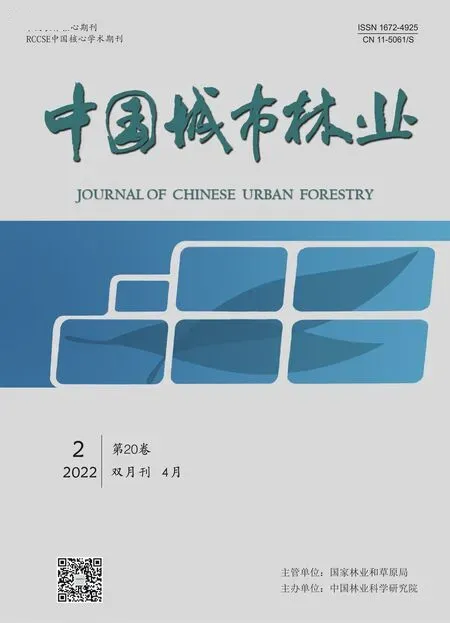森林旅游體驗對中高齡游客生活質量的影響*
周 衛 范少貞 李從治 閆 晨,2 蘭思仁,2
1 福建農林大學園林學院 福州 350002 2 國家林業與草原局森林公園工程技術研究中心 福州 350002
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愈發突出, 重視中高齡群體生活質量的改善關系到社會穩定發展。近年來, 林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持續推進, 森林康養、 森林人家等高質量森林旅游產品極大地提升了公眾的生態福祉[1], 得到了中高齡群體的喜愛與廣泛參與。 相對于人工綠地, 森林公園的植被類型更加復雜, 擁有種類繁多的喬木、 灌木和地被植物等, 形成了完整的空間結構分層。 這種優質的生態環境蘊含植物精氣和負離子等康養因子, 不僅為個體提供了愉悅的五感體驗, 而且能夠調節身體機能, 促進身體健康[1]。 中高齡游客對環境有著更高的要求,更加注重自身的健康與情感需求, 往往更傾向于在森林中開展休閑旅游活動, 這也符合他們提高幸福感、 改善生活質量的精神需要[2]。 因此, 探究森林旅游與中高齡游客生活質量的關系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旅游體驗的過程可分為認知與情感體驗兩部分[3]。 恢復性知覺作為游客認知體驗的重要組成部分, 解釋了環境所具有的使人身心恢復的特性[4]; 場所依戀則體現了人們與特定場所不斷接觸過程中產生的特殊情感與記憶經驗,包括場所依賴和場所認同兩個維度[5]。 游客幸福感集中反映了個體在旅游體驗中具有的積極態度和情感, 其包括心理情感、 自我認知和社會認同3 個方面[6]。 生活質量是個體對生活環境的整體評價與情感反映, 與個體自身生活的目標、 期望以及文化、 價值體系有關[7]。 在休閑旅游領域, 生活質量被定義為游客經旅游體驗后所感受到的滿足感以及對自身生活的美好期望, 相關研究集中于旅游地環境對當地居民生活品質、 游客福祉的影響[8-9]。 已有研究從旅游體驗出發, 驗證了恢復性知覺與場所依戀對游客幸福感的影響機制[10], 然而鮮有學者對中高齡游客生活質量的影響路徑進行探討, 且現有的研究尚無法解釋在森林旅游情境下四者之間的作用機制。 基于此, 本研究以福州國家森林公園為例, 引入幸福感作為中介變量, 通過構建結構方程模型探究森林旅游體驗對中高齡游客生活質量的影響路徑, 為森林公園的建設管理和森林旅游產品的營銷開發提供參考。
1 研究區概況
福州國家森林公園被譽為“福州之肺”, 2000年被評為國家4A 級景區, 2019 年被評為全國森林體驗基地重點建設單位, 是全國十大森林公園之一。 園內植物種類豐富, 景觀類型多樣, 具有獨特的森林小氣候, 能夠產生高濃度的負氧離子。此外, 公園地理環境優越, 園內外交通便捷, 能夠吸引大量中高齡游客進行休閑游憩、 養生保健等森林旅游活動。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假設與模型構建
本研究選取恢復性知覺作為中高齡游客的森林旅游認知體驗內容。 在旅游體驗中, 恢復性知覺(認知) 與場所依戀(情感) 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 二者之間的緊密聯系已在多種旅游情境下得到驗證。 具有恢復性的環境, 往往能引起個體的場所依戀[10]。 研究表明, 中高齡游客的恢復性知覺和場所依戀會對幸福感的提升產生積極影響, 且場所依戀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11]。 對旅游與生活質量關系的研究表明, 旅游活動能夠促進個體創造活力, 從而改善其生活質量[8]。 還有學者認為, 旅游體驗能夠對游客的家庭、 社交和文化等生活領域產生積極影響, 從而提高其整體生活滿意度[9]。 因此, 人們在旅游時獲得積極的認知體驗與情感體驗有助于對生活產生美好愿景,提高對整體生活的評價[12]。 此外, 人們經旅游體驗后, 心理上的幸福感和愉悅感也會對生活質量產生積極影響, 因而幸福感是游客生活品質的重要心理指標[13]。 綜上所述, 本研究假設中高齡游客參與森林旅游中:
H1: 恢復性知覺顯著正向影響場所依戀
H2: 恢復性知覺顯著正向影響幸福感
H3: 恢復性知覺顯著正向影響生活質量
H4: 場所依戀顯著正向影響幸福感
H5: 場所依戀顯著正向影響生活質量
H6: 幸福感顯著正向影響生活質量
結合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設, 構建中高齡游客生活質量的影響機制模型(圖1)。

圖1 中高齡游客生活質量的影響機制模型
2.2 問卷設計
經過預調研與多次修訂后, 本研究采用自填式問卷進行調查。 問卷包括兩部分內容: 第1 部分為中高齡游客人口統計特征及森林旅游參與特征, 采用選擇題方式調查; 第2 部分為量表測量題項, 采用李克特7 級量表法測量。 量表測量題包括Kang 等[14]修訂的精簡版恢復性知覺量表(設置6 個題項)、 場所依戀量表(設置6 個題項[5])、 幸福感量表(設置4 個題項[15]) 生活質量量表(設置4 個題項[16])。
2.3 數據收集與分析
依據便利抽樣方法選擇公園內50 歲以上的中高齡游客為調查對象, 于2020 年9 月9 日—9 月16 日進行調研。 考慮到部分中高齡游客存在閱讀障礙且問卷題項具有專業性, 必要時由調研組成員逐一念出問卷題項, 協助受訪者更好地填答問卷。 為滿足樣本量應是全部測量題項10 倍的要求, 共發放問卷350 份, 最終回收有效問卷310份, 有效率為88.57%。 對量表數據進行正態性檢驗, 使用SPSS 23.0 和AMOS 23.0 軟件進行數據處理與研究假設的驗證分析。
3 結果與分析
3.1 問卷調查結果與信效度分析
3.1.1 問卷調查結果
本次調查的中高齡游客中,女性占61.3%;年齡在50 ~60 歲、60 ~70 歲和71 歲以上者分別占51.3%、40.6%和8.1%;文化程度大多在初中及以下(47.4%);月收入大多在3000 元以下(67.1%)。 綜上,樣本男女比例較均衡,文化程度、經濟收入總體結構合理,具有良好的代表性。 在森林旅游參與特征方面,訪問頻率多為每周1~3 次(36.5%),停留時間多為2 ~3 h(34.8%);出游同伴多為家人、親戚(40.3%)或朋友(44.5%);出游目的以健康養生(37.7%)和休閑放松(31.9%)為主。 可見,森林環境的健康效益是中高齡群體選擇森林公園作為出游目的地的重要動力。
3.1.2 問卷信效度分析
由表1 可知, 恢復性知覺、 場所依戀、 幸福感和生活質量的Cronbach's α 系數均滿足大于0.7, 表明各量表具有較高的內部一致性。 此外,各觀測指標的標準化因素負荷量(STD) 均滿足高于0.5 的基本要求, 且通過t值>1.960 的顯著性檢驗。 各量表的平均變異抽取量(AVE) 均大于0.6, 組合信度(CR) 均大于0.7。 綜合以上分析可得, 各量表數據具有良好的收斂效度, 滿足基本的評價要求[17]。

表1 問卷信度、 效度及驗證性因子分析結果
3.2 模型適配度檢驗
在量表數據符合正態分布的基礎上, 采用極大似然法(ML) 對測量和結構模型進行參數估計。 模型的適配度可以通過絕對適配度指標和增值適配度指標進行衡量。 恢復性知覺、 場所依戀、幸福感和生活質量4 個一階測量模型的適配度檢驗結果均達到相應要求, 整體結構模型的適配度指 數 為χ2/df=1.581,RMSEA=0.043,GFI=0.921,AGFI=0.900,IFI=0.980,NFI=0.948,CFI=0.980,TLI=0.977, 符合模型適配要求[17],可進一步對研究假設進行驗證。
3.3 路徑分析與假設檢驗
采用結構方程模型對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設進行檢驗, 結果(表2) 表明, 部分影響路徑的標準化系數不顯著, 并且存在路徑系數為負數的現象。 具體而言, 研究假設H1、 H2、 H4 和H6 的標準化路徑系數分別為0.769、 0.517、 0.437 和0.795, 均通過t>1.960,P<0.05 的顯著性檢驗, 即假設H1、H2、 H4 和H6 成立。 研究假設H3、 H5 的標準化路徑系數分別為0.096 (t=0.845,P=0.389) 和-0.115 (t=-1.488,P=0.137), 均未通過顯著性檢驗, 即假設H3、 H5 不成立。

表2 結構模型的參數估計結果
假設檢驗結果表明: 中高齡游客參與森林旅游的認知體驗(恢復性知覺) 對情感體驗(場所依戀) 具有顯著的正影響; 恢復性知覺可以直接對幸福感產生影響, 又可以通過場所依戀對幸福感產生間接影響; 恢復性知覺和場所依戀對生活質量并無顯著直接影響。 這一研究結果揭示了中高齡游客的森林旅游體驗與生活質量之間并不是簡單的因果關系, 而是存在中介變量的復雜路徑。
3.4 中介效應檢驗
在剔除未通過顯著性檢驗的假設路徑后, 進一步用Bootstrap 檢驗幸福感在森林旅游體驗和生活質量之間的中介作用。 在進行2 000 次抽樣檢定后, 通過定義估計(Defined Estimands) 的方式分別計算中介路徑的標準化估計值(表3)。 以幸福感為中介變量的各影響路徑的偏差校正95%置信區間均未包含0, 且通過顯著性檢驗, 表明幸福感的中介作用顯著存在。

表3 幸福感的中介效應檢驗
幸福感的中介效應檢驗結果表明, 中高齡游客的幸福感在森林旅游體驗對生活質量的影響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進一步驗證了幸福感是個體生活質量的重要心理指標。 因此, 森林旅游體驗對中高齡游客生活質量的改善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幸福感起到了關鍵的橋梁作用。 究其原因, 幸福感是個體對生活的整體性評價, 往往表現為個體所享有的美好生活過程, 中高齡游客通過旅游體驗所獲得的幸福感將會被其視為生活的組成部分, 從而提高其對整體生活的評價。
4 討論與結論
4.1 討論
中高齡游客在進行森林旅游時, 積極的認知與情感體驗能夠提高幸福感, 從而改善其生活質量, 這與Moon 的研究一致[13]。 與以往研究結果不同的是[12], 本研究發現中高齡游客的恢復性知覺與場所依戀無法顯著直接影響其生活質量: 一方面, 中高齡游客的到訪頻率與停留時間普遍較高, 具有較高的環境認知, 對環境已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情感聯系; 另一方面, 中高齡游客感官感知系統的敏感性下降, 削弱了其在公園中的旅游體驗, 因此難以直接對生活質量產生影響。
此外, 基于本研究結果, 森林公園管理者應著重提升中高齡游客的認知與情感體驗, 以擺脫中高齡旅游市場產品過于商業化、 同質化怪圈。在強化各項基礎性服務上, 明確森林旅游產品的情感定位與所蘊含的價值意義, 積極開展針對老年團體的森林養生游, 提供不同類型、 深度的森林旅游產品, 如森林浴、 森林太極和森林冥想等高品質的養生保健活動。 這不僅能滿足中高齡游客對健康養生的需求, 還能促進中高齡游客間的情感聯系, 從而更好地改善生活質量。
4.2 結論
本文從中高齡游客參與森林旅游的認知體驗(恢復性知覺) 和情感體驗(場所依戀) 出發,引入幸福感作為中介變量, 初步揭示了森林旅游體驗對中高齡游客生活質量的影響路徑。 中高齡游客的恢復性知覺直接或通過場所依戀間接顯著正向影響幸福感, 且幸福感顯著正向影響生活質量; 中高齡游客的森林旅游體驗雖然對生活質量沒有直接顯著的影響, 但是可以通過幸福感的完全中介作用產生間接影響, 主要的影響路徑有“恢復性知覺→幸福感→生活質量” “場所依戀→幸福感→生活質量” “恢復性知覺→場所依戀→幸福感→生活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