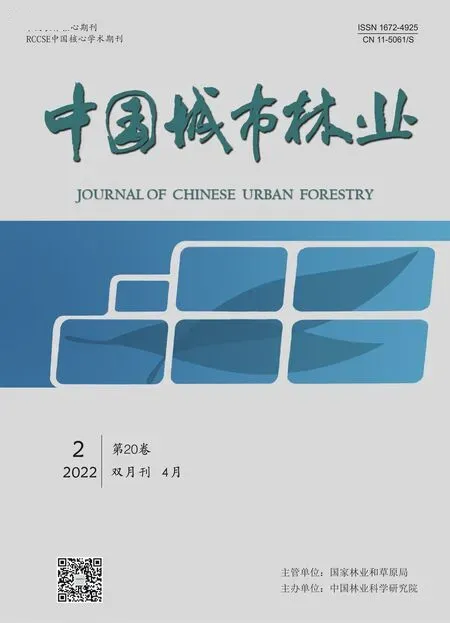山地城市綜合公園邊界物質(zhì)形態(tài)量化方法
馮 晴 劉 駿,2 黃雪飄
1 重慶大學(xué)建筑城規(guī)學(xué)院 重慶 400045 2 教育部山地城鎮(zhèn)建設(shè)與新技術(shù)重點(diǎn)實(shí)驗(yàn)室 重慶 400045
我國(guó)城市公園大多建設(shè)于20 世紀(jì), 受中國(guó)傳統(tǒng)封閉式造園及蘇聯(lián)園林模式影響, 其邊界多為傳統(tǒng)封閉式, 以圍墻等形式與城市空間相隔[1]。21 世紀(jì)以后, 隨著我國(guó)城市建設(shè)理念的發(fā)展, 城市公園在“還綠于民” 思想的指導(dǎo)下從封閉走向開(kāi)放[2], 逐漸與城市空間相融合, 公園邊界成為二者重要的過(guò)渡空間。 受地形等條件限制, 山地城市綜合公園多位于山頭、 陡坡、 深谷等不宜大規(guī)模開(kāi)發(fā)建設(shè)的破碎隙地[3], 其邊界景觀呈現(xiàn)出曲折、 高差多變、 毗鄰梯道等區(qū)別于平原城市的復(fù)雜物質(zhì)形態(tài)特征[4], 對(duì)邊界的認(rèn)知提出更高要求。
邊界是相鄰異質(zhì)空間受到邊界效應(yīng)、 邊緣效應(yīng)作用的邊緣過(guò)渡區(qū)域[5]。 形態(tài) (Morphology)一詞源自希臘語(yǔ)中的Morpheme (形) 和Logos(邏輯), 即形式的構(gòu)成邏輯[6]。 從景觀的角度理解, 形態(tài)是設(shè)計(jì)綜合基地自然條件、 功能布置和場(chǎng)地文化的直觀表達(dá)[7]。 山地城市綜合公園的邊界物質(zhì)形態(tài)涵蓋實(shí)體空間形態(tài)和空間組織兩方面本質(zhì)屬性, 相關(guān)研究多集中于基本特性、 分類(lèi)設(shè)計(jì)手法等空間組織狀態(tài), 鮮有對(duì)實(shí)體空間形態(tài)的科學(xué)量化研究, 不利于解決公園與周邊城市用地融合度低、 空間層次單調(diào)、 景觀形象欠佳、 公園邊界可達(dá)性低、 使用功能欠缺等問(wèn)題。 因此, 應(yīng)用科學(xué)、 系統(tǒng)的方法, 邏輯化、 定量化、 實(shí)證化地理性解讀山地城市綜合公園邊界物質(zhì)形態(tài), 理解其本質(zhì)屬性、 梳理其內(nèi)在邏輯, 有利于為設(shè)計(jì)實(shí)操提供更高效的指導(dǎo)。
現(xiàn)有形態(tài)量化方法研究涵蓋聚落[8-11]、 建筑[12-13]、 綠地[14-17]等多個(gè)領(lǐng)域, 常用的有長(zhǎng)寬比、 面積周長(zhǎng)比、 邊界形狀指數(shù)、 地表粗糙度、地勢(shì)起伏度等, 有效擴(kuò)展了山地城市綜合公園邊界物質(zhì)形態(tài)研究的方法與視野。 本文借鑒已有量化研究, 構(gòu)建山地城市綜合公園邊界物質(zhì)形態(tài)量化方法, 并通過(guò)重慶市中心城區(qū)的32 個(gè)公園樣本, 以因子分析、 聚類(lèi)分析的方法進(jìn)行實(shí)證研究,為山地城市綜合公園邊界物質(zhì)形態(tài)研究提供一個(gè)全新的視角, 也為山地城市綜合公園邊界景觀設(shè)計(jì)提供科學(xué)的依據(jù)。
1 研究區(qū)概況
重慶依山而建, 是典型的山地城市, 以山地地形為基底的綜合公園在中心城區(qū)廣泛分布[18],因此選重慶市中心城區(qū)為研究區(qū)域。 為保證研究結(jié)果的普適性, 經(jīng)資料搜集和實(shí)地調(diào)研對(duì)比, 對(duì)重慶市中心城區(qū)規(guī)劃的111 個(gè)綜合公園中已建的47 個(gè)公園(數(shù)據(jù)源自《重慶市主城區(qū)綠地系統(tǒng)規(guī)劃2014-2020》; 2020 年5 月重慶主城都市區(qū)工作座談會(huì)上, 主城區(qū)由9 區(qū)擴(kuò)容到含“中心城區(qū)”“主城新區(qū)” 在內(nèi)的21 區(qū), 文中的原“主城區(qū)”即現(xiàn)“中心城區(qū)” ), 按照覆蓋不同建造年代、行政區(qū)劃、 大小規(guī)模的原則進(jìn)行篩選, 最終取32個(gè)公園作為研究樣本(表1) 進(jìn)行實(shí)地調(diào)研。

表1 (續(xù))

表1 樣本公園名錄
本研究的山地城市綜合公園邊界物質(zhì)形態(tài)是指在山地城市綜合公園中, 邊界實(shí)體空間形態(tài)和空間組織所構(gòu)成的邊界物質(zhì)空間狀態(tài), 其中, 邊界實(shí)體空間形態(tài)包括公園規(guī)模、 邊界形狀復(fù)雜度等平面形態(tài), 以及公園內(nèi)外高程變化等豎向形態(tài);空間組織則表現(xiàn)為植物、 水體、 入口鋪裝、 建筑、擋土墻、 圍墻、 柵欄等多種景觀實(shí)體要素的組合搭配及其功能表達(dá)。
2 研究方法
2.1 山地城市綜合公園邊界物質(zhì)形態(tài)量化指標(biāo)體系構(gòu)建
基于對(duì)現(xiàn)有研究的梳理及對(duì)山地城市綜合公園邊界物質(zhì)形態(tài)本質(zhì)屬性的綜合考量, 本文建立了包含水平面、 垂直面、 表征描述指標(biāo)3 個(gè)維度8項(xiàng)具體因素的邊界物質(zhì)形態(tài)量化指標(biāo)體系(圖1)。

圖1 山地城市綜合公園邊界物質(zhì)形態(tài)量化指標(biāo)體系
2.1.1 水平面描述指標(biāo)
利用公園面積、 周長(zhǎng)及邊界形狀復(fù)雜度3 項(xiàng)指標(biāo)描述水平面維度的形態(tài)特征。 邊界形狀復(fù)雜度以景觀生態(tài)學(xué)中形狀指數(shù)的計(jì)算方式為參考,將樣本公園周長(zhǎng)與等面積圓形周長(zhǎng)比較得出, 反映公園邊界與等面積圓形在平面形狀上的偏離程度[19], 計(jì)算公式如式(1):

式(1) 中:S為邊界形狀復(fù)雜度;P為樣本公園周長(zhǎng)(m);A為公園面積(m2)。
2.1.2 垂直面描述指標(biāo)
高程、 坡度、 坡向等常用指標(biāo)適于局部地形的微觀刻畫(huà), 無(wú)法反映山地公園邊界與內(nèi)部核心空間的起伏關(guān)系等非均勻變化的整體地形特點(diǎn)。本文選用邊界坡向變化系數(shù)、 地勢(shì)起伏度兩項(xiàng)指標(biāo)以宏觀描述邊界在垂直面維度上的形態(tài)特征。
邊界坡向變化系數(shù)以公園內(nèi)部核心空間相對(duì)公園邊界地勢(shì)抬高、 下沉和平接3 種情況[20]的邊界長(zhǎng)度占比加權(quán)結(jié)果表達(dá)(圖2), 權(quán)重分配為抬高地形+1, 下沉地形-1, 內(nèi)外平接0。 邊界坡向變化系數(shù)的計(jì)算公式如式(2):

圖2 邊界坡向變化情況示意

式(2) 中:T為邊界坡向變化系數(shù);N1、N2分別表示抬高、 下沉地形對(duì)應(yīng)邊界長(zhǎng)度占公園周長(zhǎng)的比例。T的正負(fù)表示公園內(nèi)部核心空間與邊界的總體坡向關(guān)系, 數(shù)值大小反映邊界整體的坡度偏差程度; 一般來(lái)說(shuō), 按坡向變化系數(shù)的正負(fù)值可將邊界分為上坡型、 下坡型和平地型3 種類(lèi)型。
地勢(shì)起伏度是地貌學(xué)領(lǐng)域中用以定量描述地貌形態(tài)的指標(biāo)[5]。 本文中, 地勢(shì)起伏度是指公園紅線(xiàn)范圍內(nèi)最高、 最低高程之差, 公式如式(3):

式 (3) 中:R為公園地勢(shì)起伏度;Hmax、Hmin為公園的最高、 最低高程(m)。
2.1.3 表征描述指標(biāo)
本文以邊界行為利用度、 邊界視線(xiàn)開(kāi)敞度和邊界形式豐富度描述山地城市綜合公園邊界的物質(zhì)形態(tài)表征。 邊界行為利用度從水平面維度上表達(dá)對(duì)行為開(kāi)放程度有影響的邊界占比, 包括可進(jìn)入公園的邊界以及不可進(jìn)入但具有停留、 休憩等使用條件的可利用邊界。 其計(jì)算方式為上述兩類(lèi)邊界的平面總長(zhǎng)度與樣本公園周長(zhǎng)的比值, 如式(4) 所示:

式(4) 中:U為邊界行為利用度;e為可進(jìn)入邊界平面總長(zhǎng)(m),S為可利用邊界的平面總長(zhǎng)(m)。
邊界視線(xiàn)開(kāi)敞度描述垂直面維度上對(duì)于公園視線(xiàn)可識(shí)別性有影響的邊界占比。 其計(jì)算方式為視線(xiàn)通透、 視線(xiàn)半阻隔、 視線(xiàn)阻隔3 類(lèi)邊界長(zhǎng)度與樣本公園周長(zhǎng)比值的加權(quán)平均值, 三者的權(quán)重系數(shù)分別為1、 0.5、 0。 視線(xiàn)通透如鋪裝界面及草坪等自然界面, 視線(xiàn)半阻隔如柵欄、 擋土墻與綠化相搭配的人工界面及綠化等自然界面, 視線(xiàn)阻隔如圍墻、 擋土墻、 建筑等人工界面。 計(jì)算公式如式(5):

式(5)中:V為邊界視線(xiàn)開(kāi)敞度,v1為視線(xiàn)通透的邊界總長(zhǎng)(m),v2為視線(xiàn)半阻隔的邊界總長(zhǎng)(m)。
實(shí)地調(diào)研統(tǒng)計(jì)發(fā)現(xiàn), 山地城市綜合公園邊界的主要構(gòu)成形式包含植物、 水體、 入口鋪裝、 建筑、 擋土墻、 圍墻、 柵欄7 項(xiàng), 據(jù)此, 邊界形式豐富度的計(jì)算公式如式(6):

式(6) 中:F為邊界形式豐富度;n為樣本公園中邊界形式的種類(lèi)數(shù)量。
2.2 數(shù)據(jù)分析
本文結(jié)合Google Earth 數(shù)據(jù)源與實(shí)地測(cè)繪比對(duì)所得的平面及高程數(shù)據(jù), 將山地城市綜合公園邊界物質(zhì)形態(tài)量化指標(biāo)體系中的各項(xiàng)指標(biāo)以上述計(jì)算方法進(jìn)行量化, 形成各樣本公園形態(tài)指標(biāo)數(shù)據(jù), 并以SPSS (25.0) 統(tǒng)計(jì)軟件為數(shù)據(jù)處理工具進(jìn)行樣本合理性檢驗(yàn)、 因子分析、 聚類(lèi)分析。 根據(jù)因子分析提取指標(biāo)中影響程度較大的主要因子,而聚類(lèi)分析依據(jù)指標(biāo)數(shù)據(jù)將樣本公園進(jìn)行分類(lèi)。
3 結(jié)果與分析
3.1 樣本合理性檢驗(yàn)
提取各指標(biāo)的最小、 最大、 均值對(duì)樣本選擇的合理性進(jìn)行驗(yàn)證, 結(jié)果發(fā)現(xiàn)公園周長(zhǎng)、 公園面積及地勢(shì)起伏度3 項(xiàng)指標(biāo)的標(biāo)準(zhǔn)偏差最大(表2), 表明32 個(gè)樣本公園大小規(guī)模各異, 可較完善地表征山地城市綜合公園普遍情況。

表2 樣本公園邊界物質(zhì)形態(tài)量化指標(biāo)數(shù)據(jù)
3.2 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時(shí), 巴特利特球形度檢驗(yàn)顯著性值明顯小于1%, 與8 項(xiàng)指標(biāo)間的相關(guān)系數(shù)矩陣(表3) 共同證實(shí)了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進(jìn)行因子分析的可行性, 并得出矩陣特征值與方差貢獻(xiàn)率(表4)。 軟件提取了特征根大于1 的前3 個(gè)因子為主要成分,累積方差貢獻(xiàn)率為76.034% (表4), 可較好地描述山地城市綜合公園邊界的形態(tài)特征。 采用最大方差法進(jìn)行因子旋轉(zhuǎn)后(表5) 發(fā)現(xiàn), 第1 主成分在公園周長(zhǎng)、 地勢(shì)起伏度、 公園面積、 邊界形狀復(fù)雜度上有較大荷載, 均可體現(xiàn)山地城市綜合公園邊界的三維空間形態(tài)信息, 故命名為“三維形態(tài)因子”, 方差貢獻(xiàn)率為32.897%; 第2 主成分在邊界行為利用度、 邊界視線(xiàn)開(kāi)敞度上有較大荷載, 主要反映邊界行為、 視線(xiàn)兩方面的可達(dá)性,命名為“可達(dá)性因子”, 方差貢獻(xiàn)率為21.974%;第3 主成分在邊界坡向變化系數(shù)、 邊界形式豐富度上有較大荷載, 可反映山地城市綜合公園邊界與公園內(nèi)部核心空間的坡向過(guò)渡變化關(guān)系、 邊界的構(gòu)成形式搭配組合, 均表征邊界在空間和形式上的構(gòu)成狀態(tài), 命名為“邊界構(gòu)成因子”, 方差貢獻(xiàn)率為21.164%。

表3 指標(biāo)相關(guān)系數(shù)矩陣

表4 因子分析的矩陣特征值與方差貢獻(xiàn)率

表5 主因子荷載矩陣
3.3 聚類(lèi)分析
根據(jù)因子分析得到的3 大主要因子對(duì)32 個(gè)公園樣本數(shù)據(jù)進(jìn)行系統(tǒng)聚類(lèi)分析(圖3)。 截取表示類(lèi)別間親疏距離的0 ~25 標(biāo)尺刻度發(fā)現(xiàn), 將公園樣本分為4 類(lèi)時(shí), 各類(lèi)別所含的樣本數(shù)量較為平均, 分類(lèi)方式較為理想。 對(duì)4 類(lèi)公園樣本的邊界物質(zhì)形態(tài)特征(表6) 及建成年代(圖4) 做進(jìn)一步比較, 以分析其分布特征。

圖3 聚類(lèi)譜系圖

圖4 各類(lèi)公園樣本的建成時(shí)間分布

表6 各類(lèi)公園的邊界物質(zhì)形態(tài)特征
4 種公園類(lèi)型分別以沙坪公園、 鵝嶺公園、虎頭巖森林公園、 中央公園為代表。 從圖4、 表6可以看出: 類(lèi)型Ⅰ中建成時(shí)間早于2000 年的公園在4 類(lèi)中占比最大, 類(lèi)型Ⅳ全部建成于2000 年以后。 類(lèi)型Ⅰ規(guī)模適中, 邊界形狀復(fù)雜度、 邊界坡向變化系數(shù)、 地勢(shì)起伏度、 邊界形式豐富度指標(biāo)均處于4 類(lèi)公園中的較低水平, 因而也具有較高的邊界行為利用度。 類(lèi)型Ⅳ規(guī)模最大, 地勢(shì)起伏最明顯, 具有較高邊界形狀復(fù)雜度; 坡向變化系數(shù)均值為0.01, 地形的上升、 下沉走勢(shì)所占比例基本持平; 受最高地勢(shì)起伏度的影響, 此類(lèi)公園在視線(xiàn)可達(dá)性方面表現(xiàn)較佳, 但行為可達(dá)性較低。
總之, 各類(lèi)公園在公園面積、 公園周長(zhǎng)、 邊界形狀復(fù)雜度、 地勢(shì)起伏度上均有顯著差異, 而在邊界視線(xiàn)開(kāi)敞度、 邊界形式豐富度上差異細(xì)微。這也反映出當(dāng)前重慶市中心城區(qū)綜合公園邊界建設(shè)的薄弱, 無(wú)論規(guī)模與地形狀況, 公園邊界景觀設(shè)計(jì)均存在構(gòu)成形式組合簡(jiǎn)單均質(zhì)、 視線(xiàn)開(kāi)敞度不足等問(wèn)題。 但相對(duì)而言, 建成時(shí)間越晚的公園在邊界行為利用度、 邊界視線(xiàn)開(kāi)敞度、 邊界形式豐富度等方面表現(xiàn)愈佳。 如類(lèi)型Ⅰ中建于1930 年的北碚公園, 除3 處入口之外, 其余邊界中83%為擋土墻與圍墻、 欄桿結(jié)合的形式; 而類(lèi)型Ⅳ中建于2013 年的中央公園, 其76.3%的邊界為視野通暢的疏林草地, 設(shè)置較多入口和外圍人行空間,保證邊界視線(xiàn)、 行為雙方面的高度可達(dá)性。
4 結(jié)論與建議
4.1 結(jié)論
基于水平面、 垂直面、 表征3 方面的形態(tài)描述指標(biāo), 引入公園面積、 公園周長(zhǎng)、 邊界形狀復(fù)雜度、 邊界坡向變化系數(shù)、 公園地勢(shì)起伏度、 邊界行為利用度、 邊界視線(xiàn)開(kāi)敞度、 邊界形式豐富度8 項(xiàng)量化指標(biāo)建構(gòu)指標(biāo)體系, 并運(yùn)用因子分析將指標(biāo)提取為三維形態(tài)因子、 可達(dá)性因子、 邊界構(gòu)成因子, 初步探索出一種科學(xué)化、 系統(tǒng)化的山地城市綜合公園邊界物質(zhì)形態(tài)量化方法, 其中,三維形態(tài)因子帶來(lái)的影響程度最大。
結(jié)合32 個(gè)公園樣本的實(shí)證研究, 利用聚類(lèi)分析法, 依據(jù)邊界物質(zhì)形態(tài)將樣本公園劃分為4 類(lèi)。4 類(lèi)公園在三維形態(tài)因子方面的分異最大, 再次驗(yàn)證其對(duì)于山地城市綜合公園邊界物質(zhì)形態(tài)本質(zhì)屬性的重要表征作用。
比對(duì)聚類(lèi)分析結(jié)果與實(shí)地調(diào)研情況發(fā)現(xiàn): 水平面維度上, 山地城市綜合公園邊界的形狀復(fù)雜度高, 平面形態(tài)復(fù)雜多樣。 垂直面維度上, 高差變化豐富, 多上、 下坡型而少平地型邊界。 表征維度上, 建成年代與之具有一定相關(guān)性, 2000 年以前的公園邊界以擋土墻、 圍墻等阻隔性墻體為主, 缺少入口及停留休憩空間, 邊界行為、 視線(xiàn)可達(dá)性均低; 2000 年以后, 受政策及城市建設(shè)影響, 公園邊界多設(shè)置人行空間及可停留空間, 受地勢(shì)起伏度限制時(shí)也設(shè)置視覺(jué)焦點(diǎn)以創(chuàng)造較高視線(xiàn)可達(dá)性, 欄桿等設(shè)置也以考慮安全性為主而非單純的隔離。
4.2 建議
本文的研究方法仍有不足, 如邊界物質(zhì)形態(tài)是樣本公園分類(lèi)的依據(jù)而非分類(lèi)的直接對(duì)象。 但量化指標(biāo)的引入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對(duì)山地城市綜合公園邊界本質(zhì)屬性的認(rèn)知程度, 使以往對(duì)邊界的感性認(rèn)知有了量化數(shù)據(jù)的理性支撐。 今后的研究可深入拓展這一思路, 基于更細(xì)化的物質(zhì)形態(tài)指標(biāo)體系及更大的樣本容量對(duì)邊界物質(zhì)形態(tài)進(jìn)行識(shí)別與細(xì)分, 實(shí)現(xiàn)對(duì)山地城市綜合公園邊界景觀設(shè)計(jì)的直接指導(dǎo)。
1) 規(guī)劃階段: 與周邊城市的融合及功能互補(bǔ)。 公園選址受地形、 用地范圍等條件限制時(shí),一方面應(yīng)增加邊界形狀復(fù)雜度, 通過(guò)凹凸有致的平面形態(tài)與周邊多樣用地類(lèi)型互動(dòng)融合; 另一方面也應(yīng)依據(jù)周邊用地類(lèi)型, 結(jié)合內(nèi)外功能設(shè)計(jì)公園邊界, 實(shí)現(xiàn)公園內(nèi)外的功能互補(bǔ)。
2) 設(shè)計(jì)階段: 可達(dá)性、 功能性的補(bǔ)足和增強(qiáng)。 可達(dá)性方面, 有條件的區(qū)域可結(jié)合公園內(nèi)外功能設(shè)置坡道、 臺(tái)階、 連廊等多層次的入口空間,創(chuàng)造行為可達(dá)性的同時(shí)塑造獨(dú)特空間體驗(yàn), 并充分利用地勢(shì)起伏度高的優(yōu)勢(shì)強(qiáng)化豎向景觀, 創(chuàng)造視線(xiàn)可達(dá)性以補(bǔ)足行為可達(dá)性低的困境。 功能性方面, 應(yīng)結(jié)合地形營(yíng)造游憩空間, 提高邊界行為利用度及邊界形式豐富度, 由單一的隔離功能轉(zhuǎn)向安全性、 通行性、 可達(dá)性、 互動(dòng)性等復(fù)合的使用功能, 塑造出可游可賞、 舒適宜人、 具有豐富景觀層次的柔性邊界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