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女友”
■上海市世界外國語中學/劉蕓嘉
那是一個不同尋常的夏天,我第一次遇見了我的“女友”。
那時候她還不是我的“女友”,只是一個膽小、敏感、脆弱的女孩兒。
一個普通的傍晚,我去吃晚飯。她也許路過,也許蓄謀已久,就這樣靜靜地、悄悄地站在飯店的玻璃窗前,渴望地望著我碗里的烤魚,一下一下舔著嘴唇,仿佛這樣就能和我的味蕾相通。透明的玻璃隔在我們中間,我們的狀態卻是天壤之別。她很瘦弱,亂糟糟的金棕色毛發在陽光下好看地跳著舞,單薄的身軀仿佛敵不過微風,但是臟臟的臉龐抵擋不住靈動的模樣,尤其是一雙大眼睛水汪汪地盯著我。
一個姣好的美人胚子。
我承認,從一開始我就淪陷了。可她最終還是引來了保安的驅逐。面對保安破舊的皮鞋,她沒有反抗,只是熟練地穿過草叢向遠處逃竄,待在安全距離之外不動聲色地朝這邊張望著,停住不動。
我心軟了,制止了保安,又要來一個小碗,輕輕地夾進幾片魚肉,試圖接近她。她很害怕,驚恐地看了我一眼便朝更遠處跑去。我放下碗,離得遠遠的,溫柔地注視著她。她邁著試探的步伐,一步,兩步,她終于來到碗邊,狼吞虎咽起來。我還記得,那天的晚霞很美,很美。
后來,我常常去那個飯店,就是為了能再次碰到她。每次我都分給她一點魚肉,每次她都等我離開再吃。就這樣,過了很多很多天,我們之間終于建立起信任,她會對我表示感謝,會允許我替她梳理凌亂的毛發。她會準時在飯店門口等我,如果我來晚了,她還會輕聲埋怨。我們像情侶一樣,每個星期總有幾天在那個飯店“約會”,她會撒嬌,會躺在我的懷里蹭我,我們會期待著與對方相遇。只是,她從來不進飯店。
我們甜蜜地過了一整個夏天,天氣開始轉涼了。
有一天,我和她道別離開,在回家的路上,我正看著金色的秋風撞開一街的梧桐葉,粉色的云朵軟綿綿地在天上散步,卻突然聽到身后的草叢里傳來窸窸窣窣的聲音。我轉過身,小心翼翼地走過去,原來她一路跟著我到了小區。她有些不知所措,低下頭又充滿期待地用余光瞄著我。“怎么了?你沒有地方去嗎?跟我回家好不好?”或許是因為迫不及待,我幾乎下意識地說出了這句話,而她也愉悅地抬起了頭。命中注定般,在那個灑滿陽光的午后,我和她一大一小兩個影子慢悠悠地晃著,她就這樣闖進了我的生活。
她也許是被拋棄了,沒有什么生活的本領。我幫她洗澡,給她買好吃的東西,每天陪她散步、和她聊天,讓她住在我的臥室,允許她喝我水杯里的水。她早上會叫我起床,晚上會依偎在我的懷里。她就像天使一樣,總能讓我開心。我們平淡而幸福,普通而快樂。當然,她有時很調皮,三天兩頭就會砸碎東西,毛掉得滿地都是,但是只要她用軟綿綿的聲音道一聲歉,我所有的煩惱都會一掃而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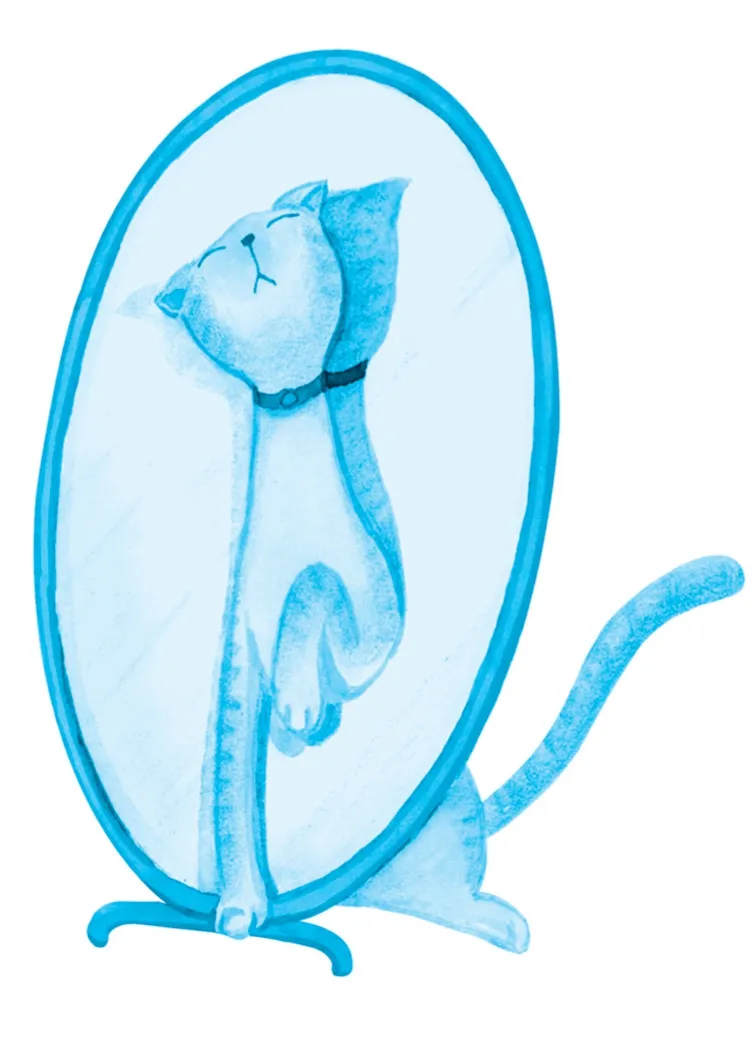
有一天,她沒有叫我起床,而是病懨懨地躺在床上,不吃飯也不喝水,一動不動。我不知道她怎么了,趕忙送她去醫院,竟得知她得了一種存活率不到30%的傳染病,大概率是流浪時感染的,現在剛過潛伏期。我急哭了,自責、愧疚、震驚、害怕,我離不開她。
她在醫院被隔離起來,在那個小小的房間里,冰冷的白色環繞著她,到處都是陌生的人和陌生的器械。她惶恐地望著我,可我卻不知道怎么解釋這一切,只能不停地安慰她:“沒事的,別怕。”我不知道會發生什么,我迫切地想要保護她,但又覺得如此無力。她鮮活的生命一點一點地流逝,聲音變得沙啞,每天只是麻木地吞下一粒又一粒藥丸,仿佛魂魄已經被吸走了。我幾乎天天去看她,白色本該是屬于天使的顏色,可是對她來說,蒼白的顏色里全是灰暗。
她在醫院住了兩個星期,所幸,她作為天使的工作還沒完成,老天沒有要收她的意思。雖然還有一點后遺癥,但她終于好起來了。經歷苦難之后的我們更加珍惜彼此了。
她依舊是那個膽小、敏感、脆弱的女孩兒,但是現在,她不會再受傷了。
我的“女友”,一只像天使一樣的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