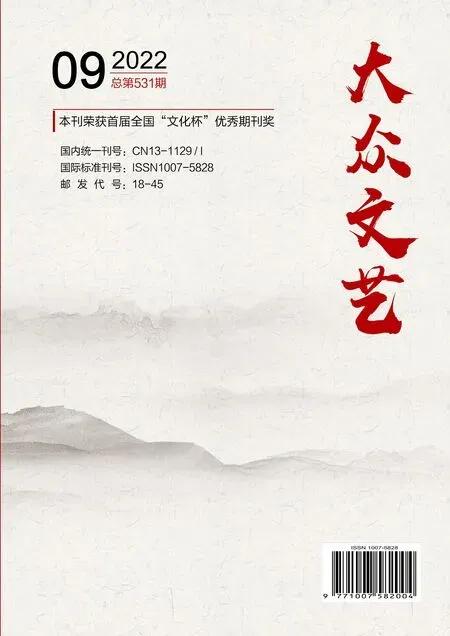蘇州古典園林意象分析
儲意揚
(江蘇大學,江蘇鎮江 212000)
蘇州園林之所以“有生命”,被譽為“我國各地園林的標本”,是因為它廣泛運用意象至造園藝術之中,自然、建筑意象與繪畫、詩歌、昆曲等文化意象互化互滲,與吳文化的土壤融洽無間。分析蘇州古典園林意象,有助于體悟建筑之美,挖掘文化價值,追尋文化根脈。
一、“疊山理水”的自然意象呈現
中國美學的審美對象理論建立在活的生命體構造理論之上,因而生活與自然緊密關聯,蘇州古典園林的造園藝術也與宇宙萬物有著本然的聯系。古代造園家強調園林中山水意象的地位,認為“石是園之骨,水是園之脈”。通過“疊山理水”的自然意象構建,追求“雖有人作,宛自天開”的效果,用自然中真山真水的構成法則來經營人工山水,使園林不顯人工斧鑿之痕,具有自然山壑的動人意趣。園林中的自然意象綜合外界分散的自然之美并對其提煉、創造、超越。蘇州園林中水景的營造幾乎可以模仿出大自然中所有的水體形態,包括湖、潭、溪、澗、噴泉等等,形態各異。不同的水體形態又分散排布,避免了賞園人產生審美疲勞,樓閣橋廊、山石花木則環繞不同水域進行排布,形成眾星捧月之態。
蘇州園林作為中國典型建筑,是反映時代和審美的媒介之一,反之,表現時代特質和審美意識也成為蘇州園林構成藝術的關鍵,建筑學家童寯即認為,情趣在園林中的重要程度,遠勝過技巧和方法。蘇州園林作為一件藝術作品,在設計和建造時,需要超越日常認知的心理時空,從審美心理時空營構。園林中的山水、樹木不僅蘊含著感官所提供的感覺材料(如色澤、形態等等),還蘊含著主體強烈的經驗因素,形態與氣節共同構成自然審美意象。以園林中假山營造為例,山林建造以“瘦、漏、透、皺”的太湖石為上選,從知覺表象觀看,是由于太湖石受到湖水的沖刷,紋理縱橫,形態奇巧,符合姿態上的美感;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太湖石與文人對于挺拔風骨、剔透血脈的精神向往若合符節,當文人以“我”觀物,將自身向往的氣概投影在園林中的奇石上時,奇石便有了人的特質;奇石挺拔剔透的韻度也被觀賞者所吸納,人便化身奇石,從自然外物界尋回了自我,審美上的移情作用使自然和個體達到了物我同一的境界。
“疊山理水”的自然意象展現了以蘇州園林為代表的中國園林與西方園林在形式和內容上本質的不同。形式上,蘇州園林不刻意追求規整的格局,更注重意境美的經營;西方園林建筑則遵循幾何規則式布局,更注重形式美的建構。內容上,蘇州園林追求自由式構圖,對自然的態度是尊重和順從,崇尚自然的樸野情趣,從自然景觀中尋找精神寄托;而西方園林則追求以藝術排斥自然,對自然的態度是征服和改造,使之接受勻稱的法則。
二、“以小見大”的建筑意象構建
造園家計成將園林藝術的精髓歸結為“巧于因借,精在體宜”,即“以小見大”的蘇州園林建筑意象構建手段。造園者將建筑物的尺度極力縮小,在有限的空間里運用揚抑、曲折、暗示等手法激發個體的主觀再創造。因此,園林中的建筑意象精巧別致,亭軒玲瓏秀麗。網師園中的引靜橋是中國園林里最短、最小的拱形橋,全場僅2.4米,但正因為這座橋搭建在園林的水池一角,延伸了水面空間,達到了最大的空間延伸效果;同時,拱形橋的精巧也能夠凸現周邊山石的壯觀雄偉,提高周邊環境的尺度感。園林在整體空間處理時使用“以小見大”的方式,使用半隔半透的分隔物引領園中人從小空間進入大空間,將外部空間的創作納入欣賞的視角,豐富了美的感受。
若追究“以小見大”建筑意象構建背后的主觀因素,不妨從園林藝術創作者和接受者的審美心理結構觀之,傳統認知中的建筑大小與時間長短構成了意識中的心理圖式,而園林藝術則體現了審美心理時空層面的超越性,既消解了部分的原有心理圖式,又生發、補充出新的表象。在空間范疇中,園林拆解了建筑原有的尺度邏輯,拋卻日常認知心理時空對象,通過構建小而精的建筑意象,總覽全景,飄瞥萬物。當明清士大夫渴望進行社會性而非政治性的退避,期望隱居卻被空間所限時,現實世界中的異己感與渴望超越現實的期盼發生沖突,從而激發將精神世界物化為客觀時空中園林的理念,將內心的人格信仰、價值取向、審美理想包容在古典園林中,這構成了蘇州的獨特隱逸文化市場——官吏并非隱居到深山里,而是隱居到城市園林綠洲中。此外,園中的小景與園外大景并沒有界限,在園林藝術中,常引入外界自然、建筑資源,借一座遠山,取一束塔影擴大院內的空間。會心山水不在高遠,小園小山足以神游。這樣的審美心理下,物的姿態跟隨“我”的情感而變化,事物的客觀大小已不再重要,園林中的建筑雖精微,卻可以任人的意志改變大小和形狀,外界景物雖遙遠,卻也能“借”來為“我”所用。文人雅士秉持著“介子納須彌”的心態,在有限的自然環境之下,內心世界得以無限擴展。
在古代,“時空的有限與無限、相對與絕對、間斷與聯系等問題,在人們的意識中產生了種種神秘的體驗……人們渴望征服時空、駕馭時空,擺脫客觀時空的束縛。”在空間尺度經歷重塑后的園林中觀賞、居住的個體,時間上的定向能力也發生了轉變。在時間范疇上,園林頗有“爛柯”故事的意味,入山砍柴者見二人下棋,觀棋片刻,發覺手中的斧柄已爛。待到歸還家鄉,才明白現實時間已經過去了百年。在“爛柯”及其衍生故事中,主角被下棋、彈琴、唱歌等游戲性的行為事件吸引,在愉悅中突破現實關系的桎梏,重構時間的尺度。而園林藝術的創作者和接受者亦是借助在園林中行、望、居、游獲得的愉悅感和撫慰,獲得消解現實悲苦的路徑,即拋卻時間概念,忘記人生的短暫和對生命有限的恐懼,達到桃花源中“不知有漢”的境界。進入園林后的個體猶如“爛柯”故事中進入仙鄉的主人翁,體驗到在時間觀念上的巨大差異。
園林對于時空尺度的重構,營造出理想型的“中國幻景”,反映了民族文化心理中共有的烏托邦情結。以審美的超越性角度理解園林建筑中“以小見大”的美感現象,完成日常認知心理時空向審美心理時空的轉換,審美主體超于“象”外,“意”在觀念中自行延展,從而在美感心理中生發更為蘊藉的“象外之象”。
三、“互化互生”的多元意象互動
蘇州園林作為綜合性藝術載體,含納了豐富的藝術文化門類,是山水、建筑與繪畫、詩歌、戲曲等多元文化意象的互動結晶,造園人與賞園人的審美心理時空在多元意象中充分互滲。
蘇州園林是兼具繪畫性與詩歌性的。造園者多借鑒中國山水畫理論,以繪畫布局方式建造古典園林,園林如同中國畫的氣質一般,保持自然形狀,力圖模仿、再現自然,凸顯含蓄蘊藉之美。元末明初山水畫家倪瓚以作畫的方式建造獅子林,在狀物寫景中抒發情趣,獅子林也被譽為“一樹一峰入畫意,幾彎幾曲遠塵心”。后世的園林研究者也關注到其繪畫屬性,童寯在《江南園林志》中指出,當時研究園林者往往重文字、輕圖畫,強調須以嶄新的繪畫視角認識園林,從超越平面的立體、透視視角研究園林。除了“畫意”,蘇州園林也飽含“詩情”。園林景“象”與文學語“象”有著密切的關聯,山水田園詩中建筑的構建方式極大地影響了人們的造園思想,白居易的“聚拳石為山,還斗水為池”奠定了構筑寫意小園的基本綱領,“枕前看鶴浴,床下見魚游”形成了園林中將水、石引入室內的設計構思。唐代王維以“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詩歌創作理念規劃、整治輞川別墅,把棲息生活和環境美化結合起來,展現出一幅四維的立體山水畫卷。蘇州園林也常以文人詩句為楹聯或匾額,表達園主人喜好自然、淡薄隱逸的情感世界。可以說,蘇州園林是畫意詩情與建筑景觀相結合的典型具象化產物。
園林意象與昆曲意象間也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兩者在審美領域的共通性為互動的產生提供了基礎,首先是自然天成,蘇州園林講求“雖有人作,宛自天開”的自然意象營造效果,而昆曲在形式、風格、語言上追求“水到渠成”的自然渾成境界;其次是以小見大,蘇州園林的建筑意象講究“以小見大”的精巧別致,而昆曲是生活的濃縮提煉,用一桌二椅、簡單的物品演繹出無限意象;最后是曲折有致,園林結構與戲曲結構一樣,講究峰回路轉,曲徑通幽。園林意象與昆曲意象的互動是雙向的,一方面,園林在昆曲的產生、創作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昆曲恰當地運用了蘇州園林的景觀意象,在園林中由構思至敷演成劇,利用現成的園林意象構建出花葉扶疏的詩性想象空間,與山水景觀不斷融合。另一方面,蘇州園林的自然意象也逐漸融入至昆曲中,昆曲劇目的題目多與園林有關,如《牡丹亭》《芙蓉樓》《翡翠園》等;園林也成為戲曲發生的背景,才子佳人“后花園私訂終身”的情節中,園林既是愛情故事的發生場所,也象征文人心目中的理想精神家園。2018年七夕,園林版昆曲《浮生六記》在蘇州滄浪亭首演,以園林自然、建筑意象為幕布,以樹聲鳥鳴為伴奏,觀眾可跟隨自己的步調邊行、邊賞、邊看,這是沉浸式昆曲演出的新嘗試,園林的精巧與昆曲的色澤交匯互通,園中景與曲中情水乳交融。
四、“天人合一”的整體意象生成
以上所述的各類意象在蘇州園林中并不是獨立存在的作為視覺對象的“景”,更是不同意象互滲、互通并兼容審美主體身體經驗和審美情感而成的“場景”。園林中的多重意象通過精妙的結構設計奏出協調的變化韻律,游廊將多個孤立意象整合起來,曲徑延展了園林的景深,豐富了景物的層次。園中的假山、樹木、建筑物等作為抑景,也對觀賞者的審美活動產生有益助推,通過先遮住主景或較美的景色,在游人漸入佳境時步移景異的表現方式,營造“先藏后露”“路轉溪頭忽現”的景觀效果,在游覽活動中激發游人豁然開朗、視野大開的審美體驗,形成新的審美意象。
“現代城市建筑和城市以極端和反常為美,堅硬、醒目、先聲奪人,卻也麻煩、不舒服、如同異物。”蘇州園林則秉持著中國文化中“人——建筑——宇宙統一”的觀念,避免了當代人造環境常帶給個體的異物感,以寬容仁厚的心態彰顯先賢無傷害原則和共享共生精神。造園者盡最大可能削弱自然環境因建筑受到的不良影響,使自然生物在園林中保持多樣性,享受自在自為狀態的同時,還能夠有利于整個園林生態系統的平衡。以戶牖為例,現代建筑的玻璃幕墻允許光線和風景進入,將節氣變化和灰塵隔絕在外,建筑與自然之間產生了一定的隔離感與邊界感;園林的軒窗則消解了此種不適感,規避了傳統建筑完全封閉的缺陷,講究與環境的聯系,在空間上更具廣延性。“軒楹高爽,窗戶鄰虛,納千頃之汪洋,收四時之爛漫。”軒窗、亭臺、樓宇作為園林中的小空間,將大空間的景致吸納進來。

耦園一景 (筆者拍攝于2021年10月1日)
園林藝術注重景中包含的氣韻,也看重景外流動的神情,個體不僅僅能夠獲得由建筑形式美激發而來的即時美感體驗,也能夠通過外部的景與物獲得內蘊之情,以更宏大、更歷時的方式延伸著“天人合一”整體意象的內化過程。蘇州園林通過情景交融的方式構建審美整體意象。如計成所述,“物情所逗,目寄心期,似意在筆先。”園林的構建是按照人的審美取向和情感追求進行排列組合的,其中的一水一石、一亭一臺皆由文人學士的好學深思和情感流動而生,因而園林是審美體驗的闡釋者。賞園人作為接受主體則是體驗的二度闡釋者,“目既往還,心亦吐納”,造園時以情入景,游園時觸景生情,在反復觀察自然景物后,賞園人內心被觸動產生表達欲,感受自然、建筑意象美感的同時,將心胸志趣投影于蘇州園林中,審美旨趣和精神追求與自然相洽。在整體意象生成中,園林與“我”物我同一,天地自然之象與人心營構之象交匯融合,構成園林富有生命的有機化空間意象。賞園人對園林意象的接受過程是造園者原體驗的接受和升華,山石林木是宇宙詩心的影現,造園者和賞園者的心靈活躍象征著宇宙的創化,藝術創作與藝術接受形成了雙向交流的過程。并且,意象生成是一個動態、變化、聯系的過程,如同創作過程中的“意隨筆轉”,在園林觀賞過程中,游人移步換景,體驗到“意隨步轉”的效果,達到身與物化,情與園融的審美境界。
自然山水、精巧建筑以及多元意象間的有機互動,使園林的玲瓏天地深深植根于吳中大地,構架起吳地文化天棚,構筑起蘇州風雅涵城,賞園人在“天人合一”的個體審美游歷過程中,得悟園林真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