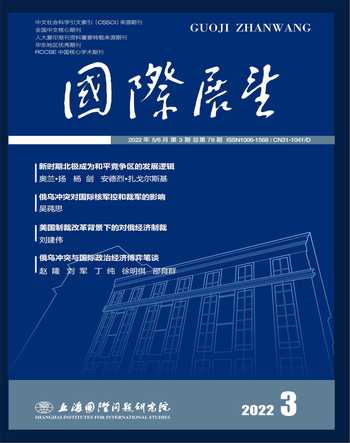“經濟強制”:理論批判與分析框架構建
解楠楠 張曉通 邢瑞磊
【關鍵詞】??強制外交 ?經濟強制 ?中美關系 ?經濟外交
【中圖分類號】?D8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568-(2022)03-0079-18
【DOI編號】?10.13851/j.cnki.gjzw.202203005
“經濟強制”(Economic Coercion,國內媒體將其譯成“經濟脅迫”)源于西方外交實踐,是國際關系和戰略研究文獻中出現頻率愈來愈高的重要術語之一。當前,關于“經濟強制”出現兩個明顯的趨向。一是“經濟強制”成為日益突出的國家政策工具;二是美國及其盟友刻意將中國正當的反制措施污名化,極力渲染所謂“中國經濟強制論”,并鼓吹通過國內立法和聯合盟友等方式進行反擊。?與武力脅迫不同,“經濟強制”作為一種工具或關系,沒有規范之意,也沒有違法之處。作為一種普遍的國家手段或工具,無論承認與否,世界上主要經濟體在過去20年中均實施過“經濟強制”。
當前,以美國為首的一些西方政要、智庫和媒體極力渲染“中國經濟強制論”以抹黑中國,操縱國際輿論,企圖將“經濟強制”塑造成繼“強迫勞動”“債務陷阱”之后對華輿論攻勢的新手段,甚至以此為其炮制的“中國威脅論”“中國霸權論”等論調提供“新證據”。西方國家的這種邏輯和行為本質上帶有強權政治和霸權色彩,而國內的一些新聞媒體在為中國正名的同時,多將“Economic Coercion”譯為更具貶義色彩的“經濟脅迫”。混淆了“強制”與“脅迫”之間的本質區別,落入了西方理論和思維的陷阱。為此,本文重點關注“經濟強制”究竟是什么,以及其與“經濟脅迫”和“霸權行徑”的區別。
“經濟強制”這一活動由來已久,?作為交叉領域的概念,涉及經濟理論和經濟現實、道德和政治、法理和法律實踐。“經濟強制”屬于“強制外交”(Coercive Diplomacy)的范疇。?但直到冷戰結束后,特別是隨著公眾對軍事干預抵制的增加,“經濟強制”作為替代性政策選項重新受到重視。
“強制”一詞,出自拉丁語,而在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利維坦》()中,“強制”首次具有了明確的政治層面的含義,指以君主作為“強制力”取代私人良知的自我管理。當前,《大英百科全書》將“強制”界定為對國家、團體或個人采取武力威脅或有限使用武力、經濟制裁、心理施壓和社會孤立等懲罰措施,以迫使其采取或停止特定行動。?“強制外交”(Coercive Diplomacy)的概念最早由美國戰略理論家托馬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在其1966年出版的專著《軍備及其影響》()中提出。在此基礎上,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亞歷山大·喬治(Alexander L.George)進行了持續的修正和發展。隨著研究的深入,“經濟強制”等一些新的術語也不斷被引入或提出。進入20世紀90年代,強制外交研究迎來了真正的黃金時代。
“強制外交”是關于操控目標國政策選擇和決策而形成的一種政策或手段,強調在軍事解決方案之外,以較小的軍事代價來達到改變目標國潛在或者正在進行的危險行為的目的。?在手段和工具上,“強制外交”包括除戰爭之外的一切措施,主要涉及軍事、外交和經濟三方面。在謝林看來,“強制外交”的核心工具是武力威脅手段一定程度的使用,“強制外交”具體包括威懾?(Deterrence)和脅迫?(Compellence)。?喬治用“強制外交”和“訛詐”(Blackmail)替代謝林提出的“脅迫”概念。在概念界定上,喬治基本上繼承了謝林的觀點,重視“強制外交”的靈活性,認為“強制外交”還包括談判等非武力手段。
當然,“強制外交”一直是有爭議的術語,最大的爭議在于武力威脅是否為界定“強制外交”的必要條件。謝林、馬克·阿姆斯圖茨(Mark R. Amstutz)、埃里克·海凌(Eric Herring)、羅伯特·阿特(Robert J. Art)、丹尼爾·貝曼(Daniel Byman)和馬修·瓦克斯曼(Matthew Waxman)?等堅持認為武力威脅是“強制外交”的根本特點甚至是唯一特點。羅伯特·阿特還提出“強制企圖”(coercive attempt)這一新概念,將通過使用以武力相威脅或使用有限武力之外的經濟制裁等其他手段達到目標統稱為“強制企圖”。還有學者將“強制外交”劃分為“戰時強制”(Wartime Compellence)和“非戰時強制”(Non-Wartime Compellence)。“戰時強制”意味著大量軍事力量之間的沖突和重大的生命損失。除了使用武力外,“戰時強制”通常還包括經濟措施,如經濟制裁和禁運。“非戰時強制”又稱狹義的強制外交,意味著較少的軍事接觸或沒有接觸以及較少或者沒有生命損失,涉及混合使用武力威脅、經濟措施。?這些爭議的存在說明,人們在“強制外交”的內涵和外延上尚未取得一致。
總之,隨著時代的發展,“強制外交”的內涵和外延也在不斷擴展,在政策工具上并非一定要以武力為手段。正如托馬斯·賴特(Thomas Wright)所描述,“在一個空前相互依賴與對權力的追逐交織在一起的世界,那些不愿卷入直接沖突的國家可能仍會采取除戰爭以外的一切措施。”?特別是在當下,隨著國際社會對戰爭高昂代價和軍事力量效用轉型以及國際體系變革的反思,國際社會不斷強化對經濟措施的使用、關注和研究,相關“經濟強制”的案例研究從金融和網絡信息領域擴展至貿易、技術、能源等多個領域。
“經濟強制”作為“強制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冷戰結束后日益重要的國家政策工具。多極時代軍事力量的合法性下降以及核武器的毀滅性后果催生了大量關于“經濟強制”的研究。與“強制外交”一樣,目前國際社會對“經濟強制”這一術語并無統一界定。?從現有文獻看,學術界對“經濟強制”基本上從工具和關系兩大相互融合的視角進行界定。
第一,作為一種政策工具,“經濟強制”通常被視為外交或軍事等政策措施的替代。因為發起國認為這些被替代措施要么不夠嚴厲(如外交抗議),要么不符合其政策目標,要么可能太危險(如秘密行動或軍事攻擊)。經濟措施往往是一條方便的、政治上受歡迎的中間道路。在這個層面上,“經濟強制”被界定為使用或威脅使用“旨在誘使(目標國家)改變某些政策或做法甚至其政府結構的經濟措施”,如大衛·鮑德溫(David A.?Baldwin)將“經濟強制”等同于“經濟制裁”,并將其界定為使用經濟手段影響對方的行為,包括信念、態度、看法、期望、情感和習性;?所采取的經濟措施的范圍和形式也在不斷擴展,從經濟封鎖、暫停援助、經濟制裁、增加海關管制到旅行禁令、切斷運輸鏈等;而且越來越多地使用“非正式”制裁。這種行為既沒有被寫入官方文件,也沒有被公開承認,卻試圖對目標國家的關鍵企業或行業施加影響,以實現戰略目標。?喬納森·科什納(Jonathan Kirshner)將“經濟強制”措施歸納為經濟援助、貨幣權力、金融權力和貿易四個類型,并認為這些工具的功能和效率(efficacy and efficiency)取決于所使用的“經濟強制”的類型和依賴程度。
第二,作為一種關系,強調“經濟強制”本質是由世界經濟體系的非對稱性相互依賴決定的。現代學者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兩部基礎性著作《權力與相互依賴》()和《經濟治國術》(),這兩部著作詳細論述了國家間財富和權力的不平衡分配以及政府在特定的影響力嘗試中可能依賴的經濟權術,即不對稱相互依賴。?羅伯特·吉爾平(Robert Gilpin)明確指出,“經濟相互依賴在社會集團以及國家之間建立了一種實力關系……相互依賴產生了一種可供利用和操縱的脆弱性。?在這個層面上,芝加哥大學法學院希巴·哈菲茲(Hiba Hafiz)將“經濟強制”界定為一種可以在經濟上被利用、使一些人的利益高于其他人的關系或交易。經濟和金融制裁是各國利用相互依賴和不對稱性優勢最明顯的例子,但不是唯一的例子。在此基礎上,以默里·斯科特·坦納(Murray Scot Tanner)為代表的學者進一步指出,“經濟強制”是經濟發達的國家對經濟脆弱的發展中國家的采取的一種手段,通常由國際上活躍的大國單獨或以國家聯盟的名義發起,其目標國通常是小國。
值得關注的是,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以及大國戰略競爭的加劇,“經濟強制”出現了新形式,即一些國家利用自身在全球經濟網絡結構的中心地位,通過掌控網絡中的重要節點來強制其他國家。例如,通過施展“全景監獄戰略”(Panopticon Effect,捕獲對手的信息流通)和“扼流閘閥戰略”?(Chokepoint Effect,切斷對手的要素流動)來獲得信息和控制優勢,實現地緣戰略目標。?亨利·法瑞爾(Henry Farrell)和亞伯拉罕·紐曼(Abraham L. Newman)等學者將這一現象概括為“相互依賴武器化”。
與“強制外交”一樣,“經濟強制”也是一個復雜的理論概念,其源于西方政策實踐,理論大多來自于西方社會,國內研究成果則比較匱乏。特別是隨著“經濟強制”當前被頻繁使用并在形式上不斷翻新,相關研究存在明顯的滯后性和西方主導的問題。由于概念使用混亂以及西方思想主導下重視強制行為目標、過程和效用等微觀基礎性研究,導致“經濟強制”的合法性有待厘清。
目前國際社會對“經濟強制”這一術語沒有統一的界定,部分學者將“經濟強制”與經濟壓力(economic pressure)、經濟制裁(economic sanction)、“經濟治國術”(economic statecraft)等術語混用。事實上,這些概念的范圍不同,如經濟制裁是“經濟強制”的重要形式,但不是唯一形式。西方社會企圖通過混淆概念為其炮制的“中國威脅論”“中國霸權論”等提供“新證據”。這種西方政治和規范偏見本質上帶有強權政治和霸權色彩。
在“強制外交”理論研究中,“強制”“強制外交”和“脅迫”等術語相互交錯,被許多學者混用。?事實上,“強制(Coercion)”與“脅迫(Compellence)”兩者之間無論是在“強制外交”理論研究中還是在詞義上都有明顯區別。
第一,在“強制外交”的理論研究中,“脅迫”一詞一直與使用武力有關。謝林和喬治都將“脅迫”界定為使用軍事力量的戰略,用以指稱使用武力威脅或使用有限武力,“脅迫”是“強制”的形式之一。在外交實踐中,1985年美國對南非實施貿易制裁,作為對南非政府施加壓力的一種手段,以結束種族隔離制度;同樣,1997年美國向世界銀行施壓,要求其推遲對克羅地亞的貸款,直到該國更嚴格地遵守《達頓和平協議》(Dayton?Agreement)關于難民和戰犯的規定。前一個事件通常被認為是經濟制裁,而后一個事件則不是,但它們都屬于“經濟強制”。?而且從國外現有文獻看,在描述“經濟強制”時,國際社會一直使用“Coercion”而非“Compellence”。基于此,對于通過經濟措施實現外交政策目標的行為描述,“經濟強制”相較于“經濟脅迫”更合適,至于“經濟強制”在什么情況下屬于“脅迫”行為,則不在本文探討的范圍之內。
第二,在詞義上,“強制”一詞與“自然”對立;在詞性上,“強制”是中性詞,不涉及規范的意義,亦無違法之處。?強制在所有人類關系中都是正常的,與合作相同,是正常行為中的一部分。人類關系中充滿了強制和合作的混合物;而“脅迫”有威脅、強迫之意,是法律常用詞,多為貶義。在所屬關系上,“強制”具有包容性,如果指稱一種特定的關系是強制性的,也不能說明其非法性,更不能說明其具有霸權性。
第三,從國際關系實踐看,“經濟強制”是一種全球現象,無論承認與否,世界上越來越多的行為體曾經或正在使用和應對“經濟強制”。這些國家既有美國、歐盟國家等西方國家,也有巴西、印度、伊朗、南非、韓國和土耳其等國家。例如,俄羅斯利用天然氣出口向鄰國施加壓力,土耳其利用其地理位置切斷亞美尼亞與西方的貿易,印度對巴基斯坦的經濟制裁等均屬于此類情況。正如全球地緣經濟議程委員會(Global Agenda Council on Geo-economics)在《經濟強制時代:地緣政治是如何擾亂供應鏈、金融系統、能源市場、貿易和互聯網》白皮書中所描述的那樣,“‘經濟強制’是一種全球現象,在過去20年世界主要經濟體都使用過,而且正在越來越頻繁地使用‘經濟強制’。”
有鑒于此,作為中性的關系或工具,“經濟強制”是一種全球現象,并不必然意味著霸權行徑。相反,“經濟強制”既可以作為實施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工具,也可作為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手段。
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社會在經濟不對稱相互依賴關系中處于優勢地位,一方面對“經濟強制”與霸權行徑之間的聯系緘口不言,另一方面則鼓噪制裁是一種有效及合法的手段。特別是在美國,“經濟強制”已從一種偶然的政策工具演變成為國家的核心政策工具之一。美國領導人利用美元和金融機構的全球主導地位、美國的市場規模和吸引力、美國企業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地位以及外國投資的廣度等?來推進其安全和外交目標。
在上述背景下,國外學者尤其是美國學者專注于強制行為目標、過程以及效用等微觀基礎性的研究。
首先,基于目標導向的研究傾向于以目標為標準對強制行為的攻防性質進行判斷。喬治首次將“強制外交”按照目標分為三類,并以此作為判斷其攻防性質的依據。?喬治認為,“阻止目標政府采取令發起國反感的某些行為,或促使目標國停止其行為或改變政策”屬于“防御性強制外交”。而“挑起反對目標政府的起義或政變,導致出現一個將按照發起國的意愿行事的新政府”屬于“進攻性強制外交”。這種對“強制外交”攻防性質的判斷,混淆了動機(進攻、侵略、防御)與目標(停止某行為、消除某行為、放棄某物)的關系。其次,基于過程導向的研究更多關注強制行為發起國和目標國博弈的過程和評估強制行為的成敗及影響因素。其中比較典型的是采用博弈論來分析發起國與目標國之間如何討價還價。這種分析模式通常將發起國或者強制行為作為戰略互動和研究的起點,這一研究在承認每一個事件都包含在國家間持續不斷的關系中這樣一個事實的同時,忽略了戰略互動本身很難分清影響的先后次序問題。再次,基于效用導向的研究更多地從“成本—收益”的邏輯來解釋制裁和相關工具的效用,以及有效強制和聯盟政治、經濟獨立之間的關系,即分析強制行為是否能夠實現限制目標國資源或迫使其調整政策的目標及其決定性因素。
上述三種導向的研究,都以發起國為研究起點,服務于西方國家戰略目標。盡管以中國為代表的廣大發展中國家認為,只有聯合國安理會才是合法的制裁來源,其他制裁是非法的,?但國內學術界對此并無過多研究,常把西方的“經濟強制”行為作為一個常數或實力的直接結果來處理。
顯然,現有研究成果在豐富和完善“經濟強制”和“強制外交”理論體系的同時,并未解決甚至強化了概念之間的模糊性以及對強制行為的政治和規范偏見,沒有厘清“經濟強制”與霸權行徑之間的聯系,為“經濟強制”的“錯用”和“濫用”創造了空間。
基于對“經濟強制”現有理論研究的反思,為進一步理解和分析“經濟強制”與霸權行徑的關系,本文將戰略思維和觀念引入“經濟強制”的分析框架,通過對中、美“經濟強制”政策和實踐進行比較研究,認為盡管中國與美國看似使用相同或者相似的經濟強制手段/工具,但卻存在本質上的差異。美國的“經濟強制”帶有明顯的霸權進攻性特征,其目標國家具有全球性,既有針對被美國界定為競爭對手的國家的全方位打擊,又有針對美國盟友和其他中小國家特定行為的打擊。而中國的“經濟強制”更傾向于積極防御性,目標國家的范圍和觸發中國反制措施的行為有限,主要針對反華行徑。
戰略思維根源于戰略價值觀,以若干基本觀念為基礎,形成于國家具體的戰略實踐和經驗之中。本文基于歷史和比較視角分析中美兩國戰略思維和觀念與“經濟強制”政策邏輯和實踐,并以此為依據對“經濟強制”進行重新定性與歸類。
之所以選擇中美兩國“經濟強制”政策實踐作為研究對象,主要基于三點考慮。一是美國是二戰后“經濟強制”的發明者和實踐者,也是國際社會使用“經濟強制”頻率最高的國家;中國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被西方國家頻繁指控實施“經濟強制”的國家。二是中、美兩國分別是世界上第一大和第二大經濟體,在世界經濟體系中均處于優勢地位,有能力實施“經濟強制”。三是中、美兩國由于在地理環境、民族歷史、政治制度、社會文化特質等方面存在差異,其戰略思維和觀念也明顯不同。
美國的戰略思維和觀念在逐步走向世界舞臺中心的歷史進程中形成并固化,?除了例外論和優越論,?還具有兩個明顯的特征。首先是使命感和霸權性。所謂的使命感是指美國人自認為是“上帝的選民”,受上帝委托對人類的發展和命運承擔一種特殊的責任。霸權性是指美國對外戰略的根本目標始終圍繞著其全球主導地位的鞏固或維系。美國的使命感和霸權性相結合就是美國人所說的“美國治下的和平”。美國維護和鞏固其全球領導地位的意圖在歷屆總統的政府文件中都有所體現。?其次是以實力為核心的利益觀和絕對安全觀。實力的核心是財富、武力以及相關的技術,在經濟和技術上表現為孜孜不倦地追求和確保美國對戰略性資源的獲取能力、全球貿易的主導地位、國際金融的控制優勢以及對戰略性技術的掌控。這種思維使得美國一直存在強烈的危機感和焦慮感,到處尋找敵人。
由于上述原因,美國形成了以維系全球霸權為目標,以軍事、經濟和技術絕對優勢為權力來源,以民主制度和價值觀為理念支撐,在拯救世界的歷史責任感驅使下奉行擴張主義和干涉主義對外政策,按照美國的意愿改造世界,具有典型的進攻性、競爭性和對立性。作為對外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國“經濟強制”可分為三大類型,并體現出若干特征。
第一,霸權型“經濟強制”。這是美國霸權思維和絕對安全觀的最直接映射,也是當前最為突出的“經濟強制”類型,其主要針對被美國界定為“競爭對手”的國家,如中國、俄羅斯等,基本邏輯則是美國的霸權地位正受到這些國家日益增長的實力的威脅。特別是在大國戰略競爭取代恐怖主義成為美國核心“關切”以來,以及中國被明確界定為“唯一有綜合實力挑戰美國所建立的國際秩序的競爭對手”?的背景下,“經濟強制”成為美國對華戰略的核心工具,經濟競爭和遏制成為美國對華經濟戰略的主色調。美國對華戰略經歷了奧巴馬政府的“制度+價值觀”競爭、特朗普政府的“經濟+安全”競爭以及當前拜登政府的兩者兼而有之的過程。?美國在貿易和技術等領域不斷升級和擴大“經濟強制”工具包,如2018年8月美國國會通過《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案》(FIRRMA),不僅將之前自愿提交審查申請調整為強制要求企業提交審查申報,還將CFIUS審查范圍擴大至外資對美企的非控制性投資。?同年,國會還頒布了《出口管制改革法案》(ECRA),把14項“新興技術”納入出口管制條例的范圍。2019年5月,美國商務部產業與安全局(BIS)新增對新興技術的管制措施等。這一系列措施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國擔心中國投資美國科技行業以獲得技術和加強中國在全球關鍵技術領域的競爭地位。
第二,霸權延伸型“經濟強制”。這類“經濟強制”的目標國家既包括美國盟友,又包括中小國家。其基本邏輯是目標國家如果與美國的競爭對手或者懲罰對象合作,則違背了美國所謂自由、民主和人權等基本價值觀。2021年7月30日美國財政部以鎮壓反政府示威為由,宣布對古巴國家革命警察總局及其局長、副局長實施制裁。美國國務院2020年12月針對土耳其采購俄羅斯S-400防空導彈系統一事,根據《以制裁反擊美國敵人法案》(CAATSA)對土耳其國防工業局(SSB)實施制裁,包括禁止美國公司與SSB有關聯的土方公司進行合作或技術轉讓,限制美國金融機構對SSB總計超過1 000萬美元的貸款,同時對德米爾以及3名與俄羅斯有聯系的自然人實施制裁等。
第三,懲罰型“經濟強制”。主要針對損害美國經濟利益的國家,通常表現為相互加征關稅,其基本邏輯是目標國家損害了美國的經濟利益,如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于2021年3月宣布,準備對英國、奧地利、印度、意大利、西班牙、土耳其這6個國家加征懲罰性關稅,理由是這些國家對美國征收數字服務稅。顯然,懲罰型“經濟強制”主要針對目標國家的行為,而前兩種“經濟強制”主要針對被美國視為競爭對手的國家及其違背美國“打擊競爭對手”意愿的國家,其主觀性和針對性相對較強,哪怕是目標國正常和合理的經濟與政治行為,都可能觸發美國的“經濟強制”。值得注意的是,當目標國家是中小國家時,“經濟強制”常常伴隨著軍事干預,或者挑起反對目標政府的動亂或政變,以期出現一個按照美國意愿行事的新政權。
從美國“經濟強制”的類型和相關案例不難看出,美國的“經濟強制”呈現三大特征。首先,目標國家的全球性。美國三大類型“經濟強制”的目標國家既包括競爭對手,又包括盟友和廣大中小國家,其覆蓋范圍具有全球性。其次,以安全為由為“經濟強制”背書,即實施經濟安全化政策,表現為以國家安全為由擴大和深化進出口管制、投資限制等,如切斷華為與關鍵供應鏈和組件的聯系,封禁與中國有關的技術、產品及服務等。再次,“經濟強制”措施從利用目標國家對美國市場或供應的依賴以阻止其進入美國國內市場為基礎,轉向利用全球關系網絡以阻止其進入全球市場為基礎,也就是將不對稱性相互依賴武器化。例如,實施經濟俱樂部策略,推動所謂“經濟繁榮網絡”“清潔網絡項目”,宣揚“自由國家之間的自由貿易”,圖謀將中國和其他對手與全球供應鏈、產業鏈深度剝離,拼湊孤立、排斥目標國家的國際經貿陣營。再如,推動“敏感技術多邊行動”,把相關盟友或伙伴糾合在一起,對目標國家進行技術封堵。?這樣的“經濟強制”措施會牽扯較多行為體(涉及目標國以外的第三方行為體),影響相對較大。
第一,中國的戰略思維和觀念呈現與美國截然不同的三大特征。首先,和平發展和共同體思維。中國自古以來就有以和為貴、和而不同的思想。道家講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儒家倡導“和為貴,和而不同”的思想。融合共生的理念充分體現在新中國成立后歷屆領導集體的對外戰略中,習近平提出“全人類共同價值”的概念,?表示“中國共產黨將繼續同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一道,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其次,底線思維。與美國的絕對安全觀和推崇武力不同,底線思維強調長遠利益與整體觀,在對外戰略上更偏向于防御性,強調“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再次,例外論和包容性。國家例外論存在兩種形式,一種是以本國更卓越為立論基礎的例外論,另一種是以本國更獨特為立論基礎的例外論。前者會使一國實行擴張型的外交政策,旨在向世界其他國家推廣本國的理念和規范;后者會使一國實行防御型的外交政策,強調各國情況的差異性。?顯然,美國優越論屬于前者,中國更傾向后者。中國一方面堅定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另一方面逐步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多極化思想,?堅持包容精神,承認有同有異,求同存異、增同減異,?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發展道路的權利,維護國際公平正義,反對把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人,反對干涉別國內政,反對以強凌弱,同時也不會以犧牲別國利益來發展自己。
第二,在這種戰略思維和觀念的指導下,中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對外戰略以尋求和擴展共同利益為基本理念,以塑造“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創更美好世界”為目標指向,并以對話協商、合作共贏、求同存異、包容開放為主要策略。?中國的“經濟強制”具有防御性,并呈現兩個特征。首先,觸發中國經濟強制的行為具有特定性,目標國家范圍有限,主要是針對部分國家、實體和個人的反華行徑及其造成的損害,要運用各類經貿杠桿和手段予以反制。本文將這種“經濟強制”稱為“糾正型經濟強制”。這樣的“經濟強制”針對目標國家已經造成的損害行為,而不存在所謂的“競爭對手”,更談不上全方位打擊。不同的是,“懲罰型經濟強制”主要是針對目標國家的經濟政策或行為及其造成的損害采取的反制行為;而“糾正型經濟強制”更多針對目標國家干涉中國內政,侵犯主權的政策或言行。?其次,中國的“經濟強制”措施主要利用目標國家對中國國內市場或供應的依賴,以阻止其進入中國市場為基礎。相較于美國越來越傾向于利用其在全球經濟網絡結構中的中心地位脅迫第三方行為體、切斷目標國家與全球經濟聯系的做法,中國的“經濟強制”涉及的范圍和造成的損害都很有限。
以中國對澳大利亞的經濟制裁為例,盡管中澳之間在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等方面存在差異,但中澳建交以來,中國堅持多元化和包容性,與澳方進行密切的經濟交往,連續十年成為澳大利亞第一大貿易伙伴國、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國、第一大進口來源地,澳大利亞成為中國第八大貿易伙伴國、第五大進口來源國。?在2019/2020財政年度,中澳雙邊貿易額達到2 510.7億澳元,同比增長6.8%,但澳大利亞莫里森政府頻繁發表污蔑和干涉中國內政的言論并對中國實施“經濟強制”措施,?中國曾多次與澳大利亞進行協商,但澳方罔顧中方的核心關切,繼續為所欲為。基于此,中國對澳大利亞實施經濟制裁,其目的在于推動中澳關系回歸正常軌道。“經濟強制”既不是中國外交的目的,也不是中國獲取利益或者權力的手段,中國更不首先使用“經濟強制”手段。中國始終認為和平與發展仍是時代主題,經濟相互依賴促進國際合作,尊重市場原則。
顯然,盡管中美兩國的“經濟強制”表面上有某種相似性,如都使用進出口限制等工具,但兩國的“經濟強制”本質上存在明顯差異,霸權型“經濟強制”和霸權延伸型“經濟強制”具有強權政治和意識形態色彩,以維持和鞏固美國霸權地位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以“競爭對手”為打擊對象,這也是當前以及未來美國“經濟強制”的突出形式,本文將其統稱為“進攻性經濟強制”。而“防御性經濟強制”以目標國已造成的損害行為為對象,利用經濟措施迫使目標國改變其已經發生的行為。與“進攻性經濟強制”不同,“防御性經濟強制”更具策略性,有推動目標國行為回歸到合理狀態的目的。
當前,“經濟強制”是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工具,是美國打壓中國等競爭對手的關鍵手段。美國是實施“進攻性經濟強制”的主要國家。從特朗普政府及其繼任者和國會兩黨成員對實施“經濟強制”的廣泛支持以及通過這些工具來解決政策問題的意圖可以判斷,在未來幾年美國將持續擴大其經濟強制工具箱及其使用的廣度和深度。當前,中國被美國明確界定為“唯一具有綜合實力挑戰美國所建立的國際秩序的競爭對手”,在中美戰略競爭的背景下,中國也成為美國“進攻性經濟強制”的主要目標國。面對美國及其盟友不斷增長的“經濟強制”行為以及個別小國妄圖綁架中歐關系、歐美關系的情況,中國需高度重視相關問題。首先,學術界和行政部門應系統研究和探討美國“經濟強制”的基礎及其變化,觸發美國“經濟強制”的機制,美國“經濟強制”的措施、形式與前景,以及國際社會防范和化解美國“經濟強制”的歷史經驗和理論啟示。一方面,要充分揭露美國對外實施“經濟強制”的事實及其雙重標準,從學理上和輿論上對“經濟強制”進行反擊,以應對西方的理論霸權和惡意宣傳;另一方面,要結合形勢變化,統籌現有的外交能力和資源,做好風險評估和相關預案。其次,中國應當密切追蹤美、歐開展所謂“反中國經濟強制”政策協調的新動向,防止其利用該議題推出更多集體反華措施。同時,應充實中國涉外法律工具箱,進一步加快對外經貿立法進程,從法理、規則等多個層面制衡和反制一些國家的對華挑釁,對各種損害中國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國家及相關實體采取必要措施,以維護自身利益。
[責任編輯:樊文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