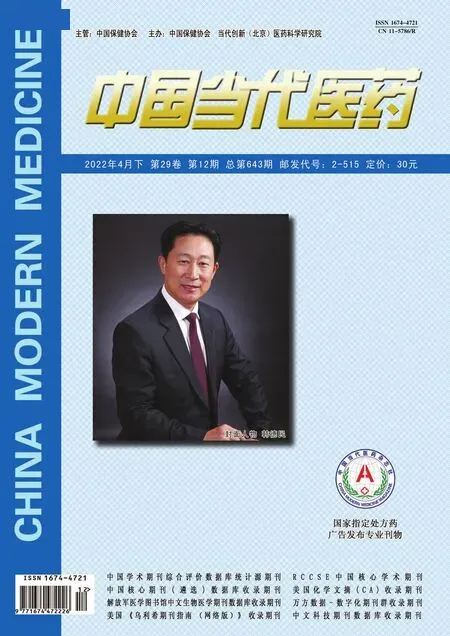妊娠期糖尿病患者腸道菌群的變化及臨床意義
郭麗華 許小歡 賴晨暉 梁玉華 孟偉偉
深圳市寶安區石巖人民醫院產科,廣東深圳 518100
妊娠期糖尿病(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GDM)指孕期初次出現一定程度的糖代謝問題,是孕產婦一種獨有的疾病[1],發病率高且有逐年升高的發展趨勢[2]。GDM 會對母嬰健康產生不良影響[3],會造成孕婦出現代謝功能障礙[4],繼而引起子癇前期、產后出血、產褥感染以及胎兒宮內窘迫、窒息等不良后果[5],應引起高度重視,積極防治。近年來,GDM 越來越受到學者的關注,如何早期發現、診斷及預防GDM 的發生,并減少GDM對母嬰的損害成為研究的熱點。 目前GDM 的發病機制不清, 尚無一種可有效預測GDM 母嬰結局的參考指標, 因此尋找一種可早期預測GDM 母嬰結局的臨床指標迫在眉睫。有研究顯示,腸道菌群紊亂是導致GDM 的發病及病情進展的影響因素之一[6]。 基于此,本研究分析GDM 患者腸道菌群的變化及臨床意義。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20年9月至2021年6月于深圳市寶安區石巖人民醫院產檢和分娩的100 例GDM 患者作為GDM 組;另選取同期80 例正常孕婦作為正常妊娠組。正常妊娠組孕婦年齡18~40 歲,平均(29.11±5.87)歲;孕齡37~41 周,平均(39.23±0.96)周;產次0~3 次,平均(1.33±0.45)次;糖尿病家族史16 例。 GDM 組孕婦年齡18~40 歲,平均(29.17±5.82)歲;孕齡37~41 周,平均(39.28±0.94)周;產次0~3 次,平均(1.35±0.43)次;糖尿病家族史19 例。兩組的年齡、孕齡、產次、糖尿病家族史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根據妊娠結局將GDM 組產婦分為正常分娩組(84 例)與不良妊娠組(16 例)。 正常分娩組孕婦年齡18~39 歲,平均(29.20±5.80)歲;孕齡37~41周,平均(39.30±0.92)周;產次0~3 次,平均(1.37±0.42)次;糖尿病家族史16 例。不良妊娠組孕婦年齡18~40 歲,平均(29.15±5.83)歲;孕齡37~41 周,平均(39.26±0.95)周;產次0~3 次,平均(1.34±0.44)次;糖尿病家族史3 例。 兩組的年齡、孕齡、產次、糖尿病家族史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本研究經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批,患者和家屬均簽署知情同意書。納入標準:①無孕前糖尿病、主要臟器疾病、高血壓者;②無其他代謝性疾病及內分泌疾病者;③入組前4 周內未使用過抗生素、微生態活菌制劑等、近4 周內無胃腸道疾病者;④18~40 歲,單胎,計劃在醫院分娩。排除標準:①曾接受不孕治療者;②合并傳染性疾病者;③神志不清、溝通障礙者;④孕期服用抗生素者。
1.2 方法
腸道菌群檢測:于孕晚期進行檢測,運用糞便微生物DNA 采集保存套裝(上海維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TinyGene 型),晨起采集糞便標本,置于含有DNA保存液的塑料管內。 0.5 h 內運送回實驗室,-80℃冰箱保存,采用培養法進行檢測,記錄腸桿菌、腸球菌、雙歧桿菌、乳桿菌、梭桿菌的菌落數。
母嬰不良妊娠結局分析:對產婦的妊娠結局進行觀察并記錄, 根據妊娠結局將GDM 組產婦分為正常分娩組與不良妊娠組。
1.3 觀察指標及評價標準
比較正常妊娠組與GDM 組孕婦的腸道菌群檢測結果、母嬰妊娠結局、正常分娩組與不良妊娠組的腸道菌群檢測結果。 ①正常妊娠組與GDM 組孕婦的腸道菌群檢測結果。 具體菌落的鑒定方法:腸桿菌采用計算發酵乳糖、染色鏡檢為G-桿菌的所有菌落;腸球菌采用計數有明顯褐色圈、 染色鏡檢為G-球菌的所有菌落; 雙歧菌采用食品衛生微生物檢驗雙歧菌檢驗;乳桿菌采用G+無芽孢桿菌、觸酶陰性、APICH50;梭桿菌采用G+芽孢桿菌。 ②正常妊娠組與GDM 組孕婦的母嬰的不良妊娠發生率。不良妊娠指不明原因的異常情況造成的孕期胚胎發育異常, 包括子癇前期、產后出血、產褥感染、過期產兒、胎兒宮內窘迫、巨大兒、新生兒窒息、新生兒低血糖。 計算公式:不良妊娠發生率=不良妊娠發生例數/總例數×100%。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PS 19.0 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用均數±標準差(±s)表示,方差齊時采用t 檢驗,方差不齊時采用校正t 檢驗;計數資料用率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以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正常妊娠組與GDM 組孕婦腸道菌群檢測結果的比較
GDM 組孕婦的腸桿菌、 腸球菌菌落數大于正常妊娠組,雙歧桿菌、乳桿菌菌落數小于正常妊娠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的梭桿菌菌落數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表1)。
表1 正常妊娠組與GDM 組孕婦腸道菌群檢測結果的比較(logN/g,±s)

表1 正常妊娠組與GDM 組孕婦腸道菌群檢測結果的比較(logN/g,±s)
注 GDM:妊娠期糖尿病
組別 例數 腸桿菌 腸球菌 雙歧桿菌 乳桿菌 梭桿菌正常妊娠組GDM 組t 值P 值80 100 8.32±0.89 9.64±1.14 8.490<0.001 7.02±0.79 8.40±1.23 8.699<0.001 8.09±0.37 7.41±0.52 9.866<0.001 6.82±0.91 5.39±0.74 11.629<0.001 3.34±1.01 3.38±0.46 0.353 0.362
2.2 正常妊娠組與GDM 組孕婦母嬰妊娠結局的比較
GDM 組孕婦的不良妊娠發生率高于正常妊娠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表2)。

表2 正常妊娠組與GDM 組孕婦母嬰妊娠結局的比較[n(%)]
2.3 正常分娩組與不良妊娠組腸道菌群檢測結果的比較
不良妊娠組孕婦的腸桿菌、腸球菌菌落數大于正常分娩組,雙歧桿菌、乳桿菌菌落數小于正常分娩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的梭桿菌菌落數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表3)。
表3 正常分娩組與不良妊娠組腸道菌群檢測結果的比較(logN/g,±s)

表3 正常分娩組與不良妊娠組腸道菌群檢測結果的比較(logN/g,±s)
組別 例數 腸桿菌 腸球菌 雙歧桿菌 乳桿菌 梭桿菌正常分娩組不良妊娠組t 值P 值84 16 9.25±0.71 10.12±0.83 4.371<0.001 7.98±0.93 9.14±1.12 4.423<0.001 7.60±0.59 6.83±0.48 4.913<0.001 5.72±0.80 5.01±0.66 3.336<0.001 3.35±0.48 3.40±0.45 0.385 0.350
3 討論
人體腸道中寄居著大量的微生物,這些微生物可通過腸道上皮屏障作用、免疫進化、營養利用等影響機體健康[7]。有報道指出,腸道菌群和代謝功能有明顯的關聯[8]。 近年來,腸道菌群與GDM 的關系也得到研究學者的認可[9],為預測GDM 母嬰結局新指標提供了一種思路、方向[10]。 Crusell 等[11]報道指出,相比于正常血糖的孕婦,GDM 孕婦腸道中多種菌群豐度更高,且其差異常延續到分娩后。 然而,有關該病腸道菌群的變化過程尚不明確[12],較多人認為,細菌脂多糖代謝參加了胰島素抵抗及糖耐量受損的過程[13]。
本研究結果顯示,GDM 組孕婦的腸桿菌、腸球菌菌落數大于正常妊娠組,雙歧桿菌、乳桿菌菌落數小于正常妊娠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提示GDM孕婦存在一定程度的腸道菌群失衡。膳食對GDM 腸道菌群會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 遵循飲食建議的GDM患者表現出更好的代謝和炎癥模式,并且與高脂飲食相關的擬桿菌數量顯著減少, 因此, 臨床應加強對GDM 孕婦的膳食指導,以改善其腸道菌群。
本研究結果還顯示,GDM 組孕婦的不良妊娠發生率高于正常妊娠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提示GDM 會對孕婦的分娩結局產負面影響,會導致不良妊娠結局風險升高, 因此及早診斷并治療GDM非常重要。 對不同母嬰分娩結局的腸道菌群比較顯示,不良妊娠組孕婦的腸桿菌、腸球菌菌落數大于正常分娩組,雙歧桿菌、乳桿菌菌落數小于正常分娩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提示腸道菌群失衡與不良妊娠之間存在一定的相關性,說明腸道菌群檢測結果可作為評估GDM 產婦不良母嬰妊娠結局的參考指標,與陳悅群等[14-15]的相關報道基本一致。
綜上所述,GDM 患者存在腸道菌群紊亂, 且母嬰不良妊娠結局發生率較高; 檢測GDM 患者的腸道菌群變化,對臨床防治GDM、改善母嬰結局有一定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