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著名作家、戲劇家、翻譯家李健吾
任文芳
古老河東,人杰地靈,名流薈萃。在近代,李健吾無疑是從這里走出的一位卓越的驕子。李健吾,筆名劉西渭,1906年出生于山西省運城市鹽湖區西曲馬村,是近代著名作家、戲劇家、翻譯家、評論家和文學研究者,為中國現代文學的興起和繁榮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顛沛流離的童年
李健吾的父親李岐山,是晉南辛亥革命主要領導人之一。李岐山有三個兒子,李健吾居次。李健吾出生后的第二年,李岐山在景梅九介紹下加入同盟會,旋即在運城、太原等地投入革命活動。童年時的李健吾隨慈母相竹筠生活在家鄉,五歲啟蒙,在關帝廟念私塾。由于李岐山常年在外,父子二人難得相聚。李岐山赴陜任職時,把李健吾送到渭南他的部下史可軒家中。在密謀討袁前夕,李健吾又被父親派心腹送到天津,在津浦線良王莊一個農家生活了近一年。1916年夏,十歲的李健吾從天津到了北京,進入北京師范大學附小上學,終于與家人團聚。
李歧山于1918年夏二次入獄后,李健吾每周去鐵獅子胡同探望父親。每次去探監,父親都要檢查他一周的功課,并為他寫五六個典故,詳細講解,令其熟記。父親勉勵他刻苦學習,正直做人。李健吾后來回憶說,一年的探監生活是他過去最苦亦最難忘的歲月,而獄中教育也使他受益匪淺。在《鐵窗吟草》中,李岐山有首《立秋日次子健吾送酒食物》,便是記錄了父子鐵窗內外相見的歡喜:“手持美酒古書并,口報家人問我安。”

李歧山遇害那年,李健吾十四歲。李岐山生前好友馮玉祥等人湊了兩千元存入銀行,李健吾一家依靠利息維持生活。為了節省房錢,他們搬到南下洼,在這個貧民區一住就是整整十年。1925年,李健吾考入清華學校(現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1930年,閻錫山兵敗下野。次年春天,李健吾與哥哥李卓吾一道回到家鄉,合殮了父母。時任陜西省主席的楊虎城聞知,派人前往祭奠。事畢,李健吾專程赴陜答謝。得知故人之子暑期將赴法留學,楊虎城送他一千元做學費。回北京時李健吾順路拜見了父親生前好友、山西省主席商震,商震讓教育廳補助他三千元學費。加上叔父李鳴鶩的資助,李健吾湊足了留法兩年的學費。
花團錦簇的文壇奇才
李歧山遇害使其一家跌入社會的底層,生活窘迫,但也使李健吾體會到了底層人民生活的艱難,為日后創作積累了綿綿不盡的題材。1923年就讀北師大附中期間,李健吾等人組織了“曦社”,在李健吾父親生前摯友景定成主編的《國風日報》上辦了《爝火旬刊》,后又辦了《爝火》雜志,并發表習作。李健吾從1925年起發表譯作,以小說、劇本為多,兼有評論文章,逐漸在創作、批評、翻譯和研究領域都成為大家。
李健吾一生在戲劇領域著力較多。獨幕劇《母親的夢》,創作于1927年,表達了李健吾對父親的緬懷和對母親的崇敬。上海全面淪陷后,李健吾回憶起早逝的父親帶領民軍走在反清反袁戰場第一線,著手創作了八折辛亥傳奇劇《草莽》(又名《販馬記》)。他曾創作了《這不過是春天》《青春》等近十部戲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青春》被改編為評劇《小女婿》,獲得第一屆中國戲劇匯演一等獎。他創作了《戰爭販子》《偽君子》及《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多部劇本;改編了許多外國劇本,如反內戰的《和平頌》《山河怨》《愛與死的搏斗》,名家托爾斯泰、契訶夫、屠格涅夫、高爾基等人的戲劇以及巴爾扎克、司湯達、繆塞等人的作品和論著等,受到葉圣陶、郭沫若的贊譽。
李健吾在小說領域頗有建樹。1925年,他考入清華學校(現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并在此期間創作和發表了多篇中長篇小說。魯迅先生曾評論他的《中條山的傳說》“是絢爛了,雖在十年后的今日,還可以看見那藏在用口碑織就的華服里面的身體和靈魂”。可見李健吾小說特色之一斑。
李健吾的散文曾受到社會各界的大加褒獎。20世紀20年代,周作人曾說過,現今有兩個年輕人的散文引起他的注意,一個是徐志摩,一個是李健吾。多少人記得上中學時,讀過一篇散文《雨中登泰山》。那篇獨具風格的泰山游記,是李健吾1960年夏赴山東時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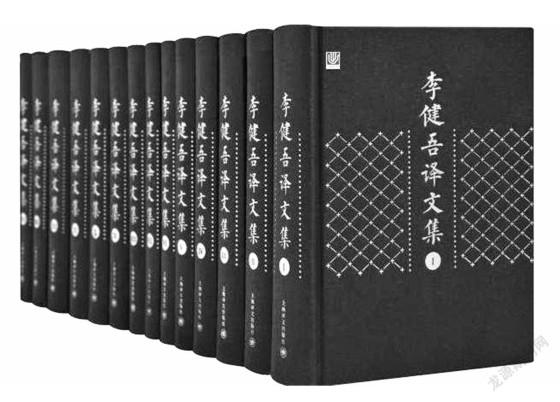
李健吾的文學評論在現代文學批評史上留下特殊印記。20世紀30年代中期起,他以劉西渭為筆名發表評論,文學評論有《咀華集》和《咀華二集》,戲劇評論有《戲劇新天》和《李健吾戲劇評論選》。“心靈探險”式的兩集《咀華集》使李健吾執京派文學批評之牛耳。他的批評立論公正,見解宏達,旁征博引,文筆華美,功力深厚。時人把暨南大學的他與北京大學的朱光潛、南開大學的梁宗岱,并稱為評論界學院派“三劍客”。作為戲劇評論家,李健吾在1957年老舍《茶館》問世之初不為人理解的情況下,第一個發表文章予以分析、稱贊。他將關漢卿《單刀會》與莫里哀《達爾杜弗》、埃斯庫羅斯《被縛的普羅米修斯》進行比較,極力稱贊《單刀會》的技巧。司馬長風在《中國新文學史》中對李健吾的評價是:“30年代的中國,有五大文藝批評家,他們是周作人、朱光潛、朱自清、李長之和劉西渭(即李健吾),其中以劉西渭的成就最高。他有周作人的淵博,但更為明通;他有朱自清的溫柔敦厚,但更為圓融無礙;他有朱光潛的融匯中西,但更為圓熟;他有李長之的灑脫豁朗,但更有深度……再進一步說,沒有劉西渭,30年代的文字批評幾乎等于零。”汪曾祺常和人講起李健吾:要講文學批評的文章誰寫得好,首推李健吾先生。
李健吾更是翻譯界的一個大師級的人物。他幾乎把法國17世紀的喜劇之王莫里哀的全部文學作品翻譯成中文,把法國19世紀的小說巨匠福樓拜的全部小說翻譯成中文,而且還翻譯了世界文學中很多名著。曾經有個小故事講道,1953年冬,多位蘇聯戲劇專家來北京和上海的戲劇學院講學,并主持師資進修班或講習班,幫助培養專業人才。在一次中央戲劇學院安排教學課程時,一位蘇聯專家說:“你們中國沒一個人懂得莫里哀和莎士比亞。”時任中央戲劇學院院長的歐陽予倩當即回答:“中國有個李健吾,他可以講莫里哀。”
李健吾對福樓拜的研究,至今國內無人能出其右。1931年至1933年留法期間,李健吾決定以法國現實主義文學大師福樓拜為研究對象,搜集有關材料,回國后為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董事會編輯委員會撰寫《福樓拜評傳》,并翻譯福樓拜的小說。1934年,長篇論文《包法利夫人》(系《福樓拜評傳》中的一章)發表后,引起鄭振鐸的關注,成為日后邀他去暨南大學任教的主要原因。林徽因也予以了關注,她給李健吾寫了一封長信,約他到家中敘談。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李健吾主要從事法國文學研究和翻譯,事實上成為新中國法國文學研究領域的開創者和領軍者。由他翻譯的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和《莫里哀喜劇全集》等,成為法國文學翻譯的典范之作。其翻譯成就堪與傅雷并駕齊驅。在外國文學中文譯品的博大海洋中,法國作品的大部分都是出自李健吾的譯筆,而不是出自傅雷。比如說: 雨果的一個不太起眼的劇本《寶劍》,也是李健吾譯的。他的譯筆還跨過法蘭西國界,涉獵其他國家的作品,比如蘇俄的作品,其勞績之巨,其聲勢之浩大,實較傅雷有過之而無不及。當時李健吾的世界文化視野要比傅雷大,對外國文學作品、文化學術堅實內涵的敏感度也勝于傅雷,顯示出他是研究型的翻譯家,而不是一個單純的翻譯者。錢鐘書最推崇“化派”式翻譯。所謂“化派”是一種文字的作品化為另一種文字的作品,而不是直譯或硬譯。就翻譯的技藝而言,傅、李兩位都是“化派”。這個化派如果還有誰的話,那就是譯了《吉爾·布拉斯》與《小癩子》的楊絳。李健吾所譯的《包法利夫人》與《莫里哀全集》都將原作的原汁原味化進了中文譯作,和傅雷所譯的《巴爾扎克作品集》、楊絳所譯的《吉爾·布拉斯》,實為中國翻譯的主流譯作,是他們構成了中國兩三個世紀以來譯壇的主流。李健吾不僅譯得多,而且譯得好。他的譯文,文筆流暢,雅俗共賞,在傳達莫里哀與福樓拜的真髓與神貌上,可謂翻譯中的極品。晚年,李健吾不顧體弱多病,在去世前一年譯完了莫里哀27部喜劇,實現心愿。
黃金般的赤子之心
“那時候我的親友都斷了來往,他的處境也危在旦夕,他竟不怕風險,特意拉我一把。黃金般的心啊!人能做到這一步是不容易的啊! ”2016年7月12日,在紀念李健吾誕辰110周年暨《李健吾文集》出版研討會上,汝龍之子汝企和念了一封父親寫給巴金的信,信中追憶“文化大革命”時期李健吾冒險送錢給他父親的事。

那時,汝龍處境不堪,李健吾伸出援手,送去200元錢,汝龍不要,李健吾放下后默默地轉身走了,他的身影長久銘刻在汝龍心中。巴金遭到批判,許多人唯恐避之不及,李健吾卻與巴金愈發親近,派女兒送去300元錢。多年之后,疾病纏身的巴金常常念叨李健吾,“他那黃金般的心,是不會從人間消失的。”在沈從文潦倒的日子里,李健吾曾去他家里看望。李健吾與妻子都很喜歡被打成右派的吳祖光,因為他為人正直,敢說真話。
對朋友、學生如此,對師長,李健吾更是竭盡所能幫助。王文顯是李健吾在清華大學讀書時的西洋文學系主任,畢業后因賞識李健吾的才華,讓他留校當了助教。抗戰時期流落上海的王文顯生活拮據,李健吾把老師的英文劇《北京政變》譯成中文,交由洪謨導演,劇名《夢里京華》,每星期去劇場收6%的上演稅,全部轉交給王文顯。當時身在內地的朱自清也將家眷托付給他,李健吾常去探望。后來每次談起,朱夫人都感慨不已。
那時,李健吾一家生活其實也非常窘迫。為了給上海劇藝社籌錢,李健吾甚至變賣了妻子的陪嫁物。女兒李維音記得,父親常于傍晚到小菜場去撿人家賣剩下的小菜,有時因撿回小販賣剩下的臭魚而高興得在媽媽面前歡呼。李健吾總是樂呵呵的,經常到小弄堂里和孩子們打鬧著玩兒,逗得他們開心地笑。他的樂觀開朗還表現在他的職業中:他癡迷莫里哀,給學生講課,他會連說帶演,有時候,他先樂得趴到了桌子底下,入了迷的學生一下就看不見老師了!
李健吾是讀著文天祥的歷史長大、講究氣節的中國書生。1945年3月,李健吾在自己改編的《金小玉》里客串角色,演出轟動了整個上海,招來了日本憲兵隊。4月19日晚,李健吾被敵人逮捕。他們用灌水等殘酷刑罰,企圖獲得進步作家鄭振鐸等在上海的住址,李健吾只字未露。在受死亡威脅的時候他對憲兵說:“告訴我的孩子們,他們的爸爸是個好人。”上海全面淪陷之初,周作人邀請他來北大當主任,李健吾毫不猶豫地拒絕了。
李健吾為人的真誠、熾熱、大氣以及對后輩的呵護也令人欽佩。柳鳴九主編的《法國文學史》(上卷)于1979年得以出版時,最先得到李健吾的“雀躍歡呼”。李健吾熱情洋溢地說:“作者為中國人在法國文學史上創出了一條路。老邁如我之流,體力已衰,自恨光陰虛度,無能為力,而他們大膽心細,把這份重擔挑起來,我又怎能不為之雀躍者再?”
1982年,李健吾去西安出席外國文學學會理事會議時,看望臥病在床的大學同學唐得源教授,還照了相,可在到達成都后,卻發現底片曝光了。旅途勞累,患了感冒,他只得提前回京。返回途中路過西安時,李健吾再訪老同學,專程補拍。回來后他一邊喘氣、咳嗽,一邊還趴在桌前給朋友寫信。心臟病加上旅行勞累,十天后李健吾不幸離開了人世。仁者天壽,無病而終,堪稱圓寂。
2008年,鹽湖區博物館設立李健吾紀念館,展示先生文學成就與生平事跡,瞻仰紀念李健吾先生的精神家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