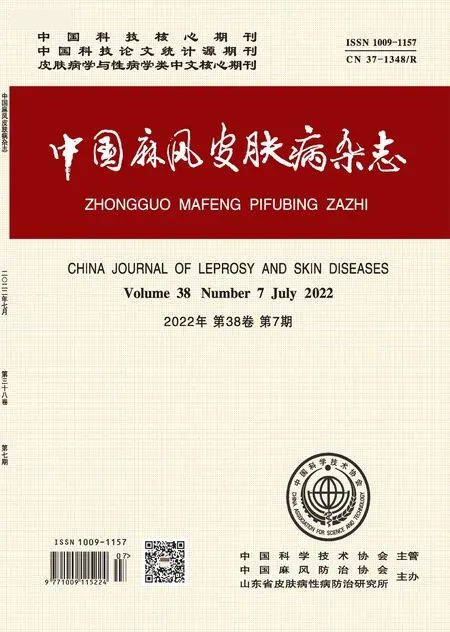銀屑病停用TNF-α拮抗劑后誘發紅皮病一例
張 帆 呂 晨 孫勇虎 張福仁
山東第一醫科大學附屬皮膚病醫院(山東省皮膚病醫院),山東省皮膚病性病防治研究所,濟南,250022
臨床資料患者,男,31歲。因“全身鱗屑性斑塊5年,加重2周”就診。患者5年前無明顯誘因全身出現鱗屑性斑塊,被當地醫院診斷為“尋常型銀屑病”,給予光療、藥浴、口服中藥等多種治療,有效,但仍反復發作。患者于11個月前開始按照標準劑量接受腫瘤壞死因子拮抗劑治療,效果佳,皮損基本消退。3個月前全身再次出現散在鱗屑性斑塊,給予甲氨蝶呤(15 mg,1次/周)聯合TNF-a拮抗劑治療,皮損仍未完全消退(圖1)。2周前,患者要求更換生物制劑,遂停用TNF-α拮抗劑及甲氨蝶呤,在等待生物制劑用藥前相關實驗室檢查結果過程中,無明顯誘因原皮損加重,逐漸出現泛發全身的鱗屑性斑塊,伴輕度發熱。體格檢查:體溫37.1℃。皮膚科查體:全身泛發鱗屑性紅斑、斑塊,融合成片,上覆銀白色鱗屑,Aus-pitz征陽性,BSA>70%,PASI:36.2分(圖2)。實驗室檢查:患者生物制劑治療過程中定期監測血常規、肝腎功能、TB-IGRA以及乙肝、丙肝、梅毒、艾滋等感染性抗體均未見異常。TNF-α拮抗劑停用前查免疫細胞因子:TNF-α 0.03 pg/mL(正常值≤16.5 pg/mL)、IFN-γ 0.06 pg/mL(正常值≤23.1 pg/mL)。診斷:紅皮病型銀屑病。治療:單一應用IL-17A拮抗劑治療(按藥物說明書推薦用法用量進行治療:每次300 mg,分別在第 0、1、2、3、4 周進行皮下注射初始給藥,隨后維持該劑量每4周給藥一次)。患者經IL-17A拮抗劑治療2周后效果明顯,皮損大部分消退(圖3)。目前已經治療1個月余,仍在隨訪中。

圖1 患者停用TNF-α拮抗劑前,軀干四肢散在紅斑、斑片、覆白色鱗屑

圖2 停用TNF-α拮抗劑2周后,患者軀干和上肢彌漫性紅斑,融合成片,境界不清,上覆白色鱗屑,下肢散在紅斑、斑塊,表面白色厚鱗屑,皮損面積>70%

圖3 患者經IL-17A拮抗劑治療2周后,原有紅斑基本消退,僅少許脫屑
討論生物制劑越來越多的應用于銀屑病的治療,銀屑病患者的生活質量得到了極大的改善[1,2],但隨之而來的一系列問題,如生物制劑的合理選擇、療效衰減、抗藥抗體或不良反應等尚缺乏相關大規模臨床或機制研究。其中,銀屑病患者治療過程中不明原因的復發或加重是重要問題之一。已有多篇文獻報道了TNF-α拮抗劑可以誘發或加重原有的銀屑病皮損,這一現象也被稱為“反常銀屑病”[3-5]。關于TNF-α拮抗劑誘發銀屑病病例報道相對較多,在一篇TNF-α拮抗劑治療207例患者的綜述中,高達85%的患者都出現了新發銀屑病,其中男女比例大約為2∶1,平均發病年齡為44.9歲(13~79歲)。發病的潛伏期差異很大,平均10.5個月。其中,銀屑病皮損最常見類型是膿皰型(52%),其次是斑塊型(49%),點狀損害占19%[6]。既往關于原有銀屑病發生惡化的病例報道相對較少,Collamer等[6]回顧的207例患者中15%出現了原有銀屑病皮損惡化,最常涉及的藥物是依那西普(62%),其次是英夫利昔單抗(23%)和阿達木單抗(15%)。M?ssner等[7]發表了5例患者在使用英夫利昔單抗治療斑塊型銀屑病期間或之后出現掌跖膿皰病,其中3例伴隨原有斑塊加重。Santos-Juanes等[8]報道了兩例中重度斑塊型銀屑病患者在依那西普治療期間出現了紅皮病,改用烏司奴單抗后皮損消退。本例患者在規律應用TNF-α拮抗劑治療8個月后全身再次出現鱗屑性紅斑、斑塊,停用2周后皮損發展為紅皮病型。潛伏期和年齡都符合先前的研究。
患者在治療前未曾發生過紅皮病,無感染或創傷等環境因素的改變。患者曾于最后一次注射TNF-α拮抗劑時聯合應用甲氨蝶呤15 mg每周一次。TNF-α拮抗劑治療效果不佳或發生惡化時,結合傳統療法可以改善病情[9]。雖有甲氨蝶呤治療銀屑病或類風濕性關節炎期間發生重癥藥物不良反應的報道[10],但本例患者在與TNF-α拮抗劑聯合治療2周內未發生任何不適,因此不考慮聯合應用甲氨蝶呤導致紅皮病的發生。我們分析,患者在TNF-α拮抗劑治療8個月后,治療反應逐漸消失。并在突然停止TNF-α拮抗劑治療后出現了銀屑病的復發和加重。
生物制劑治療銀屑病復發或加重的原因可總結為炎癥因子水平的紊亂和抗藥抗體的產生。有研究認為,漿細胞樣樹突狀細胞可能對銀屑病的復發或加重起一定作用。腫瘤壞死因子的阻斷可能允許漿細胞樣樹突狀細胞產生干擾素γ,從而使T細胞遷移到皮膚并發生銀屑病樣反應[11]。另一種假設認為,TNF-α被抑制后導致輔助性T細胞17(Th17)的增強和Treg細胞下調,隨后Th17細胞因子IL-22的產生增加,IL-22作用于角質形成細胞,形成促炎循環[12]。抗TNF-α拮抗劑抗體的產生被認為是產生耐藥的原因。Svenson等[13]在接受英夫利昔單抗治療的類風濕關節炎患者中發現了特異性的抗英夫利昔單抗抗體,并監測到與英夫利昔單抗的結合。本例患者治療過程中臨床反應逐漸消失,可能與體內產生抗體有關,由于價格昂貴,我們未曾對患者進行檢測。給予IL-17A拮抗劑后患者病情得到迅速控制,且患者血清中TNF-α以及IFN-γ在皮損加重時處于較低濃度,我們推測短暫停藥后誘發紅皮病現象可能與體內Th17細胞的產生增加有關。
對于TNF-α拮抗劑引起的銀屑病的處理,Collamer等[6]建議在病變超過5%的體表面積時,停止抗腫瘤壞死因子治療,并使用皮質類固醇和維生素D類似物進行局部治療。如果在2~3周內沒有明顯緩解,應考慮加用光療和甲氨蝶呤等全身治療。Navarro等[14]建議收集患者詳細病史,實驗室檢查及組織病理等,以排除其他皮膚病和類似銀屑病的皮疹,并提及對于嚴重類型如紅皮病型銀屑病,直接選擇替代治療,更換生物制劑的種類。
本例患者應用TNF-α拮抗劑規律治療8個月后,病情出現反復,逐漸加重,在短暫停用TNF-α拮抗劑后出現紅皮病。盡管生物制劑的安全性和有效率比傳統藥物高得多,但仍有耐藥或病情加重的情況出現,應對接受生物制劑治療的銀屑病患者密切隨訪,指導其治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