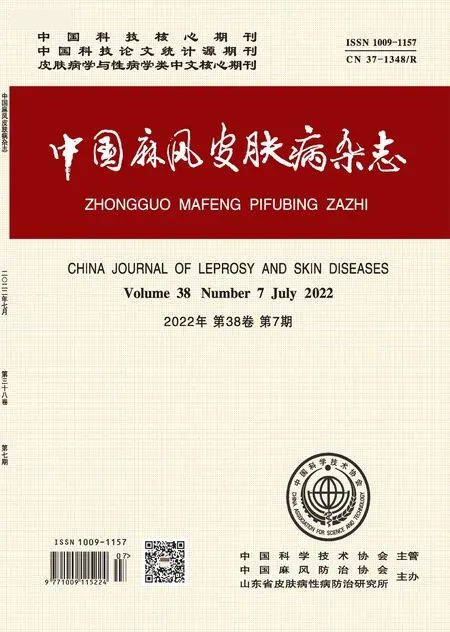麻風免疫診斷標記物研究進展
彭嘉怡 王洪生 余美文
中國醫學科學院皮膚病醫院,南京,210042
麻風是由麻風分枝桿菌(Mycobacteriumleprae, ML)引起的慢性傳染性疾病,主要侵犯皮膚、黏膜及周圍神經,若未及時診斷及治療,可導致畸殘。目前麻風免疫診斷主要包括血清抗體、細胞因子水平檢測。microRNA參與麻風分枝桿菌感染機體的免疫微環境,調節細胞因子分泌。其表達水平亦具有診斷價值。免疫標記物的具體臨床應用及何種抗原及檢測方法的敏感性和特異性更佳,一直是研究焦點。本文對血清學試驗相關抗原、實驗方法及臨床應用、細胞因子及miRNA生物標記物近年來的研究進展進行綜述,為后續有助于早期診斷麻風的研究提供參考。
1 血清學試驗
1.1 血清學抗原
1.1.1 ML基因組詮釋前 1981年首次發現酚糖酯抗原(PGL-1)有助于區分麻風分枝桿菌與其它分枝桿菌[1]。隨后,Fujiwara等[2]以PGL-1為底物,通過苯丙酰基(Phenolic)或辛基(Octyl)將酚糖酯抗原的天然二糖(Natural Disaccharide)或三糖(Trisaccharide)結構連接到小牛血清蛋白(BSA)或人血清蛋白(HSA),形成如NDO-BSA、NT-O-BSA等半合成糖蛋白抗原,發現其具有更強的免疫原性。起初,臨床上主要使用酶聯免疫吸附試驗(ELISA)檢測抗PGL-1抗體。蘸棒試驗(dipstick assay)更為簡便,其檢測結果與ELISA高度一致,為97.2%,兩者的血清陽性率亦無統計學差異[3]。2003年,一種新的橫向流測試驗(Lateral Flow test)問世,與ELISA結果的一致性為91%,診斷多菌型麻風的敏感性及特異性為97.4%及90.2%[4]。Van Hooij等[5]發現上轉換發光技術側流免疫夾心法(UCP-LFA)的MB總體檢出率及敏感性較金側流免疫夾心法(GOLD-LFA)高。PGL-1仍是目前應用最為廣泛的血清學抗原,血清學檢測相對無創,側流試驗等檢測方法更是簡便快捷,適用于現場開展,但尚不能有效取代皮膚活檢。
1.1.2 ML基因組詮釋后 2001年,Whitehead等[6]闡明了麻風分枝桿菌的基因組序列特征,發現麻風分枝桿菌基因組中僅有1604個(<50%)可編碼蛋白的功能性基因。隨著基因組時代的到來,在MB患者血清中發現越來越多重組蛋白誘導產生的特異性抗體。
目前較為廣泛應用的重組蛋白為Leprosy IDRI Diagnostic(LID-1),由麻風分枝桿菌抗原ML0405及ML2331融合形成,在癥狀尚未出現前6~8個月即可檢測到其抗體,因此其可早期診斷麻風[7]。亦有研究發現聯合化療后血清抗LID-1抗體水平顯著下降,因此LID-1亦可用于療效評估[8]。Duthie等[9]研發了基于NDO-BSA及LID-1的融合蛋白NDO-LID的側流層析法。與PGL-1相比,NDO-LID的MB和PB患者檢出率及診斷特異性更高,檢出率分別為87%和81.7%,特異性為97.4%。Chen等[10]的研究發現NDO-LID快速試驗敏感性高,而ELISA法特異性較高,治療前后NDO-LID抗體水平的差異表明其可輔助評估聯合化療效果。雖然NDO-LID已被證實在MB患者中有較高的血清學陽性率,Gomes等[11]發現女性、非棕色皮膚、生活在城鎮及和超過5個人同居均會影響抗NDO-LID抗體陽性率。但由于納入研究的樣本量小,仍需擴大樣本及在不同地區及人群中驗證上述因素與NDO-LID抗體陽性率的相關性。
1.2 血清學試驗的臨床應用 血清學檢測主要應用于麻風診斷、預測麻風反應、評估聯合化療效果、監測普通人群及家庭內接觸者。
1.2.1 用于麻風診斷 目前血清學試驗已廣泛應用于診斷麻風患者。Chen等[10]在我國云南麻風高發區對83例麻風患者及161名非麻風對照組人群的研究中發現,NDO-LID快速試驗及LID-1、NDO-LID及NDO-BSA的ELISA在MB患者中的陽性應答率均高于PB患者。其中NDO-LID快速實驗的MB患者陽性應答率最高,為94.7%,敏感性較ELISA高而特異性較低。Mar?al等[12]亦發現MB患者中抗NDO-HSA的IgM抗體、抗LID-1的IgG抗體及抗NDO-LID的IgG/M抗體滴度顯著增加,其中LID-1和NDO-LID的IgG1亞型血清學試驗的診斷性能較佳。Wang等[13]發現瘤型麻風(LL)患者NDO-BSA、主要膜蛋白II(Major membrane protein II,MMP-II)及LID-1血清陽性率分別為78.7%、59.3%及71.7%。三種抗原兩兩組合的血清學試驗中,NDO-BSA和LID-1的血清陽性率最高,為86.3%,表明多抗原聯合的血清學試驗可應用于麻風早期診斷及監測。重組抗原可提高血清學診斷的敏感性及特異性,尚需進一步研發新的具有較高敏感性及特異性的重組蛋白。
1.2.2 預測麻風反應 麻風反應分為I型麻風反應,即逆向反應(RR)和II型麻風反應,即麻風性結節性紅斑(ENL)。Hungria等[14]對452例無麻風反應的麻風患者進行研究,并用ELISA檢測其抗PGL-1、抗LID-1及抗ND-O-LID的IgM和IgG抗體滴度。其中36%患者在隨訪期間發生麻風反應,26%的患者發生RR和10%的患有ENL。盡管其抗PGL-1抗體水平較無麻風反應的高,PGL-1血清學試驗預測RR價值有限。而LID-1血清學試驗可預測查菌陽性患者ENL的發生。Serrano-Coll等[15]研究納入麻風反應患者及非麻風反應患者各40例,檢測其血清中抗NDO-LID的IgG及IgM抗體,結果顯示有麻風反應的患者抗NDO-LID的IgM及IgG抗體陽性率分別為52.5%及60%,均高于無麻風反應患者。因此,抗NDO-LID抗體可輔助預測麻風反應的發生。Devides等[16]納入224例麻風患者,其中61例患有RR及12例患有ENL,隨訪5年期間有29例患者發生麻風反應。檢測其抗PGL-1及抗NDO-LID-1抗體水平,發現非麻風反應患者抗PGL-1及抗NDO-LID抗體陽性率分別為19.2%及32.4%,RR患者的PGL-1及NDO-LID-1抗體陽性率分別為27.8%和50.8%,而ENL患者的PGL-1和NDO-LID-1抗體陽性率為66.6%和91.6%。本研究提示抗PGL-1及抗NDO-LID-1血清學試驗有助診斷ENL,而NDO-LID-1的價值更佳。Duthie等[17]發現ENL患者抗NDO-LID抗體陽性率高于無麻風反應及RR患者。盡管較高的初始NDO-LID抗體水平是ENL發生的危險因素,但NDO-LID的快速檢測方法及ELISA法均不能有效預測麻風反應發生的時間。
1.2.3 評估療效 Hungria等[18]納入263例MB患者,其中142例MB患者給予6個月聯合化療,另外121例給予12個月聯合化療,結果顯示兩組麻風患者治療期間及治療后抗PGL-1及抗NDO-LID抗體水平均下降,表明麻風特異性血清抗體滴度可反映聯合化療效果。
1.2.4 監測家庭接觸者(HHCs) HHCs患麻風風險顯著高于普通人群[13]。Do Carmo Gon?alves等[19]納入64名家庭內密切接觸者及1623名家庭周圍接觸者,發現家庭內密切接觸者NDO-LID血清學陽性率為3.7%,高于家庭周圍接觸者。此外,家庭內接觸者麻風患病率亦顯著高于家庭周圍接觸者。血清學陽性提示密切接觸人群有較高患病風險。然而,Richardus等[20]檢測隨訪期間25例患麻風及199名未患麻風的接觸者的抗PGL-1抗體水平,結果提示兩組間抗體水平無顯著性差異。此外,麻風患者接觸者患麻風前后的抗PGL-1抗體水平無顯著性差異,因此,PGL-1血清學試驗并不能準確預測麻風患者接觸者的發病。
2 細胞因子
2.1 Th細胞亞群相關細胞因子 麻風感染相關細胞因子主要為白細胞介素(IL)、γ干擾素(IFN-γ)、腫瘤壞死因子(TNF)、轉化生長因子(TGF),參與麻風免疫病理機制。麻風相關細胞因子的表達由輔助性T細胞介導,包括Th1、Th2、Treg、Th17、Th9等。IFN-γ主要由Th1細胞表達,在結核型麻風患者中占主導。一項納入了38例MB及23例PB麻風患者的研究中,PB患者外周血中IFN-γ陽性應答率高于MB患者,推斷IFN-γ可用于鑒別PB和MB[10]。Th2細胞誘導產生IL-4、IL-5、IL-6、IL-10及TGF-β等細胞因子,主要參與瘤型麻風的發病機制。Mar?al等[21]納入19例患者誘導其外周血單核細胞(PBMC)分化并檢測分泌IFN-γ、IL-4及IL-10的細胞亞群數。在MB患者中,Th細胞主要為介導IL-10及IL-4產生的Th2細胞亞群,而IFN-γ表達微弱。調節性T細胞(Treg)分泌TGF-β及IL-10。Treg可通過介導TGF-β表達下調T細胞反應導致瘤型麻風的免疫應答無能。與結核型麻風(TT)患者相比,瘤型麻風(LL)患者皮損及PBMC中TGF-β及IL-10表達水平升高。此外,瘤型麻風患者中體外誘導產生的Treg細胞數較結核型麻風患者高。此前研究發現Th17細胞亦參與麻風感染[22]。IL-17由Th17分泌,在瘤型麻風患者皮損中高表達。Santos等[23]納入28例MB及PB患者檢測其皮損、血清中IL-17A表達水平,并用流式細胞術分析表達IL-17A的細胞表型,發現TT患者皮損中表達IL-17A的CD4+T細胞多于LL患者,PB患者血清中的IL-17A濃度較MB患者高。
2.2 細胞因子檢測的臨床應用 與血清學試驗相似,因其差異性表達,細胞因子檢測亦可應用于麻風分型、預測麻風反應、監測療效及家庭內接觸者。
2.2.1 麻風分型及預測麻風反應 不同的Th細胞亞群共同參與麻風的免疫病理機制,決定了麻風感染的臨床表型。一項綜合分析多個細胞因子表達的研究中,Azevedo等[24]用實時定量聚合酶鏈式反應(qPCR)檢測87例麻風患者皮損Th1、Th2、Th17及Tregs譜相關細胞因子表達,ELISA檢測其在血清中表達水平。Th1相關靶標(mRNA)在結核樣型和界限類偏結核型麻風患者中占主導,而Th2和Tregs靶向物在瘤型和界限類偏瘤型麻風患者中占主導。麻風患者血清中IL-22、IL-6、IL-10表達較對照組高,LL中的IL-10較高。RR中,Treg相關細胞因子表達水平下降,而IL-15增加。ENL中,IL-17F及IL-8表達增加。亦有研究發現伴神經痛的麻風神經病變患者中IL-1β、TNF、TGF-β和IL-17水平較高,IL-1β水平是與麻風神經病變患者合并神經痛相關的獨立變量,可成為隨訪的重要生物標記物[25]。
2.2.2 監測療效 Cassirer-Costa等[26]用微量樣本多指標流式蛋白定量技術(CBA)檢測10例結核型麻風及14例瘤型麻風患者聯合化療前后血液中IL-1β、IL-8、TNF、IL-12p70、IFN-γ、IL-17A、IL-13及IL-10水平。其中,瘤型麻風患者治療前炎性細胞因子表達水平較高,而結核樣型麻風患者治療前炎癥細胞因子及調節性細胞因子維持平衡。細胞因子網絡證實,聯合化療改變了麻風患者尤其是結核樣型麻風患者血清細胞因子的分布特征,瘤型麻風患者細胞因子體系特征為炎癥/調節分子的強連接軸。因此,細胞因子可作為評估聯合化療效果的生物標記物。Negera等[27]納入30例ENL患者比較激素治療前后炎癥細胞因子及調節性細胞因子的表達。治療前的ENL患者TNF、IFN-γ、IL-1β及IL-17A水平顯著增高。IL-10在治療前顯著降低,而在治療后顯著升高。ENL患者TNF、IFN-γ、IL-1β及IL-17A、IL-6的mRNA表達治療后顯著降低。而皮損及血清中的IL-10及TGF-β的mRNA表達水平在治療后均顯著降低。該研究表明,激素可通過直接或間接抑制炎癥細胞因子表達相關的免疫細胞調節促炎細胞因子的產生。
2.2.3 監測HHCs Queiroz等[28]納入18例PB麻風患者、58例MB麻風患者及112名家庭接觸者,檢測其外周血中的細胞因子和趨化因子,發現隨訪期間趨化因子2(CCL-2)在HHCs及PB麻風患者中表達較高。此外,CCL-2及IFN-γ呈負相關。因此,CCL-2及IFN-γ可能成為識別HHC亞臨床感染的潛在生物標記物。
3 microRNA
3.1 microRNA參與麻風發病機制 microRNAs(miRNAs)是非編碼RNA,部分miRNAs僅在麻風中表達,從轉錄層面調節免疫反應,在麻風發病機制中發揮重要作用[29,30]。Salgado等[30]通過比較28例麻風患者miRNAs在皮損及血液中的差異化表達發現miRNAs標記物參與調節結核樣型麻風患者中的防御性免疫反應及瘤型麻風患者中的免疫抑制性反應。此外,miRNA在麻風感染中免疫系統調控、細胞凋亡、施旺細胞脫髓鞘、上皮-間充質轉化及神經痛中發揮作用。Liu等[29]發現13種miRNAs在瘤型麻風及結核樣型麻風患者中表達存在差異。其中,瘤型麻風患者皮損中差異最顯著的hsa-mir-21在麻風菌刺激的單核巨噬細胞中表達上調。其通過直接下調Toll樣受體2/1(TLR2/1)介導的25-羥基維生素D-1α-羥化酶(CYP27B1)及IL-1B表達及間接下調IL-10抑制VitD依賴的抗菌肽CAMP及DEFB4AmRNA的表達。
3.2 microRNA臨床應用 與血清學抗體、細胞因子不同,microRNA在麻風臨床應用較少,僅有少量研究表明部分microRNA可應用于麻風診斷及分型。Soares等[31]發現miRNA-21在麻風及麻風反應患者中表達上調。與結核樣型麻風和RR麻風患者相比,瘤型麻風和ENL麻風患者中miRNA-21表達水平更高,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推測microRNA有可能用于區分瘤型及結核樣型麻風,但尚需進一步驗證。Jorge等[32]用TaqMan低密度陣列方法(TLDA)分析瘤型麻風患者、結核型麻風患者及健康對照組的377種microRNAs的表達水平,隨后用qRT-PCR驗證16種差異表達的miRNAs,發現聯合4種miRNAs檢測,包括miR-101、miR-196b、miR-27b及miR-29c可進行麻風診斷,其敏感性及特異性分別為80%、91%。此外,其亦可用于區分瘤型麻風及結核樣型麻風患者,敏感性及特異性為83%及80%。即使單個microRNA并不具有診斷價值,若聯合其它microRNA標記物亦可用于麻風診斷及分型,但目前關于驗證microRNA診斷潛能的相關研究較少,其敏感性及特異性尚需進一步驗證。此外,目前尚未有研究探討microRNA在療效評估、HHC監測中的應用,其它非編碼RNA如lncRNA、piRNA在麻風中的表達水平、麻風發病機制中發揮的作用仍有待探究。因此,未來研究需聚焦于microRNA在麻風中的臨床應用,除microRNA外其它非編碼RNA在麻風中的表達和作用。
4 結語
綜上所述,血清學檢測、細胞因子及microRNA標記物均可應用于輔助麻風的早期診斷,同時有助于不同型別麻風的區分、預測麻風反應、評估療效及監測HHCs。但重組抗原如NDO-LID血清學試驗敏感性及特異性有待提高,細胞因子相關診斷性方法的敏感性及特異性研究較少。因此,未來需挖掘更多麻風特異性抗原、更多特異性細胞因子進行麻風診斷、某種或某些穩定表達的miRNA,以及其他非編碼RNA在皮損組織乃至血液中的試驗應用,以期尋找操作性強、普及性廣、敏感性和特異性較高的麻風免疫診斷標志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