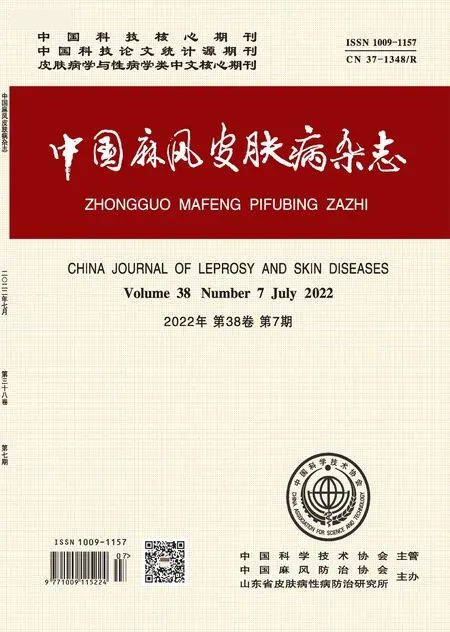間充質干細胞移植治療銀屑病研究進展
趙子葳 李俊琴 牛旭平 侯瑞霞 楊艷妮 李新華
1山西醫科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太原,030001;2山西醫科大學附屬太原市中心醫院皮膚科&免疫性皮膚病干細胞重點實驗室,太原,030009;3山西醫科大學醫院管理處,太原,030600
銀屑病(psoriasis)是一種易復發的慢性炎癥性皮膚病,它的三個組織學特征包括:表皮過度增生,真皮血管擴張及炎癥細胞浸潤[1]。遺傳學研究表明,自身免疫和炎癥反應在銀屑病中反應共存,兩者之間的平衡決定了銀屑病的臨床表現[2]。銀屑病的發病原因可概括為環境和遺傳相互作用,環境因素如創傷(Koebner現象)、藥物(如咪喹莫特)、感染(鏈球菌性咽喉炎)、吸煙及飲酒等可誘發銀屑病[3-6]。
1 銀屑病
1.1 發病機制 銀屑病是一種復雜的炎癥性皮膚病,具有遺傳易感性[7]。目前銀屑病的發病機制尚未完全闡明,多項研究證明,真皮樹突狀細胞(DC)與T細胞之間的相互作用在銀屑病發病過程中發揮重大作用,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輔助性T細胞(Th1、Th17)、NF-κB通路、IL-23/IL-17通路(IL-23、IL-12B及IL-23R)等都參與了銀屑病的發病過程及皮損處的炎癥反應[6,8]。具體過程如下:在易感因素作用下,DC活化并產生TNF和IL-23,刺激CD4+Th17和CD8+Tc17細胞活化;T細胞活化后,增殖、遷移到表皮,與自身抗原結合產生IL-22和IL-17等炎癥性細胞因子。Th17細胞因子可誘導表皮過度增殖并激活了角質形成細胞,后者又進一步產生了大量的細胞因子和趨化因子進而形成了銀屑病患者皮損處的炎癥性微環境[9,10]。
此外,在銀屑病發病過程中,DC、中性粒細胞、T細胞及角質形成細胞等相互作用維持銀屑病患者皮損處的炎癥微環境[11]。
1.2 銀屑病的免疫學特征
1.2.1 銀屑病患者皮膚中的免疫細胞 銀屑病患者皮膚中的角質形成細胞釋放抗菌肽(主要為LL37),與其他受損細胞的DNA相互結合誘導銀屑病斑塊中漿細胞樣樹突狀細胞(pDCs)分泌α-干擾素(INF-α),INF-α誘導髓系樹突狀細胞活化,與T細胞相互作用分泌大量細胞因子(IL-12、IL-6、IL-23、INF-α等),這些細胞因子通過促進角質形成細胞增殖及中性粒細胞募集激活炎癥反應[12]。然而,有研究表明,間充質干細胞(mesenchymal stem cells, MSCs)可能在銀屑病的發病過程中發揮作用[13]。
1.2.2 銀屑病患者中的間充質干細胞 MSCs是可從多種組織分離出來的、具有自我更新能力并表現出多譜系分化的基質細胞[14]。MSCs的生物學特征包括:貼壁生長;CD90、CD105、CD73、CD13及HLA-Ⅰ類分子表達陽性;CD45、CD34、CD31、CD14及HLA-Ⅱ類分子表達陰性;多向分化潛能[15,16]。
有研究發現,銀屑病患者中的MSCs在細胞因子分泌、DNA甲基化及免疫調節方面表現異常[13]。銀屑病患者中的MSCs凋亡、增殖分化及細胞因子分泌異常,導致MSCs免疫調節功能受到抑制[17]。此外,銀屑病患者中的MSCs可以刺激角質形成細胞增殖,促進角質形成細胞過度表達、異常增生、細胞周期縮短[18]。因此,MSCs在銀屑病的發病過程中發揮作用。
2 間充質干細胞的免疫調節特性
體外實驗證明,MSCs具有免疫調節特性,可以調節銀屑病患者中的免疫細胞,減輕銀屑病患者的炎癥反應,向正常的生理反應轉化。MSCs可調節樹突狀細胞、NK細胞及T淋巴細胞的細胞因子分泌,即通過抑制TNF-α及γ-干擾素(INF-γ)分泌,刺激IL-10分泌來調節免疫反應,進而影響其他免疫細胞的功能[19]。
2.1 固有免疫 在固有免疫中,髓系樹突狀細胞(mDC)在其成熟后對初始T細胞起抗原提呈作用,而骨髓間充質干細胞與DC共培養后,細胞表面的MHCⅡ類分子、CD11c、CD83和共刺激分子表達減少,IL-12表達也減少,從而削弱DC的抗原提呈功能[20]。
中性粒細胞作為抵御病毒的第一道防線,在先天免疫中發揮重要作用。在吞噬病原體后,中性粒細胞經歷自發性的細胞程序性死亡,維持細胞的動態平衡。MSCs可以影響中性粒細胞中促凋亡和抑凋亡基因(包括凋亡起始蛋白Caspase-9、Caspase-8,凋亡執行蛋白Caspase-3及抗凋亡蛋白Mcl-1)的表達水平,從而抑制中性粒細胞的凋亡,顯著延長中性粒細胞的壽命[21]。中性粒細胞在體內具有趨化運動能力和吞噬功能,在體外和MSCs共培養后發現中性粒細胞仍具有良好的趨化運動和吞噬能力,與新鮮分離的中性粒細胞相比無功能亢進作用;但中性粒細胞的活性氧(ROS)隨培養時間延長發生變化,但總體超過新鮮分離的中性粒細胞[21,22]。
2.2 適應性免疫 在適應性免疫中,T淋巴細胞具有多種生物學功能,包括釋放細胞因子、直接殺傷靶細胞、輔助或抑制B細胞產生抗體等。MSCs主要通過細胞接觸的方式抑制T細胞增殖,且呈劑量依賴性;但MSCs不會誘導T細胞凋亡,而是使受刺激的T細胞滯留在G0/G1期[23,24]。T細胞受到刺激后會分化成不同的亞型,分泌相應的細胞因子,發揮促炎、抗炎及維持免疫平衡等效應功能。Aggarwal等[25]在探究MSCs的免疫抑制作用機制時發現T細胞與人骨髓間充質干細胞(hMSCs)共培養后Th1型細胞因子INF-γ水平降低,Th2型細胞因子IL-4水平顯著增加。Mareschi等[26]得到了相同的實驗結果。這表明,MSCs可能直接與T細胞相互作用,調節Th1/Th2的平衡,抑制促炎因子的產生,促進抗炎因子的分泌。此外,MSCs還可以誘導調節性T細胞(Treg)增殖,在低氧條件下MSCs誘導Treg細胞增殖能力增強[27]。
3 臨床前研究及臨床試驗
3.1 動物實驗 MSCs的免疫調節作用和抗炎作用已經被用于治療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如系統性紅斑狼瘡、類風濕性關節炎等。Campanati等[28]將健康供者的MSCs與銀屑病患者的MSCs共培養發現,IL-6、IL-12、IL-13、IL-17A、TNF-α等炎癥因子分泌減少。由此,這為MSCs治療銀屑病提供了證據支持。因此,MSCs可用于治療銀屑病,臨床前研究多基于咪喹莫特(IMQ)誘導的小鼠模型。
Chen等[9]研究中,使用人臍帶源性間充質干細胞(hUC-MSC)輸注治療IMQ誘導的小鼠模型,結果表明輸注MSC可以減緩小鼠銀屑病的發展,紅斑、鱗屑等癥狀減輕,PASI評分下降。在本次研究中,用qRT-PCR檢測小鼠背部皮膚中炎癥因子的mRNA水平發現,IL-17、IL-23、IL-6、IL-1β等促炎細胞因子和角質形成細胞標志物S100A7、S100A8、S100A9的表達水平明顯上調,而抗炎因子IL-10的表達水平明顯下降;經MSC治療后,促炎因子和標志物的表達水平明顯降低,而IL-10顯著升高。此外,MSC輸注還會導致小鼠的中性粒細胞數量減少、功能受到抑制,抑制漿細胞樣樹突狀細胞(pDCs)分泌α-干擾素(INF-α)。王曉宇等[29]研究中,同樣用hUC-MSC輸注治療IMQ誘導的銀屑病小鼠模型,凡士林組、模型組和治療組分別外涂凡士林軟膏、5%IMQ,同時治療組靜脈注射MSC。結果表明hUC-MSC能延緩皮損的出現,并減輕皮損嚴重程度,減輕小鼠皮膚角化過度及角化不全,減少中性粒細胞及淋巴細胞浸潤;同時治療組中小鼠Th17細胞比例及TNF-α的水平明顯低于模型組。類似實驗還有很多[30,31]。
上述動物實驗中,MSCs可以緩解銀屑病小鼠的癥狀,阻止IMQ誘導的小鼠銀屑病的發展,其作用機制可能是MSCs可以抑制效應細胞的增殖和滲透入皮下,調節T細胞亞群(Th1、Th2、Tregs)的細胞因子分泌,從而導致促炎環境向抗炎環境的轉變。因此,MSCs可以作為治療銀屑病的一種新方法。
3.2 臨床試驗 目前已有研究將MSCs用于銀屑病的臨床治療。通過查找數據庫,確定了六項臨床研究,有八位銀屑病患者接受以MSCs為基礎的臨床治療。這些患者銀屑病病史最短2年,最長29年(平均14.5年),均接受過其他藥物系統或局部治療,癥狀無明顯改善。所有患者在接受MSCs移植輸注之前,均停止其他藥物治療(表1)。
Comella等[32]的病例報道中首次使用基質血管成分細胞(SVF)靜脈注射治療銀屑病患者,患者1個月后PASI評分由50.4降到0.3,12個月隨訪期內患者癥狀明顯改善,生活質量提高,且無任何不良反應。

表1 臨床試驗基本信息
Chen等[33]用臍帶間充質干細胞(UC-MSCs)治療了兩例尋常型銀屑病患者,皮損消失,且均保持四年或五年無復發。其中一例患者曾接受自體造血干細胞移植(auto-HSCT)治療彌漫性大B細胞淋巴瘤發生感染,控制感染后移植輸注UC-MSCs,淋巴瘤和銀屑病均完全緩解,并保持五年無復發,且無任何不良反應。類似地,De Jesus等[34]報道了脂肪來源的MSCs(AD-MSCs)治療兩例銀屑病患者。患者1有銀屑病關節炎,輸注MSCs后PASI評分由21.6下降到8.9,然而關節癥狀并無改善,使用依那西普和英夫利昔單抗后,關節疼痛減輕,然而兩年后感染肺結核,銀屑病和銀屑病關節炎復發。患者2在接受MSCs之前停用其他藥物,接受三劑MSCs后PASI評分由24降到8.3,但需要其他藥物配合治療,后期需要接受鈣泊三醇、抗組胺藥物等配合治療。
在最近的一項研究中,Wang等[35]報道一例19歲男性尋常型銀屑病患者接受同種異體人牙齦MSCs治療方案,經5次輸注(3×106/kg·次)后皮損完全消退,三年未復發,且無任何不良反應。Seetharaman等[36]利用間充質干細胞條件培養液(MSC-CM)局部治療一例38歲尋常型銀屑病患者,銀屑病頭皮嚴重指數(PSSI)評分由28分降到0分,生活質量得到改善,無任何不良反應。近來,Ahn等[37]報道了一例47歲男性尋常型銀屑病患者接受同種異體UC-MSCs治療方案,患者皮損消除,生活質量得到改善,未出現惡心、發熱等不良反應。
此外,還發現五項正在進行中的臨床試驗(NCT03765957、NCT03392311、NCT03265613、NCT04275024、NCT02918123),MSCs輸注類型為AD-MSCs或hUCB-MSCs;輸注劑量無確定標準,最小劑量為5×105/kg每次,最大劑量為2×108/kg每次;輸注頻率無特定標準;輸注方式為靜脈輸注,其中一項(NCT02918123)為皮下注射。
MSCs治療銀屑病的臨床療效可能優于傳統的治療方法,在所有病例報道中,以MSCs移植輸注治療為基礎的治療方案有效率為100%,均無任何嚴重不良反應,且七位銀屑病患者只有兩位復發。但是,由于未進行大規模臨床試驗,MSCs的輸注方式、輸注劑量及輸注頻率都不確定,需要進一步擴大樣本量進行研究。此外,還應考慮間充質干細胞輸注類型及同種異體/自體間充質干細胞,延長隨訪時間,以免發生不良反應。
4 小結
在炎性細胞因子作用下,MSCs對固有免疫和獲得性免疫都會產生影響,并且遷移到炎癥部位調節局部炎癥反應。有研究為MSCs治療銀屑病提供了理論證據支持[18]。
基于此,研究者首先進行了以咪喹莫特誘導的小鼠模型為基礎的動物實驗,發現MSCs治療的銀屑病小鼠皮損恢復較快,且無復發,證明了MSCs治療銀屑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但是,目前MSCs作為銀屑病的一種治療方法在臨床上應用較少,且使用的細胞類型、給藥方法及劑量存在很大差別,無法確定一個統一的標準化治療方法。
盡管在上述幾例病例報道中,MSCs用于治療銀屑病都取得了不錯的研究進展,但也應該注意到MSCs治療存在潛在風險,例如誘發感染、促進腫瘤細胞增殖等,如纖維肉瘤、淋巴瘤、黑色素瘤等[38,39]。因此,在大規模將MSCs輸注作為銀屑病的治療方法之前,還要進行大規模的前瞻性隊列研究,對患者進行隨訪觀察,記錄治療效果及不良反應,確定標準化治療方法或者根據患者類型制定治療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