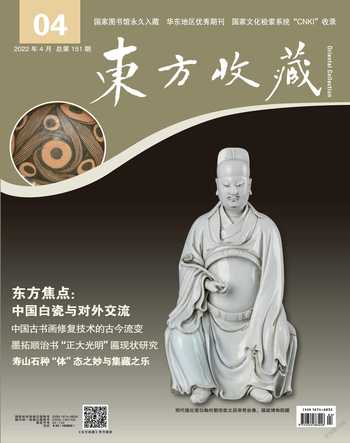魏晉南北朝繪畫藝術和人文歷史的“人文自覺”關系探究


摘要:繪畫藝術作為一個常見卻又意義復雜的術語,在歷史變革中歷久彌新,其內涵從最初的含糊混雜發展到如今,說法雖變,但萬變不離其宗。其獨立于藝術的“人文自覺”在文人化的魏晉南北朝時代得以覺醒和發展,其間蘊含的文明演化和個體意識的覺醒是與歷史文化共同作用的結果。本文以魏晉南北朝繪畫的代表作品《竹林七賢與榮啟期》及其作者陸探微為例進行分析,追根溯源并考察其發展流變的特點,以論述繪畫藝術和人文歷史的人文自覺。
關鍵詞:人文自覺;魏晉南北朝;陸探微;竹林七賢圖
一、歷史背景分析
魏晉南北朝在我國歷史上以政權交替最為頻繁、軍閥割據、戰亂動蕩讓人印象深刻。在其綿延幾百年的時間里,雜糅、滲透各種思想文化、民俗宗教,推動繪畫藝術的轉折發展。此時期的文人墨客、卿相士大夫開始展開對精神世界更高層次的追求,從而促進大批思想家和藝術家的誕生。
同時玄學和佛道興盛,在繪畫界的影響主要表現為書畫家們自我意識的能動覺醒和文化自覺的趨向成熟。這個時代的書畫藝術在 “神形”和“人文”的領域有著不斷深入的探索,這也皆受人文主義的自覺和批判理性的成熟兩方面影響。再者,結合東漢末年宦官專權、三國并立政治動蕩,正統飄零禮崩樂壞、晉分十六國的政治因素,開創了一個中國歷史上罕見的俯仰皆名士的傳奇時代。
其間被《世說新語》解釋為最能代表魏晉風度的名士集團代表“竹林七賢”由此誕生,他們隱退山林、崇尚老莊、放蕩形骸以求自娛,雖此也非其本意。例如晉書《阮籍傳》中所言:“籍本有濟世之志”,但對政治皇權旁落、禮崩樂壞、軍閥割據、家國破碎的失望,“遂酣飲為常”,并由此開始了一大批文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潮風向。
“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愿畢矣”,藝術則是其中一個極為重要的構成。而繪畫藝術則走向新的轉折,人物畫更是走向歷史巔峰,形神論審美開始進入人們的視野,繪畫藝術的本質探討和“人的覺醒”與“文的自覺” 的感性認知聯系起來。而在此之前,總的來說缺乏自覺意義上的繪畫藝術創作及藝術家。
二、竹林七賢與榮啟期壁畫分析
“竹林七賢”作為公認的文學意象,早在西晉時期就已確立,并且在不斷的歷史洪流中被不斷解構重讀。由單純的歷史人物群像不斷演變成更具普世價值的意義存在,最終取得文化符號和被推崇的文化基因“典范性”地位。這一文化符號影響力跨度廣泛且歷久彌新,在文學、哲學記載中被抽離出來,并以繪畫藝術的形式廣泛流傳于中國美術史中,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尤為突出。
在西晉左將軍陰澹《魏紀》中言:“譙郡嵇康,與阮籍、阮咸、山濤、向秀、王戎、劉伶友善,號竹林七賢,皆豪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東晉的袁宏和戴逵所著的《竹林名士傳》與《竹林七賢論》中記載:“是時竹林諸賢之風雖高,而禮教尚峻。迨元康中,遂至放蕩越禮。樂廣譏之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至于此!’樂令之言有旨哉!謂彼非玄心,徒利其縱恣而已。”由此可推論,七賢作為一個時代的名士代表集團,所代表的是對抗時代洪流的人生態度和風骨:不受世俗禮儀教條的束縛、超脫自然、崇尚本我,尋找心中曠達,而退隱山林、放蕩形骸、縱恣肆意則是他們的護身符和外在表達。
同時由于當時的禮崩樂壞,世人由重儒重新回到尊黃老之學,以“賢人”來品評世人名家是尤為被推崇的。此“賢人”摒棄儒家的“仁義道德”的品性之論,而是將才、智、識、情等多重品格能力匯于一處。故竹林七名士受到時人推崇,不僅在于其道德風骨,更有其報國可成功業的才情、智識。
通過圖片可觀察到圖文排列的互動模式和單景系列構圖方法的運用。文字與圖像重復有秩序規律地縱深一字排開,交替橫向發展的繪畫藝術構圖設計是古老的藝術技法的傳承和變革,漢代發展魏晉盛行,表達了同一系列主題的發展過程或相互關聯。
阮籍在顏延之的筆下,一句“長嘯若懷人,越禮自驚眾。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摘取了他生平最突出的兩大事件“蘇門長嘯”和“窮途而哭”,他的不拘禮法令人驚異,他的憂時憫亂令人哀思;嵇康“立俗迕流議,尋山洽隱淪。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他桀驁不馴地抨擊黑暗政治,非湯武而薄周孔,逆流而上與世俗相背;劉伶在宋代文人錢選的筆下則是“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宴。頌酒雖短章,深衷自此見”,放蕩形骸,以文控世;阮咸“仲容青云器,實稟生民秀。達音何用深,識微在金奏”,神解音律,放縱越禮;向秀“交呂既鴻軒,攀嵇亦鳳舉。流連河里游,惻愴山陽賦”,探道聞玄,著書立作,逍遙新義與儒道的相融也為后世所稱道。
阮籍長嘯、嵇康隱淪、劉伶頌酒、阮咸識微、向秀探道,這些描寫在抓住人物個性品質的同時,也在彰顯他們的精神意志風貌,在畫中與人物舉止動態、道具服飾等完美契合,例如阮籍右手一指口中長嘯,嵇康身姿挺拔、面容姣好、一股超然曠達的氣質。圖文相匹配的程度之高,足以證明當時世人對七賢的認知已經成型,同時繪畫藝術表現手法也自成體系。
由此可見《竹林七賢與榮啟期》卷軸畫的基本繪圖模式,以樹木人物相互交錯重復出現,在人物形象的藝術處理上多以“以形寫神”,講究“形散而神聚”的繪畫藝術風格,這也跟磚畫的材質影響精細度有關。畫家完成竹林七賢由文字向圖像的轉化,是魏晉時期繪畫的一大進步,同時也奠定了相對自成一體的畫風模式,為后來其他繪畫藝術表現形式的產生、轉化和發展奠定了基礎。同時“典型性”的創作原則,將集體肖像傳達成一個特定的角色、一個理想的類型,這種將非帝王將相這類政治人物符號化概念化的表達手法,是繪畫歷史上的一次大突破、大轉折,也是時代下“人的自覺意識”和“文的覺醒態勢”的發展產物。
三、陸探微“秀骨清像”的人文自覺
宋齊陸探微作為《竹林七賢與榮啟期》的作者,以其“秀骨清像”被稱為“六朝三杰”之一,他在潑墨揮毫間描繪了魏晉時期文人志士的風骨和審美,其中融匯著玄學、人文和批判理性主義思潮,是那個時代對美學的最高追求境界“窮理盡性、事絕言象”的集大成者。 陸探微師從顧愷之,作為一個集畫、才、癡三者于一體的士大夫畫家,他的繪畫藝術成就在繪畫藝術史上能達到令人稱絕的高度。“傳神寫照”的美學論在他的人物畫實踐上體現得尤為突出,在漢代“君形”說的基礎上發展,明確開創了中國繪畫重視人物內在精神刻畫的先河。
陸探微的秀骨清像以三個特點聞名于世:其一為清瘦飄逸、灑脫超然的用筆畫技;其二為以書代畫、“入骨三分”;其三為構圖細密、繁復艷麗。秀骨清像通常為身形修長柔弱、苗條纖細、膚白貌美、文弱秀氣,以期反映人物超脫如仙的氣質。畫家以清淡病秀之姿,明隱入骨忘言之狀,重視自然之美和人本之美,對超脫之“道”的極致追求,亦是對現實亂世的逃避和生存之道。作為占據統治階級地位的審美觀念,這是與當時的宗教玄學和歷史人文背景分割不開的。對于人物風采姿態的著重刻畫,表達人物品格由經學造詣、道德品質到純粹的精神追求和自由向往的人文自覺,重老莊的天命天道論,以達到“道”來追求至高的精神追求,人們崇尚心靈美、內在美和精神美,回歸人自身的本質,這是一種以人為本的人文自覺。
四、結語
魏晉南北朝時期正是一個回歸人本身的“人文自覺”的覺醒時期,人的主題和文的覺醒作為歷史發展中事物的兩面幾乎同時發生。繪畫藝術上的大師們,包括顧愷之、陸探微、張僧繇、宗炳、戴逵、曹仲達等,發展并傳承了當時代下的藝術發展規律及主導審美觀為理論指導的“人文自覺”繪畫藝術模式。著名的“繪畫六法”“骨法用筆”“氣韻生動”“畫形寫神”等更是對中國歷史文化藝術精神的奇絕的提煉概括,并不斷產生對繪畫藝術語言的“自覺”發展趨勢。
這也是為人們所熟知的“藝術文人化”的概念。畫家不再是匠人或技師,而是士大夫階層真正成為藝術創作的主題,同時政治性歌功頌德的宮廷畫不斷地被文人畫所取代。這不僅極大提高藝術文化的品位地位,同時也是繪畫藝術的一次成功的自我轉型。由畫匠弄臣擺弄風騷、炫耀畫技或為政治禮教所俘虜的奴役工具,轉變成文人士大夫抒發自我意志、獨善其身聊表胸中逸氣的自我成全手段。
也正因為這一重要的轉折,帶來繪畫藝術與人文歷史的重要融合,相輔相成,改變藝術美感的追求模式。詩詞歌賦以求欲麗,起意緣情而附體物,都更加注重流暢瀟灑、寫意抒情的美感形式,從而回歸對人和藝術本身的研究關注。正如宗白華先生所言,魏晉南北朝作為歷史上政治最為動蕩不堪、混亂不堪的時期,卻也是精神上極為富足、自由和解放的時期,智慧、熱情濃縮一體,藝術精神得以迅速發展,生命本原的色彩在此時得到極大的關注和綻放。由此可見,魏晉南北朝的繪畫藝術和人文歷史的“人文自覺”達到了一個完美的和諧狀態。
參考文獻:
1.李澤厚.美的歷程[M].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3.
2.馬鵬翔.“竹林七賢”名號之流傳與東晉中前期政局[J].中國哲學史,2008,(02):116-122.
3.李珊.論六朝“竹林七賢”圖繪模式及意涵的轉變[J].湖北美術學院學報,2018(04):4-10.
4.戴春森.由“秀骨清像”看魏晉品藻人物的理念[J].社科縱橫,2004,(03):110-111.
5.陳旭光.“人的主題”與“藝術的自覺”——論藝術自覺的精神歷程[J].藝術百家,2016,32(03):152-156.
作者簡介:
楊揚歌,單位:中國傳媒大學,專業:視覺傳達設計(廣告設計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