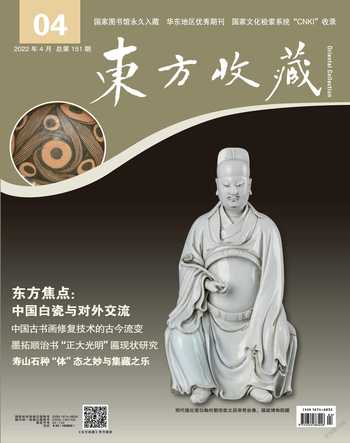抄錄《道德經(jīng)》之片想
陳元邦


筆者尤其喜歡老子的《道德經(jīng)》,全文五千余字,談不上宏文,也論不上巨著,卻蘊涵著深刻的哲理。幾千年來,人們視其為經(jīng)典,它無疑是中華傳統(tǒng)文化寶庫中一顆耀眼的明珠。
筆者也喜書法,尤喜小楷,在日課中,總覺得二者之間有著一種契合。閑暇,筆者常以小楷進行抄錄,于《道德經(jīng)》中領悟書法,于書法中表現(xiàn)《道德經(jīng)》。至今想來,已抄寫多遍,有長卷、有斗方,有楷、有行、有隸。每抄畢,總會細細品賞、細聲品讀,既欣賞書法的靈動意韻,也體會《道德經(jīng)》的內(nèi)容。
《道德經(jīng)》全文八十一章,長則兩三百字,短則數(shù)十字,每章都揭示一個方面的哲理。在抄錄中,漸漸覺得,《道德經(jīng)》中的許多內(nèi)容對學書者都有益助。
《道德經(jīng)》開篇即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凡事皆有道,書法亦有道之說。人們之所以重視臨帖,是因臨帖不止于形似,更在于神似,在于蘊藏其間的具有個性的書法之道。在《道德經(jīng)》的“有”與“無”中,“有”是書法之形,看得見、摸得著;“無”是書法中的神韻,幽微深遠,如《道德經(jīng)》所說的“玄之又玄”。學書者,就是要探索與追求這幽微深遠、體悟書道的真諦。白鶴先生在《中國書法藝術學》中說道:“追求天、地、人、書在形、意、韻上的完美統(tǒng)一,這既是書法藝術的起點,也是終極關懷。”唐代張懷瓘在《書斷》中也說:“善學書者,乃學之于造化,異類而求之,固不取乎原本,而各逞自然。”了悟在知行,體道在落實,書法就是在這了悟與體道中,去叩開“眾妙之門”。
“有無相生、長短相形,高下相傾、前后相隨”,這是《道德經(jīng)》第二章的句子。于書法而言,從中得到啟迪,書法亦有“相對論”。有無相生,在一幅作品中,章法至為重要,“字”若“有”,那留白處就是“無”,當白則白,當黑則黑,在相生間讓作品充滿生命氣息,讓人感到每個字都在呼吸。“長短相形,高下相傾”,書法之美,在于那追求“奇”中的美,在于險峻中的“正”,在于“長短相形、高下相傾”所表現(xiàn)出的那種“勢”、那種“態(tài)”。在這奇正相生的,你會感到兩個看似相互排斥的東西在這里達到了完美統(tǒng)一,創(chuàng)造出了美的和諧。欹正生姿,欹側縱放,轉換生姿,讓書法各生其姿、各顯其態(tài)。中國書法有著幾千年歷史,書家紛呈,風格迥異。米芾《蜀素帖》用險得夷,似欹反正,姿態(tài)各不相同,形成了米芾的書法風格。前后相隨,說的是氣韻相隨也。書法氣韻貫通,其作品方鮮活。有的書作,就單字來看,似乎都無可挑剔,但縱觀整幅作品,總感到缺了什么,氣韻缺也。學書者,當善于把握書作之氣韻也。
“知其白,守其黑”,此為《道德經(jīng)》第二十八章的句子。這句話的原意是,深知什么是明亮,卻安于暗昧的地位。中國的書法其實就是知黑守白,書寫的技巧也在于對“墨”的運用,在知黑守白間去表現(xiàn)這門藝術,展現(xiàn)出高貴靜穆的黑與白的生命對話。墨有五韻,其色最豐富,它可以寄托人的情感,雖聽不到音樂的震響,但處處回蕩著生命的律動。顏真卿的《祭侄文稿》,為祭奠侄子季明殉國所作的文稿,墨色在由緩而疾、由濕而枯中變化,在變化中讓人體會到縈行郁怒、哀思勃發(fā)的盡情。知其白、守其黑,還告訴我們,書法是一門寂寞的藝術,它與喧囂無緣,學書者,具以寧靜之心才能與墨結緣,在寧靜中尋得墨之趣。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此句出自《道德經(jīng)》第二十一章。老子說的是道,道是什么呢?《老子的智慧》一書中談到,道是恍恍惚惚的,說無又有,說實又虛,既看不清又摸不到。可是,在這恍恍惚惚中,它又具備了宇宙的形象。在這恍惚中,它又涵養(yǎng)了天地萬物。中國的文字萌芽于新石器時期,象形是中國文字的顯著特點,每一個點線必然蘊含著自然生命的現(xiàn)象。孫過庭在《書譜》中寫道:“心不厭精,手不忘熟”,最終達到無間心手、忘懷楷則。學書者必須總是行走于無與有、實與虛之間,總有一種恍惚與徨彷。但就是在這樣一個過程中,培養(yǎng)了書者的內(nèi)在品格,消解身心和物我的對立,達到乘物以游心、物我雙忘的境界。
“道法自然”,是《道德經(jīng)》中為人所引用最多的一個詞,該詞出自《道德經(jīng)》第二十五章。《道德經(jīng)》在第五十一章還說道:“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自然而然,與天然相近,自然所以然。一切最生動的生命現(xiàn)象均源于自然,只有將我的身心融于自然、體驗自然、感受自然,才能獲得永不枯竭的生命之源。書法從大自然中獲取靈性,“物象之形”也是“造化之理”,立象以盡意。東漢書法家蔡邕在《九勢圖》中說:“夫書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陰陽生焉。陰陽既生,形勢出矣。”唐代書法家虞世南在其《筆髓論·契妙》中也寫道:“字雖有質(zhì),跡本無為,察陰陽而動靜,體萬物以成形,達性通變,其常不主。”千年以來,人們從大自然中獲得書寫靈感,也常以大自然現(xiàn)象來評價書法。如孫過庭《書譜》中云:“凜之以風神,溫之以妍潤,鼓之以枯勁,和之以閑雅。”疾、潤、枯、雅的韻律變化,是一種書寫過程中的“物我兩忘”。道法自然,是一種修養(yǎng),一種境界,學書者應當從自然界中去獲取書法的養(yǎng)分,從碑帖中體會領悟其中的自然之性,深入大自然中體悟自然、在書寫中表現(xiàn)自然。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求和”,此句出自《道德經(jīng)》第四十二章。道是化生萬物的總原理,書法之道也是化生書法的總原理,書法若失去法與道,便失去書法之根、之本。“一點成一字之規(guī),一字乃終篇之準”,理解孫過庭的這句話,我們書寫一幅作品,第一個字就為全篇定了基調(diào),其他的字都是由第一個字生發(fā)開來的。在書寫過程中,以這一字為基準,處理好字與字之間的關系,達到“違而不犯,和而不同”的對應關系。在節(jié)奏、用墨和變化關系上,要做到“留不常遲,遣不恒疾,帶燥方潤,將濃遂枯;泯規(guī)矩于方圓,遁鉤繩之曲直,乍顯乍晦,若行若藏;窮變態(tài)于毫端,合情調(diào)于紙上”。書寫有變,才有靈動,如何變,在一字之規(guī)、終篇之準中變,但變的終極是“合情理于紙上”。老子的這段話讓筆者感到,學書者當求變,但萬變不離其宗,從大的方面來說,不能離開書法之道,從一幅作品來說,必須守好“一字之規(guī)、終篇之準”,必須把“一字之規(guī)、終篇之準”表現(xiàn)達到極致。
《道德經(jīng)》中蘊含的哲理對于學書者來說,受教匪淺,筆者只是涉之皮毛,日后當不斷體會,把它帶入到自己的學書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