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時與千秋
文昌
壬寅虎年春節,閨女網購了孫犁的《耕堂劫后十種》。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簡易十本,印制精良,捧讀方便,或坐、或臥,無不適意。春節長假,有書為伴,日子也就和新春一起鮮亮起來。
知道孫犁,是因為年輕的時候讀過他的《荷花淀》,是引領文風的一代大家。今天讀他老年時期的《耕堂劫后十種》,文字清爽簡潔,漸入化境,自然親切之風撲面而來。火氣少了,刻意少了,煙火氣卻充盈其間,所謂絢爛之極歸于平淡。
在《陋巷集》里,讀到他寫的《讀〈沈下賢集〉》,我才知道唐朝還有一個大才子沈下賢。孫犁對他推崇備至,尤其稱贊沈下賢的傳奇寫得好:“鼓吹既作,能使孤蓬自振,驚沙坐飛。”
沈下賢有一篇《答學文僧請益書》,里面講到的一個故事讓我印象深刻。古時有一個鍛金匠人,手藝精湛,日子卻過得很清苦。弟子笑曰:“師父手藝可算高超,但收獲反不如燒土窯制瓦器的人,這是什么緣故?”話還算客氣,沒有像子路那么直白地質問孔子:“君子亦有窮乎?”金匠停下手中活計,淡淡地對弟子說出了緣由:“制瓦器的人,操作簡單,獲利也薄,他的制品是賣給人使用的。早晨有人買去,晚上也許破了,就再買一件。所以他的買賣,總是很興隆,也就致富了。我的職業不同,我要苦思冥想,設計琢磨,一器成功,別人買去,就可以品玩一輩子,不用再置。所以我這里總是門前冷落,吃不飽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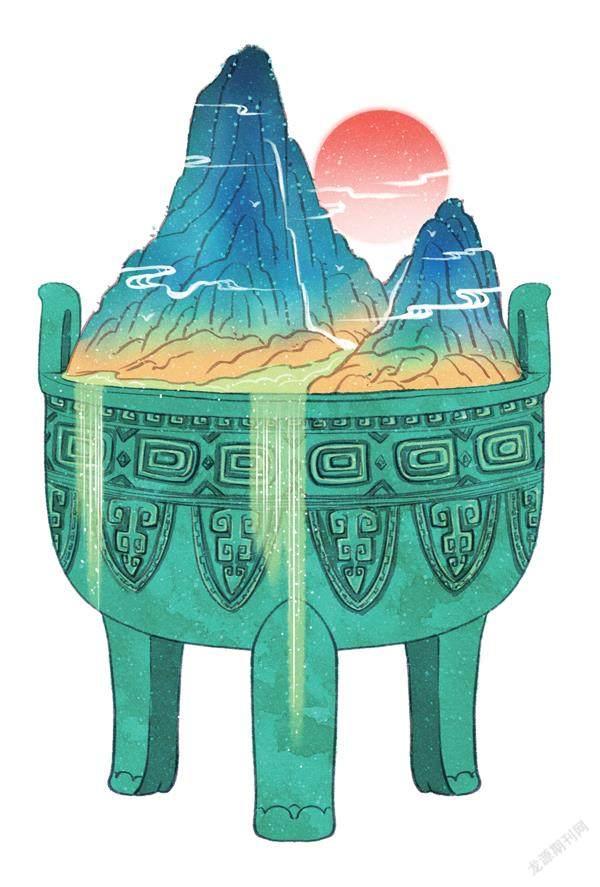
一時與千秋,取決于最初的選擇 (圖/視覺中國)
“吃不飽飯”,四個字縈繞在我的心頭,久久揮之不去。師父講完,弟子什么態度,沒有下文。我想,沈下賢編出這樣一個故事,更多是為自己打氣,是一種自我鞭策。他一定時時以故事中的金匠自況,所以才寫出好文章,留傳后世,讓孫犁嘆賞不已。
金匠也是匠人,也要吃飯。但是在金匠的眼中還有比吃飯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自己手中作品的生命力。他的作品要“苦思冥想”,要“設計琢磨”。慢工出細活,做出來的東西少了,得到的銀子就少,飯菜也就不會豐盛,“吃不飽飯”也就順理成章。燒制瓦器,沒有這些考慮,成得快,壞得也快,所以不停地壞,不停地做。買賣興隆,瓦匠的日子也就好過了。殊不知,錢來得快,瓦也碎得快,“作品”轉瞬之間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真正的藝術,總是不為“稻粱謀”。酬金不是衡量一件作品價值的唯一標尺,你不見多少傳世的名品,在當時默默無聞,甚至被人嗤之以鼻。創作他的主人們多是窮困潦倒,疲于奔命,在外國有梵高,在中國有司馬遷。浩如煙海的“作品”,煙消云散,《向日葵》留下來了,《史記》留下來了,像老酒,時間愈久愈醇。
金匠和瓦匠,職業雖然不同,但更大的不同是對行業、對自己職業的態度。金匠也可以粗制濫造,也可以弄虛作假,投機取巧換來豐厚的回報,也可賺得盆滿缽滿,一生衣食無憂。瓦匠也可以精益求精,也可以制造傳世作品,你不見長城上的青磚歷經千年,仍然“長青”。你不見太和殿上遮風擋雨的琉璃瓦穿越時空,仍然光彩奪目?
一時與千秋,其實完全取決于最初的選擇。
我很欣賞孫犁晚年的作品,類似《耕堂劫后十種》。我想,孫犁的心里也一定住著一個沈下賢故事里的金匠,所以才會在遲暮之年,筆耕不輟,又惜字如金,留下“光而不耀”玉一樣的文字,繼續溫暖著世人。
編輯:薛華? icexue0321@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