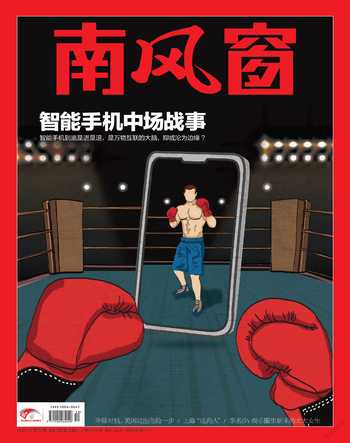外國軍援正改變烏克蘭戰況
陶短房

“我們愿意恢復我們的領土完整。”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5月1日告訴希臘記者,“作為處于戰爭狀態的國家的總統,我必須告訴你,我們需要更多(武器),我們也需要他們能更快(供應武器)。”
次日美媒報道稱,美國已將70多門M777榴彈炮(射程達20~40公里,末端采用激光制導)運抵烏克蘭,且已有200多名烏克蘭軍人接受了操作培訓。當天,烏克蘭總統辦公室主任葉爾馬克表示,烏克蘭將為收復全部領土而戰。
顯然,外國軍援的源源“補血”,是曾在2014年克里米亞和烏東危機中表現糟糕的烏克蘭軍隊如今得以持久抵抗的關鍵因素之一,也被日益視作未來烏克蘭戰爭的勝負手之一。
自2月24日戰事爆發到4月底,據不完全統計,向烏克蘭提供或明確承諾提供軍援的國家計有35個。這其中最大宗、也最關鍵的,是美英兩國的軍援。
美國早在奧巴馬時代就開始軍援烏克蘭,最初限于資金、非致命裝備和訓練;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批準向烏克蘭出售致命性輕武器。
美方2018年3月披露,對烏出售首批價值4700萬美元的致命武器(清單未公布,僅知包括210枚“標槍”反坦克導彈);2019年9月宣布,完成總價值2.5億美元“安全援助”(其中5000萬美元用于致命武器);2020年6月,提供價值2.5億美元致命武器;同月提供16艘VI型巡邏艇,價值6億美元。
拜登上臺后加大對烏軍援力度,2021年1月、3月、6月和9月,分四筆提供總價值3.35億美元軍援(明細未公布,但“全部為致命性武器”)。
烏克蘭戰事爆發翌日,美國就向烏提供了3.5億美元致命性武器,3月12日又提供了價值2億美元武器;幾天后,批準將價值8億美元的對烏軍援,納入總額136億美元的對烏援助大清單中;4月13日再單獨追加8億美元軍援;4月21日則宣布,從“大清單”中再撥付8億美元用于軍援。
4月28日,拜登要求國會批準將“援烏大清單”總額大幅提升至330億美元,其中近2/3將用于軍援。
根據4月下旬美國國防部后勤局提供的兩份情況說明書,自2月25日至3月15日,美國提供給烏克蘭的軍事裝備包括:2600枚“標槍”反坦克導彈,600枚“毒刺”便攜式防空導彈,5架二手俄制米17運輸直升機,8套偵察雷達,近4000萬發輕武器彈藥,100萬發炮彈、迫擊炮彈和手榴彈,等等。
3月16日8億美元援助清單包括: 2000枚“標槍”,7000具反坦克火箭筒,800枚“毒刺”,100架“彈簧刀”無人機,2000萬發各型彈藥,等等。
4月13日8億美元援助清單包括:18門M777輕型牽引式榴彈炮及4萬發炮彈,11架二手米-17運輸直升機,200輛裝甲運兵車,以及數目不詳的反炮位雷達。
4月21日8億美元援助清單包括:72門M777外加14.4萬發炮彈,72輛配屬M777的火炮牽引車,121架“鳳凰幽靈”戰術無人機。
英國同樣早在戰前就開始對烏軍援,2015——2021年通過“軌道行動”幫助烏克蘭培訓多達2.2萬軍人,重點是操作西方制式的防空、反裝甲便攜式武器、反炮位雷達和電子通信設備。
美國始終不肯提供烏克蘭一再懇求的戰斗機、主戰坦克、步兵戰車和自行榴彈炮等一線主力重型裝備;最新提供的M777輕型牽引式榴彈炮,實際上是專為阿富汗高原戰場量身定制、因阿富汗戰爭結束而積壓的“庫存品”。
在2022年3月16日以前,英國向烏克蘭提供了4000枚以上“標槍”及NLAW反坦克導彈;之后,英國援助的“星空”便攜式防空導彈頻頻吸引眼球,所提供的裝甲車和遠射程火炮也是西方國家中第一個提供這類裝備的。英國還通過RC-135W電子偵察機,幫助烏克蘭搜集電子情報(在烏克蘭境外飛行)。
美英之外參與對烏軍援的國家,情況差異很大,大致可分為以下幾類:
首先是東歐及原蘇聯國家,它們大多和烏克蘭“同病相憐”,軍援較為積極,但它們國力參差不齊,因此援助力度也大小不一。其中,波蘭由于是前華約國家且已改用北約制式,便將庫存的大量蘇聯制式武器裝備贈給烏克蘭;在試圖提供二手蘇制戰斗機被美國叫停后,波蘭成為首個給烏克蘭提供二手蘇制主戰坦克的北約國家(已提供了200輛T72系列)。斯洛伐克則是第一個向烏克蘭提供遠程防空導彈系統的國家。波羅的海三國和捷克也都較為積極。
其次是部分歐洲(尤其西北歐)國家和加拿大,它們對軍援烏克蘭較為熱心。加拿大的特色是,提供了一些獨有的高價值裝備,如其衛星分析系統是迄今各國對烏同類援助中分辨率最高的。在西歐國家中,意大利是第一個(4月中旬)承諾向烏克蘭提供重型裝甲戰斗車輛的;比利時、丹麥、芬蘭、荷蘭、挪威、瑞典等,援助也較多。
再次是法國和德國,它們扭扭捏捏,雖遲但到。
法國在2014——2020年曾是烏克蘭最大軍援國(16億歐元),但此后顧及法俄關系一度不愿援助“高級武器”。戰事爆發后,法國直到2月26日才宣布給烏1.2億歐元軍援,且多為非致命性裝備,加上馬克龍由于和普京頻繁接觸,飽受國內外強大壓力,因而法方近來逐步加強援烏,4月22日更宣布將提供法制“愷撒”車載155毫米榴彈炮及彈藥。
德國戰前一直拒絕向烏克蘭提供軍援,并與俄保持密切關系,開戰后被迫“逐步加碼”軍援,比如拿出5100具德國/新加坡/以色列聯合開發的“斗牛士”反坦克火箭筒、3000枚“鐵拳3”反坦克火箭筒,以及2700枚原屬東德人民軍的蘇制9K32便攜式防空導彈。
據德國《世界報》最新消息,繼“獵豹”防空戰車后,德國決定交付7輛性能極佳的PzH 2000型自行火炮給烏軍。其采用高度自動化的電控式填彈與擊發系統,1分鐘內可射出8枚炮彈,射程可達40公里。

總體上,法德兩國政府對軍援態度猶豫,迫于國內外壓力不得不“一撥一動”,但這兩國都是大國、富國,不出手則已,出手則分量不輕。
最后是其它西方國家,它們或力不從心(如盧森堡、新西蘭等),或熱情不高(如愛爾蘭),對烏軍援基本屬于錦上添花、湊熱鬧。
戰事第一階段,烏克蘭大部分國土或成為戰場、或面臨戰火威脅,軍工生產捉襟見肘,迅速到位的外國軍援起到及時“補血輸血”功能;戰事膠著后,烏克蘭方面軍工生產、倉儲設施遭受不斷襲擊,也正是依靠源源外援,才得以保持戰斗力。
鄰國最先交付的,多是冷戰時大量庫存的蘇式武器彈藥,烏軍可以“即插即用”,雖然它們并不先進卻足以救急;稍后到位的西方軍援,則是殺傷效果良好、體系依賴型不強的單兵/班組用便攜式防空、反坦克導彈和火箭筒,也不難快速形成戰斗力。
迄今軍援中,最大宗武器是反坦克導彈/火箭筒,其次是便攜式防空導彈。正是這些仿佛“打也打不完”且性能成熟的輕型反坦克、防空外援武器,幫助烏克蘭頂住了俄軍引以為傲的“裝甲洪流”。
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電子、通訊、圖文分析、戰場情報等領域,給予烏克蘭的支持看似“不致命”,實則提供了更大的“戰力倍增”,令俄的軍事行動屢屢在關鍵時刻掉鏈子。
另一方面,對烏軍援的局限性也很多。俄烏開戰之初,美國惟恐“事態升級成世界大戰”,拒絕提供“進攻性武器”,還出面阻攔了波蘭轉交本國24架二手米格-29戰斗機給烏克蘭的計劃。后來情況雖有變,但西方實際提供的軍援仍然主要是庫存、二線或積壓裝備。如德國提供的2700枚前東德庫存9K32防空導彈,竟然有700枚是廢品。
美國始終不肯提供烏克蘭一再懇求的戰斗機、主戰坦克、步兵戰車和自行榴彈炮等一線主力重型裝備;最新提供的M777輕型牽引式榴彈炮,實際上是專為阿富汗高原戰場量身定制、因阿富汗戰爭結束而積壓的“庫存品”,并不太適合平原為主、需要高機動性的烏克蘭戰場;“鳳凰幽靈”無人機,則是美方因“彈簧刀”太貴、自己舍不得給太多而替代性提供的“低值易耗品”。
上述“逐步升級”和“只給二流貨”的做法,制約了烏軍的戰斗力。由于缺乏可靠的防空襲和裝甲突擊力量,烏軍即便在戰場形勢有利或危急情況下,也不敢放手發動大規模會戰,而是總體上陷在長期被消耗、被圍攻的困境。
而且,戰事拉長導致前華約體系中,各國庫存的原蘇聯體系武器彈藥消耗嚴重,如要繼續大量供應烏軍此類軍火,需要在援助國間進行復雜的協調。目前,有這類軍火生產能力的主要是波蘭、捷克等東歐國家,但其自身裝備體系已經北約化,如要恢復華約體系武器彈藥大規模生產,可能需要富有盟國“埋單”。
另一種選擇,是讓烏克蘭強行變換軍火體系,但那樣做需要時間過渡,容易出現“戰斗力空窗”。
4月24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國防部長奧斯汀雙雙訪問烏克蘭首都基輔,顯示美國在烏克蘭危機中的戰略目標,似乎發生了根本性轉變。
在訪問結束后于波蘭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奧斯汀披露了美國介入烏克蘭戰爭的兩個目標,一是“幫助烏克蘭維護主權和領土完整”,二是“希望看到俄羅斯被削弱到令其無法再對任何國家發動類似對烏克蘭這樣的戰爭”。
第一個目標是美國長期以來公開宣稱的目標,但第二個目標則是迄今美國在烏克蘭問題戰略目標上最“激進”的言論,首次將“削弱俄羅斯總體實力”擺在臺面。而且,這一重大戰略目標修改,是在俄外長拉夫羅夫等對美發出“試圖在烏克蘭進行代理人戰爭”指控和“核戰”恐嚇僅一天后作出的。以往類似情況下,美方總會強調“這是俄方的污蔑”。
這表明,隨著俄烏戰事遷延不決,美國已從最初的謹慎小心變得更加大膽和無所顧忌,敢于把原本心照不宣的戰略目標公開。當然,另一個因素可能是,美方評估后認為:“即便美方克制,俄也不會作出美國所希望的反應”,而“通過烏克蘭戰事總體上削弱俄羅斯”這個大幅升級的戰略目標,可以讓美國政府在今后更方便高效地調動本國資金和資源,投入烏克蘭戰場。
總部位于美國華盛頓的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在4月26日由國際安全項目高級顧問坎希安(Mark F. Cancian)牽頭發布的《美對烏軍援提速》的評估報告中指出,美國對烏軍援戰略性的轉變,“含蓄地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設定,即軍援的目的已不僅僅是幫助烏克蘭頂住俄羅斯進攻,而是通過烏克蘭將俄羅斯拖入一場曠日持久、筋疲力盡的長期性戰爭,最終將其削弱甚至拖垮”。
可以預見,未來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對烏軍援,將圍繞這一更新版戰略目標展開。
4月26日,剛結束基輔之行的奧斯汀,出席了在德國拉姆施泰因空軍基地舉辦的“40國烏克蘭防務協商小組會議”。會議期間,美國等國不僅宣布擴大對烏軍援,而且倡議將這一旨在協調軍援國“節奏”的會議“常態化”。倘如此,不僅各國軍援會更高效,更有針對性,且目前僅少數國家淺嘗輒止的“第三方代理模式”,也很可能在這種新模式下更廣泛、更普遍地展開。
“第三方代理模式”是指,當事方在缺乏足夠庫存的情況下,出錢委托第三方生產或買下第三方庫存供貨。美國曾用這種方式,委托波羅的海三國向烏克蘭提供美式便攜式導彈;挪威和盧森堡也用這種方式,委托英美向烏克蘭提供武器裝備。
俄方的反制措施,無非是硬和軟的兩手。
硬手段是攻擊、癱瘓烏克蘭境內尤其西部的運輸、倉儲網絡和節點,讓外國軍援或運不進烏克蘭境內、或送不上前線。但俄本就缺乏持續大規模使用精確制導武器的能力,此次開戰后,烏在得到軍援后又針對性地加強了“點防空”能力,令俄空襲效果大幅下降。
以“癱瘓烏克蘭西部鐵路網”為例,4月24日布林肯、奧斯汀訪問基輔,系通過連通波蘭和烏克蘭的鐵路往返的。這條鐵路線要經過幾座重要橋梁,是俄勢在必得的空襲癱瘓要點。布林肯、奧斯汀往返之間,俄正好進行了號稱“開戰以來最猛烈”的一次針對性空襲,宣稱“戰果輝煌”。但此次空襲后不到12小時,布林肯和奧斯汀就平安乘坐火車返回了波蘭。俄癱瘓烏克蘭西部鐵路運輸體系的效果不過如此,而鐵路運輸體系已是各種陸路運輸途徑中最容易被破壞的了。
軟手段則是密集指責美國和北約“另有圖謀”“狼子野心”。除了拉夫羅夫外,4月26日俄安全委員會秘書帕特魯舍夫指責美國“試圖完成冷戰未竟目標,摧毀俄羅斯”;兩天后俄政府發言人佩斯科夫指責各國對烏軍援“威脅歐洲大陸安全,引發不穩定”;俄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指控西方策劃了對摩爾多瓦境內自行宣布獨立的親俄“德左共和國”的“恐怖襲擊”;俄外國情報局局長納雷什金,則指控美國和波蘭“以維和特遣隊名目向西烏克蘭派遣軍隊,意在吞并烏克蘭領土”……試圖借此爭取國際輿論同情,或逼迫援助國有所顧忌,知難而退。
但迄今這些措施僅對少數援烏國家有效。在俄堅持繼續烏克蘭境內“特別軍事行動”的前提下,這類“軟反擊”的說服力顯然難達預期。而在“奧斯汀聲明”發布后,美國顯然已不再忌諱此前“只敢做不敢說”的“代理人戰爭”,而是擺出一副“我就是要削弱你,你能奈我何?”的渾不吝姿態。如此一來,俄的“嚇阻”軟手段,恐更難對美生效。
日前,烏總統顧問阿列克謝·阿列斯托維奇在接受《日經亞洲評論》專訪時稱,由于西方提供的武器,烏軍將能在5月下旬至6月中旬之間發起反攻。客觀而言,迄今的對烏軍援,幫助烏克蘭獲得了在俄全面軍事進攻面前的生存能力,但未來的對烏軍援能否幫助烏克蘭頂住俄針對烏東地區的“重點進攻”,甚至令其獲得大規模反攻能力,目前尚不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