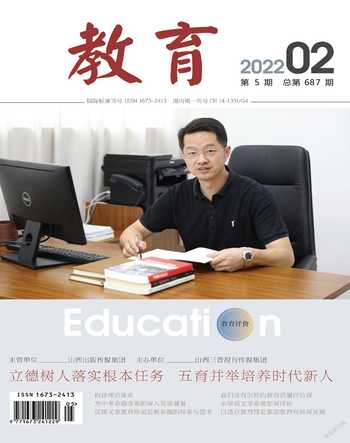我們應有怎樣的教育質量評價觀
李忠華
多年來,筆者所在管理區初考、中考成績排名幾乎年年全市倒數,因為排名倒數,初中學生數由鼎盛時期的近三千人,驟降至如今的不到三百人,小學也是擇校嚴重,筆者現任教的班級僅有兩名學生。是所在地教育均衡有問題嗎?不是的,深究其因,乃全市學校教學質量排名之弊端所致。
一
說到教育,談論最多的話題就是教育質量;說到教育質量,就會很自然地聯想到學生的考試成績;一提到考試成績,就會很自然地聯想到什么評先表模、評職晉級、先進單位等。長期以來,這條所謂的教育思想鏈深深嵌在一些部門領導、教師和家長等腦海中。“沒有考試成績,就不談有什么教育質量!”這句朗朗上口的話語,幾乎成了個別領導重視教育質量的會議口頭禪。每每進入校園,我心中總是莫名激起對“教育質量”的無限遐思:學生的考試成績與教育質量是因果關系嗎?學生成績排名就等于學校教育質量的排名嗎?還是暫且放下“教育質量排名”這個話題,說得廣遠一點。
先說人之受教育與其成長歷程。都知道教育是對人而言的,人可以被教育,人亦可以進行自我教育。一些“受教育者”可以理解為被動的,正如幼兒、小學等學校教育一樣,在一定的環境里,“受教育者”受到教育者方方面面的約束,這是一種被教育;而另一種就是自我教育,自我教育是從自己有了嚴格的律己之心開始的,這種教育要經歷漫長的被教育之歷程,才能達到化境,即自化而上升到一種境界,這種境界就是教育的高境界。可以完全進行自我教育的人,自然就不需要“被教育”了。那么,從某種意義上說,教育“被教育者”的目的就是促進其進行自我教育。自我教育的種子一旦在“被教育者”身上發芽,日久定能枝繁葉茂。這是人一生所受教育的兩種不同方式。那么,人的一生到底要經歷多長的教育歷程呢?人之受教育歷程用這樣一條“遞進式教育線”表述要清楚些:人之初→【1.被教育(自然教育;社會、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等)】→【2.被教育兼自我教育(自然教育;社會、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等)】→【3.自我教育兼被教育(自然教育;社會、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等)】→【4.不完全自我教育(自然教育;社會、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等)】→【5.完全自我教育(自然教育;社會、家庭教育等)】→【6.成人(自然教育;社會、家庭教育等)】→【7.完人(自然教育;社會、家庭教育等)】→【8.圣人(自然教育;社會、家庭教育等)】→【9.自我教育終身(自然教育;社會、家庭教育等)】→【10.名垂千古,教育后人】。竊以為,人離開學校,自然、社會、家庭教育相伴終身,人受教育的質量可以理解為是人的成長增量。
從上面這條教育線可以看出,人之初到成人乃至圣人,道路是漫長的。回說到前面提到的“教學質量排名”,談論最多的要數九年義務教育質量了,話題包括初考、中考,初考排名和中考排名等。義務教育歷程指的是短短九年,對應前面我自以為的“遞進式教育線”大概就是2、3、4級吧,“九年學習”能保證大多數人達到“被教育的同時兼生發自我教育”,這就是很不錯的教育質量了。很顯然,我以為的教育質量與彼教育質量不是一個概念,甚至可以說不在一個理論層面。記得德國著名教育家第斯多惠曾經說過:“教育的藝術,不在于傳授知識和本領,而在于激勵、喚醒和鼓舞。”我是很崇尚這種教育觀的,激勵、喚醒與鼓舞,都是從教育的功能上去理論,如果一定要說到“教育質量問題”,這個概念太大了,是無法斷然定論的,因為我覺得教育是一張無形的網,無邊無際。若某人一定要評價、談及教育質量高低,可以說,即使有評價方案和標準,其評價衡量的也是極其片面的教育質量問題。
再說,我們的九年義務教育質量,應該包括德、智、體、美、勞等各個方面,前面言及的教育質量僅僅指的是應試科目的考試成績,還不能說成是智育成績。試想,我們現在的教育把體、音、美都納入考核,這三類即使與原應試科目成績合并,一起來言及某某學校的教育質量,也是不全面的。縱觀各地各校的教育質量之評價現實,特別是義務教育階段,都是以學生的考試分數為依據的。譬如,把某班學生的某單科成績合并,計算什么“一分三率”等,得到的是一個“分值”,用這個“分值”來評判科任教師的教學質量。同樣,可以得到另一個“分值”,兩個“分值”相比較,兩個教師的單科教學質量就有高低之分了。同理,采用這種評價方法,年級相比較,學校相比較,于是,教師有了名師非名師之別,班級有了重點非重點之別,學校有了名校非名校之別,區域教育質量在家長心目中也就自然而然地有了落后與先進之別。學校教學質量排名,家長不擇校才怪呢!
繼續說這兩個根據“教學質量公式”得出的“分值”,若說其意義是兩個班學生成績之各自達標概率,或許還勉強說得過去,但怎么能用這僅僅代表學生成績達標概率的一個“分值”來評判兩位科任教師的教學質量之差別,繼而上升為評判學校教育乃至整個地區教育質量之優劣呢?學生分數有高有低,反映的是不同的個體差異、基礎差異等內因,而外因呢?就更多了,比如不同學校的辦學條件不同等等。的確,沒有比較,就不能鑒別,但是,我們要考慮某二者相比較是否遵循“比較性原則”。我們知道,中心學校與偏遠學校僅僅就辦學條件而言,就有天壤之別,何況還有師資等各種差異,彼此又將如何比較呢?所以說,人本之差別、分班之差別都不能相比,更何況還有年級差別、學校差別以及區域差別存在。總之,用學生分數排名來衡量各個學校的教學質量好壞,繼而理解為區域教育質量有高有低是毫無理論依據的。一句話,學生的考試成績只能是學生之間的相提并論。
二
回到文章開頭的話題,學校教學質量可以排名,但這種教學思維所反映出的教育觀念,我卻不認同。教學質量是無法排名的,教育質量更不能分優劣,只能是“有無”問題。而偏偏各地都盛行“教學質量”排名,那到底又是怎么排名的呢?據了解,成績排名是以考試科目的“一分三率”為基數,通過上面規定的一個“一分三率”總值換算公式:總評分=平均分計分+優分率計分+合格率計分+低分率計分。具體即【班級平均分÷學校(或學區、分局)總平均分×30×0.8(計滿30分止)+班級優分率÷學校(或學區、分局)總優分率×20×0.8(計滿20分止)+班級合格率÷學校(或學區、分局)總合格率×30×0.8(計滿30分止)+20-班級低分率×100(最低計0分)】。這樣輸入學生成績,靠電腦計算而得出的總值大小來決定,這個排名實質上就是各校或各地教學質量的優劣等次。本來,我們一貫強調“狠抓教學成績,努力提高教育質量”無可厚非,但片面地把一個地方的教育質量歸結為部分統考科目的“一分三率總值”之排名先后,未免過于狹隘。眾所周知,黨的十八大明確指出,要“把立德樹人作為教育的根本任務,全面實施素質教育,培養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也就是說,衡量教育質量就是“立德樹人”這把尺子。而近幾年來,我們衡量某個教育片區的教育質量完全是看該地教學應考科目的“一分三率”總值的排名情況,值大,排名前;成績好,教育質量優。只要有了考試高分,就有了所謂的“教育質量”,“名校長”“功勛班主任”“十佳教師”“教育先進縣市”等各種榮譽自然會接踵而至,可謂是“一分值萬金”。通過“質量公式”得出的“分值”來考評一個教師教學成績并冠以好壞之名,來衡量一個地方教育質量并冠以先進落后之名,這樣的評價是不合乎“學生異同性教育”原則、“學生成長性教育”規律以及“區域落差性教育區別考量”政策的。看重考試科目,自然淡化甚至忽略在教育層面占據更大比重的其他非考試科目,于是,就有了“評幾個優秀學生”就是德育、“搞一個美育節”就是美育教育、“辦一屆運動會”就是體育教育等做法,德、美、體等素質教育成了少數學生短時期參與的一個教育范本。無需贅言,用一個公式計算出來的“分值”來考量優劣的行為,或者說能量化考評的行為,那不是教育行為,那個“分值”體現的更不是教育的質量。因為教育是藝術,用北師大教授肖川的話說,就是“教育就是一個不完美的人,帶領一群不完美的人,走向完美的過程”。
再說說何為“教育”。教育即生長,是一項慢功夫,古今中外無數教育家為之闡發理論。德育是培養和鼓勵學生崇高的精神追求,而不是灌輸規范;智育是通過學習教科書,如語文、數學等來發展學生好奇心與理性思考能力,而不是灌輸知識,教科書更不是學校用來考量學生誰聰敏和誰愚笨的“試金石”;美育是培育學生豐富的靈魂,而不是灌輸某種技藝——如畫畫等。又何為“教育質量”呢?《教育大辭典》的解釋:“教育質量是對教育水平高低和效果優劣的評價,最終體現在培養對象的質量上。”教育質量有宏觀與微觀之分,從宏觀層面看,教育質量即整個教育體系的質量,體現在社會的風氣、人們的核心價值觀等方面。微觀教育質量最終體現在培養對象的質量上,其衡量標準是各級各類學校的培養目標。再者,“教育質量”與“教學質量”又有何區別呢?答案如下:1.教學與教育是部分與整體的關系。教育包括教學,教學是學校進行教育的一個基本途徑;除教學外,學校還通過課外活動、生產勞動、社會實踐等途徑對學生進行教育。2.教學是教師的“教”和學生的“學”所組成的一種人類特有的人才培養活動。通過這種活動,教師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地引導學生積極自覺地學習和加速掌握文化科學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促進學生多方面素質全面提高等。
三
說到底,用學生考試成績排名,進而為各學校教育質量之排名,凸顯了“教育”與“教學”概念含混推論的結果。我們的教育總是在進行“應試教育與素質教育”之變、之爭,把過去的定位為“應試教育”,把現在的定位為“素質教育”。所謂教育,是心靈的觸動與滋養;所謂教育,從改變自己開始,到改變他人也不會結束;所謂教育,玄遠而綿長,積力于亙古,發力成就著未來。還是用“一條線談論”來表述自己對教育的理解吧:教育【素質教育;應試教育(考核科目、考試科目)】→教育質量【素質教育質量;應試教育質量(考核等級、考試分數)】→教育質量評價【素質教育質量是主觀隱形而延后的;應試教育質量(考核等級、考試分數)是客觀實際而即時的】。從“一條線談論”可以看出,用“考試分數”代表“教育質量”難道不是明顯的“盲人摸象”思想嗎?不是錯誤的“以偏概全”理論嗎?單說教育質量之素質教育質量就是隱形的、延后的,也就是說一個階段或時期的教育,后一個階段或時期才能予以評價。而應試之教育有開始、有經過、有結果,我們平常說的教育質量應該指的是其結果,即學生的各科期末考試分數,這個分數說明的只是學生受教育的一個“獲知值”,怎么能用應試單科教學的學生分數去衡量教師作為“學高為師、身正為范”之教育教學的質量,乃至排名評判各個學校之整個教育教學的質量呢?
不能深刻體會上面的道理,令人不可思議的事就自然順理成章地發生。之前提到的教學質量公式是當下正施行的,幾年前的教學質量公式與此有所不同,原來教學質量公式大概是這樣的:平均分×0.4÷4+合格率×0.35+優分率×0.25-低分率×0.05。曾記得原“教學質量公式”在用于計算應考科目的教學質量的同時,還被推及至評判非考試科目教學質量。當時幾乎各學校都是這樣考慮的——討論將“教學質量公式”打幾折后,就可以用來衡量非考試科目的成績了。各學校是不統一的,有的七折,有的八折。時至今日,教學質量公式雖有變化,但其所映射的教育思想一點沒變,用教學質量公式計算出來的“分值”,衡量教師依然,衡量學校依然,評價教師教學能力依然,評價學校教育質量依然。
其實,考試和其他各種展示活動一樣,只是學生自己檢測、反饋和提升的一種方式,分數也不過是學生在修學某種能力道路上的一幕“風景”,或者說是一個成長“足跡”。一些人機械地把考試分數看作是教學質量,并理解為教育質量,在學生的試卷分數上做大研究、做大文章并賦予一定的內涵及價值取向,這是毫無意義的。教育質量體現在孩子的一生中,影射在社會上,因此,教育質量的優劣是不能用一個簡單的“分值”來標識的。再說,教育質量的本質是人的成長,包含著人文氣息與人本特質,是發展的,是需要期待的,故不是“即時”可以定論的。
原教學質量公式(平均分×0.4÷4+合格率×0.35+優分率×0.25-低分率×0.05)以及現教學質量公式(總評分=平均分計分+優分率計分+合格率計分+低分率計分),不知起于何時,終于何時。這一用來評判教育質量的功利性尺度,是個別教育管理者高高舉起的“指揮棒”。在這根“指揮棒”下,分數和名次就成了師生的成績,成了學校的業績,更成了管理者的政績。我們辦學做教育,只有從功利價值觀提升為使命價值觀,讓教育質量始終對應學生的成長使命和社會發展使命,我們的教育才有希望回到本源,回到教育最基本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