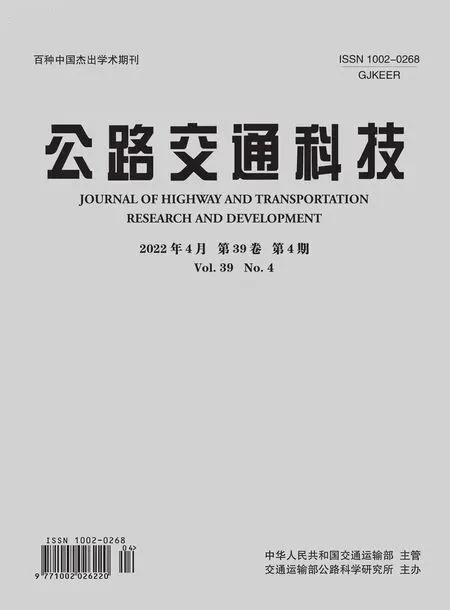流線形雙邊主梁斷面橋梁顫振穩定性能研究
白 樺,魏洋洋,劉博祥,馬 韜
(1.長安大學 公路學院,陜西 西安 710064;2. 中鐵第一勘察設計院集團有限公司,陜西 西安 710043)
0 引言
近年來,斜拉橋因其超強的跨越能力,以及輕盈優美的結構造型,得到了橋梁設計者的廣泛青睞。雙邊主梁因結構自重輕、施工吊裝方便、受力性能優越等優點在大跨度斜拉橋中被廣泛應用[1],比如馬鞍山長江公路大橋、鄂東長江大橋、荊岳長江大橋等[2-3]。
流線形雙邊主梁是為了優化常規鈍體雙邊主梁氣動性能而產生的,在鈍體雙邊主梁的基礎上給主梁兩端加上風嘴以改善大跨度斜拉橋的風致振動問題,但由于雙邊主梁的斷面形式,在梁底會形成比流線形斷面更加復雜的繞流。葛耀君[4]通過節段模型風洞試驗,對顆珠山橋顫振穩定性進行研究,發現鈍體雙邊主梁斷面無法滿足顫振檢驗風速的要求,增設風嘴后,其顫振控制效果相當好,顫振臨界風速提高了30%,并且風嘴還可以改善結構的其他風振性能。李陸蔚[5]通過風洞試驗和理論分析相結合的方法,研究了半封閉式風嘴橋梁的顫振穩定性能,結果表明全封閉和半封閉式風嘴在顫振、渦激共振以及靜風荷載等方面基本沒有明顯差異。孟曉亮等[6]研究了椒江二橋風嘴角度變化對橋梁渦振和顫振性能的影響,結果表明較尖的風嘴角度在一定程度上能降低豎彎渦振振幅,但可能對扭轉渦振帶來不利影響;較尖風嘴不會降低橋梁的顫振臨界風速。鄧斌[7]等利用數值模擬的方法研究了3種斷面的靜風穩定性和顫振穩定性,結果表明流線形雙邊主梁斷面的顫振穩定性滿足要求。楊詠昕等[8]對開口邊主梁的研究表明,增設風嘴可以改善氣流的分離和繞流形態,邊緣風嘴對繞流氣流的平滑梳理作用可以提高其顫振性能。朱樂東等[9]對典型斷面的軟顫振現象進行了研究,發現橋梁斷面的流線性越差,越容易發生軟顫振。對于流線形雙邊主梁,多孔導流板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其豎向渦激振動,豎向渦振對于多孔導流板的位置比較敏感[10]。方根深等[11]對流線形雙邊主梁斷面進行了風洞試驗,并結合理論分析,研究了其顫振穩定性能,并探討了抑流板對其顫振性能的影響。可以看出,對于流線形雙邊主梁的風致穩定性研究取得了長足進展,尤其是在對穩定性的控制措施方面,但這些措施大都是基于實際工程問題而提出,對于某些具體措施的細化研究還有待深入。
本研究采用FLUENT軟件對流線形雙邊主梁斷面的顫振導數和顫振臨界風速進行計算,分析了風嘴角度和高寬比對流線形雙邊主梁顫振穩定性能的影響。并通過顫振導數、氣動阻尼、氣動剛度和POD技術進一步研究了這些參數對其顫振穩定性能的影響機理[12-16]。
1 工程背景
以某斜拉橋流線形雙邊主梁斷面為研究對象,主梁中心處梁高3.3 m,全寬為31.5 m(含風嘴),頂面寬31.0 m,主梁斷面如圖1所示。

圖1 主梁標準斷面(單位:cm)Fig.1 Standard section of main girder (unit:cm)
2 顫振理論
根據片條假定[17-18],橋梁單位長度剛性二維節段模型的顫振運動方程為:
(1)
(2)
式中,h和α分別為模型豎向和扭轉方向的位移;m和I分別時單位長度上模型的等效質量和等效質量慣矩;ωh及ωα為橋梁的豎彎模態和扭轉模態的固有圓頻率;ξh和ξα分別是橋梁的豎彎模態和扭轉模態的阻尼比;ρ為空氣的密度;U為來流速度;B為橋梁寬度。將K=Bω/U代入上式,并通過各個自由度之間的激勵-反饋作用,建立起模型的運動方程,通過求解運動方程便可以得到系統在各個方向的運動規律。利用這種二維三自由度耦合顫振分析方法的基本原理,可以將系統各個自由度牽連耦合運動的氣動阻尼和氣動剛度的產生分為5條途徑[19]。
系統扭轉牽連運動的氣動阻尼可表示為:
(3)
系統扭轉牽連運動的氣動剛度可表示為:
(4)
系統豎彎牽連運動的氣動阻尼可表示為:
(5)
系統豎彎牽連運動的氣動剛度可表示為:
(6)
3 數值模擬
3.1 網格劃分與邊界條件
計算域設置為20B×30B,B為模型的寬度,如圖2所示,斷面的迎風側距流場入口為10B;背風側距流場出口為20B,可以保證邊界附近的流場參數較好地與所選定的邊界條件相容,同時又可以避免出現漩渦回流[20];

圖2 計算域邊界條件Fig.2 Boundary condition of calculation area
入口邊界條件采用Velocity-inlet;出口邊界條件使用Pressure out,出口壓力為0;主梁邊界條件為壁面無滑移;計算域上下面設置為Symmetry。
采用ANSYS ICEM軟件對網格進行劃分,局部網格進行加密,布置如圖3所示。

圖3 局部區域網格Fig.3 Grid of local area
為了避免網格對計算結果的影響,分別計算了12萬,15萬,18萬,21萬,24萬的網格。圖4給出了不同網格數量計算得到的斷面平均阻力系數CD。可見,隨著網格數量的增多,CD的變化幅度逐漸趨緩。網格數量達到21萬后,阻力系數CD的變化幅度很小。21萬和24萬的網格計算結果的相對誤差僅為0.01%,故本研究計算網格選擇了21萬。圖5給出了第1層網格至壁面的無量綱距離y+值,均小于1,所以計算網格可以滿足SSTk-ω兩方程湍流模型對網格壁面y+值的要求。

圖4 網格無關性驗證結果Fig.4 Grid independence verification result

圖5 壁面y+值Fig.5 Wall y+ value
3.2 計算工況
3.2.1 風嘴角度
由于風嘴角度對流線形雙邊主梁的氣動穩定性能有顯著影響,本研究在原始設計方案基礎上改變風嘴角度,計算了45°,90°兩種風嘴的顫振導數,由顫振導數、氣動阻尼、氣動剛度和模型表面壓力波動特性總結、分析風嘴角度對顫振穩定性能影響的機理。風嘴變化方式如圖6所示。

圖6 風嘴變化方式Fig.6 Changes of wind fairing
3.2.2 主梁寬高比
主梁寬高比是影響橋梁經濟指標的一個關鍵因素,為了解寬高比對橋梁氣動穩定性能的影響,分別計算了寬高比為8,10和12,這3種主梁斷面的顫振導數。寬高比的變化如圖7所示。

圖7 主梁寬高比變化方式Fig.7 Changes of aspect ratio of main girder
4 計算結果及分析
4.1 不同風嘴角度對顫振穩定性的影響
4.1.1 顫振導數分析
借助CFD動網格技術采用強迫振動法計算得到8個顫振導數,顫振導數隨風嘴角度的變化如圖8所示。45°風嘴的顫振臨界風速為87 m/s,90°風嘴的顫振臨界風速為115 m/s。

圖8 不同風嘴角度的顫振導數Fig.8 Flutter derivatives of different wind fairing angles

4.1.2 顫振機理分析


圖9 不同風嘴角度下的氣動阻尼Fig.9 Aerodynamic damping values with different wind fairing angles
從圖9(a)可以看出,90°風嘴的A項氣動阻尼的值比45°風嘴的A項值大,而B,C,E項的氣動阻尼兩種風嘴基本沒差別,只有對系統扭轉不利的D項氣動阻尼90°風嘴對應的值比45°風嘴對應的值較大,但由于A項氣動阻尼的變化更大,可以抵消D項的變化。




圖10 不同風嘴下的氣動剛度Fig.10 Aerodynamic stiffnesses with different wind fairing angles
通過對不同風嘴斷面的氣動阻尼和氣動剛度分析可見: 90°風嘴使豎彎和扭轉運動的A項氣動阻尼和氣動剛度有所提高,故 90°風嘴的顫振穩定性較45°風嘴更好。
4.2 不同寬高比對顫振穩定性的影響
4.2.1 顫振臨界風速
計算了寬高比為8,10和12時的顫振導數,采用半逆解法得到寬高比為8時的顫振臨界風速為98 m/s,寬高比為10時的顫振臨界風速為101 m/s,寬高比為12時的顫振臨界風速為114 m/s,故流線形雙邊主梁斷面的顫振穩定性能隨著斷面寬高比的增大而提高。
4.2.2 顫振機理分析
圖11 為不同寬高比斷面的系統扭轉牽連運動氣動阻尼,可見,D項耦合氣動負阻尼是導致系統的扭彎耦合顫振的最主要原因。A項氣動阻尼對于系統扭轉運動的穩定性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隨著D項氣動負阻尼增大,最終會抵消掉A項氣動正阻尼對系統的穩定作用。對于A項氣動阻尼而言,相同風速寬高比為12時的A項氣動阻尼值最大,寬高比為8時的A項氣動阻尼值最小。C,E項耦合氣動阻尼對于扭轉運動穩定性也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與之相反,D項氣動阻尼對于系統的穩定具有不利作用。

圖11 不同寬高比斷面的系統扭轉牽連運動的氣動阻尼Fig.11 Aerodynamic damping values of systematic torsional motion of section with different aspect ratios


圖12 不同寬高比斷面的系統豎彎牽連運動的氣動阻尼Fig.12 Aerodynamic damping values of systematic heaving motion of setion with different aspect ratios
圖13為不同寬高比斷面的系統扭轉牽連運動的氣動剛度,A項是扭轉運動自身所形成的氣動剛度。D項耦合氣動剛度使得扭轉穩定性提高。其他3項耦合氣動剛度對于系統扭轉運動影響不大。

圖13 不同寬高比斷面的系統扭轉牽連運動的氣動剛度Fig.13 Aerodynamic stiffness of systematic torsional motion of section with different aspect ratios
圖14為不同寬高比斷面的系統豎彎牽連運動的氣動剛度,A項氣動剛度對于提高豎彎運動的頻率發揮了主要作用。此外,B,C和E也不同程度的提高了系統豎彎運動的頻率,只有D項氣動剛度會使豎彎運動頻率降低。3種不同寬高比下的豎彎運動氣動剛度基本一致。

圖14 不同寬高比斷面的系統豎彎牽連運動的氣動剛度Fig.14 Aerodynamic stiffness of systematic vertical bending motion of section with different aspect ratios
從以上分析可見,寬高比對于系統的扭轉穩定性具有顯著影響,且隨著寬高比的增大,扭轉穩定性更好。而寬高比對于扭轉氣動剛度、豎彎氣動阻尼及氣動剛度的影響不顯著。
5 流線形雙邊主梁表面壓力波動特征
以90°風嘴為對象進行表面壓力特征研究,在表面總共布置476個測點進行同步測量,采樣頻率為200 Hz。
5.1 流線形雙邊主梁表面壓力對顫振穩定性的影響
為了更清楚的了解流線形雙邊主梁表面壓力對顫振穩定性能的影響規律,找到影響橋梁顫振穩定性能的敏感區域。便于有針對性的設置氣動措施來提高橋梁的顫振穩定性能,將模型表面分成了8個區,如圖15所示。其中左邊箱的上表面為1區,下表面及右側相鄰腹板為7區,右邊箱的上表面為3區,下表面及左側相鄰腹板為5區,兩個邊箱之間部分的上表面為2區,下表面為6區。

圖15 流線形雙邊主梁表面分區Fig.15 Partition of streamlined double-sided girder
對每個分區的壓力進行積分求得不同區域風壓對升力矩系數的貢獻,結果如圖16所示。從升力矩系數的幅值看,6區,7區和8區的壓力是升力矩波動的主導因素,1區壓力對于升力矩波動的影響也比較大,2區,3區和4區,5區的影響較其他分區小。6區,7區和8區的相位保持一致,與5區相位相比稍有滯后,與1區的相位比差了半個周期。3區,4區的相位與1區相比也稍有滯后,而2區的相位與1區的相位差為1/4個周期。可以看出,1區,6區,7區和8區為引起流線形雙邊主梁扭轉顫振的主動部分。

圖16 各分區升力矩系數Fig.16 Lift moment coefficient of each area
5.2 基于POD方法的流線形雙邊主梁顫振機理分析
將測得的模型表面壓力減去均值后進行POD分解,本算例共有476階模態,圖17為前4階模態本征值所占比例。可以看出,第1階模態的貢獻為93.91%,第2階模態的貢獻為4.54%,前4階模態的累計貢獻為99.9%。由此可知通過前4階模態能很好的重建流線形雙邊主梁的風壓場。由于第1階模態的貢獻很大,故第1階模態是引起顫振的主要原因。

圖17 模態本征值所占比例Fig.17 Proportion of modal eigenvalues
表面壓力的前4階主坐標時程如圖18所示,可見:第1階的幅值明顯大于第2,3,4階的幅值,所以第1階模態是引起顫振失穩的關鍵模態。

圖18 主坐標時程Fig.18 Time history of principal coordinate
前4階本征模態如圖19所示,各階的壓力波動均比較大。從圖19(a)可以看出,在1區前一半范圍內,壓力為正值且變化不大,而在后一半范圍,表面壓力由負值變為正值,保持為較小的恒定值,2區,6區,7區和8區的壓力均為正值且值保持為定值;3區中間部分測點的壓力值較其他部分有很明顯的增大,4區,5區的壓力值較其他區域小。圖19(b)的1區前半部分值為恒定的負值,后半部分壓力為正值且向2區的方向成遞減趨勢。2區的壓力值均為負值且其絕對值在橫風向逐漸增大。而其他區域的壓力值均較第1階相應區域的小。對于圖19(c),第3階1區上表面的壓力為負值,7區及8區的壓力均為正值;2區的壓力與第2階基本相同,6區的壓力為負值且在斷面中心偏右部分出現峰值。右邊箱的壓力很小。第3階的能量占總能量的0.98%,圖19(d)中出現了相鄰監測點壓力正負交替出現的現象,圖19(c)也出現類似的現象,這主要是斷面外形引起的特征紊流形成的結果。

圖19 90°風嘴斷面表面壓力POD模態Fig.19 POD modes of surface pressure at 90° wind fairing section
可以看出,前4階模態的壓力值在1區的中間部位有較明顯的變化,這很可能是由于在此處生成的較小漩渦引起的;壓力在1區和2區之間也有很明顯的增大,但在3區并沒有較大的壓力分布,這可能是由于漩渦經過2區,并在2區得到充分發展,然后在2區末端漩渦脫落。
為了更深入地了解風嘴角度的引起的表面脈動壓力變化,圖20給出了風嘴角度為45°斷面前4階模態的表面壓力分布。

圖20 45°風嘴斷面壓力POD模態Fig.20 POD modes of surface pressure at 45° wind fairing section
由圖20可見,能量占比最大的第1階模態在1區,6區,7區和8區的壓力值都比90°風嘴相應區域大,這也反應了這些區域是引起顫振的主要原因。與90°風嘴的表面壓力分布相比,2區的壓力值略大,3區的壓力值也比較連續,并且2區與3區之間并沒有產生壓力突然變化的現象,其他區域壓力分布比較相似;第2階模態在2區的壓力值基本保持為恒定值,3區的壓力值與2區類似,只是在3區中間部分壓力突然由負值變為正值;第3階模態在2區的壓力很小,但在3區壓力持續增大,在3區中間部分達到峰值后開始減小;第4階模態的2區沒有壓力,在3區壓力出現且持續增大,在3區中間部分達到峰值。與90°風嘴斷面前4階模態相比,45°風嘴斷面前4階模態壓力在2區與3區之間比較連續;45°風嘴斷面上表面出現壓力峰值的位置與90°風嘴斷面相比有所滯后。
通過以上比較可以看出,風嘴角度變化引起斷面脈動壓力分布的變化主要體現在上表面區;風嘴由尖(45°)變得比較鈍(90°)時,壓力在上表面開始變得不連續,且壓力峰值的位置開始前移。原因主要是當風嘴較尖時,斷面流線形較好,大尺度渦從2區開始逐步發展,在3區中間部分達到最大,至右側風嘴處才完全脫落;當風嘴變鈍之后,大尺度渦脫在上表面脫落的區域提前,在2區形成并由一定發展,隨后在2區與3區之間出現脫落,并沒有再附到下游斷面上。
6 結論
(1)風嘴角度對流線形雙邊主梁顫振穩定性的影響比較顯著。90°風嘴對于系統氣動阻尼的提高更加顯著,對顫振穩定性更有利。
(2)寬高比主要影響流線形雙邊主梁豎彎運動,寬高比越大,結構的顫振穩定性越好。
(3)根據流線形雙邊主梁斷面表面壓力對升力矩系數的貢獻,判斷流線形雙邊主梁左邊箱部分及兩個邊箱之間部分的下表面是誘發顫振失穩的主要原因。
(4)基于脈動風壓POD分解方法判斷不同風嘴角度會引起上表面壓力分布的不同,風嘴角度比較尖時,漩渦脫落的位置在下游風嘴處,隨著風嘴角度變鈍,漩渦脫落的位置會向上游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