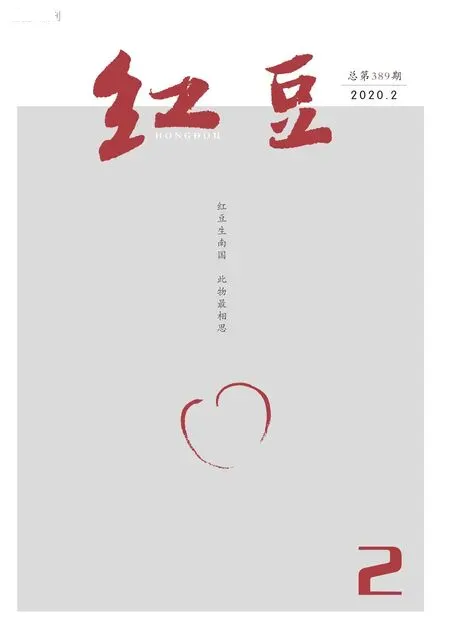我與《紅豆》的緣起
次仁羅布
許多年前,我就知道有一本刊物叫《紅豆》,它在文學期刊里名氣還是比較響亮的。至于它是哪里辦的,倒沒有太多的注意。我常常對許多影響很大的文學刊物懷著一種崇敬的心情,覺得它離我是那么的遙遠、神圣,在那上面能發表作品的都是最具實力的作家。因而,我很少給文學名刊投稿,主要原因是自己心虛,說直接點就是對自己寫出的作品缺乏信心。
很多朋友會覺得我說這話有點矯情,其實真的不是這么一回事。每當自己寫完一篇作品,有時自我感覺很茫然,有時又感覺什么都不是,只能把寫好的小說發給最好的知己,請她談談閱讀感受。在一次次的意見、建議中不斷進行修改,完善內容,字斟句酌,在反復錘煉中讓作品的品質得到提升。我就是在聽取別人的意見中前行,所以可以稱作是最沒有自信的一個作家。這里我稱自己為作家,心里還是怯怯的,“作者”“作家”這兩個詞許多時候會困擾著我,寫文章時我更愿意稱呼自己為作者。作家在我的心目中是那些為人類寫出不朽作品的偉大人物,作者離他們相去甚遠,達不到他們的精神高度,只能望其項背,匍匐前行。一個作者是要拿作品立身、拿作品說話的。
扯了這么遠,主要是想說《紅豆》竟然看上我,看上一個寫作很不自信的我。
跟《紅豆》的緣起,是中國作家協會舉辦的一個活動。我們一行人坐上大巴從駐地去活動點,正好在大巴車上認識了旁座的張凱老師。他給我介紹《紅豆》這本雜志,還熱情地跟我約稿,邀我到廣西南寧。我們的交談很融洽,相互留了電話號碼并加了微信。那時我才知道《紅豆》是南寧市文聯主辦的刊物。沒有想到過了幾個月,張凱老師打來電話跟我約稿。這讓我心里很溫暖,想著他一直惦記之前跟我約定的事。我也欣然接受,說好年底交一篇作品。我開始創作短篇小說《那片白云處是你的故鄉》,這個素材老早就在我腦海里縈繞,只是不知道從哪里切入最好。因為我住的那個社區分來了幾個牧區易地搬遷過來的人,他們穿著環衛工人的服裝,拿著一把大掃帚在每個巷子里掃地。他們天不亮就上班,天黑才回家,中午坐在巷子的一個角落里,吃自帶的飯菜。這種場景,讓我的心里很是疼痛。以往他們馳騁在遼闊的草原,無拘無束、自由散漫慣了,但到了城里就禁錮在一個社區里,他們心里的落差、痛苦誰人能理解?他們適應城市生活過程中的那份煎熬與掙扎又有幾人知曉?這些問題讓我很困擾。有一次我問一名領導:“他們幸福嗎?”她皺眉思索片刻后說:“只能犧牲他們這一代來換取下一代的幸福!”我帶著很多的問題完成了這篇小說。當我把最后的定稿發過去時,比答應的時間晚了十多天。
最讓我意外的是,作品發表在二〇一九年《紅豆》第一期的頭條上,不久被《小說選刊》轉載。時任主編丘曉蘭還寫了一篇《想起一首歌》的文章,談編輯這篇小說的體會與過程。讀完讓我對編輯的一絲不茍與責任心肅然起敬。
二〇一九年底,我受《廣西文學》編輯部的邀請,參加年度優秀作品頒獎會。沒有想到的是,張凱老師專程跑到酒店來看望我,還挽留我在南寧多待幾天。只因我要趕去云南魯甸,那邊還有關于脫貧攻堅的采訪任務,時間不能耽誤。我跟張凱老師在房間里聊了一會兒,答應再給《紅豆》一篇小說。《紅豆》不僅刊發作者作品,還積極向全國各大選刊推薦作品,對作者和作品是非常負責任的。難怪微信里的“《紅豆》優秀作者群”里有那么多全國優秀的作家,他們都信任這本刊物,信任這些編輯,把將作品交給《紅豆》當成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我跟《紅豆》的再次續緣是在二〇二〇年底,當時我已完成云南魯甸的脫貧攻堅報告文學,騰出時間完成了短篇小說《達瓦爾旬努》,但是自己不敢確定這篇作品寫成什么樣子了,發給我的第一讀者,請她感覺一下。她沒過多久就給我回復微信,提出了作品中存在的一些細節問題和個別錯別字,我也仔細地進行了修改,再次發過去,給出的是肯定和認可。我這才有信心,把作品給《紅豆》發過去。《達瓦爾旬努》被《紅豆》雜志刊登在二〇二一年第一期,作品被《長江文藝·好小說》和《思南文學選刊》等轉載。這一切都得益于《紅豆》這個平臺,正因它的影響力,許多選刊才對它關注,才使作品的影響力擴大。
作為一名寫作者,我對《紅豆》這本刊物充滿感激!也期待《紅豆》越辦越好,多出精品,多出年輕的作者。
責任編輯? ?謝? ?蓉
特邀編輯? ?張? ?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