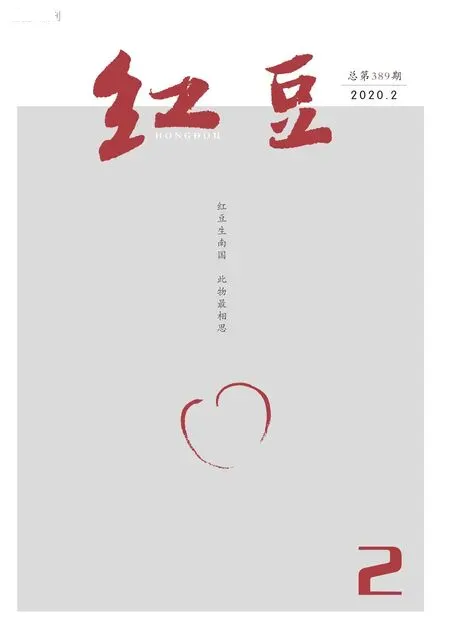草木深
伍岳
農(nóng)歷八月,暑熱還未散盡,秋風(fēng)只在清晨與夜間拂動微涼。南方的秋天來得潤,葉片完全沒有枯黃凋零的跡象,而山上一種叫作“八月拿”的野果已經(jīng)成熟。
清晨,留在村里的中青年,邀約結(jié)伴上山摘“拿”。大家陸續(xù)聚集起來,走山路,騎摩托車相對方便,技術(shù)夠好的話,能夠直接騎到山腰。他們把蛇皮袋往尾箱一放,三五個(gè)人,坐兩三輛騎摩托車,就在澄澈的天空下,一路轟鳴,驚起一群白鷺。如今的鄉(xiāng)村,留守的人少,只有逢年過節(jié)才顯出熱鬧,如果換作以前,到這個(gè)季節(jié),田間到處是農(nóng)忙的景象,山上則是砍柴與嬉鬧的身影。
“八月拿”是贛南鄉(xiāng)村一種常見的野生植物,學(xué)名為木通,但在地方上,卻以方言“八月拿”“牛卵坨”等叫法為主。史料和文人墨客的詩詞中,似乎難以找到相關(guān)記載,也許是它過于普通,又或者它只在少數(shù)地區(qū)生長,我未曾考據(jù)。它屬于野生藤本植物,第二年開始結(jié)果,第三年進(jìn)入盛果期。花期在四五月,果期則要到八至十月。未成熟時(shí),果皮呈綠色,成熟時(shí),表皮、果實(shí)顏色轉(zhuǎn)為金黃色,故得此名。其果實(shí)呈腎形或長橢圓形,稍彎曲,與芒果相似,卻要糙一些,內(nèi)部果肉略像成熟的軟柿子,一顆一顆粘連,籽黑色,像西瓜籽,但是圓潤一些。其果實(shí)富含維生素B、維生素C,味道香甜可口。
近年來,有商家開始人工種植,對外售賣,卻沒有了兒時(shí)的味道,要尋味的話,還得上山去。“八月拿”滿山遍野,藤長根深,往近旁的樹一繞,任性生長。三月,當(dāng)它撐開五至七片枝葉時(shí),仿佛新生的手掌,要去觸碰明媚的春光;五月,蜜蜂和蝴蝶的熱鬧唱過了幾個(gè)山頭,為群芳傳播授粉;九月,綠浪中點(diǎn)綴的金黃,是童年無法復(fù)制的記憶。與其他野果一樣,它對贛南的土壤氣候極其適應(yīng),不畏旱澇,只管鉚足了勁,頑強(qiáng)地生長著。
小的時(shí)候,我們一群人徒步上山,往密林深處探尋,大家互相照應(yīng),以免掉隊(duì)。“八月拿”的果實(shí)綴滿土崖畔,星星點(diǎn)點(diǎn)掩映在綠浪之中。長在泥路近旁崖壁上的“八月拿”,我們便隨手撿了石頭,一個(gè)勁地往枝干上扔,砸下來的概率不大,大家卻玩得極有興致。真正能摘到許多“八月拿”的地方在山窩里,植被茂密,從遠(yuǎn)處看,根本沒有路可進(jìn),等我們沿斜坡小道攀下去以后,才發(fā)現(xiàn)下面別有洞天。細(xì)竹、杉木、腎蕨等,還有一些不知名的藤蔓,架起一個(gè)內(nèi)部鏤空的原始空間,人彎腰可以鉆進(jìn)去,頭頂雖有植被,卻透出光,視線還算良好,地面鋪了一層落葉,許是年久積累下來的。大家彼此喊著,以免走散,用手撥開一些枝干,穿梭在忽緩忽陡的地面,貓著身子向前;有人發(fā)現(xiàn)了目標(biāo),大喊一聲,其他人便循聲而去。大家摘下來的果實(shí),用衣服兜著,或者用蛇皮袋裝,偶爾還能找到成串的果實(shí)。一般來說,拳頭大小的果實(shí)才好吃,太小的和被鳥雀啄食過的會被扔掉,有些熟透了,卻未被采摘或啄食的,掉在地上,不免讓人感到惋惜。小半天過去,大家邊從山窩里出來邊吃,回到主路,路上是剝掉的皮和吐出的籽,嘴里是如蜜的果瓤,歡聲笑語,連說話聲都是甜的。回到家,母親看到我一身臟兮兮的污漬,自然免不了一頓訓(xùn)誡,我卻也顧不得了。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人走出深山,走向遠(yuǎn)方,到城里務(wù)工、定居,孩子們到城里學(xué)校讀書,鄉(xiāng)愁留給了月亮、鄉(xiāng)音和逐漸剝落的老屋土墻,越偏遠(yuǎn)的村莊,這種情況越甚。同時(shí)留下來的,就是“八月拿”這些野果,它們難登大雅之堂,只管在山林間恣意生長,卻成為無數(shù)人童年的味覺記憶。
最近一次摘“拿”,是在一個(gè)較為偏遠(yuǎn)的村莊駐村,村名叫紅桃,位于羅霄山脈余脈。該村附近群山環(huán)繞,郁郁蔥蔥,正是摘“拿”的好去處。夏末時(shí)節(jié),我便約外幾個(gè)鄰村的駐村干部,一同上山摘“拿”。如今,借助新農(nóng)村建設(shè)、精準(zhǔn)扶貧和鄉(xiāng)村振興的東風(fēng),村莊交通便捷,路面基本上已經(jīng)硬化,汽車能開到山腳,把車子往路邊一停,大家便動身上山。作為鄉(xiāng)干部,我們是走慣了山路的,并不懼怕山路陡峭。一番折騰,“八月拿”摘在手里,我們仿佛又變回了那個(gè)饞嘴的少年——那種揮之不去的甜,深藏在我們的味蕾中,不會隨著心境變化而有所改變,山和土地一直在那里哺育著一切努力生長的萬物,給它們一個(gè)歸宿。
相對于“八月拿”來講,拐棗名氣可就大了許多,《詩經(jīng)·南山有壹》就記載著:“南山有枸(枸即枳椇,拐棗的學(xué)名)”的詩句,而古語有云,“枳枸來巢,言其味甘,故飛鳥慕而巢之”,可見其歷史悠久。拐棗分布廣,在黃河流域以及長江流域各地,都可以找到它的蹤跡。朝鮮、俄羅斯等國也有生長。因?yàn)樗墓麑?shí)形態(tài)與“卍”字相似,古人按諧音給它取了萬壽樹的別名。拐棗還有醫(yī)用價(jià)值,其梗、果實(shí)、種子、葉片及根莖均可入藥,其藥用最早見于《唐本草》,李時(shí)珍《本草綱目》稱它“味甘、性平、無毒,止渴除煩,去膈上熱,潤五臟,利大小便,功同蜂蜜” 。
上一次摘拐棗,是前幾年在村里搞精準(zhǔn)扶貧的時(shí)候。彼時(shí),霜降一過,水稻早已收割完,稻茬佇立于空曠中,伴著牛哞哞叫和雀鳥的鳴叫,我和同事入戶走訪完貧困戶后離開,在折返村委會的途中,同事驚奇地發(fā)現(xiàn)水泥路面上落葉之間有些星星點(diǎn)點(diǎn)的東西,抬頭一看,滿樹的拐棗正掛在那里。拐棗樹葉片已經(jīng)不多,枝頭上掛滿了果實(shí),綠棕色,和樹皮顏色相近,形狀歪七扭八,筷子粗細(xì),猶如雞爪,不認(rèn)識的人可能以為這是種子,而且還是頂丑的種子,但我們卻找樹枝鉤下來吃。掉落在地面上的很多已經(jīng)干癟,樹上的挺飽滿,熟透了,就不覺得澀,而味覺總會把人牽扯回最初的記憶。
我還記得,第一次接觸拐棗,是在很小的時(shí)候,六七歲的樣子。那時(shí)候,我們把家搬到我母親當(dāng)年工作的江西省第一制糖廠。
江西省第一制糖廠在二十世紀(jì)算是一顆璀璨明珠,偌大的院落,類似于如今的一個(gè)社區(qū),住房、工廠、醫(yī)院、學(xué)校、食堂、禮堂、球場等一應(yīng)俱全,這些場所給了我們充分的游玩空間。一次,我們一群小伙伴——我已經(jīng)忘記大部分人的名字——繞過廠區(qū),往圍墻外走,圍墻外是上猶江,我們熟練地從圍墻裂開的一條縫擠出去,沿著墻角,到一塊稍大的平地時(shí),我們從一個(gè)青磚堆砌的墻基攀下去,墻的高度應(yīng)該不到一米八,但是當(dāng)年年紀(jì)小,身高不夠,探不到地,前面一個(gè)踩著磚縫滑下去后,就幫忙來托。整個(gè)隊(duì)伍下來以后,我們并沒有確切的目的地,只是一心要出來玩,就這樣緩緩地往前走。
臨近河灘時(shí),發(fā)現(xiàn)有一棵碩大的拐棗樹立在那里,大家嚷起來。地上沒有多少,多數(shù)還在樹上,我們便撿起地上的樹枝去扔。扔不下來,有人就直接爬上樹,用力去搖。吃了一陣,我們一人一把揣兜里帶回去,說笑聲中都是拐棗味。聽人說拐棗可以泡酒,取白酒一瓶,新鮮拐棗一把,去拐籽,清洗三遍,開水殺菌一遍,晾干,取棗入瓶,泡半月以上即可品嘗,味道甘美。
回憶起這些野果時(shí),我想,人類文明不管發(fā)展到什么階段,都擺脫不了向自然索取這一事實(shí),向大山和土地索取食物,向河流索取瓊漿。大自然無私地向我們提供飽腹、保暖、治病等的物品,人類應(yīng)該懂得感恩,并與自然和諧共生,達(dá)到生態(tài)的平衡,否則,向自然過度索取的后果,是人類無法承受的。
歲月有去無回,轉(zhuǎn)瞬之間,我也已經(jīng)做了父親。女兒四歲多了,卻還沒有吃過拐棗,市場上似乎也不興賣。我第一次見拐棗的糖廠廠址還在那里,只是已經(jīng)倒閉二十多年,輝煌不再,這個(gè)曾有過兩三萬名職工的地方,留在了幾代人無法磨滅的記憶里,如今已然改建為社區(qū),許多家具廠在這里“落戶”,多數(shù)是外地務(wù)工者。土木結(jié)構(gòu)的房屋還在,白色墻體早已剝落,露出黃色凹凸不平的泥土,斑駁了歲月的同時(shí),與如今社會的發(fā)展似乎有些格格不入。我在前幾年回去過一次,拍了些照片,當(dāng)我重新翻看這些照片的時(shí)候,我突然冒出個(gè)想法,要等我女兒再大一點(diǎn)、能記事的時(shí)候,帶她重走一遍我小時(shí)候住過的地方,尤其是那些還保留著一點(diǎn)當(dāng)年模樣的地方,然后,再去找一找那些在味覺上留給我童年印記的野果,找一找那些只能從泥土里給予我們的東西,也算是給女兒留下可供她回味的童年。
責(zé)任編輯? ?練彩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