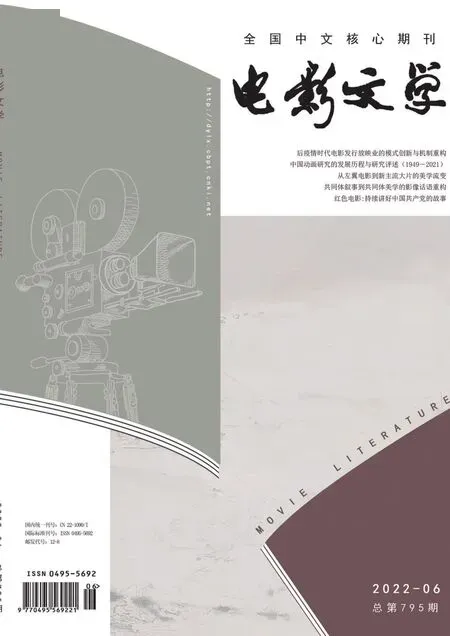《藍白之上》:非物質文化遺產題材紀錄片的影像建構
馬 麗
(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北京 100048)
2016年播出的紀錄片《藍白之上》主要展現了云南大理喜洲鎮周城村的白族扎染這一有著1000多年的非遺文化。紀錄片圍繞著扎染的操作步驟和流程,通過空間影像的建構,生動而細致地呈現了扎染技藝的特點和所蘊含的民族文化與地域特色,以及在扎染的傳承和創新方面的成功嘗試,不僅表現了扎染技術的延續,還展現了扎染精神的傳承和扎染傳承人對標準的堅守。
一、源自日常生活的影像素材采集
埃德曼說“藝術是理解自身生活狀態并將其轉化為最有趣最絕妙東西的智慧過程”。藝術與生活密不可分,非物質文化遺產本身具有民族性和生活性的典型特征,非遺類紀錄片的責任和宗旨之一就是用藝術的方式記錄和展現深度融入生活的文化遺產。取材于生活的影像能夠更加準確地把握文化之根和藝術之源,《藍白之上》的影像建構在這方面也下了很大的功夫,通過生活中的素材塑造出了一人、一城、一村、一事的人間煙火氣,用真人、真事傳達真情、真感,最是動人。
(一)勞動場景的展現
1.獨自勞動
段銀開作為影片的主要人物,在銀幕上呈現給觀眾的是一個勤勞的白族婦女的形象,影片花費大量的鏡頭記錄她制作扎染的全部流程,染料制作、繪圖、制版、印花、扎花、染布、拆線、漂洗都親力親為,呈現了豐富而真實的勞動場景。影片開始,段銀開拿著竹編籃子采摘染色用的板藍根,板藍根每年4月采摘1次,8月采摘1次,12月采摘1次,接著就是將板藍根撒入染色大缸制作染料,每次打80到100下,每天打3次。這些詳細的數據不僅是段銀開作為非遺傳承人對于扎染技藝的熟悉,更是扎染本身繁重工作內容的生動寫照,讓觀眾感受到了手工技藝的珍貴與不易。
2.集體勞動
在周城村,扎染是每個白族婦女的拿手活計和必備技能。片中婦女們聚在一起穿針引線扎花的鏡頭多達10余處,母女二人,婆媳二人,祖孫二人,年輕女孩二人或三五鄰里聚在一起扎花的場景不僅給觀眾以視覺的享受,老人們唱著古樸調子更是帶給紀錄片濃厚的生活氣息,唱歌的內容也是講述生活瑣事,喜怒哀樂,讓觀眾深切體會到了白族婦女集體勞動的日常生活狀態。通過集體勞動的展現,描繪了白族婦女的勤勞,也感受到了一針一線中的工匠精神。白族人通過這一針一線縫出了柴米油鹽生活所需,也縫出了扎染的未來,現在的白族扎染受到越來越多人的喜愛。
(二)休閑場景的展現
相比于緊張的勞作,生活中的休閑場景有效地調節了紀錄片的節奏。段銀開作為其家族內將扎染發揚光大的人,肩負著推動扎染在后代中傳承的重要使命。從其口述中得知,段銀開的扎染情結來自日常生活中父母的耳濡目染,自己的努力更是源于對扎染的熱愛,扎染已經融入了白族人的血脈當中,白族人從生到死離不開扎染,小孩的衣服、腰帶、包袱都是藍白之色的扎染布制作,死了穿著藍白的扎染布料入葬。段銀開將這份手藝傳給了自己的女兒,片中有一段溫馨而恬靜的畫面,段銀開和女兒在天井里對坐,一起扎花,閑聊,更多的時候僅是安靜地做著手里的活計,段銀開從6歲女兒段興語的身上看到了自己小時候的影子。在這每天的對坐閑聊的休閑場景中,扎染技藝實現了傳承,女兒扎花時專注的表情和熟練的動作,預示著扎染后繼有人。
(三)生活困境的展現
非遺傳承有苦也有樂,苦樂交織才會凝聚出非遺絢爛的生命色彩。生存是每個人面臨的壓力,對于依賴扎染生活的周城白族人來說,扎染生意的好壞直接關系著生活的質量,從段銀開的口述可知,2003年到2004年當地染布坊有10來家,因為虧錢做不下去,現在只剩下3到4家。要生活下去卻不能斷了傳承,周城的白族人面臨著多重的壓力,這種壓力也讓觀眾深有同感,普通人每天都面臨著生活和生存的兩難選擇。作為扎染傳承人的段銀開并沒有放棄,執著而堅定地繼續著扎染事業。“傳中有變”是時代的需要,也是非遺傳承的必然選擇路徑。段銀開大膽創新,研發新的植物扎染產品,鏡頭展示了紅色、綠色的扎染布匹,以及用這些色彩鮮艷的布匹做成服裝和包包,豐富的扎染商品種類,推動了扎染的發展,讓扎染的商品成為外地游客購買的熱門紀念品,甚至登上了國際服裝展示的大舞臺,受到了全世界的關注,創新讓段銀開染出了新的人生色彩和民族色彩。片中展示了多件彩色的扎染作品,以及整部紀錄片中段銀開穿著彩色的扎染衣服,無時無刻不在昭示著這場變革的成功,觀眾也能通過畫面由物及人,透過影像看精神,真切感受到扎染傳承人的快樂、富足、傳承和堅守。
二、視聽結合的影像建構方式
讓·米特里說“電影本質上是一種具體的藝術,是將具體事物變成表意系統的藝術”。人、物、音樂、山、水是構成藝術的常見元素,《藍白之上》的影像建構采用的是視聽結合的方式,營造了一種詩境的氛圍,詩境的構成是通過一系列的地域和民族文化符號的靈動呈現與合理組合。
(一)影像建構的色彩搭配——藍白之韻
電影的基調顏色是感情基調的真實反映,也是影片風格的體現,不僅可以烘托氛圍,表達情感,更可以帶給人意境美的享受。《藍白之上》的色彩簡單而專一,即藍和白。紀錄片的開頭和結尾,導演都將鏡頭聚焦了蒼山的雪白,洱海的深藍,以及藍天中飄動的白云。青瓦白墻的居住院落,藍色和白色成為大理重要的文化介質,體現了人與環境和諧共生的至高境界。藍色通常被認為是憂郁和冷靜的色調,白色則象征純潔、美麗、明亮,但在這部紀錄片中,藍色絲毫不會讓人感到憂郁,因為大理的山水、白族的文化賦予了藍色新的生命內涵。紀錄片開頭,作為扎染傳承人的段銀開表述了自己對藍和白的喜愛,既是個人最喜歡的顏色,也是白族的顏色,家鄉大理的顏色,藍色和白色滲入到了白族人的精神層面,成為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凈凈做事的精神指引。這種喜愛并非淺薄表述,而是與扎染人融為一體,為整部紀錄片奠定了藍白基調。紀錄片以快速切換五光十色的多個場景為起始,讓觀眾感受到世界有很多的顏色。緊接著,一塊傳統扎染的藍白相間的布匹覆蓋了整個鏡頭,引入了紀錄片的顏色主體,即藍色和白色,接著就是藍天上白云飄過的景象,將人為塑造的藍色和白色與大自然的藍白融為一體,蘊含了天人合一的美好意愿。紀錄片的中間,導演給了存放板藍根的大缸一個特寫鏡頭,大缸中的水變成了藍色,向觀眾訴說著扎染藍色的源頭是蒼山之上的植物板藍根。此外,掛在天井中的一條條染好的藍白色的布隨風飄蕩的鏡頭也出現了多次,將藍白的顏色基調不斷強化。影片結尾部分,將段銀開在紀錄片開頭的解說詞又重復了一遍,作為與影片開頭的呼應,配以的影像則換成了大理的蒼山、洱海、藍天、白云,及在水上撐著竹筏捕魚的大理人,將恬靜和美的大理生活真實地展現,沒有電腦合成與虛構,都是實實在在,真真切切。
不同的民族、地域、時代有著不同的喜歡的顏色,世界雖是多彩,但屬于大理和白族的顏色永遠是藍色和白色,藍色和白色融入到白族人民的血液當中,世間唯有藍白得以慰藉靈魂,雖然現在的扎染有了更多豐富的色彩,但藍和白永遠是扎染的根,是扎染這門傳統技藝的源頭。經歷了千百年,扎染的精神在千萬白族人生命中延續與發展。
(二)影片音樂的使用
音樂的使用在紀錄片中十分普遍。《藍白之上》中的音樂運用恰到好處,但主要作用是輔助圖像畫面完成影像塑造。輕靈歡快和幽遠空靈是音樂整體風格,在影片的開頭,伴隨著輕靈而歡快的音樂,紀錄片的名稱被以藝術的字體書寫出來,在介紹大理的山、水的部分,伴隨的是幽遠空靈的音樂,與云南的地理位置及風光十分契合。片中采摘板藍根、制作植物染料、扎花、染色等情景都是配以歡快的音樂,當扎染作品完成,母女二人一起展示勞動成果的畫面中,凝重幽遠的音樂烘托出了扎染傳統技藝的歷史厚重,帶給觀眾藝術的震撼。紀錄片的結尾,鏡頭再次展現了蒼山的白雪,洱海的深藍,緩慢而厚重的音樂完美契合了扎染技藝傳承的延續,以及不忘山水間藍白之根的影片主題氛圍。
三、凸顯文化印記的影像建構特色
技藝的誕生與發展離不開所在地域與民族文化,《藍白之上》中的影像也關注了云南文化和白族文化元素,為紀錄片的影像構建打上了文化的印記。
(一)本主文化的展現
白族傳統文化中,蘊含著對自然物的崇拜,崇拜天、崇拜地、崇拜水、崇拜石,白族奉行本主文化,塑造了白族人勤勞、勇敢、自信、開放的民族性格。大理的蒼山、洱海、藍天、白云是白族人的生之所依,死之所往,白族的扎染也與這方山水、天地密不可分,染料來自蒼山,染布的水來自洱海,扎染的顏色來自天空之藍,蒼山上的白雪,藍色和白色是大理的顏色,民族的顏色。本主文化既是白族人民的精神支柱,也是生活指引,生存所依,已經融合血脈當中,融入到扎染技藝之中,也融入到了精美的充滿文化和歷史氣息的扎染作品當中。透過布匹中的藍白之韻,觀眾可以感受到其中蘊含的勤勞、樸實、勇敢的本主文化氣息,染布堅持使用自然植物染色,經由白族男人和女人勤勞而靈巧的雙手完成扎花、染色,在傳統的歌聲中,一針一線縫出了大理的山水氣韻,讓扎染本身充滿了靈性,不再是一塊不會說話的布匹或者一件簡單的衣服,而是一段歌,一首曲,一行詩,一段情,讓觀眾十分向往和留戀。
(二)民居特色
整部紀錄片的鏡頭大部分是在白族傳統的民居中拍攝完成的。紀錄片中的民居特色留給觀眾深刻印象,民居是家園文化的重要載體,中華民族對于家的向往和熱戀是由來已久,在寫著“藝林藏秀”的照壁,寬敞方正的大天井里,段銀開在這里晾曬染好的布,放著制作染料的水缸,片中一個鏡頭就是段銀開在水缸中撒入板藍根制作染料,說明這是工作的場所,也是母女交流,傳承技藝的絕佳地點。在這里女兒跟媽媽學習扎花,雖然并沒有很多的話語,片中段銀開和女兒動作上的交流也只有一次,就是媽媽幫助女兒剪去扎花時露出的線頭。雖然這只是一幅安靜的畫面,卻充滿了溫馨和恬靜的生活氣息,觀眾能夠真切感受到母女的心是在一起的。同樣,天井、照壁、精美裝飾的圍墻,還有瓦頂飛檐,給紀錄片增添了很多的民族魅力。
《藍白之上》的成功在于將非遺傳承中的傳統藝術與技藝的展示和傳統匠人職業精神的傳承完美結合。不僅展示了扎染的多彩文化,還塑造了扎染精神與智慧的活態傳承。展現了扎染技藝所蘊含的大理獨特的韻味,為非遺類紀錄片的制作提供了可參考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