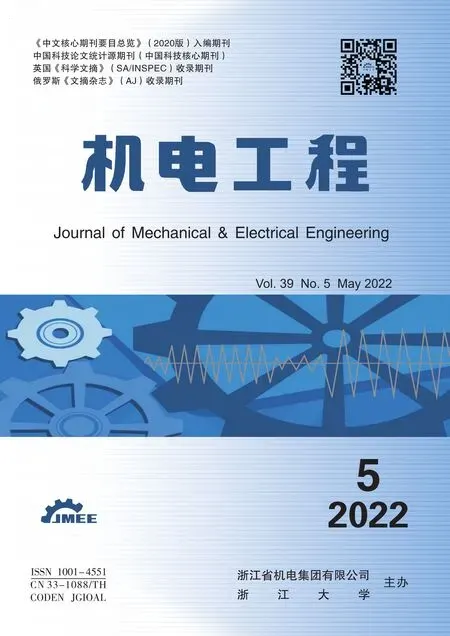乘用車輪轂軸頸承載能力研究*
陳偉軍,黃德杰,汪 峰,楊 杰,靳 陽
(浙江萬向精工有限公司,浙江 杭州 311215)
0 引 言
乘用車輪轂軸的承載能力是乘用車輪端的一項非常重要的指標,涉及到整車行駛安全性。隨著汽車行業的發展,現有輪端軸承的壽命越來越高,已可做到與整車等壽命,因輪轂軸承滾道剝落引起的失效比例越來越少。
隨著輪轂軸承滾道的壽命得到了強化,在輪轂軸承軸端失效的短板逐漸凸顯出來。在實際使用過程中,輪轂軸承軸端頻繁發生沖擊斷軸、疲勞斷裂等安全事故[1-3]。
尹輝俊等人[4]基于NX.Nastran軟件與試驗,對乘用車車軸疲勞的性能進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一種疲勞設計方案;但該研究缺乏對車軸實際應用工況中沖擊特性的考慮。操龍飛等人[5]分析了輪轂軸斷裂的沖擊原因,提出了一種改進軸頸R角的熱處理建議,而該建議中熱處理的有效性尚未得到證實。胡春燕等人[6]研究了輪轂軸斷裂的疲勞特性,提出了輪轂軸斷裂缺陷的原因在于鍛造工藝不合理。
以上學者的研究均停留在轂軸斷裂失效分析與原因的可能性推測上,而未進行其失效復現與改進方案的論證,因此,較難為輪轂軸的設計給出準確的指導意見。
筆者通過從斷裂問題失效分析、產品優化工藝、試驗論證多維角度確定產品承載能力的關鍵因素,為指導可靠承載能力的輪轂軸頸設計提供重要參考。
1 問題背景
某車型在終端客戶使用過程中,不斷發生軸頸沖擊斷裂的安全問題,導致了成千上萬輛該型汽車被召回。
車軸斷裂圖如圖1所示。

圖1 車軸斷裂圖
經調查,該車軸在設計過程中經過了多輪次的開發論證:首先,參考了客戶的國外設計圖紙;其次,按照客戶的設計輸入要求進行了精密設計計算校核;再次,在試驗臺架上進行了耐久性與疲勞強度試驗;最終,也通過了客戶處的整車道路試驗。
即使經過多輪開發把關,仍無法將該問題避免于產品的開發階段。
問題發生后,筆者對發生斷裂的車軸工作條件進行了分析,發現所有發生斷裂的車軸均存在路面行駛過程中的側向沖擊特征,沖擊的惡劣程度高低不一。
為此,輪轂軸承供應商對整車的設計過程重新進行了審查,發現按照主機客戶的開發要求,該產品未按照SAE J175或GB/T 15704等標準進行沖擊試驗的論證[7-9],并未確認出該產品的抗沖擊能力,主機客戶與軸承供應商均未識別出抗沖擊需求,開發過程中僅以靜態壓力試驗所規定的壓斷載荷來確定產品的強度,顯然該試驗并不能完全替代沖擊試驗。
問題發生后,輪轂軸承供應商重新進行組織,進行了抗沖擊性輪轂軸新產品試制、試驗探索與分析,為進一步解決該問題找到了方案。
2 樣品斷裂分析及優化
筆者在大量的斷裂失效樣品中選取1組樣品進行深入的斷裂原因分析。
2.1 斷裂源定位
低倍顯微鏡下斷口宏觀形貌圖如圖2所示。

圖2 斷口宏觀形貌圖
斷口起源于軸頸的外徑表面,裂口源集中于一點,呈發散狀,向軸頸的對面擴展,并發生整體斷裂[10]。軸頸截面的外層組織細膩,為淬火組織,內部組織粗大,為正火組織。
斷裂位置截面圖如圖3所示。

圖3 斷裂位置截面圖
通過軸頸總成顯示:斷裂截面位于軸頸與輪轂軸承連接配合的轉折截面,為應力集中的一個截面,在該截面上的工作應力最大,屬于軸頸的薄弱截面。
2.2 原因分析
為分析斷裂的原因,筆者進一步開展了對其加工尺寸、材質與熱處理的分析。
與軸頸沖擊強度有關的因素包括:軸頸直徑、斷裂源外表面圓弧、斷裂源圓弧粗糙度、斷裂源處夾雜物水平、熱處理硬度、組織、晶粒度、流線因素,經過系統的分析排查。
斷裂原因調查分析結果如表1所示。

表1 斷裂原因調查分析結果
軸頸表層淬火組織如圖4所示。

圖4 軸頸表面淬火組織500X
軸頸芯部組織如圖5所示。

圖5 軸頸芯部組織500X
筆者將與斷裂有關的所有因素進行逐一排查分析,未發現不符合設計要求的項目,該零件不存在缺陷,從設計角度能夠滿足使用要求,需要進一步對軸頸進行優化設計與試驗論證。
2.3 樣品優化
經過與同類產品在其他客戶處(如大眾、奧迪、捷豹路虎、福特等)的使用情況調查可知[11,12],軸頸材質均為SAE1055,對軸頸的熱處理方式主要有4種:正火、正火+表面淬回火、調質、調質+表面淬回火[13]。
為研究不同的工藝條件對產品性能的影響,筆者采用了4種工藝方法進行產品的性能論證。
工藝試制樣品的性能參數如表2所示。

表2 工藝試制樣品的性能參數
3 試驗結果及改進
3.1 試驗項目
完成樣品試樣后,筆者為論證4種工藝方法對產品的承載能力,開展4類強度與剛度試驗,綜合對比評估試樣的性能。
4類試驗規劃如表3所示。

表3 4類試驗規劃
3.2 試驗結果與分析
筆者依據表3試驗條件開展4類試驗,試驗結果與分析如下:
3.2.1 靜壓試驗
在拉壓力試驗機上,筆者對樣品開展了靜態壓力試驗,靜壓試驗結果如圖6所示。

圖6 靜壓試驗結果
從測試結果可看出:
(1)4種工藝狀態下的樣品試驗結果均滿足了客戶的要求,但是未采用表面淬回火工藝的樣件承載能力更好,相比采用表面淬回火工藝樣件提升承載能力約60%;
(2)采用調質工藝樣件相比正火工藝樣件,承載能力提升約5%,差異不顯著;
(3)通過對比載荷從0增加到斷裂的過程中,未采用表面淬火的正火與調質樣件的載荷位移曲線線型一致,在斷裂前均存在塑性的拱形特征,而采用了表面淬火的正火與調質樣件線型一致,在斷裂前無塑性的拱形特征,表現出了瞬斷。
未采用表面淬火的正火零件斷裂曲線圖如圖7所示。

圖7 未采用表面淬火的正火零件斷裂曲線圖
采用表面淬火的正火零件的試驗曲線圖如圖8所示。

圖8 采用表面淬火的正火零件斷裂曲線
從曲線可看出,4種工藝狀態下的彈性階段的直線位移范圍均維持在約9 mm,彈性變形效果是一致的。
3.2.2 沖擊試驗
在沖擊試驗機上,筆者對樣品開展了沖擊試驗,沖擊試驗結果如表4所示。

表4 沖擊試驗結果
從測試結果可以看出:
(1)4種工藝狀態下的樣品,僅有未采用表面淬火的正火與調質零件兩種狀態能夠順利通過沖擊試驗,而采用表面淬火的正火與調質零件均無法通過沖擊試驗,即使把沖擊載荷從470 kg降低至350 kg,下降26%,軸頸仍發生斷裂;
(2)軸頸表面未采用淬火處理的零件在沖擊后均存在一定的角變形。
未經表面淬火零件沖擊試驗后角變形圖如圖9所示。

圖9 未經表面淬火零件沖擊試驗后角變形
圖9中,顯然該角變形吸收了沖擊能量,抵抗住了斷裂,而軸頸表面采用淬火處理的零件在沖擊后均為瞬斷,在斷裂前無變形特征,把裂口拼合未見塑性變形。
3.2.3 剛性試驗
筆者采用力矩剛性試驗機對樣品開展了剛性試驗。剛性試驗的目的在于評估軸頸零件在較大的轉向條件載荷下,仍具有較好的抵抗變形能力。按照設計規范要求,需要滿足在1.0 G側向加速度載荷下,軸頸仍處于彈性變形階段。
試驗過程中,筆者對每個試驗樣品從0 G載荷作為起點,依次按照如下程序施加試驗載荷:
(1)0→0.3 G→0(循環3遍);
(2)0→0.6 G→0(循環3遍);
(3)0→0.8 G→0(循環3遍);
(4)0→1.0 G→0(循環3遍);
(5)0→1.2 G→0(循環3遍)。
每個樣品累計循環15次,4種工藝樣品試驗過程中,其剛性角度變化過程圖如圖10所示。

圖10 剛性角度變化過程圖
從測試結果可看出:
(1)4種工藝狀態下的樣品變形效果一致,在從0~1.2 G范圍內的載荷施加,載荷回零時,變形角度均可回零,可見4種工藝狀態的樣品均能夠滿足1.0 G載荷條件下不發生塑性變形的設計要求;
(2)載荷越大,變形角度也越大,但均在彈性變形角度范圍內,從0.3 G載荷到1.2 G載荷,彈性變形角度增加了330%。
3.2.4 疲勞強度試驗
筆者采用旋轉彎曲疲勞試驗機開展了4種工藝狀態樣品的旋轉彎曲疲勞試驗,在要求的彎曲載荷條件下,所有試驗樣品均試驗至軸頸斷裂失效。
試驗對比結果的Weibull可靠度分析結果如表5所示。

表5 Weibull可靠度分析結果
從測試結果可看出:
4種工藝狀態的樣品均能夠滿足L50≥460 000循環的壽命設計要求[14],未采用表面淬火的樣件L50可靠度壽命比采用表面淬火的樣件低約10%,但未采用表面淬火的樣件L10可靠度壽命比采用表面淬火的樣件高約10%,雖然4種狀態均滿足了設計壽命要求,但是未淬火的零件壽命可靠度更好。
從壽命的離散性Weibull曲線斜率也可看出,未采用表面淬火的零件壽命離散度更小[15]。
3.3 工藝改進
因在開發階段,主機客戶對產品抗沖擊性能未識別出來,僅通過靜壓試驗不足以反映產品的抗沖擊水平。通過以上分析與測試可知,即使產品能夠通過靜壓、剛性與疲勞強度試驗,產品仍存在抗沖擊能力不足的風險,這也導致了售后失效與產品召回的問題。經輪轂軸供應商對產品沖擊試驗的追加,已證明了采用表面感應熱處理工藝方法的弊端,產品抗沖擊能力急劇下降。
為此,筆者對軸頸的加工工藝重新做了修改,工藝3因采用調質工藝成本較高,但表現出來的產品綜合性能與工藝1接近,結合對工藝成本的控制,采用了工藝1作為產品改進后的生產工藝,并進行批量生產。
經過持續跟蹤在終端客戶2年來的市場表現,該類沖擊失效已被完全杜絕,使該類車行車的安全性得到了保證。
4 結束語
針對軸頸沖擊斷裂問題,筆者分析了斷裂的原因,調查了不同汽車主機客戶處的軸頸熱處理工藝,重新規劃了4種熱處理工藝,對產品進行了試樣與試驗論證。
試驗結果顯示:
(1)相比采用表面感應淬火處理的軸頸,未采用表面感應淬火處理的軸頸靜載承受能力提升了60%,抗沖擊能力提升高于26%,滿足國家標準要求;
(2)相比采用軸頸表面感應淬火處理的零件,疲勞強度壽命的離散度有所下降,同時,在1.2 G載荷條件下的抗塑性變形能力也滿足客戶技術條件;
(3)經過把原工藝2調整為工藝1,并按照工藝1方法進行批量生產供貨,在市場應用中已實現了對沖擊斷裂失效安全問題的杜絕,取得了顯著效果。
為了提升對抗沖擊型乘用車軸頸的設計能力,筆者在后續將基于ADMAS與ANSYS等有限元軟件工具,進行沖擊工況的模擬研究[16],以提升其設計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