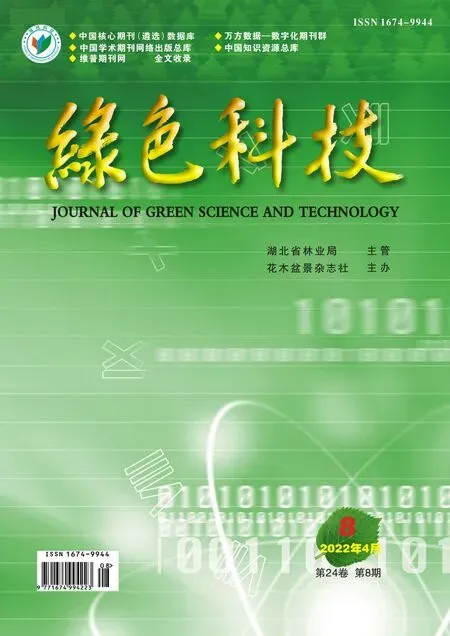干旱半干旱流域下墊面植被影響水循環機理及干預方式
傅光華
(國家林業和草原局產業發展規劃院,北京 100010)
1 引言
宏觀生態學是從生態學研究尺度對群落生態、生態系統生態進行研究的生態學科分支[1]。為研究大尺度宏觀生態的影響,筆者在《生態文明建立的體制因素——區域生態治理理論與實踐》[2]中提出區域宏觀生態學和生態異變概念,即從一個區域、流域甚至跨流域的大尺度空間研究生態行為,比宏觀生態學更宏觀,主要通過整體和趨勢性的生態現象研究人與自然的關系;生態異變指發生宏觀生態性質變化的大變化,是趨勢性改變。宏觀生態研究可以在眾多微觀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總結和梳理出共性的規律,但又與微觀研究或中觀研究存在很大區別,宏觀生態考量的是大跨度、共性的發展趨勢和規律,更具有前瞻性,主要為決策和宏觀布局服務。
由于水汽對地球水圈、大氣圈、巖石圈和生物圈的影響關聯度強,大氣水循環在區域宏觀生態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水是引起生態異變的重要因素,尤其在干旱半干旱地區,水是導致脆弱化、退化甚至異變的關鍵要素,研究影響水汽循環的內環境影響因素,對區域宏觀生態治理政策制定、重大工程布局及有針對性采取適度人工干預措施均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2 研究方法
研究發現黃河流域有兩大巧合:一是幾千年前隨著華夏文明的開啟和單一農耕社會的形成,導致黃河流域進入生態退化過程,同時也伴隨著干旱化趨勢的逐步形成,這種宏觀生態異變趨勢卻從新中國成立后開始出現停滯,進而逐步出現了逆轉的跡象,1999年開展退耕還林還草工程后,西部地區監測的多項數據出現跳躍式大幅改善,這些都與流域生態環境,尤其是地表植被蓋度變化高度正相關;二是2014年底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投入運行,黃河中上游的陜西、甘肅等地區監測的降水量從2015年開始明顯增加。揭示這些巧合的內在邏輯是基本動機,從氣象學研究的地域外輸入水汽和輸出水汽研究來看,尚未發現因境外水汽輸送變化導致的明顯證據,研究結果顯示主要是內部因素造成了水汽循環的變化。這就是本文的思路和分析邏輯。
具體方法:
(1)建立黃河流域大氣水汽循環模型,結合模型參數從理論上分析流域宏觀生態層面影響因子,證明水是影響干旱半干旱地區生態系統的核心要素,是眾多相關因子的“關鍵少數”,并從水汽循環機理揭示內在影響因素,尋找干預目標。
(2)以現有研究成果為基礎,驗證和分析下墊面植被圈在流域級區域宏觀生態異變中的作用,梳理實踐過程中表征的影響水汽循環因素。
(3)根據主要影響因素,提出干預手段。
3 大氣水循環
3.1 大氣水汽循環基本模型
陸桂華等在《全球水循環研究進展》[3]中介紹了國際上水循環研究進展,指出水循環是地球上最重要的物質循環之一,是聯系地水圈、大氣圈、巖石圈和生物圈的紐帶。水循環的變化深刻影響著全球水資源、能量和化學物質的分布與改變,關系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和生產活動,世界氣象組織于1979年啟動的世界氣候研究計劃(WCP)表明,水分循環與能量是影響全球或區域尺度氣象變化的主要因素。為了研究氣候變化條件下海洋—大氣—陸面間能量與水分相互作用和轉換及其對氣候的反饋,世界氣象組織于1988年組織并實施了地球能量與水循環實驗(GEWEX)。在另一項重要國際計劃——國際地圈生物圈計劃(IGBP)的實施過程中,科學家們發現土壤—植被—大氣系統(Soil—Plant—Atmosphere Continuum,SPAC)對能量和水汽通量的作用直接影響到全球尺度的水循環過程。
姚俊強等在《新疆大氣水汽再循環過程變化及機制研究》[4]提出,大氣水分循環過程是水循環過程的一個重要分支。大氣降水一般有兩個來源:局部蒸發的水汽(即大氣水汽再循環)和外部水汽輸送(平流水汽)。大氣水汽再循環是水循環的關鍵組成部分,它連接著陸地表面和大氣,平衡著地球系統的水和能量循環。
參考張良等《祁連山地區大氣水循環研究(Ⅱ)》[5]中“圖1水循環模型”原理,提出本研究水循環模型圖(圖1),且張良等提出的幾個等式關系:I=PI+OI,E=PE+OE,O=OI+OE在本研究模型中依然適應。

圖1 水循環模型(參考張良等水循環模型)
根據物質守恒定律,本研究進一步提出某一區域內的水總平衡關系方程式:
I+W=O+R+S+B
(1)
B=BE+BB
(2)
E=BE+SE
(3)
式(1)~(3)中:I為域外水汽輸入量;W為地表徑流域外輸入水量;O為本域輸出水汽總量;R為本域地表徑流輸出水量;S為下墊面下滲量;B為生物等消耗量;E為總蒸散水汽量;BE為植被蒸騰水汽量;SE為地表土壤蒸散水汽量。
盡管就水物質總量及總輸入、總輸出角度分析,似乎對研究區域內水汽沒有太大意義,但是,受輻射、氣流、氣壓等多種因子影響,從大尺度考慮,內部的大氣水汽和地表水總處于一種蒸發、凝聚和降水的循環動態,尤其是E直接關系內部水汽循環效率。
3.2 大高程差流域大氣水汽循環模型
這種區域有幾個特定條件,一是大尺度的流域,易于形成復雜的水汽自循環;二是流域兩端海拔高程差比較大,在暖氣流季節溫差和壓差能夠形成對流層氣流的弱“煙囪效應”,盡管不會有真“煙囪效應”那么強烈的效果,但形成的弱升流效應疊加對流層復雜的氣象,一定程度上會對水汽產生影響。結合圖1水循環基本原理和地形構造提出本研究水循環模型圖Ⅰ(圖2)。

圖2 大高程差流域大氣水循環模型Ⅰ圖
該模型主要特點是流域兩端海拔高程差比較大,壓差和溫差梯度變化疊加大坡度下墊面比較容易影響對流層氣流,氣溫隨高度升高而降低,氣溫垂直分布特征和地面熱力性質的非均勻性,形成大規模的強烈對流運動和無規則的湍流運動,驅動大氣從低海拔向高海拔流動,把水汽從下游向上游轉移,實際效果與“煙囪效應”有點類似。
這一模型有一種特例,就是符合模型條件的干旱半干旱流域。由于這種環境條件對水汽量的變化很敏感,表征上的變化比較容易顯現,如隨著地表植被的增加,上游水汽和降水量也會逐步緩慢增加,在水汽積累到一定程度后,形成半濕潤、濕潤大氣環境,同時,隨著降水增多,地面慢慢由干燥變得濕潤,形成局部地區的大氣地面濕化耦合現象(大氣和地表土壤同時處于干半濕潤及以上狀態,根據《農業氣候區劃及方法》,將我國濕潤系數分為七級,分別為干旱、半干旱、干半濕潤、濕半濕潤、濕潤、潮濕以及過濕),且隨著下中游水汽條件的改善和蒸散效應積累,上游的濕潤區范圍會緩慢加大,濕潤線沿著流域坡向逐步下移。
從圖2中可以看出,如果把整個流域作為一個單元,根據物質和能量守恒定律,影響流域水循環的因子有:域外水汽輸入量(I)、本區域輸出水汽(O)、地表徑流域外輸入水量(W)、地表徑流本域輸出水量(R)。I是由更大尺度的大氣環流和氣候帶決定的,主要由平流水汽形成,在目前的科技條件下人工干預的條件尚不具備;影響O的因素除了更大尺度的大氣環流和氣候帶外,還有一個途經本區域的過程,必然會受到本域眾多因素的影響,尤其是地水圈和生物圈;W和R是人工干預可供選擇的因素,如調水工程。
就區域內部,決定水分效能和利用效率的是水循環效率。影響大氣水分循環的主要因子是下墊面表面積和溫度,而植物對表面積和溫度的影響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植物從土壤中吸收水分,并以水汽形式向大氣中散失,這一過程稱為植物蒸騰。植物蒸騰過程是植物本身不同器官和它所在環境相互作用及反饋影響的結果。許迪等在《冬小麥—夏玉米種植模式的農田水量平衡模擬以及入滲補給規律分析》[6]中表明,植物所吸收的大部分水分(98%~99%)均通過蒸騰作用以水蒸汽的方式散失到大氣中。當植物冠層不能夠完全封閉陸地表面或地表裸露時,土壤中的水分和水汽則直接散發到大氣中,稱為土壤蒸發。植物蒸騰和土壤蒸發統稱蒸散發(亦稱騰發或蒸散)。
劉樹華等在《干旱、半干旱地區蒸散過程的模式》[7]中提出,一定區域內進入大氣水汽再循環的蒸發水汽與下墊面植被關系密切。地表土壤—植被—大氣系統中的蒸散是陸地水循環過程的重要子過程,決定了從土壤和植被進入大氣水分的多少,及伴隨著這一過程的潛熱和感熱的變化。從而顯著影響下墊面的氣候和環境條件,對于區域內動植物的生存、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劉樹華等研究還表明,在干旱半干旱地區植被冠層內空氣濕度的比濕變化在一天中呈現“M”形變化趨勢,由于綠洲環流和植被的主動生理調節作用,當上午氣溫升到一定高度時,環流開始形成,帶走部分綠洲上的水汽,而植被為了保證自身的蓄水量,蒸騰作用減弱而光合作用增強,通過氣孔釋放的水汽減少;當下午溫度回落后,葉片氣孔擴張,蒸騰作用增強,由綠洲向其它區域的水汽輸送減少,因此冠層內空氣濕度又開始上升直至達到峰值。地表植被不僅喬木、灌木存在蒸散效應,草本同樣存在,宋小寧等在《半干旱地區遙感雙層蒸散模型研究》[8]表明,在草原生態系統中,植被蒸發蒸騰是水分損失的一個重要途徑。陳昌毓等《甘肅干旱半干旱地區林木蒸散量估算和水分適生度研究》[9]也從另一個角度研究證明植被的蒸散效應,甘肅干旱半干旱區喬木薪炭林和喬木用材林生長期水分蒸散量,河西走廊區域分別為250~600 mm和450~850 mm,甘肅黃土高原區域分別為200~550mm和 370~700 mm;灌木林正常生長的水分蒸散量約為喬木的1/3~2/3,為170~390 mm。這些研究都證明,下墊面生物圈是大氣水汽循環的重要參與者,在水汽循環中,植被在地下水—生物圈—水汽蒸散—水氣混合體轉移或降水循環過程中處于關鍵環節。
在干早半干早地區,植被通常不能將土壤表面完全覆蓋,在干旱季節時更是如此。由于干旱半干旱地區下墊面土壤含水量較少,尤其表土層長年處于干燥狀態,裸露地表的蒸發水分非常有限,像西部地區,盡管年蒸發量超過2000 mm,但年降水僅幾百毫米,甚至幾十毫米,地表可蒸發到大氣中的水分量很有限。但是,下墊面底層往往比較濕潤,在沒有植被的地方,因受地表層和地心層保護,地下水難以蒸發,可在有植被的地方,卻因植被根系的吸水作用,通過植物組織將地下水轉移到葉面,再通過植物蒸騰出去,從而增加水循環的數量,提高了水資源的利用效率。在圖2基礎上,增加地表植被因素和植被蒸騰效應提出本研究的干旱半干旱地區植被參與水循環模型圖Ⅱ(圖3)。

圖3 干旱半干旱區域植被影響水循環模型Ⅱ
模型Ⅱ很好地解釋了干旱半干旱地區存在的一種現象,流域中下游地區隨著地表層植被的增加,地表層反而呈現干裂化現象。朱仲元的《干旱半干旱地區天然植被蒸散發模型與植被需水量研究》[10]指出,由于這一區域植被大多為稀疏植被,稀疏植被裸露表層土壤(0~15 cm)中的含水量對土壤蒸發系數的影響很明顯。因為根系生長與水分吸收緊密聯系,根系吸收水分促進根系生長,而根系生長反過來又增加了根系吸水的深度。
基于這一邏輯,本研究提出一種非常有必要的人工干預方式:在大高程差干旱半干旱地區,隨著生態建設的推進和植被不斷恢復的同時,植被導致的蒸騰作用加大,即公式(2)中植被蒸騰水汽量BE增加了,隨著中下游地區下墊面水分通過蒸騰—大氣弱“煙囪效益”將水分BE中的一部分不斷輸送到了上游地區,根據公式(1),在水汽外輸入量(I、O)不變的前提下,通過內部循環上游增加了,中下游必然就會減少,表征結果呈現的就是中下游地表濕潤度下降,甚至呈現局部干裂等缺水癥狀,實際上是下中游水因蒸騰遷移而失衡的結果,即表層地下水蒸散量大于降水補水量。因此,在條件可能的情況下,對中下游開展流域級生態調水補水就顯得非常有必要。
4 植被對水循環影響在黃河流域生態異變千年趨勢中的作用
黃河流域是典型的圖2模型,有記載的幾千年歷史中,流域生態異變歷經由圖3模型逐步退化為圖2模型,新中國成立后正在逐步恢復為圖3模型的過程,這也是研究該模型的價值所在,對黃河流域生態修復和有針對性開展適度人工干預具有現實意義。
4.1 幾千年的黃河流域生態退化史
來自黃河管理委員會的數據[11]顯示,黃河發源于青藏高原巴顏喀拉山北麓約古宗列盆地,蜿蜒東流,穿越黃土高原及黃淮海大平原,注入渤海,干流全長5464 km,水面落差4480 m,流域總面積79.5萬km2(含內流區面積4.2萬km2)。黃河流域構成我國重要的生態屏障,是連接青藏高原、黃土高原、華北平原的生態廊道,擁有三江源、祁連山等多個國家公園和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在我國5000多年文明史中,黃河流域有3000多年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鄒逸鱗對我國歷史上幾千年的生態環境變遷做過比較系統的研究[12,13],葛全勝等從氣候的角度對我國歷史上主要流域的氣候變化及影響作了研究[14],相關成果表明,黃河流域在歷史上植被豐富,大約在距今4000~5000年,黃河流域谷物農業時代的開啟進入土地深度利用時期,也宣告了黃河流域生態危機之門的開啟。從生態學的視角看,中國不同歷史時期人口增長、人口遷移、各種類型的墾殖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巨大。北宋以后,中國人口出現明顯的長期上升趨勢,人口壓力導致農墾與山林亂砍濫伐的加劇,特別是到了清代中葉生態環境嚴重惡化,人類無限的索取最終超過自然資源承載力,黃河流域生態退化進入大趨勢的低谷期。數據顯示,春秋時期,黃河含沙量約為10 kg/m3,到了明代中期,含沙量為28.3 kg/m3,可謂“一碗黃河水,半碗黃泥沙”。
4.2 黃河流域生態進入良性回歸期
黃河流域幾千年生態退化趨勢直到新中國成立后才逐步被逆止,并逐步進入逆轉和緩慢進入一種恢復的新趨勢狀態,這種局面的出現,是新中國體制生態自覺內在驅動的結果[2]。從數據看,新中國成立初我國森林覆蓋率約為8.6%,截至1981年森林覆蓋率12%,凈增森林面積約33萬km2,加上采伐及造林更新面積約74萬km2,新中國成立前30年全國完成造林綠化面積107萬km2,超過國土面積的11%。尤其在干旱半干旱地區,盡管造林平均成活率僅在30%左右,但通過三北防護林工程、太行山綠化工程及國土綠化工程的實施,黃河流域植被恢復取得初步成效[15]。根據計偉等的研究,至2018年,黃河流域草地、農田和森林三大生態系統占全流域面積的比例分別為48.35%、25.08%和13.46%,森林和草地蓋度達到61.81%,從時間變化上看,20世紀80年代后黃河流域植被覆蓋度變化可以分為3個階段: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末總體上表現出增加趨勢,20世紀90年代末至21世紀初期植被覆蓋度波動較大,2004年后植被覆蓋度持續增長[16]。
1999年開始實施的“退耕還林還草”工程,使得整個流域的植被覆蓋發生了顯著的變化[17]。馬柱國等研究表明,黃河流域大部分地區植被覆蓋在 2000 年以后明顯變好,且黃河中下游植被覆蓋增加最為顯著,整個黃河流域植被覆蓋指數增加幅度達36.6%。其中,上游流域(蘭州站以上集水區)1982~2017年增加了22.8%;中下游流域增加43.9%[18]。近年來黃土高原輸沙量的銳減,其主要原因也是造林綠化增加了下墊面的植被覆蓋率,遏制了因降水產生的水土流失,減少了輸入河流的泥沙。張艷芳等研究指出,從歸一化植被指數(NDVI)和標準化降水—蒸散指數(SPEI)來看,黃河源區2000年以來總體上均呈波動上升趨勢,即植被覆蓋狀況略有好轉,干旱程度有所降低,黃河源區總體而言氣象干旱呈現出緩解的趨勢[19]。
4.3 黃河上游大氣地面濕化水汽主要為流域內水汽循環輸送
張良等[5]應用劉國緯的水文循環大氣過程模型研究了祁連山地區的大氣水循環變化特征,結果表明:祁連山區域總降水量在2014年之前的51年中表現為緩慢增加的趨勢,境外輸送水汽對于當地降雨的貢獻呈減小趨勢,局地蒸發產生的水汽對于當地降水的貢獻增加,表現為21世紀初期由局地蒸發產生的降水量比1960年代增加33.0 mm;水文外循環系數表現為明顯的下降趨勢,表明境外輸送水汽在祁連山地區水文循環中的作用降低;與之相反,水文內循環系數呈明顯的上升趨勢,表明由蒸發產生的降水使區域水循環加強。王可麗等的研究也表明,西北地區中部的水汽輻合輸送與西風帶波動的相關性不很密切,而與南亞夏季風的相關性相對較好[20],張玉娟等通過對西北地區東、西部地區1951~2000年近50年對流層整層大氣可降水量的變化趨勢開展了研究,并在其論文《西北地區大氣水分特征及相關問題的初步研究》[21]中指出,西北地區全年水汽輸送主要來自與其南面相鄰的青藏高原中西部的西南暖濕氣流以及陜西南部的東南暖濕氣流,西北地區西部的塔里木盆地以及其南面相鄰的青藏高原上空以及四川盆地北部常年維持水汽的輻合。而陜西南部的東南暖濕氣流、四川盆地暖濕氣流及南亞夏季風影響與黃河中下游的水汽上升通道存在疊加影響。
甘肅省氣象局總工程師張強認為“西北地區西部降水增加趨勢持續了30多年,這是一個相對較長的降水趨勢增加期,也超過了計算基準氣候態的30年氣候期限,所以西北地區西部降水增加趨勢基本可以肯定了”“區域氣候條件有所改善,氣候舒適度有所提升;水資源總量有所增加,水循環機制有所改善,徑流量和湖泊面積有所增大;部分地區的生態環境向好發展,一些脆弱敏感區域的生態退化趨勢受到一定遏制;農作物適宜種植面積有所擴展,農業氣候資源有所優化”[22]。
任怡等[23]研究發現,2000~2013年黃河上游源區段由干旱逐漸轉為正常偏濕潤。也有基于多組帕爾默干旱強度指數(PDSI)的分析表明,黃河源區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氣象和水文干旱均有緩解的跡象。上游年降水量增加了33 mm,中下游流域年降水量減少了31.6 mm。
鄭子彥等[24]研究表明,黃河源區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降水總體呈現出不斷增多的態勢,其長期趨勢達到每10年7.28 mm。其中,1951~2000年,黃河源區降水變化非常平穩,僅以每10年3.76 mm不顯著的趨勢呈微弱的增長;但自2001年之后,降水量以每年3.22 mm的速度迅猛增多,幾乎是1951~2000年增速的10倍。
監測數據[25]表明,2015年后陜西的降雨期拉長了,汛期提前,結束得晚。多個縣的林業部門監測統計表明,年降水一般增加30~50 mm。時間與南水北調中線工程2014年底全線通水高度契合。
5 結論與展望
(1)基于水循環模基本型,提出了區域內水汽總平衡關系等式、大高程差流域大氣水循環模型Ⅰ和干旱半干旱流域植被影響水循環模型Ⅱ,以及在這種特定模式下水循環和水汽隨氣流向上游轉移。大高程差流域因壓差、溫差和地表熱輻射效應,在暖季形成對流層氣流類似“煙囪效應”的弱升流效應,一定程度會導致下中游水汽向上游轉移。這一模型在干旱半干旱流域屬于一種特例,由于干旱半干旱區域對水汽變化的敏感性,表征上的變化比較容易顯現,如隨著植被恢復和蒸騰加大,在下中游或呈現局部干裂化現象,在上游呈現大氣地面濕化耦合現象。
(2)影響大氣水分循環的主要因子是下墊面表面積和溫度,而下墊面植被是關鍵因子。結合干旱半干旱流域植被影響水循環模型Ⅱ,提出一種非常有必要的人工干預方式:在干旱半干旱流域治理過程中,隨著植被等生態恢復的持續,應對流域水輸入適當開展人工干預,即對中下游開展流域級生態調水補水。且這一結論從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和相關監測數據得到了驗證。
(3)應用兩個模型(Ⅰ、Ⅱ)研究黃河流域幾千年來生態變化表明,黃河流域在有記載的幾千年歷史中,流域生態異變歷經由模型Ⅱ逐步退化為模型Ⅰ,新中國成立后正在逐步恢復為模型Ⅱ的過程,展現該模型的研究價值。植被對水循環影響是黃河流域生態異變千年趨勢形成和變化的重要因素,反映的是人為干擾對植被、進而對流域整個生態系統的影響。新中國成立后一系列生態工程的實施,是黃河流域生態異變趨勢逆轉的重要原因,而保持這種良好局面繼續深化的可行干預措施是繼續實施流域治理和生態修復等高質量發展。
(4)1960年代以來,黃河流域水汽變化與新中國生態建設史高度契合,與大高程差干旱半干旱流域隨著植被恢復及生態環境改善會先在上游出現流域大氣地面濕化耦合現象相符。監測和研究數據說明,黃河流域已進入上游濕潤化的初始階段,且這種趨勢隨著生態建設力度加大和大型生態干預工程建成在明顯加快,也表明流域生態千年退化趨勢已經步入逆轉的良好局面。東線、中線生態調水補水工程的生態促進作用在區域宏觀生態層面得到了驗證,對加快西線工程建設的必要性有了新的認識。